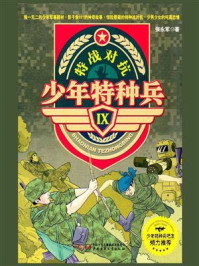司马洛觉得莫先生有时很讨厌,他知道这个人是不大有幽默感的,且有时还是令人太难受,似乎太过铁石心肠了。
也许莫先生的工作是使他需要如此的。
莫先生主持着一个世界性的反罪恶组织,他所对付的人,都是需要用很硬的心肠的。
莫先生也是认为司马洛许多时候是心肠太软,以致使他陷入不必要的险境。
但也许他们正是最佳拍档。他们的软与硬,许多时候刚好能够互补不足。
这时莫先生从抽屉中抽出一件东西来,丢在桌上,亮闪闪的,是一粒金属珠;不过不是浑圆,而且距圆形仍远,只是略为呈圆形罢了。
莫先生说:“认得这个吗?”
司马洛拿起来看看,说道:“我连这个是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白金!”莫先生说。
“我看又不像是白金。”司马洛说。
莫先生说:“世界上骗人的事很多,说是白金,其实中间只有少量的白金。一只白金合金牙齿。”
“这不是一只白金牙齿!”司马洛说。
“熔掉了再凝固起来,就不像牙齿了。”莫先生说。
“你问我认不认得?”
“这是菲腊的牙齿!”莫先生说。
“哦!”司马洛说:“那一次菲腊的假牙,白金成份果然很少……但怎会在你手上?”
“菲腊已经死了!”莫先生说。
司马洛马上把那粒金属丢下,脸也青了。
莫先生说:“这就是菲腊剩下来的东西之一!”
“菲腊……死了……你把他的牙齿拿来……”司马洛愤怒地说。
菲腊是一个能人,与司马洛的感情也相当好,因此他就为了这而震怒。菲腊也是莫先生的好朋友之一,而莫先生拿着菲腊遗下不断的牙齿,却像是一件玩具。
莫先生拿起那牙齿,在手中把玩着,说道:“菲腊是死于烈火,没有什么剩下来。等于一个人火葬,就只剩下一大堆骨头和牙齿。”
“为什么……”司马洛心中立即有非常多的问题。
“有些大骨头是烧不掉的,”莫先生说:“但最难烧掉的还是牙齿,这一次的火非常之烈,几乎只烧剩牙齿。”
莫先生接着又说:“而这只是金属的牙齿,金属是很难毁灭的,假如要加热到使它化成气体而消散,那不知要多高的热度,科学目前还是不易做到的,所以这牙齿只是熔掉了。看这牙齿,就知道热度大概有多高!”
“这应该是不锈钢,混有一些白金,”司马洛说:“除非是火葬。”
“火葬的热度也是未必能把这牙齿熔掉,”莫先生说:“而且这不是火葬,菲腊是给烧死的。”
“究竟发生了什么?”司马洛咬着牙问。
他对菲腊的遭遇更重视过烧掉这牙齿的热度。
莫先生按亮了那可作为大萤幕用的墙壁,其上就出现了画面。一片泥地,其上有一些残缺的头骨及牙齿。
莫先生说:“他的尸体就是在这里发现的,或者应该说是没有尸体。”
司马洛看着,心中一阵阵冰凉。
不论菲腊是如何死的,总之他是死了,他半生做正义的工作,也仍然是为了这个而死了。
司马洛也是差不多的人,他未必是本领比菲腊高很多,他认为他只是运气够好而仍然活着。
莫先生也许是看着太多的手下来了又死去了,他不能伤心,正如医生不能为每一个死去的病人而伤心。
司马洛用不着出声,只是看下去。
莫先生亦在旁边加一些旁白。
莫先生说:“我是派他去调查火蛇事件,他没有成功,这就是行动失败留下来的东西!”
火蛇事件?那萤幕上亦有把这个资料显映出来。
火蛇是一种机密的军事研究的代号,怀疑其中有人泄露情报,菲腊就是负责监视一个叫史特加的科学家。史特加很可能是把情报出售。
司马洛说:“史特加又如何呢?”
莫先生说:“这里是他的牙齿!”
萤幕上显现另一些牙床骨及牙齿的放大图。
人的牙齿没有人相同,不能顶包,虽然是整个人都不见了,牙齿仍是可以辨认。
但是史特加的牙齿则是散开了的。
萤幕上又出现了另一个镜头,乃是碎裂了的牙床骨加上一些塑料再砌好,然后把这些牙齿再插回。
司马洛说:“他的牙床……”
“史特加被人猛力打过,牙床骨碎掉了,牙齿也脱飞,也许他在起火之前已经死掉了,但即使他未死掉,他也是会给烧死了。”
“这样猛烈的火?”司马洛问。
“来源不明,”莫先生说:“你看这些……”
萤幕上又出现一些特写镜头,乃是那里地上的泥土。有些泥土已经结了块,乃是烧熔了之后冷凝了的。泥土之中有大量的矽,矽也就是制玻璃的主要原料,矽的熔点并不高,所以就会有如玻璃那样烧熔而又再冷凝成块。可以把不锈钢亦烧熔的热度,泥土当然亦可以烧熔的了。
但是那里是一片荒地——
“这样高的热度,”莫先生说:“在一个炉里当然不难做到,但是在一片荒地上?我们只是相信,他们是被某一种武器烧掉的,应该是一喷就喷出高热,把两个人都只烧剩下了这些。总之是就地烧掉,不是事后才挪来的!”
“他俩在那里干什么?”司马洛问。
“很可能是在死前打架,”莫先生说:“史特加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人,孔武有力,假如打起来,菲腊也未必是一定赢的,也许菲腊拿一件武器把他的牙床打成这样。”
“例如什么武器?”司马洛问。
“一块石头就可以了。”莫先生说:“你知道,人是很脆弱的!”
“是第三者做的。”司马洛说。
莫先生不出声,他有时如此是因为尊重司马洛的意见,有时是因为司马洛所讲的他早已知道。
司马洛说下去道:“菲腊用不着打那么多下,只要打一下,人就失去抵抗力,他用不着打第二下。史特加的牙床骨是碎得一塌糊涂的!”
这个道理乃是,菲腊不是一个杀手,假如他需要用到这个方法的话,那只要一下就够了,而且菲腊是正在调查,他杀死了史特加最没有用。假如他需要与史特加打起来,那一定是因为他已查出了史特加有些古怪,那就更不能让史特加死掉了。
莫先生没有出声。
司马洛又说:“是怎么找到他们的呢?”
萤幕上出现了两部汽车。
这是因为两人都已失踪了,便展开搜查,警方发现了他们的两部车停在荒郊。
莫先生说:“看来他们是在那里会面,有人把他们烧掉了。”
“或者另有两个可能性!”司马洛说:“第一个就是史特加去那里与某些人相会,菲腊跟来了,发现了一些秘密,两人就被一齐毁灭了。第二就是史特加到那里去会某一些人,他被这些人打得死去活来,菲腊插手。他也被消灭了。我比较相信最后一种情形。”
那也是因为他不认为菲腊会这样杀死史特加。
莫先生说:“无论如何,杀菲腊与史特加的凶手的手上是有一件非常摩利的武器,可以把人烧掉,只剩下这些!”
这是相当明显的,这件武器也许很轻便,也许很沉重,但是一定是能搬动的,这个地点,不可能筑起一座高温焚化炉,用完之后又拆掉而不剩下任何痕迹。
莫先生又说:“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
“我来接手?”司马洛问。
“你是一位朋友,不是我的手下!”莫先生说:“况且你是一个一流高手!这件事情,你来接手最好。我找你来当然也是为了这个!”
“什么是火蛇?”司马洛问。
莫先生指指萤幕,那上面也是有所显示,但是非常简单,只是“最高机密”。
“岂有此理!”司马洛说:“这个我们早已知道了,那是什么?”
莫先生摇头:“你不能知道!”
司马洛说:“菲腊却能知道?”
“菲腊也是不知道!”莫先生说:“史特加当然知道,但史特加不是我们的人。”
“这是什么意思?”司马洛说:“我们为他们做事,我们却不能知道?”
“他们也不是很热必要我们做这事,”莫先生说:“现在是我们热心,我们死了一个人。”
“你是说在此之前他们是很热心要我们的帮忙,所以派去了菲腊,现在又不热心了?”
“是的,”莫先生说:“就是这样的情形!”
“那么,”司马洛说:“这就是太不正常了。现在出了事,应是更急的。”
“也许他们对我们失了信心,”莫先生说:“他们要自己来!”
“他们有人吗?”司马洛问。
“他们有人、”莫先生说:“但是他们的人不及我们。”
“他们应该知道。”司马洛说:“这事他们仍是需要我们,而且更加需要。因为史特加可能已出卖了一些很重要的秘密,人家才会把他灭口。”
“是呀!”莫先生说:“但这是你的工作!”
那个地方的外面有个招牌,上面写着的是李安纳食品公司。这里就是史特加工作的地方。
那里的闸门口却有武装的守卫。
司马洛的车子在那闸门口的前面停下来。
这是铁丝网的闸门,门内的旁边有一座守卫事。
本来一个地方要保密是应该用封密的铁门的,铁丝网的闸门,就可以望得见里面;不过,这里的铁丝网闸门之设,却是为了方便其内的人可以望出来。
因为在门外向内望,只是看得见围墙一边的草地,以及草地尽头的另一度高高的围墙。
其他什么都看不见。
人与车进去,都要转一个大弯,绕过守卫亭后面的一座建筑物(看来是护卫员的休息室)。换句话说,这里的进口是在围墙的角落处,即使站到一边去斜看,仍是看不见中央的部份。
守卫的人则是老远就看见司马洛的车子来。
司马洛按响号叫开门。
一个护卫员走到铁丝网闸门的前面,问道:“什么事?”
“我是卫生局派来的,”司马洛说:“我要来检查一下这里的卫生设备。这只是循例公事!”
“我们不知道有这件事。”那人说。
“知道就没有意思了!”司马洛说:“你们会把一切都弄得干干净净,那我就来了也等于没有来!”
那人说:“你有证件吗?”
司马洛拿出钱包打开来扬一扬,里面有许多信用咭和各种证件。
那人做了一个手势,退后,闸门便开了。
司马洛把车子开进去,沿着当中的汽车路开到那里的一座两层建筑物的门口。
那里也有一个招牌,有玻璃门,旁边有停车的地方。司马洛把车子停好了。
他下车,推开玻璃门进去,里面有一个柜台,后面坐着一个美丽的女接待员。
她对他作一个甜蜜的微笑,从后面走出来说:“请跟我来!”
她领他进入走廊,到了一个门口,说道:“这里就是了,你自己进去,他们会招待你!”
司马洛看着她:“你不能带我去吗?”
她笑笑地说:“那不是我的工作范围,我是不方便进去的。”
司马洛耸耸肩:“出来时跟你谈!”
她还是微笑:“我五点钟下班,不要太迟!”
司马洛推门进去,那里面是一间会客厅,尽头又有一扇门,却不是玻璃门。
会客厅里面已有两个人坐着。他们放下手上的报纸,手上的枪就现出来,指住他。
司马洛道:“噢,对不起,看来是我摸错了房间!”
那两人毫无表情。
司马洛要退回去,但是他进来的那扇门已不能打开了。
那边另一扇门打开,有第三个人走进来,走到他的身边,伸手在他的身上摸索了一遍,摸不到他有怀着武器。
那人把他的证件搜了出来,看了一遍,说:“你没有卫生局的证件!”
“我呃……”司马洛说:“只是开玩笑。”
那人说:“你坐下来,告诉我们你是谁好吗?”
“我是……来找霍利先生的。”司马洛说。
“你有约会他吗?”那人说。
“没有。”司马洛说。
“那么你应该先打电话来,”那人说:“让他拒绝。”
“你肯定他会拒绝?”司马洛苦笑着问。
“假如他是肯见你的,”那人说:“你就用不着这样混进来了!”
“很好!”司马洛说:“我现在就走。”
“你既然进来了,就没有走得那么容易。”那人说。
司马洛说:“你想怎样呢?”
“你要回答一些问题,”那人说:“例如你是要干什么?是谁派你来的?”
司马洛说:“我不是已经回答了吗?”
“你要给我们满意的答案!”那人说。
司马洛苦笑:“我只是要见霍利先生。”
另一人说:“我们是不喜欢动粗的,不过你也不要逼人太甚!”
这时某处一个米高峰却传来一把声音,说道:“让他走吧!”
那三个人都显得有些尴尬。
司马洛说:“那是霍利先生吗?”
那三个人都不回答这问题,但那把声音说:“是!”
司马洛说:“我可以跟你谈谈吗?”
“你现在就是正在跟我谈。”
“我是说见面!”司马洛说:“我是菲腊的同事,我是为了——你知道是什么事的。”
“我不想跟你谈!”霍利先生说。
“但是……这事并不是就此便结束的了,”司马洛说:“我还要工作下去。”
“我不需要你!”霍利先生说。
“你……这是合作的问题!”司马洛说:“我们死了一个人,那是我的朋友。”
“我也死了一个朋友!”崔利先生说。
“如此我们不是敌人。”司马洛说。
“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霍利先生说:“我们不需要你!”
“但是……”司马洛说。
“现在,请你离开吧!”霍利先生说。
那三个人已推着他送向门口。
司马洛耸耸肩,只好出去,这时那扇门又能开了。
霍利先生的声音忽然又说:“等一等,告诉我,为什么你不先来一个电话呢?”
“我想看看混进这里来有多容易。”司马洛说。
“唔!”霍利先生说:“现在你已经看到有多容易了!”
“是呀!”司马洛说:“你们这里的保安工作做得不错,但是在外面,你还是需要我!”
“这个以后再讲吧!”霍利先生说:“目前,你是已经浪费了我很多时间。”
司马洛只好走了。
他又经过外面那个女接待员的位子,她对他微笑说:“再见!”
司马洛说:“真的是再见吗?”
“我刚刚是这样说了!”她说。
“那我什么时候再见到你呢?”司马洛问。
“你下一次再来时就可以见到我了!”她对他甜蜜地微笑着。
“这太久了!”司马洛说:“而且这里情调也不好,你什么时间下班?”
“你不能在这里等我下班!”她说。
“这里情调不好!”司马洛说:“我在别处等不是更好吗?几点钟?什么地方?”
她说:“我恐怕这是不大可能了,我有很多约会,也许要一个月之后!”她仍是甜美地微笑,但是语气却是拒人于千里之外。
司马洛却不放弃道:“那么我迟些再打电话给你!”
“很好。”她说。
“我可以得到你的电话号码吗?”他递上他的一张名片。
她说:“我白天都是在这里,打到这里来就可以了!”
司马洛叹一口气:“你对我印象不好?”
“我没有说不好。”她说。
“我希望你不要把我的名片丢掉!”司马洛说。
“我从不丢掉别人的名片!”她说:“我这里有一个抽屉可以放,我家里也有一个手袋是放这个的!”
司马洛苦笑地出去了。
他回到停车场,拿了他的车子,开到闸口。
闸门打开了。
就在此时,隆然一声爆炸,他看到那屋子的门口有火烟喷出。
他立即停车。
一个守卫提起枪来对他,司马洛觉得不妙,连忙低下头再开车。
车窗给射穿了一个洞,子弹经过他的头部附近的地方。
他叫道:“不关我事!”
但他知道这时是有理说不清的,因此在闸门关上之前,他的车子就冲了出去。
枪弹一阵阵射出来。
跟着,他就远去了,车身吃了好几颗枪弹而没有大碍,已脱离了射程;但是他从望后镜中看到有两部车从那闸门内追出来。
司马洛加速逃走。
他是领先了一大段路的,而且他的车很快,所以那两部车没有追上他。
他回到了市区,把车子在路边停好,就下车召了一部的士。他要放弃那车子,因为找他的人会先找他这部车子的。
他乘着的士,一面取出无线电话与莫先生通话。
莫先生知道发生了这件事情,由于他有手下在附近监视着,但是他不知道实在发生了什么。
莫先生说:“我还以为是你做的!”
“就是不是我做的!”司马洛说:“你有对霍利讲吗?”
“他并没有对我投诉!”莫先生说。
“我看是门口的地方发生爆炸!”司马洛说:“那位接待处的小姐可能是首当其冲。”
莫先生吃吃笑道:“你还是骑士作风,最关心美丽的女人。”
“妈的!”司马洛说:“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莫先生没有幽默感,有的时候确实令人很讨厌。
莫先生说:“这是人命关天,但是他们没有召救伤车,所以她应该是没事了!”
“他们那里面……也许有好些设备!”司马洛说:“也许他们自己能够……”
“总是不及一座医院那么好的,”莫先生说:“所以假如是严重,他们还是要召救伤车来把伤车送到医院去。”
“唔!”司马洛说:“这倒是真的。”
莫先生说:“这件事情倒是发生得很奇怪!”
“是呀!”司马洛说:“不是我做的,就是那里面的人做的了。那地方外人是不容易进去的。”
“那是霍利的问题了!”莫先生说。
“他以为是我做的,”司马洛说:“这不应该澄清一下吗?”
“假如他认为是你做的,那他就是一个大傻瓜!”莫先生说:“解释也没有用,这一次解释了,又有下次,又有再下一次!”
“我还是要知道那个女的有没有受伤!”司马洛说:“你替我留意一下吧!”
“这没有问题。”莫先生说。
那位接待小姐有没有受伤,是很快会知道的,正如莫先生所说,假如是重伤,一定会有救伤车去,但是没有救伤车到。假如只是受了轻伤,那则是肯定里面有人有能力治理的,因此这就要她下班时才知道。
假如她到下班时间还未出来,就可能有问题。
而在同一时间,莫先生的手下亦监视着司马洛弃下的车子,看看有什么人接近。
那位接待小姐在过了下班时间之后一小时还是没有出来。
似乎是有些问题了。
但这时却有人接近司马洛的车子。
那是一个年轻男人,他的车子就在旁边停下。
他的车子已经过了两次,看不到附近有可疑之处,那是因为他不容易看到莫先生的人员在这里埋伏。
他也是本领相当高强的了。
他一开门下车就关上车门,随即蹲下,便在司马洛那车子的车门上动手,很快就把车门弄开了,跟着便坐进了司马洛的车中。
他在车中弄了一阵,就下车,关上车门,回到自己的车上,开走了。
司马洛虽然不在那里,亦得到了报告。
莫先生与他联络。
莫先生说:“看来那个人是在你的车子上装了炸弹,你回去拿车子,一开就爆炸!”
司马洛说:“这会是霍利的人吗?”
“我不知道、”莫先生说:“不过照正常情形看,霍利是不会这样做的。”
“照表面的情形看,”司马洛说:“假如我也炸死了,我就没有机会否认那里面的爆炸是我做的了。那样,他们的内奸就不会现形!”
“也许是的,”莫先生说:“不过,假如我是这个内奸,如此做却是冒险一些!”
“是呀,”司马洛说:“不过他们看来也是不想我活下去,所以要这样做。”
“跟这个装炸弹的人谈谈就知道了。”莫先生说。
“让我跟他谈!”司马洛说。
“很好……呀……你的梦中情人出现了!”莫先生说道。
“她怎样了?”司马洛问。
“她开车出来,那不会有事。”莫先生说:“她只是下班迟了一些而已!”
“那么我先跟她谈。”司马洛说。
“那个装炸弹的人呢?”莫先生问。
“那个人让他走吧,”司马洛说:“看看他到什么地方去,与什么人联络更好!”
“对了,欲擒先纵,”莫先生说:“我也并无异议!”
那个女接待员叫费碧芝,她是自己一个人住在市区的,而正如莫先生所说,她当然是无恙,才能够自己驾车出来了。
她回到了她所住的大厦,回到她的单位,开门进去。
此时天已经黑了。
她开了灯,把手袋向沙发上一丢,就伸手拉落了衣服背后的拉链,看来她是很急于洗一个澡。
这时司马洛从厨房中踏出来,她“哇”的叫了起来,呆在那里。
“我是一个君子,”司马洛说:“我本来可以等你多脱一些衣服才出来的。”
她把衣服的拉链拉回。
“我已等了你好久了!”他又说。
“我问你是怎么进来的?”她说。
司马洛微笑,走近她的身边,说:“你是说怎么我进来了而你也不知道,是吗?”
他把她的长头发一摸,摸到了一根脱下了而未跌落的。用两手拉着,说:“把这个粘在门口近地面的地方,假如有人开过门,头发就断掉或是跌落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对手是我就不那么有效,因为我也用过这方法许多次、进来之后叫人在外面粘回就行了!”
她说:“你想怎样?”
“我?”司马洛老实不客气地在沙发上一坐:“假如你是急于洗澡,你可以洗了再出来。”
她并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她只好在他的身边坐下。
司马洛把她的手袋拿到另一边,这表面是为了让她可以有更多地方坐,实在却是为了使她远离那手袋,正如她坐过来,表面是友善一些,实在却可能是为了接近她的手袋。女人的东西多数是放在手袋内,包括武器。
她身上现在穿着的那套衣服,看来不像是可以内藏武器的。
一个有头发粘在门口提防别人的女人,也是一个值得提防的女人。
费碧芝说:“你要谈些什么呢?”
司马洛说:“我一直都在担心你给炸伤了!”
“担心?”费碧芝冷笑。
“我不是对你印象很好吗?”:司马洛说:“难道你忘记了吗?我在你的面前赖着不走,可惜你对我毫无好感!”
“你也在那里用了特别多时间。”她说。
“你相信那爆炸是我弄的?”司马洛问。
“你是一个外来的人!”她说。
“霍利先生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我只是一个小职员罢了,”她说:“他不会跟我商量这些事情的。”
“你不是一个小职员,”可马洛说:“你看着我进去,我很可能永不出来。你能知道这种事,你就不是小职员,而且你家门口又粘有一条头发!”
她耸耸肩:“我们也不认为是你做的,但假如不是你做的。就是一个我们里面的人做的了,这就问题很严重!”
“现在问题就是很严重,”司马洛说:“因为那件事情的确不是我做的。”
费碧芝不出声。
司马洛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只知道爆炸,我以为你会有危险!”
费碧芝说:“我的对面有一盆铁树,你也看见的,那铁树的盆里藏着爆炸品。”
“你仍能活着,”司马洛说:“那却是大奇迹了!”
“我那时刚好走开了。”她说。
“那不是非常之巧合吗?”司马洛说。
“我走到那边窗子看你走,”她说:“墙角刚好遮挡住。”
“我仍认为你是运气太好了!”司马洛说。
“我认为那炸弹是为你而设的,”她说:“但是炸得迟了一些。假如我要炸死你,那你怎可以活着走出去?我那柜台是炸弹炸不动的,我只要伏下就行。”
“但是门口的守卫差点把我枪杀了,”司马洛说:“就是为了那爆炸。”
“也许不是炸得太迟,而是为了刺激那些守卫!”她说。
“对了,”司马洛说:“你放炸弹,你的柜台也是可以保护你的。你说你走到窗前看我,你看着我到了闸门口就引爆。不错,假如你当场炸死我,你也难逃责任,假如我是被枪杀,那就表示炸弹是我放的!”
“我没有这样做!”她仍然非常冷静。
司马洛看了她一阵,耸耸肩道:“也许是的,那是入口,一定有电视眼看着,把一切也录影了下来,你不能做任何不对的事!”
“对了,”她说:“你现在聪明起来了,而且你也应该知道,霍利先生亦是不笨的。”
司马洛说:“那么,就正如我刚才讲过,不是我放的炸弹,你们就有很大的问题。”
“真的不是你放的吗?”她说。
“那炸弹的杀伤力如何呢?”司马洛问。
她凝视着他:“我那柜台没有炸坏,因为它构造特殊,但是我的上身在柜台之上,假如当时我是坐在那里,那么我的头也会给炸掉了!”
司马洛说:“假如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你就明白我不会要杀你。也许我会放一个很响的炸弹,制造混乱,但是我不会放一个杀伤力强的炸弹!”
“我也是这样想,”费碧芝说:“你要杀我的话有许多方法,但重要的是你没有动机。”
“因此,”司马洛说:“你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人在那里放炸弹,是你们里面的人。”
“但是看不出是谁放的。”费碧芝说。
“你下班之后就没有人了。”司马洛说。
“电视眼是日夜不停的,”费碧芝说:“也有录影。我迟了下班就是研究那些录影带!”
“与霍利先生一起?”司马洛问。
她不出声,这就是默认了,她果然是霍利先生手下的一个重要人物,她却是坐在一个似乎不重要的地方。
司马洛说:“电视眼不是全部时间都可以看到每一个地方的。”
“尤其是花盆那边。”费碧芝说:“一天有许多人出入都经过那里,其中一个人可以乘电视眼不朝着这边时一手把炸弹放进去!”
“究竟要杀的是你还是我呢?”司马洛问。
费碧芝不出声。
“也许是要杀你而嫁祸在我的身上,”司马洛说:“那么你就是知道一些你不应该知道的事情了!”
费碧芝还是不出声。
司马洛说:“我不是救了你一命的人吗?”
“那是巧合!”费碧芝说。
“那是我的运气好,”司马洛说:“你与我合作一些,对你没有坏处,我的好运气会沾一些在你的身上!”
“我们不需要你。”费碧芝说。
“为什么你们总是这样说呢?”司马洛说:“史特加死了,你们反而更不紧张。你们不知史特加出卖了一些什么。”
费碧芝想了一阵才说道:“就是因为史特加死了,所以才不紧张,因为……既然你救了我一命,我就不妨告诉你:我们这里所作的研究,霍利先生知道一半,史特加知道一半,史特加死了,研究就做不下去。史特加所知的一半卖掉也没有用,还要有霍利先生知道的一半。史特加活着,我们怕他会查出霍利先生所知的一半而出卖,但他死了就不能!”
“那么,”司马洛说:“霍利先生不是很危险吗?假设史特加把他所知的一半卖掉了,那么只要把霍利先生捉去……”
费碧芝摇着头:“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以为只是要一些文件或图样就行吗?这事还要人的脑筋。史特加活着才有用,否则我们大可以用他留下的文件图样研究下去!”
“哦。”司马洛说:“那么火蛇就是这样完了?”
“是的。”费碧芝说:“因此霍利先生很烦恼,这整个地方都是作研究用的,现在却是没有工作可做了!”
“火蛇究竟是什么呢?”司马洛问。
她耸耸肩不出声。
司马洛说:“难道让我知道也不行吗?杀死我的朋友和史特加的人显然是已经知道了。”
“我也是不清楚。”费碧芝说:“这是真的,有许多事情,我是不需要知道的。”
“但是,”司马洛说:“你知道史特加和菲腊是怎么死的吗?”
她点点头。
“他们给烧掉了。”司马洛说:“用什么武器可以做到如此呢?”
“照我所知,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武器!”
“也许火蛇就是一件武器!”司马洛说:“而他们就是给火蛇杀了。”
“那不是火蛇!”费碧芝甚为肯定地说。
“但是无论如何!”司马洛说:“我们的敌人的手上已经有了一件非常犀利的武器了!”
费碧芝不出声。
“你们也显然并不是没有事做。”司马洛说:“炸弹爆炸是一定有原因的。而且,刚才也有人在我的车子里装了炸弹!”
“有这样的事?”费碧芝说:“你们已经捉到了人?”
“正在跟踪,看看他到何处去,我一会儿就去跟这人谈谈!”
费碧芝说:“我也去。”
司马洛微笑看着她:“你不是说你们的事与我无关的吗?”
费碧芝咬着牙,一时之间,眼睛里像要喷出火来似的。她说:“这个人是要炸死你!”
“那又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司马洛问。
“这也是可能想把我炸死的人!”费碧芝说。
“看来你的口才不太好!”司马洛说。
费碧芝叹一口气说:“刚才你说过要我合作,为什么又不让我们合作呢?你是不是要我这样讲?”
司马洛说:“这话有什么难讲吗?”
“我还没有得到霍利先生准许与你合作。”她说。
“那你就不要去好了。”
“但是,”她有些娇媚地说:“有些事情,我也是可以自动决定的!”
“先斩后奏?”司马洛微笑:“我没有猜错,坐在门口的人,未必就是地位很低的人,还要看看是一个什么地方!”
“是呀!”她说:“我们一起去。”
“你能做些什么呢?”司马洛问。
“你到时就会知道。”她说:“一个人能在门口粘一条头发,也不是一个太普通的人。”
“这倒是真的!”司马洛拿起无线电话,与莫先生联络,讲了一阵之后,他说:“你还是洗一个澡吧,还没有到时间!”
她看着他。她是个美丽女人,有一双美丽的眼睛,而这双眼睛不但美丽,还会提出问题。
他说:“随便你吧,我不会趁你洗澡的时候走掉,我还需要你!”
“很好。”她说着就伸手去把拉链再拉下。
她又不是在他的面前表演脱衣服,只是不当他存在,或是当他是一位很熟的同性朋友似的。
她一面拉一面进入睡房,亦没有关门,出来时她只有内衣裤穿在身上,手拿着另一套干净的用以替换。
她进入了浴室。
司马洛可以看到她有非常好的身材。这是一如他所预料的,虽然她身上还有内衣裤,也是瞒不了太多的。
她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出来。她又走回睡房中,再出来时已换了一套衣服,这一次是T恤牛仔裤。
那是方便行动的打扮。
她已经让他看过了,她有很好的天赋本钱,这显然是她半裸而走来走去的用意。
他说:“你没有武器?”
她说:“你在这里已不少时间,当然也已经搜过我的一切?”
“很对不起!”司马洛说:“不速之客多数会做这样无聊的事情。”
“我不用武器!”她说。
“哦。”司马洛说:“防不胜防,也许这更可怕。”
她微笑道:“我给你的印象就是可怕吗?”
“这是对别人而言!”司马洛说:“我却不怕你!”
“我也不怕你!”费碧芝说:“虽然我知道你是一个可怕的人,但只是对别人而言。”
“我们走吧。”司马洛说。
那个放炸弹的人已经回到了家中。
他并没有去与什么人联络,他只是回到了家中,躺在床上,头上戴了耳筒听音乐。
这是现代年轻人的习惯,有些人认为是不太好的习惯,因为跟他讲话他听不到,有什么危险他也是听不到。
不过,也许他没有戴那个亦是听不到的。
他住的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地方,乃是在天台上加建的一个较小的单位。
这屋顶上还有一个天窗。
这人躺在床上,就刚好能看到这天窗。这天窗没有铁栅,其他的窗子有铁栅,不能爬入,门可是关上了。要未经他同意而进来,那天窗就是唯一的入口。
这人欣赏着他的音乐,有时闭上眼睛,有时睁开眼睛。
在一次闭上眼睛时,天窗就有一双脚伸了进来。
他再张开眼睛时。那双脚的主人亦已进来。
这人就是费碧芝。
那人大吃一惊,然而在他能做什么之前,费碧芝已经坠落下来了。
费碧芝实在是跳下来的,不过这样的跳用不着实力,只要让身子坠下来就行了。
事实上她还要减少堕力。
她踏在那人的身上一弹,就跳到地上。
这样重的人从高处落下而踏在身上,那人的肋骨很可能会全部碎掉,也因此费碧芝是一只脚踏在他有胸部而一只脚踏在床上,主要受力的还是床,她是减少了踏在那人身上之力。她不想这人死掉。
这样的给踏一下,那人虽然是实在没受什么伤,但却也觉得有如给大货车撞中了似的,肺内空气都挤出去了,眼前一黑,全身也是一时之间麻痹了。
他躺在那里看不见什么,也不能动。费碧芝就趁这个机会过去开了大门让司马洛进来。
费碧芝果然证明了,她是能做什么的,而且她也果然是比有武器的人更危险,有武器的人失去了武器就威力大减,她的威力却不会失去。假如知道有武器,也可以防范,看不见有武器,就不知道她会做一些什么事情,那就更是防不胜防了。
司马洛一入到屋子去,就在屋中走来走去,拿着一只仪器探测着,那是探测爆炸品的仪器。
费碧芝则是搜那人的身。
那人的身上并没有什么,司马洛则是找到了很多。他在一只箱子里找到了一大块塑胶炸药。
司马洛说:“住在这下面的人,不知道他们有多幸运!”
他却不是说这东西随时可能爆炸而把这屋子炸掉了,他是说现在用的炸药也进步得多了,这些狂徒们也使用各种形式的塑胶炸药。塑胶炸药的好处就是安全得多,而自己不会爆炸,要装上讯管引爆才爆炸,假如没有引爆,它就只是像粘土一样,掷出去也不怕。
费碧芝说:“这人的身上没有什么!”
司马洛也搜出了信管及其他装引爆的零件。
这个人是一个对爆炸相当有研究的人。
毫无疑问,司马洛那车子是已经给他装了炸弹。
这个人终于从痛苦之中恢复过来,就看见了费碧芝与司马洛在房内。
他很生气,但是亦有些佩服,对方能用这办法入屋制服他。那天窗在屋顶,而他那屋顶是很危险的地方,不易攀上去,又是斜的,一失足就会直滚下街上去了。假如对方是来敲门搜查之类,他可以拿着他的炸药抗拒,现在则是什么都没有了。
他仍是作最后一击,他便一跳跳了起来。
他一跳起来,费碧芝就把他一拉,他在空中打了两个转,又仆回床上,这一次是面部向下。
床虽然是软的,但他转了两转,也感到天旋地转,而伏到了床上,他的口鼻亦被枕头挡住了,一时不能呼吸。
费碧芝说:“你不要想抵抗,我空手也可以把你杀掉!”
司马洛不怀疑这一点,那人亦是不怀疑这一点。
那人慢慢地转过来仰躺着说:“我可以坐起来吗?”
费碧芝摸摸他的脸:“躺着不是更舒服吗?”
一个美女摸自己的脸,在目前这情形之下,却是一点也不好受。
这个美女的手随时可以化温柔为刚劲。
司马洛说:“朋友、你是认得我的!”
“我不认得你!”那人说。
“但是你在我的车上装了一只炸弹。”司马洛说。
那人不出声。
司马洛说:“你是不准备回答吗?”
那人说:“我不知道那是你的车子,我只知道某处有一部车子,我去弄!”
司马洛相信他讲的是真话。这个人的专长不是跟踪,所以跟踪的事情应该是由别人做,而通知他去装。
费碧芝说:“那么是谁叫你去弄的?”
那人又不出声。
司马洛说:“你知道你现在是已经完蛋了吗?你合作,那对你也许有好处!”
那人说:“你不能逼我,你们这些走狗!”
“什么走狗?”司马洛说:“我替谁做走狗?你根本不认识我。”
“你当然是那些野心家的走狗!你们制造战争和恐怖,破坏和平。”
“是吗?”司马洛说:“你的语气我很熟悉,以前也听过了。我们破坏和平?那你装一个炸弹又算是什么?我们并没有装炸弹炸无辜的人。”
“你们的炸弹一炸,就整个世界毁灭了!”那人说:“你们这种人一定要用这种手段对付,这是用你们的手段,只是小模规而已。”
司马洛与费碧芝交换了一个眼色。
他们都可以看出这人忽然又无畏地狂热起来了。
司马洛听这口气就毛骨悚然。这人是属于那些反战份子、反核分子、和平份子之类,他们自称是如此。司马洛则是称他们为恐怖份子或者城市游击队之类。
司马洛一见到这种人总是十分头痛,他们什么都反,实在也不知道自己反些什么。他们也常常会参加什么和平示威之类的游行,而这总是多数演变为打斗流血,要得到的是和平,但结果是混乱和暴力。
他们总是没有想到,他们根本没有证明到什么。
他们也是没有想到他们是受利用的人,幕后的指挥者并没有那么崇高的理想,而是别有用心。
当然,这些小卒们并未必是真的有那么崇高的理想,他们做这些事情多数是为了个人的遭遇,也是在自己骗自己,他们多数都是出身环境复杂,各有不同,但差不多都有共同的原因,就是要找一个藉口发泄他们个人的恨意。
司马洛说:“现在,假如你不招供,我们只好用你们的手段了!”
“你可以杀我!”那人说:“但是你不能够使我出卖我的朋友。”
费碧芝一动手,那人便离开了床上,转了一个身,一屁股坐在地上。这一坐,把他痛得呆住了。
司马洛说:“你看,你们的手段!”
那人却是固执地闭着嘴巴。
费碧芝用强是可以使他不敢抵抗,但那并不等于说能使他招供。
费碧芝说:“我再给你一个机会,是谁叫你做这件事情的?”
“实在是你们!”那人说:“世界上没有你们这种人,就不会那么乱了!”
费碧芝看看司马洛,那是要征求司马洛的意见,看看他认为应该怎样做。
司马洛说:“我们让他考虑一下吧!”
费碧芝于是就退开,但她仍是站着,不坐下来,如此她就随时都可以行动。
那人感到迷惘,不知如何是好,而他亦怀疑对方是有诡计的。司马洛则是拿起手提电话与莫先生通话。后来,他听了一阵之后就把电话关了,看着那人。
那人也看着他,有时看看费碧芝。
司马洛说:“沙洛思,今年三十二岁,十二岁父母死去了,是死在工厂大火之中,得不到赔偿。你很聪明,自己考到奖学金读书,在大学化学系毕业,也许这就是你学到弄炸弹的地方。”
“电脑?”沙洛思说:“你们有每一个人的资料,监视、控制和威胁每一个人!”
司马洛看过他的证件,莫先生就可以从那边用电脑找出他的资料了。
“电脑也告诉我,你的反叛性很强!”司马洛又说:“你几乎什么都反,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赞成的,你只赞成反!”
“这个世界,”沙洛思说:“太多不公平的事!”
“是呀!”司马洛说:“你是不敢照镜子的人,世界全错,只有你对,你不敢抚心自问,问自己有没有做过错的事。”
“我只是……”
“为了你的原则,”司马洛说:“不用你告诉我,那一套我告诉你,我可以背得出来。你这种傻瓜我见过不少了,你不愿去想的一件事,就是你的父母死去而得不到赔偿,你也失去了幸福!”
“那些人……用各种藉口逃避责任……”
“你指的那些人应该是保险公司,”司马洛说:“但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人都有错,现在已经不容许这种错了,你却向现在的人报复二十年前的事!”
“这个世界……”
“你不满这个世界,”司马洛喝道:“你可有另一个快速的方法,就是把自己杀掉,就与此脱离了!”
“我要杀死所有的人!”沙洛思吼道。
“你所讲的和平何去了?”司马洛说:“你炸死过的人,他们有没有得到赔偿?他们有儿女,他们的儿女将来又要杀谁?”
“你不明白!”沙洛思说:“你藉口很多!”
“我问你,你杀的人有没有儿女,他们是不是与你一样?他们做错了什么?”
“我不想跟你讲!”沙洛思说。
司马洛转对费碧芝说:“这个人,你认为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处置呢?”
他很希望她能说出他所想的,而她也是果然能够。她说:“就是把他带回去,他从此失踪,我们设法使他招供,但这办法收效不大,到他招供出来时,他的同党们都已逃了!”
“这就是你们的典型手段!”沙洛思说。
司马洛并没有看他,而只是看着费碧芝。
费碧芝说:“另一个办法就是把他的宝贝工具拿走,这就像把一条毒蛇的牙拔去,他暂时是没有用的!”
司马洛说:“那么你又赞成用哪一种办法呢?”
费碧芝说:“后一种,反正前一种也没有用处!”
“很好!”司马洛说:“你的想法也是跟我一样的,我们把他的东西带走。”
他立即就动手收拾沙洛思的炸药及讯管等物。
沙洛思说:“我呢?我怎样?”
“你是你的事情!”司马洛说:“我们可不是要把你带走,我不用你们的手段!难道我把你杀掉了才走吗?这事我做不到!”
“你们……”沙洛思几乎是哀鸣似地说:“你们不能够就这样把我丢下!”
“那你想怎样?”司马洛说:“跟我们走吗?”
“他们……他们会杀我!”沙洛思说。
“为什么呢?”费碧芝说:“他们是你的朋友呀!”
其实他们都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沙洛思失败了,沙洛思在车上装了炸弹,而炸弹没有爆炸,沙洛思又失去了炸药,假如沙洛思对那些人报告,那些人就会认为他是一个大威胁,非杀他灭口不可。假如他不提这事,他又是瞒骗那些人,那些人也是会杀他。这种事情,沙洛思应该是最清楚的,因为他是内幕人士,他亦一定看见这种事情发生过。他是一个已经完蛋的人。
沙洛思也说:“我对他们的安全有威胁。”
费碧芝说:“为了和平,你可以牺牲性命!”
司马洛说:“你也可以自杀!你用不着用这些炸弹,我可以教你几个自杀的方法。”
“我不想死!”沙洛思说。
“呀!”费碧芝说:“你不想死,别人死多少都不要紧,你却为了和平而死都不行,你不想做烈士?”
“这个……”沙洛思说:“我不想死!”
他简直要哭起来似的。
说他是一个智者也可以,说他是自私也可以。有些人是可以为他们的“理想”而舍身成仁的,那些却是最傻的傻瓜,也是给驱在最前头作牺牲的人,而沙洛思显然并不属于这一类傻瓜。
“那你想怎办呢?”司马洛问。
“我需要保护!”沙洛思说。
“我们保护你?”司马洛说:“那是要有条件的,你要跟我们合作才行。”
“好吧!”沙洛思说:“我合作!”
司马洛说:“很好,你大概也知道,你首先是要对我们提供一些人名。”
沙洛思说:“你会保护我?”
“是的,”司马洛说:“我们不会带你回去,我们只会派两个人在这里陪着你,你合作下去,随机应变,你大概也明白的吧?”
“我明白了!”沙洛思低着头,用两手掩着脸。
司马洛把两个莫先生手下的人叫来了,跟着就和费碧芝一起离开。
司马洛回到了车中,对她说:“你知道我们有的是什么敌人?”
“是和平份子,”费碧芝说:“好战的和平份子,我一听就头痛!怎么世界上有这许多傻瓜!”
“我已经把他分析得很清楚了,”司马洛说:“自以为是最伟大的人往往也是最小器的人,和平之道就是宽恕,他们不愿意去接受这方法。能分析清楚这些人的也不只我,利用他们的人亦是能够如此,所以有这许多人有利用他们。总之,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的对手就是这样的人,那么火蛇一定是一件武器,而他们要反对的就是武器!”
“幕后人的真正目的就是把火蛇夺过去!”费碧芝说。
“有外人知道了,”司马洛说:“霍利先生为什么要守秘密呢?连你也是不能知道真相!”
“我也许是不需要知道。”费碧芝说。
“你现在知道了,”司马洛说:“你也知道那是没有用的了,史特加已经死去了,火蛇已经制造不成了,那些人还是不肯放手,他们究想要什么呢?”
“要的是你,”费碧芝说:“你来查,他们就要杀你了。”
“我奇怪为什么用这方法?”司马洛说:“这是很冒险的方法,会暴露秘密,暴露你公司里还有内奸。现在就是已经暴露了。”
“我猜公司里又会有人死了!”费碧芝说。
司马洛叹一口气:“你们选人,似乎选得太糟了,保安严密,却不会选人!”
“人的心有时会变,”费碧芝说:“而且,科学方面的人才难找,有许多人亦是很怪,性格不易捉摸,需要用这个人的才能,就只好将就一些了!”
“这样说,”司马洛说:“你似乎认为有问题的就是其中的科学家,而不是那些保安人员。”
“应该是的,”费碧芝说:“保安人员较为易找,他们的资格当然也是经过很严格的审查了!”
“这倒是真的!”司马洛说。
“而且史特加也是一个科学家!”费碧芝说。
“我倒没有想到原来他在你们那里的地位是如此重要的,”司马洛说:“没有他就不行,没有他就没有火蛇,他却要把这些秘密出卖给一些人。为了什么呢?为了钱?他在你们那里的待遇也不差。而且,假如火蛇是一件武器,他忽然有这许多钱,你以为他是不是很可疑呢?假如他把钱收起来不用,那他就不需要这些钱了!”
“我不知道。”费碧芝说。
“你们有保安人员,却懵然不觉?”司马洛说。
“我们是有保安人员,”费碧芝说:“但是他们通常不调查像史特加这样重要的人物,等于不去调查霍利先生。”
“现在调查霍利先生吗?”司马洛问。
“霍利先生是无可怀疑的!”费碧芝说。
“在此之前史特加也是的。”司马洛说。
“但是……你总得信任一些人,”费碧芝说:“我现在信任你,你也信任我。”
“我对你也只是作有限度的信任而已!”司马洛说:“我仍然有人在调查着你。”
费碧芝没好气地瞪他一眼:“总之,我们发觉有不对时已很迟了!”
“你们查出了什么?”司马洛问。
“那是你们的工作。”费碧芝说:“你们的人,你的朋友菲腊,发现了什么?”
“他没有机会报告!”司马洛说:“你们这边最初又是发觉有什么不对呢?”
“那是霍利先生说的,”费碧芝说:“霍利先生有一种感觉!”
“只是感觉?”司马洛说。
“你要知道,”费碧芝说:“史特加是火蛇的重要设计人,他是不必把什么东西偷出去的,他知道的一切都在他有脑中。他要偷的是霍利先生那一部份,那一部份亦是在霍利先生的脑中。他要刺探,霍利先生自然就会有所感觉了!”
“卖给哪些人?”司马洛说:“史特加应该知道那些是什么人。也许他不是为钱,而是受到了某种威胁?”
“我不知道,”费碧芝说:“那是菲腊的工作。”
“菲腊又没有报告,”司马洛说:“也许我们的调查又要从头开始了。”
“看来是如此,”费碧芝说:“不过目前先解决这些手头的事情吧!”
司马洛把车子停下来。他说:“这一次还是由你来动手吗?”
“这一次,”费碧芝说:“谁动手也不要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