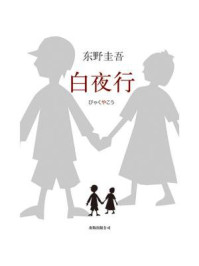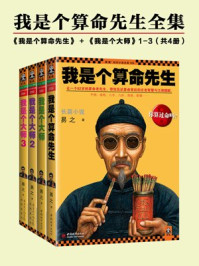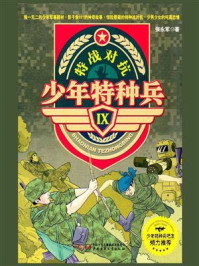以下为心理学中对恋童癖的定义:
恋童癖这个词源于希腊语,原意为对儿童的爱,在DSM-Ⅳ-TR 标准里,他被列为性欲倒错的一种形式,诊断要点至少6个月以来,反复多次地通过与未发育儿童(一般在13岁以下)的性活动来激起性幻想、性渴望或者性行为,这种性幻想产生了明显的痛苦烦恼,或在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方面造成功能性缺损。
引发因素:早期不适宜的性联想和性经验,两情相悦的成人性唤起模式未能得到充分发展,适应性的社交技能未能得到充分发展。
劳伦·B.阿洛伊所著的《变态心理学》中,如此总结恋童癖:
“典型的恋童癖并不是那种生活在社会边缘的‘肮脏人士’,他们多是遵纪守法的良好公民,年纪多在20至40岁区间,大多数也不是隐藏在校园周围的陌生人所为,通常与受害者或者其家人熟悉。”
也就是说这类人往往看起来斯文体面,甚至充满爱心,很容易被误认是喜欢孩子的好人。他们逼迫受害者的手段通常不是暴力,而是利用孩子本能畏惧大人的弱点,要求他们顺服。
这其中最严重、最可怕的是偏爱型性骚扰,他们实际以儿童为性伙伴,一般未婚,喜欢男性儿童,并不认为自己行为异常。他们与儿童的接触是有计划的,不是冲动或者应激的突发事件。男性恋童症者对男孩实行性侵害的行为,如果未能及时制止,受害者会多达上百人,人数是以女孩为对象的性侵害的数倍甚至几十倍,再犯或多次重犯的比例也要高很多。
这么推算,在梁丰然任教的六年里,济得小学可能受害人数简直不敢想象。
鄂奇哲从泰国回来后再也见不到那种标志的嘲笑,只有冷冷自语:“可罗进监狱后天天烂屁股,对于这种人远远不够。”
“可这种人竟成了小学老师。”
因为严重睡眠匮乏,我胃里只反酸,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疯狂。
“邓先明为了自己前途,对梁公子肯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梁公子一进济得,他就整出个记忆法来圈钱,真是嗅觉敏锐。”
“可济得的学生大多都非富即贵。”
“大多,别忘了,也有像黄逸这种孩子,以为能在这里改变命运。哼,确实是改变了。”
鄂奇哲连冷笑的力气也没有,困倦地缩在沙发里,他根本睡不着,随着光线的折射,那座绞刑架越来越近。
“陈发说过,他还有更劲爆的新闻,十有八九会是这个,告诉他如果不配合,我会想尽办法把他塞回到犯罪案底里,一辈子就只能待在这座美丽的岛国,而且我会对外宣称是他在放料。”他的声音泛着金属的冷光。
“你有什么计划?”
“小学校园性侵案,恐怕这才是让梁玉超真正害怕的。我们该怎么对待敌人的痛点?”
“毫不留情地痛击。”
看着颚奇哲冷峻的面孔,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陈发的表情相当错愕,我们都清楚,他没有退路。
这个报道是他的意外发现,更是他的双重保险。在采访先明记忆法骗局的过程中,他发现曾有学生以伤害罪向警方报案,名侦探和狗仔的嗅觉都是举世无双,正如我们,他也很快发现了这件事。
我再次仔细阅读陈发的文章,和之前比较,这次他文风显得有些犹豫,甚至有几处流出了同情。
受访少年是梁丰然的学生,13岁的少年诉告记者梁丰然以补习功课为名,在其住所实行性侵害,达十余次。家长出面后,邓先明却只让妻子尹淑真出面谈判,花钱了事。
我摘录一段报道如下:
记者:你父母为什么没想过报警?
少年:当然是因为钱,还有什么。
记者:为了钱能这么做?你可是他们的儿子?
少年:我不知道,债主天天上门要债,可能他们真的需要这些钱吧。
记者:你恨这些人吗?
少年:我很多次想死,可这些坏人还没死,我就不能死,我得活着,看着他们遭到报应。
记者:那你恨你父母吗?
少年:我们校长太太把那摞钱像倒垃圾一样扔给我们,他们却一声不响把钞票数得整整齐齐,带我回家,让我退学。你说我恨不恨他们?
记者:那你为什么要来找我?
少年:全世界没人相信我,因为我是小孩,警察不相信我,大人都不相信我,全世界都不相信我。我知道很多人看你们的杂志,只有这样,才能抓住那些坏人。
报道在2001年,梁丰然刚回国,就欲望难耐,或者是,有恃无恐。
“你为什么不报道?”我冷冷地问陈发。
“我疯了?我只是个狗仔。有些线我碰不得。”
“你想过这个孩子,或者其他孩子的人生吗?”
“我不是慈善家。”他开始躲避我的眼神。
“现在给你个机会,帮我们找到那个少年。”
陈发反弹式地站起。
“否则你也逃不了。”似乎说这句话的不是我,而是鄂奇哲。
“我找不到他。那男孩不让我拍照,只答应我刊发报道后,会提供更多的证据,我只记得是个马来族男孩。你说我没帮过他?这些年我把这事烂在肚子里,否则还不知道他有没有命活到现在。”
“什么证据?”
“他说是录像,他偷走了那个变态录的一段录像,真他妈恶心。”
“我找人做面部拼图,你帮我们找到那男孩。”
“还有两三天那老头就要被绞死了,你们清醒一点吧!一切都没用了!没用!”
陈发打翻桌上的杯子,从咖啡厅逃跑。
而我却平静走入早在门口等待多时的鄂奇哲的车里。我们两个人出神望着周末街道上的人潮人海,而佐哈里的车正停在马路对面。
似乎现在一切渐渐明了。
梁丰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偏爱型恋童癖,受害人数不敢想象。而邓先明则因为名利而纵容,甚至可以说——
“包庇,这也是梁丰然选择到济得的原因。”鄂奇哲再一次斩断了我的思路。
“邓先明甚至可能利用这个来升官发财,毕竟他有梁玉超的把柄。”
“这同时也是把双刃剑。”
“能让邓先明携全家出逃的,恐怕也只有梁玉超。”我坚定地推断。
“可这也会让他自己身败名裂。不到鱼死网破,他不会走到这步。”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显然有人打破了他们的如意算盘。”
鄂奇哲卯足了劲,在信号灯变换的瞬间,驾车冲了出去,佐哈里的车则紧随其后。
“是不是这个男孩手里的证据?”
那个13岁的男孩似乎并不会轻易放手。
“这些都不算证据,这个佐哈里应该很清楚我到泰国找到可罗,希姆肯定要采取行动,时间不多了。”
岂止是不多,距离那场死刑只剩最后76个小时。
一切越来越清晰,但凶手仍是谜团。现在有两种假设,凶手是梁丰然或另有其人。
假设梁丰然为凶手。
可能的犯罪动机:邓先明因某种原因企图曝光性侵儿童的犯罪事实,因而受到梁氏父子的要挟,被杀人灭口,梁丰然为逃脱治罪,隐姓埋名。
如此假设,随之而来的不解却更多:
首先,邓先明因为署长任期临近,于情于理不敢和梁家作对。
其次,梁家杀人灭口的理由并不充分,梁丰然敢如此堂而皇之犯罪,知情人绝不仅邓先明,很可能还有当年的副校长希姆一众人,甚至还有校董会,以全家灭门手段反而会将事态复杂化。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梁丰然完全没必要以失踪的方式来脱罪,毫无道理。
“所以——”鄂奇哲终于开口。
“所以,凶手极可能是另有其人,他的目标是邓先明一家和梁丰然。”我说出了他心底的答案。
“如果假设成立,肯定会和性侵案有直接关系。”他难得附和我。
“凶手思维缜密,会驾驶汽车,是一个成年人,他既知道邓家会逃到朗尾,又掌握黄呈坚的一举一动,用妓女拖延时间,几乎天衣无缝,关键他是怎么做到的?每一步都刚刚好,就像是在写推理小说。”
鄂奇哲则挑起眉毛回答:“所谓推理小说,就是作者用知情者的旁观角度在讲故事”
“知情者?你指什么?”我警觉道。
“现在说还为时尚早,等会一开锣,某些人才会露出马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