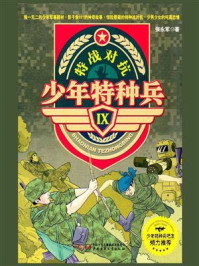现在的局面越来越有意思。
6岁的邓沐灵将6岁的黄逸推下楼梯。
我看着笔记本写的这行字,突然有点冷。
而鄂奇哲在我身后走来走去,“无名”依然潮湿阴冷,我呆望着墙角冒出的绿霉,下一秒,鄂奇哲那张可恶的脸挡在中间。
“想什么心事呢?”他又歪嘴笑了。
“想不通,儿童之间的误伤不应该搞得这么复杂吧。家长道歉赔钱和解,用不着这么神神秘秘。”
“那如果不是误伤呢?”鄂奇哲直回身子。
“她们才6岁!”我也站了起来。
“恶魔,从出生那天就是恶魔,6岁,足够成熟了。”
鄂奇哲说完,只冷笑一声。
还有17天黄呈坚就要执行死刑,再见他恐怕得需要一周,现在必须分秒必争,我立刻拨打了轮椅少女的电话。
少女对这次见面比较抗拒,我们就冒着大雨等在她打工的工厂门口。
下班时间过了许久,穿着红色雨衣的少女才在风雨中艰难转动着轮椅出了大门。泥浆溅脏了那美丽的脸,我快跑上前为她撑伞。
“我们知道,推你的是邓沐灵。”
我看不清,她脸上,到底是雨水,还是眼泪。
2006年4月17日,下午1点20分,黄逸从楼梯跌落,而她身后,只有邓沐灵。
“她为什么要推你?”
我们回到无名,我刚将怀里的少女放在沙发,鄂奇哲凌厉的提问就跟上来。
我赶紧找来毛毯围在少女身上,顺便递给鄂奇哲闭嘴的眼神。
他立刻心领神会,退到一边看我笑话。我微笑地递过一杯温水,坐在她身边,边说边盯着她的表情变化。
“我相信你父亲是清白无辜的,但你得把实情告诉我们,我们才能准确推断。实话实说,你父亲脱罪难度非常大,而且,只剩下17天——”
“确切说是16天22个小时。6月8日下午四点,你父亲就会被绞死。”鄂奇哲猝不及防地插嘴。
我们三个同时看着墙上的挂钟,此刻是5月23日下午6点整。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少女抓着头发大哭起来。
“你这些年一定问过自己很多次,到底为什么,她会推你?”鄂奇哲再次盘腿坐在少女面前,目光锁定对方。
“是文艺节,我想了很久,是文艺节。本来班级领唱的是她,可她突然感冒了,不得不换成我。”
“她父亲是校长,以前什么风头都是这丫头的吧。”
少女只是在哭。
“你告诉老师了吗?”
她的哭声,比窗外的雨声更瓢泼,将整个无名没顶,我张大嘴用力呼吸。
“我告诉了每个人,老师,同学,还有爸爸,可是没用,没用——”
又是这句“没用”。
“你爸爸不可能这么冷漠吧。”鄂奇哲毫不动情,置身事外观察着少女。
“我爸让我不要告诉任何人,说要带我去国外做手术。当时我非常恨他,他让我对每个人撒谎,他说,只有撒谎,我们才有钱去治病。”
“看来你父亲和邓家谈妥了。”
鄂奇哲说完起身,叼着根烟又站在窗边,这该死的大雨依然没完没了。我只觉得墙角那块绿霉吐出枝蔓,湿冷入骨。
轮椅少女走后,雨反而更猛烈,我看着密密麻麻的雨滴,却想起少女脸上的泪。
“如果这么看。黄根本没有犯罪动机,他们已经达成和解意向,如果杀了邓先明,他女儿反而得不到钱治疗。”
鄂奇哲冷冰冰的话,让我回到现实,回身看见他又怪异地笑起来:“同时,他们父女更不敢告诉警方真相,因为这么一来只会更加证据确凿,有意思,太有意思了。”
我们心里清楚这个凶手很聪明,甚至有点过分聪明了。
我迅速整理好桌上的面部拼图素材,准备出门。
“那个妓女可能是突破口。我明天就想办法再去探监。”
“署长已经给我带话了,让我们别再去监狱。你已经露馅了,再想见他,除非是观摩死刑。”鄂奇哲边说边按下打火机,抖动的火苗没点燃烟,只照亮了他的脸。
我把背包摔在桌上,那张黄呈坚的案底照片飘飘悠悠落在我的脚面上。
“有意思。真的太有意思了。这个凶手知道黄呈坚当天的全部行踪。甚至安排好了妓女制造时间证据,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故事也不会如此无缝对接。”
“简直是上帝视角,能知道黄呈坚一举一动。”
颚奇哲听到这句话戏谑地瞪大眼睛,腮帮子鼓鼓地憋着笑。我立刻察觉到什么,瞬间恍然大悟。
“凶手在跟踪黄呈坚!他在跟踪!”
颚奇哲伸了个懒腰,懒散地说:“警方案底显示黄呈坚进出高速路口的时间,就说明他们有相关监控资料。这里面可能就藏着凶手的信息。”
这个案子到现在,好像才有了一丝柳暗花明的意味。
我竟有点记不清那天的日期,反正是个星期一。当我们走进济得小学,这个湿冷的案子开始变奏,铺垫了那么久,暴风雨终于来了。
济得小学原址是殖民地修建的教会学校,岛国独立后经数十年的扩建翻修,成为今天富丽堂皇的名校。这里的学生非富即贵,像黄逸这种中下层阶级出身的孩子倒是异类。
这所学校校董会成员都是晋古当地的名门望族,颇为神秘,关于这所学校的传言很多,邓先明从一名小学校长一跃升到教育署长,恰能说明济得的背景之深。
邓先明在此任教二十年,任校长八年,而现任校长希姆,这位占族土著后裔,自邓先明去世至今已担任校长整整12年。在他的掌控之下,济得已脱胎换骨。希姆这个人更是狠角色,甚至有传闻和某些占族黑帮来往密切。
表面济得是学校,实际上它是一座宫殿,只为贵胄权势所有。
秘书陪我们在校长室已经等了半个小时,希姆的声音通过扩音器,飘荡在校园每一个角落。
他的声音强劲有力,本人更是身材魁梧。希姆迅速签完手头所有的文件,对我们始终保持距离。
“我还要去开会,长话短说。或者,我直接说吧。这个案子已经定性,犯人也缉拿归案。本人久仰鄂侦探的大名,但这次恐怕板上钉钉了。”希姆扫了眼手表,示意着秘书。
可颚奇哲根本不管这套,想让他走可不容易。
“咱们就当回忆往事好了,毕竟死者是您的前辈,除非校长您不想,或者担心什么。”
岛国的人基本都听说过颚奇哲难缠的诨名,和他扯上关系多半没好事。希姆想了想,让秘书离开,甚至还给颚奇哲递了一根烟。
“你们是怀疑我?为了当个校长,我犯不着杀这么多人。”
“这倒是,可您接任校长倒挺意外吧?”
“我是由校董会直接任命的,合情合法。”
颚奇哲点了点烟灰,突然出其不意抛出准备多时的“重磅炸弹”。
“那个叫黄逸的小女孩受伤,您应该记得吧?这事不小,您当时任副校长,肯定应该记得。”
希姆慢慢吸了口烟,在想着什么,然后回答说记不清。
“那谁能记得这件事?我们想了解些情况。”
希姆打了个电话,几分钟后,一个穿制服的马来男人走进来。
“这是我们安保部部长,叫佐哈里。”
那男人虽满头白发,却挺年轻,整个人像根柱子,笔直又平板。关键面目可怖,戴着巨大的眼罩,几乎遮住一半面容。
“佐哈里初中毕业后就在学校里做校工,当时就是他送那少女去的医院。”
“这您倒记得清楚。”
鄂奇哲总算逮着机会,希姆面露尴尬,挤出了一丝笑容。
我们跟佐哈里走到操场,鄂奇哲想抽烟,却被佐哈里严肃制止,这次鄂奇哲倒乖乖顺从。
佐哈里的讲述简洁明了,2006年4月17日,下午课间时间,他正在清扫走廊,突然听见尖叫声,走过去看见瘫倒在楼梯口的黄逸。
佐哈里领我们到出事地,是座欧式风格塔楼,曾是教堂的钟楼,出事的那段楼梯长而陡,顶层是全开放的阶梯教室。
“当时楼梯上有人吗?”
“没注意。”佐哈里回答得很快。
“黄逸说有人推她,你没看见?”
“记不清了。马上要放学,我要到校门口执勤,您们请便。”佐哈里边用对讲机召集安保人员,边快步离开。
鄂奇哲蹲在那段楼梯口仰望,我也蹲下来。顶层的一切一览无余,人的本能反应不可能不向上张望,邓沐灵只有6岁,估计早吓傻在原地,所以,佐哈里肯定在撒谎。
我们驶出校门口时,佐哈里正一丝不苟地指挥交通,一个小男孩因为追逐同伴突然闯进车道,在我猛踩刹车前,佐哈里已经用身体挡在车前,他直勾勾瞪着我们,片刻才缓缓放行。
“这个学校里净是谎言。”我透过后视镜,看见这所华丽堂皇的学校渐渐消失。
鄂奇哲只习惯性地撇撇嘴。“所谓人类灵魂的工程,恐怕自己就是个烂尾楼。”
“必须盯着希姆和佐哈里”我说。
鄂奇哲边点头默认边说:
“黄逸这个事被封锁得这么严,这些人肯定内外勾结,没有王牌,撬不动他们的嘴。你去查查,2006年前5年内,济得小学或者邓先明本人有过什么特殊新闻,看看能不能找到些线索。我去和署长谈谈,他曾经承诺会无条件协助,至少把尸检报告拿到。那个在现场的安保说起火5分钟内他就赶到现场,却没听到任何人的呼救声,这完全不合常理,除非——”
“除非,他们早就死了,火灾不过是个假象。还有尸体邪教图案,总觉得在欲盖弥彰。”
“那快行动吧,美男子。”鄂奇哲突然龇牙笑了,我厌恶地立刻跳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