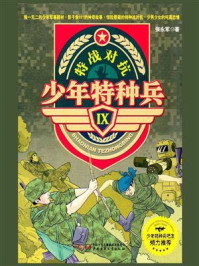第二天刚破晓,我就等在黄呈坚曾经工作的物流公司,公司主营食品配送,全天运营。我等到9点才见到负责人。
负责人听到我的来访倒挺热情,让会计找来当年的配送记录。
“到现在我都不相信,老黄能做出这种事,当时我是后辈,他是我们这班最认真勤快的人,拼命赚钱养家,听说要供女儿念名校,学费很高。哎,女儿是他的心头肉。”
负责人还找出他参与请愿游行的照片。
“没用了,警察只想着赶紧抓住凶手,快点结案。无论说什么,他也被认定为凶手了。”
“你们当时没向警方提供配送信息?”
“实话实说,这条记录没有问题,这是个老客户,几乎每个月我们都定时送货。”负责人说完递给我那天的记录。
记录只有寥寥数字。
2006年6月21日,货车A0015晚7点出发送100袋面粉至朗尾文茂酒店。
负责人挑给我看,几乎每个月,他们都会为这家酒店配送原材料,时间都在20号左右,至今如此。
看来凶手熟知邓先明和黄呈坚的一切,只有一点,我仍不解。
“案发当时是午夜,为什么这次送货这么晚?”
“当天本应该下午出发,但老黄突然中午请假,说是4点来,没想到7点多才回来。”
“他没说原因?”
“老黄不爱说话,我们一般也不多问。”
走出物流公司才不过10点,这该死的雨季,让人终日活在傍晚里,眼见最后一丝光亮消失。
午饭,我才和鄂奇哲碰面,我说了今早的收获,同时抛出了疑问。
“黄呈坚请假的那7个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凶手就像是这起凶杀案的编剧,所有角色,都在他的掌控之下。”
鄂奇哲只是风卷残云地消灭所有食物,满足地吸着拉茶,可实际上他空手而归。邓家的亲友都不清楚邓先明一家为什么会去朗尾。当时邓先明还为自己和儿女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他们肯定是有特殊的目的,这也就成了目前关键的疑点。
酒足饭饱后的颚奇哲,边剔牙边慢悠悠地说:“与其在瞎猜,不如问下当事人。”
“黄呈坚是死刑犯,一般人可见不着。”
“神父和心理医生除外。”鄂奇哲歪嘴,朝我笑了。
他这个人就是诡计多端,而我正巴不得能见见本人。
可突然他又收起笑,换了张面孔,冷冷地说:“你见到黄呈坚,问他三个问题,第一,请假那七个小时去做了什么?第二,10点抵达朗尾卸货完毕后,为什么他11点40才出现在高速路口,一个多小时发生了什么?第三,他知不知道,推她女儿的人是谁?”
“你怀疑这个也是凶手做局?”我停下笔记吃惊地问。
“一种推测,我看那个少女的反应,似乎她清楚是谁推了她。”
想要以心理医生的身份见到死刑犯不是件容易事,老师高奇再一次帮了我们,湖内老屋案之后,我都数不清受到老师多少次恩惠,是感激,亦是激励。
警方只给我半个小时时间,我终于见到了这位著名的黄呈坚。和案底照片比,他至少老了半个世纪,穿着死刑犯的橙红色囚服,还有沉重的脚镣。
我简短说明来意,没想到黄开口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找你们,是不是要花很多钱,现在中止,需要付多少违约金?”
我只好耐心解释我们这次并不是为了钱,但黄呈坚似乎什么都没听见,只喃喃自语着,反复说着花钱,为什么要花这个钱,浪费,还有这一句。
“没用了,没用。”
这话似乎听得耳熟。
“您女儿从孤儿院走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我们,为了您女儿,您也不能放弃。”
“今天狱警通知我,我的刑期定下来了,下个月8号,我明天就要转到特殊牢房,等死。所以说——”黄呈坚抬起麻木的眼皮。“一切都没用了。”
“有用,当然有用,为了,为了——”我脑袋快速分析对方的心理弱点,当然是他唯一又可怜的女儿。“为了不让您的女儿以杀人犯女儿的身份活一生。”
趁着黄呈坚短暂的沉默,我加快进程,狱警已在玻璃窗外认真打量起我,更因为离6月8日执行死刑的时间,只剩17天。
“6月21日中午12点到晚7点之间,你突然请假,到底是去做什么?”
黄呈坚看着我,同时余光扫到门口的狱警。
“从现在开始,必须要不假思索地告诉我们真实答案,可能,还有一线生机。你应该知道鄂奇哲是谁。”
黄假装咳嗽,边小声回答:“我去了邓先明的家。我听说他请假,所以去他家里理论,没想等到7点也没见人。”
“警方不清楚?”
“我没敢说,怕说了,更被认定为杀人凶手。”
“为什么你去邓家?”
黄呈坚眨了下眼,我预感情况不妙。
“因为,我女儿的伤势,学校必须得负责。”
“邓先明是校长,但不至于要找到他家里去吧?”
“济得小学他一个人说了算,他不同意,没人敢答应,我女儿还欠着医药费,必须赶紧结清,才能去做手术。如果,手术做了,她现在应该——”
“什么手术?”
“去新加坡做复位手术。”
“哦?”我竟然像鄂奇哲一样拖长了声调,真令人反感,接着我迅速进入第二个问题。
“那6月21日晚10点10分离开送货酒店,到11点40分驶向高速口,有一个多小时的空白时间,你当时在做什么?”
“我,我——”
“别想,立刻回答我。”
“我找了站街女。”黄叹了口气。
“你和警察说了吗?”
“他们不信。说了也没用。”
“妓女的名字相貌你还记得吗?”
“我在路边遇见一个拦我车的站街女,叫NINI,就是普通本地人的样貌,黑瘦矮小,20岁左右。我托朋友四处找这个女人也没找到。站街女可能一天换好几个名字。”
我迅速在笔记上用红笔加重写了妓女这两个字。
“我还会再来,到时我会做面部拼图,这两天,你一定要仔细回想那女人的相貌,这可能会救你的命。”
黄认真点头,铁门突然被推开,几个预警闯进来要带走犯人。
在他们给黄呈坚上手铐脚镣的间隙,金属的摩擦声像钟鸣,一切迅速退回到那个时刻。
我在本子上快划出几个字,贴在玻璃窗上。
黄呈坚像困兽被人重新捆绑,越过层层混乱,他辨认出我写的那几个歪曲的字,在关门那一刻,他朝我点点头。
我吐口气,瘫在椅子上,警卫命令我立刻离开,我神情恍惚地走出这座重刑监狱,鄂奇哲在门口冲着阳光吐着烟圈,原来今天是难得的晴天,这算不算晴天霹雳。
“是那个人吗?”
我点点头,然后上车。
我那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其实是个名字,很好听的名字:邓沐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