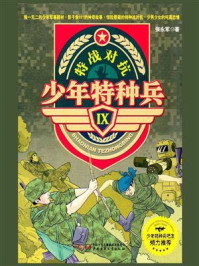等我再见到这个男人时,他全副武装,只露出一双充满红血丝的双眼。
鄂奇哲不为所动,打开投影仪,冷冷地说。
“这三个女孩,你认识吗?”
那男人看着她们的脸,更惊惶失措。
“她们都曾和你签过包养合同?”
“是。”
他声音抖得模糊不清。
“可是我身体没问题。签合同前,我都为她们做了最全面的体检。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有些人艾滋病毒潜伏能十几年。”鄂奇哲开始不耐烦起来,强迫性追问着。
“岳超认识吗?”
“不清楚。”
鄂奇哲打开岳超的放大照片,他却浑然不动。
“你肯定认识他。”
“我还有老婆,还有孩子,我最小的孩子才8个月。”
他除了痛哭,说不出话来,什么神话的人,剖开,都差不多脆弱。
“岳超,你的大学同学,他以前叫作岳子明,因为你自保,所以让他背了黑锅。”
“如果我承认了开除的就是我,可我,没有立场承认。”他越说越冷静。
“你毁了他的梦想,还有人生,对于岳超这类底层出身,大学就是他们一生的转折。”
“他就用这些女的报复我?他不过是被大学开除,那我呢,我全部都被他毁了。”
“毁你的,是你自己。”
这位‘投资之神’痛哭流涕,我可以安慰莎莎,可对这个像老狗一样的男人,却丝毫不想靠近。
“你们的合约是多长时间?”
“两年。”
“你从哪年开始玩这个?”
“应该是2006年左右。”
根据张恺的自述,在2006年的秋天,N&F俱乐部少部分人开始玩起性虐游戏,在风投的高压力下,这些白天衣冠楚楚的精英,入夜后潜成了一头野兽。
还有5天就到凶手提出的截止日,而今天,也许会有张新照片。
张恺将包养合同和所附体检报告转交给我们,这三个女孩都曾是健康的姑娘,两年间不约而同染上了艾滋病,前两个女孩可以断定在合同期间和岳超发生过关系,加上岳超存在复仇可能,恐怕传染源是岳超,而不是这三个女孩。
每个人的包养合同到期日几乎都是照片中标注的死亡日期前的一个月左右。这三个女孩似乎都是岳超精心挑选之作,她们如猛虎,扑向这个圈子。
张恺、莎莎,还有那些面具下的男男女女几乎都被感染,一时间,曼京和华中街人心惶惶,卫生署不得不出面,强制所有性工作者验血。漩涡越来越大,N&F俱乐部被查封,连金哥都被带走问话。卫生署正好借机大力宣传预防艾滋病的知识。连我走在大街上,也被一位老阿婆硬塞给了一本预防知识手册。
我推开无名侦探社的大门,鄂奇哲还在呆呆地看着这三个女孩的照片。我一瞅手表,已经快下午三点,可那个信封却没如约而来。
“现在全岛普及预防知识,我们无形中还做了件好事。”我用心洗了好几遍手,才开始啃苹果。
“张恺在签包养合同之前都会让这些女孩体检。他做了万全的措施,没想到,还是中了这个连环套。岳超利用完女孩再灭口,情理之中。”我嘴里的苹果搅乱了发音,黏黏糊糊地说着。
而他却一反常态地极度认真,每当他身上散发出紧绷的气味时,我们所侦破的案子也就要迎来大结局了。
“这些女孩不过是岳超的工具,他会这么呵护她们的尸体吗?他是失败者的报复心态,而凶手不同,分明在惋惜,怜悯。”
我直接咽下苹果,这正说中我心里的谜团。
“岳超不可能,那小护士似乎也没理由善待她们。”
鄂奇哲瘫在沙发上,下一秒似乎就要想起鼾声,可突然却发出清晰有力的声音。
“璐璐和索玛姐姐的话都印证两位受害者在合同结束前后开始自暴自弃,甚至流露出轻生念头。现在看毫无疑问,是艾滋病,虽然她们漫无目的活着,可这个重创毁了她们年轻的生命。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她们知道了病情,是谁告诉她们的?”
“难道是岳超?”
“应该不是别人。”
“可这太残忍了。”我自语。
可他只冷笑一声:“可她们也好不到哪去。”
“你指什么?”
他只把那些包养合同书抛给我,那是杜仪的合同,她是2008年2月10日到期,死亡时间是同年的3月6日。
“那年2月14日,她还因为卖淫被抓,不知道会传染了多少人。”他冷冷地又追上了一句“她们不死,不知道还会祸害多少人。”
鄂奇哲话音未落,就听见门外有人走上摇摇坠坠的木制楼梯,我屏住呼吸,他却嘲笑起来。
“你认为他会亲自送上门来?”
说完接着大步流星地拽开门,正要敲门的快递员吓得脸色发白。
信封里面的依旧是一张照片,一张没有脸的照片。
照片背面写了两个字:
鼓掌
同样构图画面里女孩的脸被完全抹去,只能看见她瀑布般的长发,和白色蕾丝衣领,蕾丝花纹和第二张照片相同,但第二张照片里,蕾丝花边卡在肩膀上,这张则合身服帖。
“鼓掌?什么意思?”
鄂奇哲却哈哈大笑,连连说着:“妙,妙。”
“什么意思。”
“这才是凶手想看到的结局吧。”
“什么结局?”
鄂奇哲只拿起那本预防手册,良久没作声。
在我追问下,他才又从电脑里调出岳超在监狱里服刑的照片,岳超如病患一般枯瘦,像极了索玛的姐姐,出狱时估计病情已经全面爆发。
而他只是平缓拖出了自己的结论。
“这几个女孩都是因为岳超被感染,她们浑然不觉,直到岳超弃用她们时,才被告知患病,但之后她们没停下放纵的脚步,自私甚至充满恶意继续传染给别人,正如岳超一般,于是凶手动手,杀死她们,似乎也在怀念她们。”
他边说边放大最后寄来的照片,同时把第二张照片中白色蕾丝的部分一再放大。
“你看出什么?”他问。
其实他完全多此一举,明显,这件白蕾丝连衣裙是第四位受害者的,索玛是硬套上的,估计更加丰满的杜仪只能搭在胸上,而偏胖的陈芳甚至穿不上它。
“第四位被害者更纤小,而且,她对凶手意义重大。”
他仍然放大第四位受害者的局部,直到最终像素模糊。
“这就像是记忆,越努力,越模糊。”他终于罢手。
“凶手是谁?”我望着那模糊的色块。
“谁能同时知道这几个女孩染上艾滋,谁就是凶手。”鄂奇哲终于先回到沙发里,回到了常态。
“是岳超诊所里的人?岳超,小护士,还有谁?”讲到这时,我已豁然开朗。
而他只转过头,露出了那个捉摸不透的笑。
我们敲开那位老护士家楼上客房房门时,只看见晃荡的两条腿,她的死亡甚至比照片的女孩们都美丽。
她吊死在水晶灯上,垂头好像正看着桌上那一本手绘彩虹封面的相册,一页页翻开,是她的女孩从婴儿变成天使,又堕入深渊的故事。
相册最后几张照片我印象尤深,那是老护士在诊所里偷拍手术台上女儿熟睡的照片,她拍了一张又一张,似乎,这一刻,她才是她的宝贝。
8月8日,风和日丽,我们收到了那个信封,里面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岳超死亡时全身溃烂的照片,照片背后写道:
“罪恶强加别人,只会让自己罪孽深重,一个多月前对他临终探望中,陈英告诉我这一切,他因为医疗事故感染上艾滋病,心生恨意走上了复仇的罪恶之路,没想到我也成为了这罪恶的一部分,所以请求你们以这种方式公布于众,拯救别人,更是拯救我自己,谢谢。”
另一张是她女儿站在曼京街头大笑的照片,她那么美,又那么脆弱。
我翻过照片,看见了她留下的最后一行字。
“今天是她的生日,也是她的忌辰,是我亲手送走了她。她是我挚爱的女儿,当我知道她得病为时已晚,我尝试了各种办法劝她治病,可她却仍然我行我素,她毁灭了自己,也要去毁灭别人。当我死死掐住她的脖子,她却一直笑着,至死都那么不堪。那一刻我真想松手,可如果她不死,她就会肆无忌惮地将疾病传染给任何无辜的人。后来我遇见同样如她的女孩们,同样美丽,也同样无情,她们不幸被感染,却故意继续制造不幸,仅仅是因为她们自私的恶意。幸好,她们的灵魂终于能摆脱这些美丽却邪恶的躯体,希望,另一个世界里,真的有天使。”
在某个阴冷的下午,我特意走向那个公园,路人寥寥,远处长椅上坐着一个穿着红色紧身皮衣的女人,渔网袜紧勒大腿上的赘肉,她没精打采打着瞌睡,可能是闻到我身上的香水,眯着眼睛朝我这面瞥来,使劲挤出微笑,冲我招了招手。我摇摇头,转身而去。
那就是杜仪的母亲,如果杜仪没踏进这个圈套,如今还活着,等她红颜老去时,会不会也是这般模样呢?
可是这一切,早已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