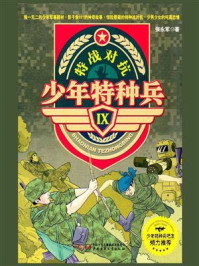夜幕降临,很多人换了张面孔活着,包括,这座城市。
曼京,岛国首都的南部,不过三五条街口,却是夜色里最繁华、最热闹,也最危险的地方,混杂着各种语言肤色,塞满了悲欢离合,毕竟这里是可以媲美芭堤雅的红灯区。
2022年某个炎热的夜晚,鄂奇哲竟约我在这见面,让我愕然又好奇。
可真到了曼京,我倒挺失望,不过是布满数十家酒吧的小街,小贩扎堆,垃圾满地。
我去得太早,女孩们才陆陆续续坐着摩托上班,她们面容倦怠,顶着满头发卷,身体被短裤吊带裹得呼之欲出,趿着人字拖晃晃悠悠走进各家夜总会的后门。
天色完全暗了,灯连起成片,当街角垃圾秽物被人头攒动完全盖住,这才是曼京。
一瞬间这条街涌进了无数穿着三点式的艳俗女郎。浓妆下,我看不清她们的年龄相貌。
而鄂奇哲在这寻欢作乐的氤氲中,缩在那件米黄色防水风衣里,卓尔不群走来,我耳边甚至响起拉风的电影配乐。
我们刚坐在窗口的位子,兔女郎趁机凑过来递上了酒水牌,而鄂奇哲却塞给了她一张大钞,低头耳语几句,女郎抖了抖兔尾巴,欢快地进入后台。
我当然要借题发挥。
“原来大侦探也有七情六欲,我还以为你是无性恋呢。”
他边吐烟圈,边把一个信封扔在桌上。
里面是一张照片,我先看到白底,一行已经花了的潦草字体,写着2008年3月6日,反过来,我身体瞬间凉了。
那是一张有年代感的彩色照片,一张女孩的脸,从雪白的脖颈到波浪卷的头发,她画着精致的妆容,仿佛睡美人一般。
“这个女孩应该很年轻。”
鄂奇哲歪嘴一笑。“你果然对女人敏锐。19岁,或者说,只活到19岁。”
“受害者的家属呢?你们谈过了?”
“委托我的,不是被害者一方——”
我猛抬眼看鄂奇哲,同时注意到,桌上还有一张卡片。
字迹依旧潦草。
“如果你不及时制止我,我身体里的恶魔一定会再杀人。它越来越强大,我要控制不住它了。请抓住我,抓住恶魔。”
“可能是恶作剧,你现在声名在外。”我谨慎回答。
“可这个女孩真的失踪了,可没人知道具体时间,也没人报警。”
“为什么?”
鄂奇哲陷在沙发里,仰头吐出口烟。
“她是个站街女。13岁就离家出走,母亲也是娼妓,这种女孩是下手最好的目标。”
“无人知晓。”我边说想起了那部同名电影里的情节。
“我决定接这个案子。”
“为什么?”
“‘我身体里的恶魔一定会再杀人’,这句话说明什么?”
“不止这一个受害人?”
鄂奇哲的笑容在昏暗的灯光下若隐若现,而我总觉得有些蹊跷,这像是一个圈套,可真要是能活捉一个可能具有多重人格分裂的表现型杀人狂,那绝对会对我的心理学博士论文大有益处。
我快速浏览案件基本信息,非常简短,或者说,一目了然。
女孩叫杜仪,其母杜娜曾是舞女,生父不详。杜仪12岁辍学,有少管所记录,未成年就在曼京做站街女,曾因卖淫被捕多次。
“大概是个误入歧途的可怜女孩,不过信息也太少了,就这么几页纸。”
“女孩的资料不多,但案底不少。我找到了和她一同被捕过三次的女人,也许算是和她比较亲密的‘同事’。”
“她在哪?”
鄂奇哲又撇嘴笑了。显然这才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
不消片刻,这间酒吧的妈妈桑风风火火迎来,她冲我眨了下眼睛,才看到鄂奇哲手里杜仪的照片。
“我见过的女孩太多了,这是谁啊?”妈妈桑只扫了一眼就放下照片。
“你和她一起进去过三次,不可能一点印象都没有吧。最后一次你们被捕的时间是2008年2月14号,日子还挺浪漫。大概不到一个月,她就失踪了。”
“啊,是这个丫头。”
妈妈桑低头点燃了一根烟,砸吧嘴,直盯着鄂奇哲,许久没再说话,突然间她眉头一展。
“我说这么面熟,你不是那个大侦探吗?这丫头难道是死了?”
鄂奇哲把装钱的信封掏出来。
“你需要的是回答,不是提问。”
妈妈桑立刻了然于心。
“你和她在一起工作?”
“我们都跟着晨哥干,在NANA酒吧。”
“她失踪了这么久,你没找过她?”
“这些人来来走走,说实话,十年前我们还不如牲口,生生死死的事多了。哪像如今这些丫头活得潇洒,一个个像大小姐悠闲。”
“要认真回答问题哦。”鄂奇哲笑着晃了晃那信封。
妈妈桑赶紧给我们倒酒,扭着水蛇腰笑了。
“晨哥手下女孩大概有七八个吧,每晚都6点上班。突然有一天这丫头就不来了,她的长相你们也看到了,绝对是头牌红人,一般客人不接,尤其是那两年好像更大牌,不出台,只陪酒。”
“那她还因为卖淫被抓?”
“那是她自己发疯。那一阵发神经,什么人都睡。我们都以为她私奔了,毕竟当时她挺小,被骗了不稀奇。”
“她有关系要好的小姐妹吗?”
“有一个叫璐璐的,后来上岸嫁人了,早没联系。”
“我要一张这个璐璐的照片。”
妈妈桑扭着身体摩挲鄂奇哲手背,突然抽走那个信封,满意堆起笑容,还不忘悄悄打量我。
夜已深沉,我倚在酒吧窗户,这条街上,年轻的脸庞早晚会被更年轻的面孔取代,循环往返,生生不息。街角有几个恨不得将胸口全敞开的不再年轻的女人,主动牵着往来男人的手,却被一次次甩开。如果杜仪活到今天,很可能会落得这种境地吧。
不久后,妈妈桑如约送来一张杜仪和璐璐的合照。两个年轻女孩并排坐在一间日式榻榻米的房间,屋内雅致整洁,侧面窗口洒进的阳光正照在她们身上,而玻璃窗的掠影里映出一个红色十字架。
她们应该同龄,如今已经三十多岁。
杜仪目前已知的关联人,一个是璐璐,一个是老板晨哥,还有就是生母杜娜。
而这三个人的命运如今却大不相同。
晨哥多年前因械斗暴死街头,杜娜如今快60岁还在公园做暗娼。而璐璐却嫁人生子,甚至还做了幼儿教师。
幼儿园门口的车流已经散去,老师们陆续下班,璐璐笑着走出大门,她看起来比照片更秀美,纤弱白皙,那个她企图摆脱多年的噩梦,恐怕要再次降临了。
她看到那张合影后,吓得差点晕倒,只无助惶恐地连连询问。
“你们想要什么?”
她根本听不进解释,躲在车里不肯出来。
“我欠晨哥的账都还清了,你们还想干嘛?”
“我们是为了照片上的那个女孩而来的。”
等我们坐在咖啡厅里,璐璐已经平静下来。
“我不清楚她现在的情况,我们十几年没见了。”
鄂奇哲把那张凶手寄来的照片递过去。
“你们恐怕永远也见不着了。”
璐璐捂住嘴巴,眼泪不停落在手背上。我看见她在发抖,特意为她点了一杯热茶。
“这种结局,其实,其实也不意外。毕竟那样活着,根本没有明天。”
鄂奇哲递给她一支烟,璐璐犹豫了一下,才接过去。
“这玩意,我10年都没碰了。”
“杜仪是个什么样的女孩?”鄂奇哲敏锐地盯着对方。
“她是,是个,很特别的女孩。外表很美,可内心,怎么说,一无所有。”
“怎么说?”
“我是被逼的,我那个死鬼老爸欠了一屁股赌债,我不得不做这行。可没人逼她,晨哥也控制不了她,她可以随心所欲做任何事,如果我是她,我绝不会踏进那个地狱。”
“是她自甘堕落?”
“可以这么说吧。她什么客人都接,拼命接客,也玩命花钱,其实她不缺钱。我问过为什么这,她说也不知道,说就是喜欢这么活着。”
“她不养她妈?”
“她们早断绝关系了吧。反正,我从没听她提过。她应该非常恨她。”
“因为她卖淫?”
璐璐抽烟的姿势已不熟练,烟灰磕在袖口上。
“因为她妈妈的男友,她12岁跑出来,就是因为被那个人强奸了。那男人也是个龟头,管着她妈妈几个。然后她开始在街头揽客,什么苦都吃过,直到在晨哥手下大红。”
“那个人渣叫什么?”
璐璐本来拒绝回答,可大名鼎鼎的鄂奇哲显然让她感到顾忌。
“马跃,大家都叫他毒佬。后来这男人还曾恬不知耻找她要钱,听说拍了裸照什么。”
“杜仪给他钱了?”
“她什么风浪没见过,根本不在乎,找晨哥揍了那男人一顿。”
我快速记下这个马跃的个人信息,刚落笔,就又听见鄂奇哲幽幽问道:“这么多年,你没想过她可能早就死了?”
璐璐冷笑一声,深深又吸了口烟,这次娴熟优雅,甚至有些妩媚。
“她活着和死了又有什么分别?谁会在意她?关心她?她这么美,却成了一生的诅咒,死了倒好。如果我没逃出来,也希望一了百了。”
就这样,马跃是我们第一个嫌疑人,可杜仪的社会关系极复杂,天天和陌生人见面,也有随机杀人的概率。
我们找到‘毒佬’时,他正跪地乞讨,被人砍断了双手。
鄂奇哲把一张大钞放进那个只有硬币的塑料盆里。
他木然抬起头,看见我手里杜仪的照片,立刻爆发出一连串汇集了难以想象低劣的污言秽语。
鄂奇哲拉起我,显然这并不是会善待杜仪尸体的人,我们无言地快步穿过了几个街口,就来到了无名侦探社。
开门的那一刻,我看到从门缝里塞进来的那封信。
依然是没有寄信地址,我隔着信封就摸到,那又是一张照片。
另一个更美丽的少女长眠于画面之上。她简直像是安睡的仙子,嘴唇微张,有种脱尘的高级美感,更楚楚动人。和杜仪几乎是同一个角度,唯一不同是脖子边上有着一段白色的蕾丝边。
照片背后,还是那个潦草的字迹,2010年7月3日。
下面还跟着几行字。
“我等得太久了,如果你们没能力及时阻止我,也许不久后收到的会是今年的照片,我在这儿等着你们来抓,麻烦,快一点。”
凶手显然换了另一种语气,也许是另一重人格,或者,根本就是一个圈套。
距离上次邮照片的时间,恰好整一周。
我将这两张照片扫描放大数倍比较,发现她们用了同一款淡粉色的眼影和同色系的唇釉。
我的一位女性朋友是知名美妆博主,精通复古彩妆盘,我把局部放大照片发给她,让她协助寻找相关信息。
两天后,她反馈这款彩妆是某欧洲大牌在2005年推出的“处女之吻”桃粉色系列,她特意强调了照片上的化妆技术不错,能把一个单色眼影晕染的层次分明。
“处女之吻,真是讽刺。”
我瞬间跌进沉思中,反复思索的几个问题:凶手为被害人精心勾勒精致清纯的妆容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化妆手法的原因,嫌疑人可不可能是一个女人?
现在又出现一个绝美女孩的尸体,出现了更多疑问。而新被害者身份要比杜仪难查得多,警方没案底,妈妈桑和璐璐也对女孩毫无印象。
“难道她不是妓女?”
“至少失踪人口里也应该有记录,可什么都查不到。”
“比杜仪还无人知晓。”
“或者,她根本没有户籍。”鄂奇哲终于看了我一眼,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