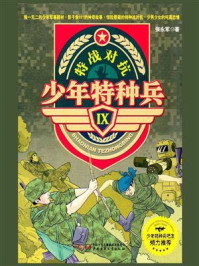5月29日下午3点,那篇本该于17年前刊发的报道终于重见天日,而作者陈发在一小时前登上飞机,永远逃离了这座岛屿。
我们没想到会如此顺利。
朗尾的暴风骤雨,终于席卷全岛。
前教育部长之子,济得小学,恋童癖,政治腐败,还有——朗尾杀人案。
鄂奇哲让我在网络召集当年梁丰然性侵的受害人,仅仅5个小时,有十几人实名控告梁丰然,他们此刻身在全球各地,却永远都忘不掉济得的残忍。
我打开电视,媒体和抗议人群包围了富丽堂皇的济得小学,象牙白的围墙成了各种愤怒的发泄场,而我在想,为什么,这些人会沉默十几年?为什么,济得这种学校还会教书育人十几年?
内阁召开特别会议,宣布成立专门调查组,当晚8点,在炽如白昼的闪光灯下,一身黑装的梁玉超上了警车,接连被捕的还有校长希姆和当年校董会成员。黄逸和亲友们再次走上街头抗议,呼吁重审黄呈坚杀人一案,在法院静坐抗议的人群由十几人到黎明破晓时分的数千人。我用手机看着现场直播,突然间泪流满面,我们这座破烂不堪的小岛,仍还有一丝希望,足矣。
经过一夜,司法部还是不表态,只对外宣称召开紧急会议。
而在大洋彼岸的帕孔匆忙间起草一份声明,她声称在6月19日曾去过朗尾,将当时协会所有现金交于邓先明,当时邓先明一家受到某人威胁,正在朗尾等待出逃邻国的船只,那些钱自然也都毁于那场大火。
显然这个说法非常可笑,不过有一点倒可信,邓先明当时肯定受到某人的威胁,那个人不是梁玉超,而是掌握性侵证据的凶手。
如今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征集线索,因为没有验尸报告和火灾责任认定书,更需要找到当年亲历的消防员,在全岛的推波助澜下,终于有位当年执勤的消防员回应了我们。
当时的火灾现场果然没有所谓邪恶图案,那个消防员甚至听到有人曾呼救,但冲上楼时伤者已经死亡,屋内起火点燃烧比一般火势猛烈,在大雨的环境中,绝对不同寻常。
此刻是5月30日上午9点,距离死刑还有64个小时。
没有实质性证据,根本无法翻案,这就是无法逾越的现实。
所有人都不会想到,此刻混乱中,鄂奇哲和我潜入了济得小学。
这所学校更像是战败后的宫殿,一夜间,光辉全被剥夺。
到此的理由,一是躲避媒体,二是寻找线索,比如当年的学生资料。
一旦目标是邓家和梁丰然,凶手只可能是受害者或者其家属。
六年里,梁丰然的每一个男学生,尤其是家境普通的学生,都可能是受害者。检方很快就会查封所有文件,那场死刑也已迫在眉睫,而我们面对的是一间巨大的档案室。
我们先从梁丰然历年的年终考评表开始,确定每学期所教的班级,从而筛选出2000至2006年间全部男学生资料487份。
鄂奇哲看着我整理出密密麻麻的档案,沉思片刻说:“先排除15、16年,那时梁丰然得了性病,陈发那篇报道里的那个男生是几岁?”
“2001年当时是13岁。”
“那就是1988年出生,邓希凡也在那年出生。”
这句话简直点醒梦中人。
邓先明尹淑真夫妇为了名利不择手段,甚至助纣为虐。
连6岁的邓沐灵都心狠手辣。
只剩一个被冠以天才之名的邓希凡。
这个少年仿佛已等待了许久,立刻就浮出水面。
他叫阿布巴,马来族人,父母一栏填写的是商贩。小学三年级转学至济得,在转校前年年是全校第一,来到济得重点班第二个学期就超过邓希凡,获得年级第一,此后一直和邓希凡交换领跑,直到2001年缺席考试,同年3月退学,理由不详。
这张脸在哪见过,我确实见过这个人,他像个透明人,无处不在。
我也在1988年出生,其实还有个我们认识的人也在1988年出生。
如果真是他,为了这个机会,他等待了整整5年。
等到18岁,他终于可以动手了。同样也是18岁。
鄂奇哲和我坐在黄逸摔下那段楼梯之上的阶梯教室,夕阳西下,尘埃落定。
我们疲倦地倒在椅子里。
“我们有高速路口的监控录像,只要确定这个人当天是否去过朗尾,一切便知分晓。”我无意识脱口而出,像在梦中。
可我们能阻止这场似乎不可避免的死刑吗?
如今的科技可以轻而易举地锁定这个男人,那晚他果然超速先赶到高速路口,请君入瓮,但直到监控结束,他也并未着急返回晋古。
他是梁丰然性侵的受害者,被邓先明夫妇用钱打发了事,和邓希凡有着竞争的关系,目睹邓沐灵推人的全过程,可警察不相信他,记者欺骗他,父母只为了钱,他所求助的一切,都没用,一切都没用,他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尽管仅剩下一只眼睛,他也要看着这些坏人得到报应。他用手握的证据,制造了这场一箭五雕的好戏。他是济得的透明人,更是这里的知情者。
可这一切都仅是推测,他没留下任何的证据,即使我们能找到那名叫NINI的妓女指认他,即使他有无数个犯罪动机,可这都不是治罪的证据。
5月31日6点,我们在济得静悄悄的操场上迎来了黎明,一切进入了倒计时。
“怎么办?”这是我总爱说的口头禅。
“他当时在暴风骤雨里点燃这把火,火并不容易点着,小区安保人员3分钟内赶到现场,10分钟后消防车赶到,还记得消防人员说过的细节吗?他记得当时有人在喊救命,但跑过去只看到尸体。”
“所以呢?”
“因为当晚的特殊天气,大火可能不一定能烧死邓家四口,而凶手要确保每一个人都得死,所以要留在现场。”
“这怎么可能?在学校里他是透明人,可那是火灾,肯定有人会看见他。”
“如果他穿上消防员的衣服?然后在消防队员赶到前确保每一个人死亡,或者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
我不敢置信,却突然想起了网上流传的那段消防执法视频。
因为视频现场浓烟密布,一团混乱,我和专业人员只能一帧帧地筛选对比。鄂奇哲则走入抗议请愿队伍里,疯狂造势。
电视无人机镜头里,圆形广场静坐人群塞满了通向周围的各条支干道路,从天空看,就是发出一道道光芒的太阳。
5月31日下午1点,司法部、高等法院联合举行发布会,态度坚决,无证据,不立案。
此后的半个小时,我终于找到一张他模糊的侧脸照片。我们立刻让律师提交所有证据,而我们,得亲自会一会这位高超的凶手。
佐哈里的家住在城郊独栋老房子,虽然年久失修,但仍有些曾经的派头,它和梁丰然曾租住的房子极为相似。
明媚午后让满院的鲜花争奇斗艳,而窗户里,却关着黑夜。
敲门无人应,只轻轻一推,我们就走了进去。
这里没有我预想如恐怖电影里的恶臭肮脏,除了黑暗,这里芳香扑鼻,我能感受到房间里到处都是花。
上下三层都没人,日光越来越稀薄,房间里没有电,下一个黎明,就是黄呈坚的死期。
“梁丰然家有个很大的地下室。”鄂奇哲边说边开始用力跺地板,终于,传来一个久远的回响。
他打开暗门,冷光从地下涌上。
“欢迎光临。”那个声音却客气,如好客的主人。
我顺着旋转楼梯一阶阶下去,只瞬间跌倒在地,整个空间仿佛旋转起来,每一个截面都是空旷无望的白色,墙立面的灯线则让这里成为在太空里漂泊的质子,无边无际的流浪,无穷无尽的囚禁。
佐哈里坐在一把透明的椅子上,手里铁链牵着一只巨大宠物,它似犬若熊,全身黑毛,匍匐在地,粗重喘息,这让我们本能止步。
佐哈里只笑着拍拍宠物的脑袋,然后才说:“我知道你们肯定能找到这,那房子现在既漂亮又干净,地下室改成了很前卫的工作室,知道以前是用来做什么吗?我们5、6个小孩被脱光了,丢进去,里面是十几个,畜生。”
佐哈里边说边用皮鞭划过宠物背上的皮毛,突然狠狠抽了一鞭子,宠物却老老实实地悉听尊便。
“来不及了,这个世界不会为谁改变,我13岁就知道这个道理,可你们还是不懂,没用,一切都没用。”
鄂奇哲倒对那只宠物颇感兴趣,想要走上前,那物突然直立想要扑倒鄂奇哲,佐哈里使劲拽着铁链,才放倒了它。
我这才看清楚,这全身粗毛的,是一个人,立刻恶心地吐了一地。
鄂奇哲却大笑起来,这也逗得佐哈里笑起来。
“真有你的!”鄂奇哲竖起大拇指。
“他本来就不是人,现在不过露出畜生的本面。”
“但你不能让黄呈坚当你的替死鬼。”鄂奇哲绕过人兽,走到佐哈里的面前。
“跟恶魔缠斗,你得先变成恶魔。”
“为什么找黄呈坚?”
“这种父母,还不如死刑处决了,女儿被人摔成瘫痪,还低三下四地去求罪犯施舍,就为了那点钱,钱,比自己儿女重要吗?”
“他和你父母不一样,他是为了女儿治病。”
我说完,佐哈里却怒瞪着我,似乎要松开手中的铁链。
“这种保护不了子女的父母就得死。”
鄂奇哲见状,立刻转移他的注意力。
“邓先明,尹淑真的死我倒是理解,邓希凡呢?他是你的老同学。”
“老同学。”佐哈里再一次大笑。“我父母想要我出人头地,想要改变艰难的家境,他们以为上了济得这种名校,我们就会改变。其实什么都不会,我仍是下等阶层小商贩的儿子,可我却比天才的邓希凡成绩更好,真是讽刺。在济得最后一年,邓希凡突然约我去梁丰然家参加课外活动,他只有毁了我,才能,保住他所谓的天才称号,真可怜。”
话音未落,我眼见佐哈里把一个匕首捅进了人兽的脊背,人兽痛苦在地上打滚。
“还有邓家那个小不点。我眼睁睁看她把同学推下楼,那个受伤的小女孩在我怀里可怜地呻吟,我抬头望过去,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这个无边的空间从来就没有平衡,我紧紧踩住我以为的地面,其实我到底在哪个平面?我到底是倒立还是直行?我听见佐哈里的笑声渐渐飘远,然后,他的声音从包围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里冒出,一曲共鸣,一声回响,最终让我迷失于此。
“她在笑,她竟然在笑。”
说完,他掏出了打火机,像18岁那年一样,点燃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