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视节目类型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服务于两个传播主体—节目制作者以及观众的文化实践。换言之,电视节目生产者的传播意图与受众群体的观看需求都会对节目类型的发展产生影响。显然,按照罗兰·巴特关于艺术作品两种文本的分类
 ,谈话类节目属于典型的作者式文本,或者菲斯克所说的生产者式文本。作为大众文化产品,谈话类节目播出后,受众群体通过对这一生产者文本“权且利用”来制造快感,生发意义。
,谈话类节目属于典型的作者式文本,或者菲斯克所说的生产者式文本。作为大众文化产品,谈话类节目播出后,受众群体通过对这一生产者文本“权且利用”来制造快感,生发意义。
从1993年首档谈话类节目《东方直播室》与观众见面至今,30年的时间里,谈话类节目在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不同阶段,体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发展特征。近年来,随着传播生态、传播格局的剧烈变化,谈话类节目市场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一大批曾经家喻户晓的老牌访谈节目纷纷停播,例如《杨澜访谈录》《康熙来了》《锵锵三人行》《艺术人生》《超级访问》等。这些知名访谈节目在历经10余年发展后纷纷退场,侧面证明了对于当下的受众群体来说,传统演播室人物访谈节目在市场上已呈现疲软之势。“谈话+”现象兴起,类型融合成为新媒体谈话类节目发展新趋势。另一方面,在谈话类节目头部市场又涌现了一批新节目,这些节目保留了谈话的基本形式,但又结合了其他类型节目的特点,呈现同中有异的新样态和新特征。谈话类节目正进入一场新旧交替的变革局面。比较典型的类型融合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当前,新媒体谈话类节目的发展可谓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一定程度上,优秀的新媒体谈话类节目,其成功之处往往在于为受众提供一种思考,或者治愈焦虑的力量。有鉴于此,新媒体谈话类节目在节目形态、类型融合上进一步呈现多元发展的状态。
谈话类节目类型融合历程中,具有标杆意义的事件,当属2016年老牌访谈节目《鲁豫有约》的改版升级。新版节目的名称是《鲁豫有约大咖一日行》。通过与“大咖一日行”,节目由传统谈话类型,升级为新型的“真人秀式访谈”。可以说,自这一刻起,“谈话+真人秀”这一节目模式正式进入电视节目市场。显然,改版后节目中主持人与嘉宾的对话交流依然是“不变”的主旋律,但是节目采用全外景拍摄,给嘉宾人物留有足够丰富的镜头,且字幕、音效、蒙太奇式剪辑手法都处处流露出真人秀节目后期包装特征,使节目风格有了巨大的转变。“谈话+真人秀”模式给当时深陷低谷困境的传统谈话类节目开辟了一条突围之路,也影响了后续越来越多的人物访谈节目,开始让主持人进入嘉宾的日常生活,从而更加全面、立体地展现嘉宾自然真实的一面,以满足观众对嘉宾的好奇心与窥视欲。
当然,真人秀元素的加入,也使本来相对可控的谈话类节目,出现了更多的悬念。以《鲁豫有约大咖一日行》采访某位知名企业家的节目为例。采访过程中,一开始是有些“冷场”的。显然,身为名人的嘉宾已经接受过太多次采访,很难轻易放下内心的戒备。于是,主持人改换了一种“唠家常”式的提问方式,冷不丁地提问嘉宾:“你儿子怕你吗?”这里,主持人的本意,是在看似平常的提问中,迅速在程序性话轮导入之下,将谈话进行推进。嘉宾对这个问题似乎很感兴趣,同时也给出了意想不到的回答,成为整个谈话过程中的一个亮点
 。嘉宾回答:“不怕,他不怕我”,“我们两人相互影响,相互洗脑”。
。嘉宾回答:“不怕,他不怕我”,“我们两人相互影响,相互洗脑”。
谈话中,主持人抓住嘉宾作为父亲的社会角色,就子女的家庭教育与个人发展方面进行发问。一方面,这让谈话更加具有层次感,而不是在杂乱无章的问题中,让嘉宾不厌其烦地机械回答。另一方面,主持人在语境的把控方面也是十分强的,能够针对嘉宾的情感及心理情绪等要素,基于场面氛围的控制,实现访谈的有效设计,不仅不会让嘉宾尴尬,还提升了节目效果。
前有《罗辑思维》等新媒体综艺节目开启了知识文化的脱口秀时代,后有《朗读者》《阅读·阅美》《见字如面》等朗诵节目走红荧屏,“谈话+文化”正是近年来上升势头迅猛的融合类型。这类节目,通过读诗歌、读书信等文化交流方式,为谈话类节目增添了更多的人文情怀与厚重情感,引发观众文化共情与情感共鸣,既避免了一般文化类节目“曲高和寡”的尴尬,又使得节目保持了一种高质量与高格调。
《朗读者》这样的节目中,所谓“谈话”的过程与其说是对谈,更类似于“诵读”。只不过,节目邀请的诵读主体较为特殊。一般来说,这一类节目中诵读嘉宾的身份往往具备权威性,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当然,之所以邀请他们来参加节目,正因为他们的角色不局限于文学家、作家、文化学者,还包括社会各界的领军人物、佼佼者。他们是信仰的坚守者、敬业的践行者、情感的守望者,如航天员杨利伟、医学专家吴孟超、舞蹈家谭元元、开办公益学校的张桂梅等
 。这些嘉宾身份的权威性及其励志故事令受众折服,因而具有强大的情感感召力和说服力。二是诵读嘉宾的身上折射出我们这个民族珍贵的精神力量与文化品格,其情感说服力在于能够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这些嘉宾身份的权威性及其励志故事令受众折服,因而具有强大的情感感召力和说服力。二是诵读嘉宾的身上折射出我们这个民族珍贵的精神力量与文化品格,其情感说服力在于能够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以《朗读者》第三季第四期节目为例,世界冠军在亲子陪伴中的无奈缺席,主持人在亲情与事业之间的两难抉择,极限运动员所克服的身体残缺与病痛,生物学专家要忍耐的孤独、艰险与贫穷。节目在诵读主体身上所洞悉、挖掘并传达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他们的执着坚守闪烁着人性的熠熠光辉,他们成为一个时代极富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载体。有些嘉宾的吟诵也许在技巧上比不上专业播音员、主持人,但其感染力与说服力却并未因此而折损。所以当有传播“声誉”的诵读者回归普通人的情感表达时,一种来自权威的距离感和理性说服被转化为传者与受者间亲切而有感染力的情感交互。
“谈话+美食”类节目属于一种垂直类、小切口的融合类型,这类节目往往具有极其浓郁的生活气息,因而深受广大观众的青睐。《拜托了冰箱》《厨房的秘密》《熟悉的味道》《谁是你的菜》等多个谈话类节目中,创作者都有意加入了美食制作环节,展现了充满烟火气息的饮食文化与明星嘉宾的生活状态。正因此,这种慢节奏的饭局聊天氛围不失轻松感、愉悦感,是观众心中所谓“下饭综艺”的首选类型。
这种“谈话+”的融合形态,也必然使得节目表达变得更为多元化。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类型与技巧之间的冲突”并不必然意味着节目类型的“交班换岗”,而因为吸纳了新的节目元素和表达技巧,导致了类型本身的发展演变。显然,“谈话”焦点的退隐并非意味着从节目离场,类型融合也并非简单的类型嫁接,“融合”表现在节目各环节自然过渡,而不是将各环节生硬地拼凑在一起
 。其实,各种节目类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谓是由来已久。即便在前互联网时代,传统意义上的谈话类节目也尝试过引入其他类型节目元素。
。其实,各种节目类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谓是由来已久。即便在前互联网时代,传统意义上的谈话类节目也尝试过引入其他类型节目元素。
例如,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早年间曾推出了一档高端人物类访谈节目《咏乐汇》。在这档节目中,最为关键的节目环节,就是主持人与嘉宾之间的饭局。整个节目的谈话部分,都是在“饭局”这一情境下展开的。根据每期邀请到嘉宾的背景、特点,饭局中提供的每一道菜,都有其特殊的含义,与嘉宾背后的人生经历有联系。很显然,美食在其中便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可以说,这是谈话类节目发展历程中较早运用“谈话+美食”的做法,收获了不错的效果。
互联网传播语境下,互联网思维的运用在综艺节目中逐渐凸显,其中,脱口秀节目的创新也处于新的议题讨论中。腾讯视频自制的美食脱口秀节目《拜托了冰箱》,融合“开冰箱+品美食+聊生活”等多种元素,从用户思维出发进行节目创新,节目抓住了现代人喜欢边吃饭、边看剧的心理,为观众尤其是年轻群体打造了一档“最强下饭综艺”,映射出了现代生活的真实面貌
 。
。
“谈话+观察”类节目则是近几年来新媒体综艺节目市场崛起的一种全新类型。一大批聚焦职场、独居、夫妻、婆媳话题的观察类节目,如《这是谁的家》《我要这样生活》《让生活好看》《妻子的浪漫旅行》等节目都纷纷设置了演播室谈话现场,节目邀请嘉宾的亲属好友来到演播室,观察、解读嘉宾的生活状态,这种双线叙事模式能够恰当地捕捉节目看点,为节目增加娱乐效果,并调动观众情感走向。此外,也有一些“谈话+观察”类节目没有设置“棚内讨论”环节,而是让主持人作为“观察者”直接进入嘉宾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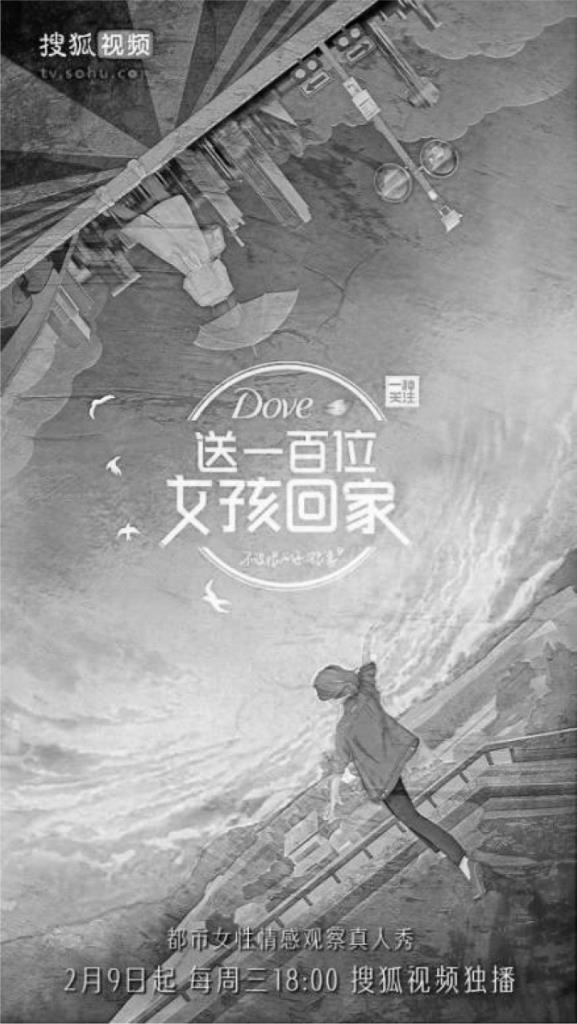
图2-1 搜狐视频出品女性情感观察
节目《送一百位女孩回家》第一季
例如新媒体谈话类节目《送一百位女孩回家》聚焦在大城市奋斗的年轻女性群体,展现了大量女性真实生存状态的画面,主持人化身“观察者”,用“陪伴式”访谈来倾听当代都市女性的人生困惑、成长烦恼。例如,在第五季的首期节目中,一位身为脱口秀演员的女嘉宾无意中的一段话,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节目里,这位女嘉宾说道:“在脱口秀这个舞台上,一个纯粹的女性失败者,是不可以存在的,一个女性,大家希望她至少有一些闪光点。”(图2-1)
不难发现,这位女嘉宾的观点无意中提到了当下不少职场女性所面临的困境。社会有时似乎对女性更严苛,女性必须拥有某种美好的品质才能走到台前。因此,节目实际上是借助嘉宾的观点输出,传递出以下信息:不要轻易否定自己,每个女孩都有存在的独特价值。节目的播出,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女性群体在生活中所承受的压力,从而引发观众去思考女性群体所面临的困境
 。
。
除此之外,一些较有代表性的新媒体谈话类节目,在谈话环节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其他类型的元素。例如,腾讯视频播出的《饭局的诱惑》就是这样一档典型的新媒体谈话类节目。在节目中,除以美食为主要话题的“谈话”核心载体外,还加入了较为烧脑的“狼人杀”桌游环节。
显然,类似这样的游戏环节,丰富了节目样式,同时游戏本身的不确定性考验着嘉宾在台本之外的临场发挥,为访谈节目增加了趣味性。事实上,在谈话类节目发展变局中,越来越多的新兴节目不再拘泥于传统谈话类节目的形态,开始大胆地突破类型框架的界限,呈现出一种类型融合的新趋势。
当前,发展历史悠久且制作经验丰富的新媒体谈话类节目,呈现出明显的回暖趋势,重新进入大众的视野。显然,优质的谈话类节目永远都不缺受众。对未来的新媒体谈话类节目来说,创新迭代无疑是不可回避的必经之路。对创作者而言,如何进行高效创新,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一方面,需要在保证节目品质的前提下,不断尝试新的节目形式、类型元素与话题设计,让节目保有一种动态的发展平衡。另一方面,也需要发掘新的视角、新的观点,真正让观众收获更多有价值的信息输入。
在国产谈话类节目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中,传播媒介、传播生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在这个“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时代,个人表达渠道畅通多了,谈话类节目自然跟随着媒介生态的转场发生了诸多变化。与此同时,谈话类节目队伍不断扩大,同质化问题尤为突出,而观众群体日益分化的观看需求也让谈话类节目遭遇了巨大的竞争挑战,这些外部与内部的变化因素影响着谈话类节目类型变化。
类型是事物的集合,它既体现了一类事物内部的共通性,又体现出该类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排他性,存在着可辨别的界限。但是,“类型”又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渐变成型,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发展中。正如学者简森·米特所指出的那样:“类型是文化的产物,由媒介实践组成,并且受制于不断的变化和再定义。”
 ”谈话类节目同样不是永恒固定的,它也有着渐变发展的过程。这背后也不乏产业的推动。因为从接受心理的角度来讲,观众的审美期待决定了,一档电视节目应该让观众体会到“既新颖又熟悉”。过于超前,难以得到观众的认同;因循守旧,又很难真正脱颖而出。
”谈话类节目同样不是永恒固定的,它也有着渐变发展的过程。这背后也不乏产业的推动。因为从接受心理的角度来讲,观众的审美期待决定了,一档电视节目应该让观众体会到“既新颖又熟悉”。过于超前,难以得到观众的认同;因循守旧,又很难真正脱颖而出。
新媒体谈话类节目的创作者正是“把惯例与符合那些模式的素材‘发明’联系起来”,在这种旧模式与新内容的不断组合、碰撞中,势必出现被称为所谓“类型模糊”的现象
 。当然,类型的意义更多的是对于创作者、研究者来说,对受众而言,这并不是影响他们是否选择观看一档节目的关键。
。当然,类型的意义更多的是对于创作者、研究者来说,对受众而言,这并不是影响他们是否选择观看一档节目的关键。
这种节目形态的互融由来已久。事实上,新世纪初,已有一些谈话类节目进行过类似的“混搭”尝试。例如早在200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的人物访谈节目《咏乐汇》,就是借助饭局的形式来呈现谈话现场。节目中安排的每一道菜肴都有其特殊的用意,与嘉宾背后的人生经历相关联。不难看出,美食为谈话进程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颇为巧合的是,同一年湖南卫视推出的公德礼仪文化脱口秀节目《天天向上》,除了主持团队与嘉宾的“谈话”环节之外,还安排了固定的歌舞表演和游戏环节。可以说,这样的混搭使它更像是一档传统意义上的电视综艺节目。
不同类型的元素互融,其实在节目类型的演变中是一种常态化现象。当下的一些谈话类节目中也依然看得见这种变化。例如《天天向上》在2018年又推出新版块“看不见的伪装者”,融入悬疑与侦探元素,开启了推理脱口秀模式。少儿脱口秀《了不起的孩子》第三季节目中,将原有的VCR视频环节改为外景真人秀拍摄。总的来说,这种互融一方面让谈话类节目增加了新鲜感,另一方面,“谈话”环节仍然在节目中占据核心地位。
然而,在众多新媒体谈话类节目中,这种互融的趋势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融合态势。类型交融的格局从微观发展到宏观,对节目的影响不再只是局部的,而是贯穿整体。甚至作为观众的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越来越多的谈话类节目开始从沙发上“站”起来了。
例如《鲁豫有约一日行》在节目形式上有了颠覆性的突破,将真人秀节目与访谈节目相结合。曾经被观众们熟悉的标志性黄色沙发消失了,主持人走出演播室,用一天的时间探访嘉宾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真实状态。同一位主持人与优酷网合作推出的谈话类节目《豫见后来》则是打出“记录式访谈节目”的旗号,依旧采用了外景跟拍的形式,节目嘉宾则是一些社会话题人物,如当年辞职信上写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河南高中女教师、毕业卖猪肉的北大高才生等。这些普通人,曾经都因为自己做出的人生选择,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事件热度褪去后,他们究竟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豫见后来》便是通过追溯“后来”的方式,重新唤起观众对于“过去”的关切。
近年来的一些新媒体谈话类节目,有意识地模糊类型边界,收获了较好的效果。例如,腾讯视频出品的两档谈话类节目《奇遇人生》《仅三天可见》也存在着较为“另类”的节目形态。《奇遇人生》由主持人陪同嘉宾进行一次未知的旅行体验,让嘉宾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完成对自我的重新剖析和认知,谈话话题随着嘉宾的活动而自然展开,在旅行的过程中搭建起开放式的谈话场景。《仅三天可见》主打社交观察,安排主持人与一些极具争议的嘉宾共同相处三天,并在节目尾声进行一次谈话。在这里,主持人已经不仅仅是访谈者的角色,更是一个社交参与者,以主持人的观察视角帮助观众去理解嘉宾性格和行为背后的真实心态。这两档节目均采用纪实性的拍摄手法,从整体上看,节目糅合了“谈话+纪实+旅行”类节目的特征。从观众口碑和人气来看,这种“1+1+1”的模式确实起到了大于3的传播效果。
此外,一些IP化发展的新媒体综艺节目也采取了“谈话+”的节目模式。例如,为年轻观众熟悉的《拜托了××》系列与《我家×××》系列。《拜托了冰箱》是“谈话+美食”的形式,《拜托了衣橱》则是“谈话+时尚”的形式。《我家那小子》《我家那闺女》《我家小两口》三档节目都融合了观察类真人秀与演播室谈话类节目的形态,除了户外真人秀的第一现场,还设置了室内演播室谈话的第二现场,演播室嘉宾的“谈话”功能是站在观众视角,引导话题讨论的走向。从以上这些“谈话+”节目可看出,类型融合的态势愈来愈明,非谈话元素在节目中大幅增加,“谈话”不再是节目唯一的焦点。尽管“谈话”作为不可或缺的基因和底色,会始终贯穿于节目中,但它已发生了位置上的偏移,从曾经的节目焦点退隐成为节目的基本表达语态,让观众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非谈话内容上。当然,类型的本质意义离不开观众的认可。对新媒体谈话类节目来说,观众和市场事实上决定了未来类型进一步融合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