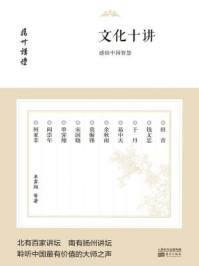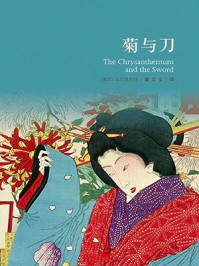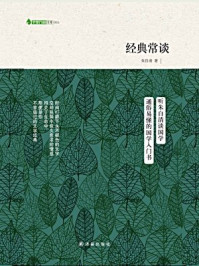自然科学是最先开始对这个世界进行量化的学科,它将数字、微积分和图表系统性地用于测量、比较和分析变化。19世纪中叶开始,逐步兴起的社会科学也开始量化人类的感官体验、心理现象和群体行为。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早期定量概念与图形技术案例包括:古斯塔夫·费希纳(Gustav Fechner)在1850年发明的用于测量心理感官的“最小可觉差法”(the just noticeable difference),心理学家L. L.瑟斯顿(L. L. Thurstone)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提出的“因素分析法”(factor analysis),雅各布·莫雷诺(Jacob Moreno)在20世纪30年代引入的社会人际关系图(graphs showing structures of social groups)。 [1]
按照逻辑而言,接下来开始使用量化、数字模型、数据可视化的学科应该是媒体、数字文化研究和人文学科。我之所以说它们是可实现的且是必然的,是因为文化的生产、传播、参与都达到了新的规模。随着数十亿人创造、修改、分享、管理数字文化器物,使用应用程序、社交网络、博客和网站进行交流, 如今的文化规模已经接近物理或生物现象的规模了 。通过每天与数字器物进行几十亿次在线互动,定量分析已具有科学规律的普遍性(如幂律和无标度网络),可以解释许多规律和模式。这种新规模让文化学(science of culture)的理论成为可能。这些我将在第二章中做更详细的讨论。
2008年,我第一次在文章中表达了我对文化分析的看法。 [2] 下一节中,我将如实地向大家呈现这篇题为《从新媒体到更多媒体》(“From New Media to More Media”)的文章,因为它很好地捕捉了数字文化在规模上“爆炸”的整个过程。如今,有数十亿人参与媒体创作和分享,我们也可以自由地访问由他人创建的数万亿媒体,这一切都显得如此简单易行。同样,由专业人士创作的数百万文化作品也可以通过免费或付费的方式获取,如在Spotify平台上收听音乐,在奈飞(Netflix)网站上观看电影,还有一些针对特定语种的作品集,例如,俄罗斯文学作品共享网站proza.ru拥有700万短篇故事和小说,另一个俄罗斯最大的诗歌创作及发布网站stihi.ru 收录了4000万首诗歌。
然而,首先我想从历史的语境来分析这篇文章,并介绍当今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观点。第一届国际AAAI网络与社交媒体会议(International AAAI Conference on Web and Social Media,简称ICWSM)于2007年举行
 ,这一年开始,社交媒体的定量分析研究开始逐渐壮大。组织者如此描述大会目标:“大会旨在将不同课题领域(例如,计算机科学、语言学、心理学、统计学、社会学、多媒体、语义网络技术)的研究人员召集在一起,共同探讨正在进行的有关网络博客和社交媒体的研究。”
,这一年开始,社交媒体的定量分析研究开始逐渐壮大。组织者如此描述大会目标:“大会旨在将不同课题领域(例如,计算机科学、语言学、心理学、统计学、社会学、多媒体、语义网络技术)的研究人员召集在一起,共同探讨正在进行的有关网络博客和社交媒体的研究。”
 但是请注意,BitTorrent公司在更早的时候就已发行了大量专业媒体和软件。同样,自1981年以来,人们就在Usenet新闻组中发布主题并讨论,也就是说,在此之后25年各大公司运营的社交媒体网站才开始兴起。其他用来发布文本和讨论的流行互联网通信平台,包括BBSes(电子公告牌系统,于1978年上线)、论坛、邮件列表和博客。据估算,百度在2015年拥有50多万个群组;
[3]
广受欢迎的专业性在线问答网站Quora,在2017年拥有1亿的月活跃用户量;
[4]
专门用来分享学术和阅读论文的平台Academia(academia.edu)则拥有5500万用户。
但是请注意,BitTorrent公司在更早的时候就已发行了大量专业媒体和软件。同样,自1981年以来,人们就在Usenet新闻组中发布主题并讨论,也就是说,在此之后25年各大公司运营的社交媒体网站才开始兴起。其他用来发布文本和讨论的流行互联网通信平台,包括BBSes(电子公告牌系统,于1978年上线)、论坛、邮件列表和博客。据估算,百度在2015年拥有50多万个群组;
[3]
广受欢迎的专业性在线问答网站Quora,在2017年拥有1亿的月活跃用户量;
[4]
专门用来分享学术和阅读论文的平台Academia(academia.edu)则拥有5500万用户。

虽然分享形式、平台、媒体类型、搜索和推荐、公开分享与私密分享、隐私预期及其他数字生态系统元素都可能在未来发生变化,但是多人参与的媒体创作现象不太可能会消失。所以,需要记住数字文化史上每一个新范式兴起的时刻,以及那些在当下看来十分寻常而在曾经非常新奇且前所未有的情况。我特意保存了原文本中的一些细节——例如,2008年专业网站上分享的产品组合的数量,以及这些最早的网站的名称和参考资料。
这篇文章先回顾了数字文化的新规模,称其为“从新媒体到更多媒体”的转变。显然,社交媒体的增长已经是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内容之一,然而文章中提到的另一个发展中的领域还未受到应有的关注。这指的是1990年之后便迅速在世界范围内成长起来的 专业文化工业和创新领域的教育项目 。全世界的专业文化、媒体生产和教育行业都因为规模的增长而遇到了一个真实的挑战:“在此之前,如果需要关于文化的报告,我们只需要重点关注世界上少数的几个大城市和学校,但是现在我们要如何同时关注数以万计的城市和教育机构呢?”
因此,增加的用户生成的数字内容和大量历史文化器物的数字化,并不是促进大众将文化视为数字并使用计算方法进行文化分析的唯一条件。文化全球化促成了数百个全球规模的时装周和艺术双年展、数以千计的新文化节、数以万计的新文化组织,以及众多其他类型的文化活动和项目。这也让我们意识到,若不借助计算机工具,我们就无法更专业地探索文化世界。
有些公司会采取扩大雇佣规模并且使用多种方法结合的方式对消费者(如生活方式产品、时尚、住宿和健身等)市场趋势进行检测和预测。例如,WGSN是一家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趋势预测服务公司,根据2020年初官网信息,该公司每月发布250个时尚趋势报告,每季发布150个秀场分析报告,并追踪12000个品牌和零售商。它们采用的方法包括:分析社交媒体数据,参加每年数百场的时装秀并拍摄照片,整理行业销售报告,筛选和追踪时尚社群和网络红人,以及为顾客创建自定义数据分析面板。
 该公司一共雇用了250名“预测师和数据科学家”。
该公司一共雇用了250名“预测师和数据科学家”。

WGSN和同类公司持续对多个产品类别和消费行业、地理区域和人群的趋势进行分析。诸如Urban Outfitters之类的大型零售商店也都有自己的预测团队。
 当然,所有的大型消费企业都在利用各种方法进行市场调查,从焦点小组访谈和调查到对社交媒体和神经营销学(neuromarketing)的计算分析。其中神经营销学涉及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脑电图、眼动追踪和其他技术,用于捕获消费者对产品和内容的情绪波动与认知反应。
[5]
当然,所有的大型消费企业都在利用各种方法进行市场调查,从焦点小组访谈和调查到对社交媒体和神经营销学(neuromarketing)的计算分析。其中神经营销学涉及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脑电图、眼动追踪和其他技术,用于捕获消费者对产品和内容的情绪波动与认知反应。
[5]
然而,大量的研究工作(虽然是我们作为个体文化分析研究者无法与之抗衡的)仅仅涵盖了当代文化中与消费者行为相关的个别领域。所有与这种行为非直接相关的理念、对话、图像、想象和体验对这个行业而言几乎是无用的。幸运的是,当今的世界要么反映在数字在线“镜像”中(肯定存在很多遗漏和扭曲),要么直接作为数字“事物”存在:网络帖文、评论、项目、公告、链接,以及其他组成。许多情况下,这种允许大规模访问的在线信息,既允许大公司,也允许个人或小型研究团队对其展开计算和探索。
作品集网站(portfolio sites)可作为一个不错的网络资源来分析创意产业的趋势。我在2008年的文章中引用了建筑、设计、动态图形和数据可视化领域中专业作品集共享与项目共享站点的早期案例。这些网站上几乎有来自每个国家的专业人士和学生分享的他们的项目作品,这也成为21世纪头10年中期全球专业文化空间兴起的例证。在这样一个空间中,使用相同设计工具组合(例如Adobe Creative Cloud应用软件)的参与者可以看到彼此的工作、竞争相同的任务、吸引关注者,以及发布他们各自的项目。在2008年,虽然这类专业网站上的项目和作品集数量与现在相比相对较少,但是这一领域已经初具雏形。例如,截至2008年5月7日,美国专注于创意行业投资的社区型网站Coroflot(coroflot.com)共收录了90657件作品集,到了2009年10月11日,作品集数量已增长至157476件。
如今,Behance(behance.net)已经成为设计、摄影、时尚,以及几十个创意领域的专业人士用来分享作品集的首选网站。该网站创建于2006年,截至2015年末,它已经拥有60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会员。根据当年公司报告,来自乌克兰和巴西圣保罗的用户数量在该年度增长最为迅速。
 “
在别处
”项目中,我们一共研究了82684个公开定位的Behance会员账号。其中,样本中的账号都是创建于2007年5月22日至2019年2月9日之间,它们的地理位置中包括了5567个不同的城市和162个国家。截至2019年,账号数最多的20座城市揭示了一种新的数字文化地理格局:20世纪昔日的文化工业中心与21世纪才出现的发展中城市、前社会主义国家区域三者的共存。以下是按照账号数量降序排列的城市列表:伦敦、莫斯科、纽约、巴黎、巴塞罗那、洛杉矶、首尔、布宜诺斯艾利斯、旧金山、柏林、蒙特利尔、圣彼得堡、圣保罗、基辅、布鲁克林、华沙、伊斯坦布尔、米兰、布达佩斯、多伦多。
“
在别处
”项目中,我们一共研究了82684个公开定位的Behance会员账号。其中,样本中的账号都是创建于2007年5月22日至2019年2月9日之间,它们的地理位置中包括了5567个不同的城市和162个国家。截至2019年,账号数最多的20座城市揭示了一种新的数字文化地理格局:20世纪昔日的文化工业中心与21世纪才出现的发展中城市、前社会主义国家区域三者的共存。以下是按照账号数量降序排列的城市列表:伦敦、莫斯科、纽约、巴黎、巴塞罗那、洛杉矶、首尔、布宜诺斯艾利斯、旧金山、柏林、蒙特利尔、圣彼得堡、圣保罗、基辅、布鲁克林、华沙、伊斯坦布尔、米兰、布达佩斯、多伦多。
我们已经从“ 新媒体”(new media) 阶段转移到了“ 更多媒体”(more media) 阶段(2004年—)。
我们生成、获取、分析、可视化和存储的数据量(包括文化内容)正在呈指数爆炸级增长。2008年8月25日,谷歌的软件工程师们在博客上宣布,经过多次日计算,谷歌目前索引网页数量已经达到1万亿。
[6]
同月,YouTube也在报告中宣称,它们的用户平均每分钟上传30个小时的新视频。
 2008年11月,Flickr(雅虎旗下图片分享网站)上的照片数量达到了30亿。
[7]
2008年11月,Flickr(雅虎旗下图片分享网站)上的照片数量达到了30亿。
[7]
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是这个不断膨胀的信息世界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2008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70%的数字世界是由个体创造的”。
 换言之,用户创建的媒体规模已经可以很好地与计算机(监视系统、基于传感器的应用程序、支持“云计算”的数据中心等)采集和创建的数据量形成竞争关系。
换言之,用户创建的媒体规模已经可以很好地与计算机(监视系统、基于传感器的应用程序、支持“云计算”的数据中心等)采集和创建的数据量形成竞争关系。
在过去的10年中,专业和非专业的媒体制作人数量呈指数级增长,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化局面,挑战了常规的文化调查和研究方式。创作和分享文化内容(博客、照片、视频、评论、话题讨论等)已经成为上亿人的日常习惯。鉴于具有富媒体(rich media)
 功能的移动电话数量预计会进一步增加,这一数据只会继续保持增长。2008年年初,全世界共有22亿部移动电话。到201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达到40亿,增长主要来自中国、印度和非洲。
功能的移动电话数量预计会进一步增加,这一数据只会继续保持增长。2008年年初,全世界共有22亿部移动电话。到201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达到40亿,增长主要来自中国、印度和非洲。

设想一下:用户每周在Flickr上传的图像数量可能比全世界所有艺术馆的图像馆藏总数还要多。
与此同时,在许多新近全球化的国家中,随着专业教育和文化机构的迅速发展,通过网络即时获得文化新闻的能力与媒体和设计软件的普及都大大增加了参与全球性文化生产和讨论的文化专业人员的数量。目前,越来越多的学生、艺术家、设计师都有机会获取相同的理念、信息、工具。我们不再用文化中心和地区来做区分。(事实上,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刚开始步入全球化的国家的学生、文化专业人员、政府往往比那些曾经的世界文化中心更愿意接纳新的理念。)
如果你想了解文化和数字全球化影响的实际案例,可以访问一些比较热门的作品集网站,上面会有媒体与设计领域的专业人士和学生项目的案例,顺便留意一下这些创作者都来自哪里。不妨看看以下网站:Xplsv.tv(动图、动画网站)、Coroflot.com(来自世界各地的设计作品集网站)、Archinect.com(建筑设计类网站)、Infosthetics.com(信息可视化网站)。举个例子,我在2008年12月24日浏览Xplsv.tv时发现,网站上“艺术家”列表中前3个项目分别来自古巴、匈牙利和挪威。同样,我在同一天访问Coroflot.com时发现,第一页的索引集呈现出了相似的全球文化地理格局。在20世纪的西方文化之都——纽约和米兰旁边,我也发现了来自上海、滑铁卢(比利时)、布拉迪斯拉发(斯洛伐克)和首尔的作品。

此前,文化研究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可以通过较小的数据集推出理论和历史(例如,“经典好莱坞电影”“意大利文艺复兴”等)。然而,我们该如何探索包括了数十亿的文化物品和大量创作者的“全球数字文化”呢?之前,你可以通过不断关注较少数量的世界首都和学校的动态来研究撰写关于文化的内容。但是,我们该如何持续关注数万座城市和教育机构的动态呢?
随着计算机、数字媒体软件、消费类电子产品和计算机网络的普及,世界各地的文化媒介及创造的媒体数量呈指数级增长,导致我们利用20世纪的理论工具和方法来理解当下的全球文化进展和动态变得非常困难。但如果我们利用计算机、软件和海量“原生数据”文化内容,采用通过传统工具无法完成的方式来追踪全球文化,会得出怎样的结果?
为了研究这些问题,以及理解用于文化创造、文化分享的软件是如何利用它无处不在的特点改变了“文化”的本质,我们于2007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和加利福尼亚电信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实行了“软件研究计划”(网址为softwarestudies.com)。我们和研究人员、学生在实验室中开展工作。我们在开发一种崭新的用于研究、教学与呈现文化器物、文化动态和文化流的范式,我们将这个范式称为“ 文化分析 ”。
科学、商业、政府及其他机构如今都依赖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大型数据集和数据流的分析与可视化技术,使用了统计数据分析、数据挖掘、信息可视化、科学可视化、视觉分析、视觉分析和模拟。因此,我们提议可以系统地将这些技术应用于当代文化数据。过去10年,博物馆、图书馆和公司的数字化进程(比如谷歌和亚马逊的图书扫描功能),加上最近几年网络文化内容的爆炸式增长——庞大的数据集已经形成。
在我们看来,系统地运用 大规模计算分析和交互式文化模式可视化 将成为人文学科和文化批评的基本研究方法。当人文学家开始将交互式可视化作为他们工作中的标准工具时(就像许多科学家做的那样),会发生什么?如果幻灯片使艺术史研究成为可能,如果电影投影仪与录像机使电影研究成为可能,那么随着可视化和数据分析的普及,哪些新的文化学科可能会兴起呢?
在我们实验室里,我们一直在开发用于电影、卡通、动画、摄影、视频游戏、网站、设计、建筑及其他视觉媒体的可视化和分析技术。我们所有项目的核心理念是将3个方向的发展融合起来:(1)海量的文化数据集;(2)图像处理技术与用于自动分析视觉媒体的图像处理和计算机视觉技术;(3)借助来自信息与科学可视化、媒体设计和数字艺术等领域的技术,用视觉的方式呈现分析结果。
我们目前正在着手研究的其中一个方向是开发具有实时追踪全球文化功能的视觉系统。可以把它完全想象成一个实时的道路流量监控系统(汽车导航系统),然而不一样的是它有一堵如墙那么大的显示屏,分辨率也高出数千倍,显示的不是公路上的车流,而是全世界 实时的文化流 。可以想象,将一面墙大小的显示屏分成许多块,每一块显示屏上显示着不同的文化、社会和经济新闻与趋势的实时和历史数据,这种做法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文化分析所需的 情境意识 。同样,一面墙大小的显示屏此时正在播放用超级计算机制作的模拟地震的动画。只是不同的是,这里的“地震”指的是大大小小的文化事件,例如热门软件发布了新的版本、宣布一个重要建筑项目的开工等。透过这些屏幕,我们所看到的是文化“地震”在不同时期和空间上的影响。在这张墙面大小的图像上显示着文化生产的长尾,你可以放大查看每个产品和它们丰富的数据信息(例如,zillow.com网站上的房地产地图),并且这些数据还会不断地通过网络提取获得实时更新。想象一个这样的可视化的场景,它展示了世界各地的人如何对由某个粉丝群新发布的视频进行混剪,或者一个新的设计软件如何逐渐影响到当今人们参与思考和想象的方式(Alias和Maya软件引领了一种新的建筑语言)。这些就是我们想要创建的项目。
前一节的2008年的文章中提到的想法,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了。2005年10月,我第一次意识到可以借助计算机工具研究全球文化。在几周之后的11月14日,谷歌发布了一款名为“谷歌分析”的免费产品。 [8] 这款软件能收集并分析你的网站或博客访问情况的所有信息。它有一个丰富的交互式视觉界面,允许用户通过表格、不同类型的图表和地图来研究这些访问的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细节。
我当时还没有想到要怎么用一个词去形容大规模文化分析的可能性,但当我看到谷歌分析的界面时,简直完全符合我的所有想象。如果有一个类似的界面用于近距离观察全球文化趋势呢?我想到了几个词用来概括我脑海里的想法,其中就包括 计算文化分析(computational cultural analysis) 。截至2007年春季,我最终选定了一个更短的术语: 文化分析 。
我们实验室于2007年5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和加利福尼亚电信与信息技术研究所正式启用。我们的第一个项目是名为“文化分析研究环境”的设计原型。系统交互界面受到了谷歌分析的启发。然而,和谷歌分析中的网站访问数据不同,我想要建立一个可用来 探索所有数字化的、原生数字的文化器物和活动的系统 。为了保证当代文化的覆盖范围,系统将通过爬取数百万个文化组织(如博物馆)、作品集站点(如Coroflot和Archinect)及个人创建的网站和博客来不断更新驱动该系统的数据。
彩图1显示了我们在2008年春季创建的这个界面的三种设计。在彩图2中,博士后研究员杰里米·道格拉斯站在一台可视化超级计算机前,上面是两个不同的设计方案。这台可视化超级计算机是早期于加利福尼亚电信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制造的。显示屏由70个30寸的苹果计算机显示器拼接在一起。
[9]
当时,这是用于学术研究的最大的可视化墙之一,我们希望未来开发的系统可以用上这面显示墙。该墙面的尺寸为9.7米×2.3米,综合分辨率为35640×8000像素,即约2.85亿像素。它由18台具有100个CPU(中央处理器)和38个GPU(图形处理器)的计算机来驱动。为了能够将任意分辨率的图像加载到这70个显示器上,并支持与这些图像的交互,加利福尼亚电信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开发了定制软件。

我受邀在加利福尼亚电信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工作,在那里我看到了这样一台视觉超级计算机,它的显示屏尺寸、分辨率、处理能力和图形处理能力比普通计算机高出许多倍,这不仅拓宽了我的视野,还愈发增强了我对科研的决心——无论是从直观还是隐含的角度看。我们的第一个成果是一个交互式界面原型,从概念到雏形都由我们亲自设计,它会从各个层面的细节探寻全球文化趋势。在我的设想中,研究人员可以在这个界面上随意选择想要放大的地理位置,查看该地理位置产生过的当代文化环境、媒介及其他文化活动的统计数据。这些统计数据将始终置于全球相应的数字活动之内。除了谷歌分析之外,我的另一个灵感来源是Gapminder World,一个分享经济和社会数据的交互式可视化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由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开发,于2006年上线。

我们为想象中的“文化分析研究环境”绘制了三个不同的界面(见彩图1)。一个界面显示了文化生产的长尾,作品按流行程度排序,点击可查看作品的图像。这些作品可以是空间设计、建筑、时尚单品、书本、网站、音乐视频等。在第二个界面展示的是一幅世界地图,其中交错叠加的线条代表了文化主题和趋势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路径。在第三个界面是一幅网络视图,展示了不同主题、话题、设计样式、风格和技术在不同文化领域(电影、网页、设计、流行音乐、游戏等)的联系。该网络视图的灵感来自21世纪头10年初期开始出现的科学地图(maps of the sciences)。它们显示了科学领域或研究范式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来自数百万份科学出版物或用户在科学数据库中访问论文的引用统计分析。 [10] 我们的系统则显示对数百万文化器物计算分析处理后得出的主题、话题和技术分类。
“文化分析研究环境”的用户将在所有3种数据视图之间切换,放大缩小,在更大的环境中寻找趋势并做比较,同时在后台对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和分析。界面一侧的图表会显示当前所选地理区域、文化活动或文化类型的统计数据。
当时, 社交媒体和监测面板(social media and monitoring dashboards) 类型尚未存在,它们在几年之后才开始流行起来。回想起来,我们的推测设计——交互界面的原型,刚好满足了这种类型。如今,媒体监控面板被数以百万计的公司、非营利组织(包括大学)和个人所使用,帮助了解人们在网上对它/他们的评价、与竞争对手作比较,而且还可以研究有关任何关键词、网址或品牌的全球互动和网络帖文。由于它们捕捉的数据类型大多数是社交网络上的活动(关注、分享、点赞等)以及博客和网站的帖子,因此也可以将这些面板作为文化分析工具使用。虽然暂时还无法实现我们在2005年所许下的目标,但它们的存在对文化研究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例如,结合社群媒体的企业管理平台Sprout Social出品的一款热门面板产品可以监测Twitter、脸书、Instagram、领英和Pinterest。
 一个名叫Mention的平台可以监测“四十多种语言的数十亿个源”。
一个名叫Mention的平台可以监测“四十多种语言的数十亿个源”。
 然而,另一个数字消费者情报公司Brandwatch则可以检测“2006年以来的每一条Twitter上的推文”。
然而,另一个数字消费者情报公司Brandwatch则可以检测“2006年以来的每一条Twitter上的推文”。
 谷歌趋势可以显示自2004年以来任意地区的任意字词的搜索量,你可以查看网页、图片、新闻和YouTube视频的搜索结果。还有诸如DataSift的社交数据平台,收集来自几十个社交网络、博客、新闻网站和其他来源的数据;通过检测话题、语言、情绪、提及的产品、公司和地点名称来优化数据,并对其进行分类。将其提供给付费客户,然后客户就可以据此展开他们自己的分析。
谷歌趋势可以显示自2004年以来任意地区的任意字词的搜索量,你可以查看网页、图片、新闻和YouTube视频的搜索结果。还有诸如DataSift的社交数据平台,收集来自几十个社交网络、博客、新闻网站和其他来源的数据;通过检测话题、语言、情绪、提及的产品、公司和地点名称来优化数据,并对其进行分类。将其提供给付费客户,然后客户就可以据此展开他们自己的分析。

社交媒体监测面板可以对一些线上文化活动进行实时分析。如今,我们在2008年提出的“文化分析研究环境”项目——一个在全球文化环境下的主题交互式可视化项目,已可以由一支小团队创建并部署在云端上。然而,软件开发变得相对容易的背后,也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与2005年相比,我们所需要扫描的文化帖子、项目、工程和作品集的数量要多得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对我而言,一个更大的挑战正在慢慢浮出水面:监测博客和社交媒体帖子中的文本数据趋势,例如搜索某个特定品牌的名称或其他文本元素的出现情况。21世纪10年代计算机视觉技术取得进步之后,监测大量照片和视频中出现的主题趋势也成为可能。但这还远远不足以全方位地监测文化媒体的美学和语义特征,以及众多文化器物之间微小但至关重要的差异,尤其是在世界范围内。因此,虽然原则上我们是可以构建一幅地图来实时显示当前存在于各个地理位置和媒体类型中的文化DNA,但这幅地图还是无法捕捉到所有内容。它可能会漏掉大多数最独一无二的文化器物。这一点将在书的结论部分,即题为“文化分析的目标是为了研究规律吗?(是与否)”的章节中作更详细的讨论。
我之所以对算法进行大型文化数据分析很感兴趣,是因为目睹了“冷战”结束后兴起的文化全球化现象。所谓“发展中国家”开始涌现一批一批的新演员和机构,后共产主义国家也开始参与由想法、照片、意义和软件组成的虚拟网络世界中。只有我们不断地添加更多的文化器物和位置信息,我们才有可能完成这张不断膨胀的宇宙“地图”。这一切之所以发生,完全是由于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共同催化,使得这个世界可以被完整地“上传”至互联网。因此,在我的定义中,“文化分析”都是从使用计算和设计方法探索及分析当代世界文化开始的。阅读本书的读者和研究者对文化分析可能会有自己的理解,而我想说的是,任何一种解读都是有价值的。
历史上就已经出现过对大型文化数据集进行计算的工作,正如我们今天做的。在描述和分析文化上面,从传统至现今借助过的工具包括图表、可视化、操作化、统计学、数学,以及最近的模拟和数字计算机。 [11] 重要的是,数学和可视化在文化分析中的应用竟然比计算机早了几十年。举个例子,俄罗斯诗人和文学理论家安德烈·别雷(Andrei Bely)利用统计学的方法研究了俄罗斯诗歌文本的韵律节奏。别雷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的儿子,他利用统计方法建立了一套图形系统,分析诗歌结构并将其形象地表现出来。这些研究收录在他的著作《象征主义》(1910)一书中。 [12]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A. L.克罗伯(A. L. Kroeber)在1919年发表的颇具影响力的文章《时尚作为社会秩序更迭的明证》(“On the Principle of Order in Civilization as Exemplified by Changes of Fashion”)。在这篇文章中,克罗伯对19世纪女性时尚样式的变化进行了定量分析和解释。
德尔·海姆斯在《计算机在人类学中的应用》(1965)的导言中提到,计算机的主要优势在当时已经为一些人所熟知。他在书中向读者解释了计算机的用途,也是我认为最好的一个版本:“简单地说,使用适当的计算机技术,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发现数据中的相关性和规律,即使这些数字在过去往往因为数量太大而无法被理解。同样地,它也能使我们看到将想法应用于数据的书面结果。总而言之,计算机的崛起是势不可挡的。” [13]
在21世纪的头几年,数字艺术家和设计师们创造了文化模式下的数据可视化,这是一种极具想象力的研究方法。马丁·瓦滕伯格(Martin Wattenberg)的“歌曲的形状”(The Shape of Song,2001)与费尔南达·维埃加斯(Fernanda Viégas)和马丁·瓦滕伯格共同创造的“流动的历史”(History Flow,2003)项目,分别将音乐作品的特征和维基百科历史的页面变化进行了可视化。
 马克·汉森(Mark Hansen)和本·鲁宾(Ben Rubin)的“监听站”(Listening Post,2001—2002)装置截取了网络聊天室中的实时对话信息,过滤并提取部分文字片段后在上百个排列整齐的屏幕上滚动播放。
[14]
贾森·萨拉万(Jason Salavan)的《史上最卖座电影,1×1》(
The Top Grossing Film of All Time, 1×1;
2000)作品中,电影《泰坦尼克号》的所有画面都被简化为只含有主要颜色的像素块,按照矩形网格排列,呈现出视觉效果变化与电影节奏互相呼应的效果。
[15]
乔治·莱格迪(George Legrady)为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搭建的“让无形变为有形”(
Making Visible the Invisible
,2004—2005)装置,是将图书馆的实时借阅信息进行了数据可视化。
马克·汉森(Mark Hansen)和本·鲁宾(Ben Rubin)的“监听站”(Listening Post,2001—2002)装置截取了网络聊天室中的实时对话信息,过滤并提取部分文字片段后在上百个排列整齐的屏幕上滚动播放。
[14]
贾森·萨拉万(Jason Salavan)的《史上最卖座电影,1×1》(
The Top Grossing Film of All Time, 1×1;
2000)作品中,电影《泰坦尼克号》的所有画面都被简化为只含有主要颜色的像素块,按照矩形网格排列,呈现出视觉效果变化与电影节奏互相呼应的效果。
[15]
乔治·莱格迪(George Legrady)为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搭建的“让无形变为有形”(
Making Visible the Invisible
,2004—2005)装置,是将图书馆的实时借阅信息进行了数据可视化。
 (我将在第三部分详细讨论其中的几个项目。)
(我将在第三部分详细讨论其中的几个项目。)
数字人文学者已经发表了许多定量和计算文本分析的历史记载。在美国,人文计算领域被视为数字人文学科的先驱,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分析少量文学和其他类型的文本。 [16] 最近,不同国家的学者开始质疑这些美国中心论的说法并不断扩散。虽然这是一个好的趋势,但如果能将历史视角扩展到人文学科之外会更好。
正如我在书中所指出的,文化分析并不只适用于某个领域,而是可以涵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文化分析也不局限于学术研究,而是涵盖了相关的媒体、数据设计(data design)和艺术项目。因为数学和可视化方法在文化分析上的运用比计算机超前了几十年,所以我们不能认为文化分析只存在于计算或者大数据时代。例如,20世纪的许多作曲家发明了初步的图像乐谱系统,这些手绘的可视化其实也是文化分析的一种,而且更容易被读懂。其他的手绘可视化还有建筑和城市设计的手绘图、舞谱系统;又如吉加·维尔托夫和谢尔盖·艾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等导演于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电影可视化作品。
[1] Gustav Theodor Fechner, Elements of Psychophys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6); L. L. Thurstone, “The Vectors of Mind,” Psychological Review 41 (1934): 1–32; Jacob Levy Moreno, Who Shall Survive? A New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of Human Interrelations (Washington, DC: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Publ. Co, 1934).
[2] 该文本的后期版本参见:Lev Manovich, “Cultural Analytics: Visualizing Cultural Patterns in the Era of ‘More Media,’” Domus 923 (March 2009), http://manovich.net/index.php/projects/cultural-analytics-visualizing-cultural-patterns。
[3] “How Many Online Forums Are in Existence?,” Quora, accessed October 11, 2017, https://www.quora.com/How-many-online-forums-are-in-existence.
[4] “How Many People Use Quora?,” Quora, accessed October 11, 2017, https://www.quora.com/How-many-people-use-Quora-7?redirected_qid=12824.
[5] Uma Karmarkar and Hilke Plassmann, “Consumer Neuroscie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2, no. 1 (2019): 174–195.
[6] Jesse Alpert and Nissan Hajaj, “We Knew the Web Was Big ...,” Google Official Blog, July 25, 2008, http://googleblog.blogspot.com/2008/07/we-knew-web-was-big.html.
[7] Heather Champ, “3 Billion!,” Flickr Blog, November 3, 2008, http://blog.flickr.net/en/2008/11/03/3-billion/.
[8] “A Brief History of Google Analytics, Part One,” Digital State, May 1, 2014, http://digitalstatemarketing.com/articles/brief-history-google-analytics-part-one.
[9] Lev Manovich, “Cultural Analytics Visualizations on Ultra High Resolution Displays,” Software Studies Initiative (blog), December 24, 2008, http://lab.softwarestudies.com/2008/12/cultural-analytics-hiperspace-and.html.
[10] Brandon Keim, “Map of Science Looks Like Milky Way,” Wired, March 11, 2009, https://www.wired.com/2009/03/mapofscience/.
[11] Operationalization is the practice in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of defining concepts through measurement operations. For example, in psychology, emotion can be measured in a number of ways, such as by facial expression, body movements, choice of vocabulary, and tone of voice.
[12] Lynn Gamwell, Mathematics and Art: A Cultural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169–170.
[13] Hymes, The Use of Computers in Anthropology, 29–30.
[14] Peter Eleey, “Mark Hansen and Ben Rubin,” Frieze, May 6, 2003, https://frieze.com/article/mark-hansen-and-ben-rubin.
[15] Jason Salavon, The Top Grossing Film of All Time, 1 x 1, 2000, 有机玻璃上的数字C版画(digital C-print), 47"×72", http://www.salavon.com/work/TopGrossingFilmAllTime/。
[16] Susan Hockey, “The History of Humanities Computing,” in 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 ed. Susan Schreibman, Ray Siemens, and John Unsworth (Oxford: Blackwell, 2004), 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