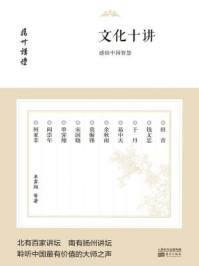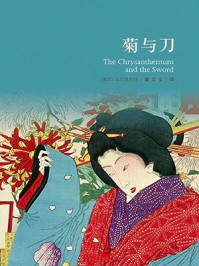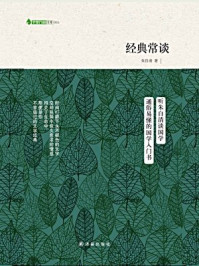“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比那江南风景,觉得更为有趣。”清末小说家刘鹗在《老残游记》中用这寥寥数笔便勾勒出泉城济南的神韵所在。济南市的中心是一片被古护城河环绕的老街区,占地3.2平方公里,由46条明清时期的古街巷纵横交错而成。这片老街区始建于1371年,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老街相当于明代济南城的范围,所以这里也被当地人称为“明府城”。
走进济南的老街,会有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代都市的感受。常年恒温的泉水喷涌而出,经年不息,老街内的房屋临泉而筑,80多处泉水流淌在小巷民居间,形成了“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泉城风貌。

■“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诗意生活
老济南人经常用“清泉石上流”来形容老街,过去的老街巷多是石板路,在街上随手掀起一块石头,底下都是一汪清水,走到街上甚至会不小心把鞋弄湿。这种“依泉而居”的诗意生活滋润了济南人,荡漾出一片如水般清澈甘甜的日子。
明府城北面有一处泉池,名为百花洲。盛夏时节,岸边杨柳扶风,水中鱼翔浅底,一排灰瓦白墙的院落倒映其中,宛若江南。现在百花洲东岸一带的民居,在宋代原本是水中小岛,人们住在岛上与北面的大明湖隔水相望。但是由于济南的地势南高北低,每到夏季洪涝时节,泉水和雨水在大明湖汇集,水患时有发生。
宋熙宁四年(1071年),52岁的曾巩调任齐州知州,他深知治理水患对于济南城的重要性,于是他捐出自己修建官邸的银两,又将自己多年来的积蓄贴补进去,带领人民疏浚河道,建起了济南城的北门水闸,使得湖水注入小清河。从此之后,大明湖成为蓄水之地,北城的水患被彻底解决。时至今日,大明湖北水门依然能够调节大明湖与护城河之间的水量,发挥调蓄洪水的作用。

■大明湖畔的百花洲

■曾巩带领百姓修筑的“曾堤”
曾巩还带领百姓用疏浚大明湖的淤泥,修筑了一条贯穿南北的“百花堤”,方便人们从南岸百花洲前往大明湖北岸,这条堤又被称为“曾堤”。相传,苏轼就是看到“百花堤”后,深受启发,才修建了杭州西湖的“苏堤”。
曾巩在济南任职的两年多,不但在济南的建设发展中厥功至伟,而且还留下了很多咏赞泉城风光的佳作,成为研究济南历史变迁不可多得的资料。后人为纪念他,在大明湖畔修建“南丰祠”,成为济南一处重要人文景观。
风光秀丽的大明湖畔,不仅留下了“不爱钱”的曾巩的身影,也记载了一位“不惜死”的将军死守济南城的故事。
明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率领北军兵临济南。正在外地运送粮草的山东参政铁铉,听闻消息马上掉头驰援。朱棣命人把敦促铁铉投降的书信用弓箭射入城内,铁铉则将《周公辅成王论》射回给朱棣,劝其效法周公,忠心辅佐建文帝。
铁铉将济南城内的官兵和百姓组织起来,歃血为盟,死守城池。在他的带领下,济南城固守了3个月。
由于济南的军事地位极重要,若取得济南,进可南下攻打、退可画疆自守,故而朱棣对济南城志在必得。不料攻城不利,朱棣情急之下命令士兵用火炮攻击。眼看城墙就要倒塌,铁铉急中生智,让守城将士把明太祖朱元璋的灵牌悬于城上,济南城得以保全。

■位于大明湖畔的“铁公祠”
朱棣兵围济南数月不克,只好撤军北返。两年后,当他再次率军南下,仍对铁铉心有余悸,便绕过济南直取南京。智勇双全的铁铉使济南城两次免受战火之灾,被当地人尊称为“城神”。
朱棣称帝后,处死了拒不投降的铁铉,却对他心存敬佩。史料记载,朱棣“日对群臣言,每称铉忠”。
男儿到死心如铁,铁铉人如其名。为了纪念这位舍生取义的武将,后人在大明湖北岸修建铁公祠。几百年来,铁公祠香火不绝。不怕死的英雄守住了武将的气节,也把君子之风的浩然正气留在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甘甜的泉水,浸润了无数才子大家的文思雅趣,变得愈发清澈无瑕。孔子的仁德礼治,李清照的细腻婉约,张养浩的警辟深远,辛弃疾的豪意奔放,都融入这一汪清泉之中,润泽人心。

■泉城老街上的文庙
孔孟之乡,自古就有崇文尚德的传统。文风炽盛的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明清时期修建的孔庙和贡院。相传,孔子九世孙听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消息后,与弟子们一起,把家中祖传的《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偷偷藏在墙壁夹层中,才使这些书籍得以传世,“鲁壁藏书”的典故也就由此流芳百世。
时隔2000年,这种精神仍然薪火相递般地传承下来。出生于蒲松龄故里的路大荒,是中国最早出版《聊斋全集》的著名学者,被誉为“20世纪蒲松龄研究的第一人”。1937年年底淄川县城被攻陷后,为了得到珍贵的蒲松龄手稿,日寇向路大荒开出优厚条件,邀其出山,但是被他严词拒绝。在日寇的威逼利诱下,路大荒被迫从淄川转移到济南。日寇对路大荒的祖宅进行了严密的搜查,将他没来得及转移的文物字画、古籍善本统统掠走,临走还放火将房屋烧毁。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在路大荒看来,守住了国之文脉,哪怕山河破碎,中华也不会亡。他背着土布包袱辗转来到济南,用“鲁壁藏书”的古法,把珍贵的蒲松龄手稿藏于墙壁中,隐居在明府城老街。1962年,67岁的路大荒将珍藏多年的《聊斋文集手稿》捐献给国家,成为山东省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路大荒捐赠的蒲松龄手稿
在泉城老街,像路大荒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王献唐、屈万里、鞠思敏、辛铸九,这些仁人志士,把守护中华文明当作自己的本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将许多珍贵的文稿、书籍保存了下来。当今天的人们有幸翻阅这些古籍时,也应该记住他们的付出和牺牲。
路大荒的孙女路方红从小生长在老街。1972年路大荒去世的时候,路方红19岁,“那时候爷爷脑中风,瘫痪在床,身体一天天衰弱。我印象很深,有一天他让我把出版于1962年的《蒲松龄集》从门楣上拿下来,告诉我翻到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然后让我在这个字后面加一句话,说等再版的时候可以把这句话加上。”退休后,路方红整理了爷爷的手稿和日记,撰写出20万字的《路大荒传》。她说,爷爷把蒲松龄的手稿捐献给了国家,她也要把爷爷的手稿全部捐献出来。
上善若水,润泽万物。清冽的泉水流成溪,汇成河,聚成湖,鲜活了老街,也让明取舍、知大义的君子之风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田。
泉城老街上早就有了自来水,但人们还是喜欢喝泉水。一早一晚,打水的人络绎不绝,他们看到那些从泉眼当中冒出的甘泉,心里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打水的工具也是各式各样,大桶小桶,肩扛手提,仿佛只有这泉水泡出的茶、煮出的饭才有滋味。
走在老街上,随便推开一处院门,主人都会用泉水泡上一杯茶热情地招待客人,还会如数家珍地介绍起老街老巷和每一处泉名的来历。亲切而又爽直的济南话,听起来就像叮咚作响的泉水,酣畅淋漓。
始建于清末的曲水亭街15号,院中有一眼从未干枯过的“佐泉”,65岁的王俐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看着老照片,她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家门口的曲水河泉水清冽,撸起袖子的妇人在泉边搓洗着衣裳,青石板路有些坑洼,小孩儿结伴踩水去……王俐小时候,每到酷热的夏天,大人们会把西瓜浸入井里,夜幕降临,一家人围坐在小院里吃西瓜、聊天,其乐融融。王俐讲述的,是曲水亭街15号的故事,也是泉畔人家的泉水生活。

■王俐珍藏的老照片
老街居民临泉而居,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许多用泉爱泉的规矩。周慧琴老人住在起凤桥街9号,院子里的泉叫起凤泉,几十年来,全家泡茶做饭用的都是泉水。老人说:“这个街上基本上早起来没有洗衣服的,全得让给这打水的。我们都没有顺手往河里倒脏东西的习惯,老街人都懂得这个规矩。”世世代代住在老街的居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先清理河道,为了保护这份“泉水叮咚”的日子,老街人组织起“护泉志愿者”队伍,像守护自己的亲人一样守护着这汪泉水。
随着城市的发展,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留下老济南记忆的街巷越来越少,“渴饮泉水闲赏荷,不辞长做济南人”,老街人改编的这句诗代表了内心对家乡最深沉的热爱。
如今,节水保泉成为所有人的共识。保住泉水,就是保住了泉城的魂。泉水见证着济南的发展变迁,激发了这座古老城市的潜能。老街人也明白,只有用心维护泉水的欢腾,泉水才能给这座城市带来欢笑。
“老屋苍苔半亩居,石梁浮动上游鱼。一池新绿芙蓉水,矮几花阴坐著书。”清代诗人董芸曾这样描写芙蓉街。芙蓉街是明府城街区中最繁华的一条街,因街上有眼芙蓉泉而得名。明清时期,芙蓉街周围有抚院、布政司等衙门,许多商家在此开店。“瑞蚨祥”的前身“瑞蚨”布店、济南第一家眼镜店、最大的百货店都曾开在这条街上。

■开在芙蓉街上的玉谦旗袍店
在热闹喧嚣的芙蓉街上,“玉谦旗袍店”铺面不大,却是远近闻名的百年老字号,也见证了老街150多年的历史。旗袍店门两侧的楹联“门前圣水芙蓉泉,旗袍世家数百年”,不仅道出了它的历史,同时也向人们描绘了芙蓉街当年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的繁荣景象。玉谦旗袍店创始于清代同治年间,当时的旗袍样式为衣身宽博、平直硬朗、衣长到脚踝。洋务运动时期,西方文化流入中国,玉谦旗袍店适应时代潮流,将旗袍设计为领子低、腰身收紧、衣长缩短的“改良款”。他们最先是缝制长袍马褂,到了同治年间又增加了旗袍和四季便服等,且缝制质量远近闻名。迁址来到芙蓉街之后,于家传人凭着精湛的技艺和诚信的经营,在老城内外数十家旗袍店中脱颖而出,几年内就誉满泉城。
出生于1958年的于仁谦是旗袍店的第五代传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就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制衣。在父亲的精心指导下,他的制作技艺日臻成熟。年轻时,他曾经在济南服装三厂当过10年制衣工人,改革开放之后,他便接替年迈的父亲,成为玉谦旗袍店第五代掌门人。
于仁谦入行50年,始终坚持手工制作。旗袍制作讲究镶边、绲边、嵌边、岩条、盘扣、贴花、绣花、手绘八大工艺,这些年来,于仁谦在秉承了八大制作工艺的基础上,潜心研究、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求发展。为此,他曾在中国服装文化函授中心进修过传统服装制作,并系统研究过日本服装文化与中国服装文化的渊源。对于面料的选择,于仁谦并没有局限于原有的面料,而是根据顾客的需求进行创新发展。多年来,真丝立绒面料被视为旗袍制作的“禁区”,因为这种透明、超薄的面料易卷、怕烫,而且很难缝制,但是有些顾客对这种华丽质感的面料非常喜欢。想顾客所想、让顾客满意,是玉谦旗袍店的经营理念,面对顾客的期求,于仁谦查阅了大量的技术资料,走访了许多专家,经过反复试制,终于攻克了这个技术难题,这让真丝立绒的旗袍制作成为他的“绝活”,成为传统服饰与时尚服装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
量体裁衣是玉谦旗袍店最大的特色,于仁谦创新的经纬立量法制作一件旗袍需要测量60多个数据,花费半个多小时,做一件旗袍至少需要3天时间。为了让玉谦旗袍店融合传统和潮流,他还将欧式晚礼服的设计运用到旗袍的设计中,从而使得制作出的旗袍格调更加高雅、款式更为新颖。10多年来,他为国内外著名影星、著名主持人做过各式旗袍和中式服装,为玉谦旗袍店赢得了极好的声誉。虽然现在开一间旗袍店赚不了多少钱,但他愿意守着一份老手艺,过着平淡如水的日子。
老城老街老手艺,是一座城市不改的初心与守望。在泉城老街,有很多老手艺人,他们用一生的时光守着一门技艺,为济南留下了传统,也留下了生活和文化的印记。直到今天,济南依旧享有“曲山艺海”的美誉。老街上的芙蓉馆每天上午都会有公益演出,为曲艺新秀和新段子、新曲目提供表演的舞台,也为老街居民提供了免费欣赏演出的场所。
经年不息的泉水、善解人意的杨柳,在四季轮回中抚慰着济南人,也让这座城市变得有情有义。山环水绕间,生活在老街里的人不求名山大川的激情澎湃,守着一泓清泉穿堂入院,就这样不急不躁、平和安逸地生活着。
大明湖畔,曲水亭旁。从小生活在历下老城区的房泽秋感受最多的就是邻里间的和睦温馨与守望互助。从19岁青春年少到54岁华发已生,只因一句承诺,房泽秋将毫无血缘关系的瘫痪老人接到家中照顾35年,用几十年如一日的付出诠释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中华传统美德,讲述了一个小家大爱的美德故事。
1979年,时年61岁一直未婚的李玉柱在工作时突发脑血栓住进了医院,因为两家关系好,年仅19岁的房泽秋便挑起了照顾李玉柱的担子,她每逢周五都去照顾老人,帮他洗衣服做饭:“老人住院1年多,医生告诉我,每到周四,老人就时时刻刻盯着病房门口等我。听到这,我决心将老人带回家。”房泽秋看到李玉柱老人行动不便,加上无人照顾,和母亲简单商量后,就将老人接到自己家中承担起了赡养的义务。一句承诺:“爷爷,您跟我走吧,我来养活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35年的陪伴与守候。
君子重诺,一诺千金。结婚后的房泽秋将老人接入自己家中,丈夫丁海开始分担照顾老人的责任。房泽秋起初在济南市丝绸印染厂工作,后来下岗了,家中生活并不宽裕,但房泽秋和丈夫两人还是选择共同照顾老人,相濡以沫,共守承诺。后来家里的条件慢慢变好,可平静的日子却没能维持多久。2012年,房泽秋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去世,给整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尽管悲痛,房泽秋的儿子于霄宁还是选择接过担子,继续照顾老人。
于霄宁辞去了北京的工作,选择在家兼职,方便照顾老人。背老人去医院、给老人洗澡等重活,于宵宁都接了过来。后来,于宵宁的妻子也和家人一起分担起照顾老人的重任。这35年里,房泽秋一家搬到哪里,李玉柱老人就跟到哪里。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人和房家,早已亲如一家。
2014年12月24日,李玉柱老人安然辞世,享年97岁。老人对房泽秋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多亏你了,谢谢你。”
房泽秋用35年书写了践诺和孝行的济南故事。老人虽然走了,但是房泽秋觉得,老人生前得到各界人士的关心,为了回报社会,自己要继续做好事,传递正能量。房泽秋成立了“志愿服务团”,帮助需要照顾的老人。“从一个房泽秋到一万个房泽秋”,这是房泽秋的心愿。为了这个心愿,她努力带动更多人加入敬老爱老助老的队伍。房泽秋志愿服务驿站从老年人的多种需求出发,组建以社区居民志愿者为主体的组织网络,开展关爱空巢老人、孤寡老人等困难老人群体的志愿服务。志愿者们通过排查摸底、建立帮扶台账、电话沟通、入户问候、邻里互助的方式,对辖区需要帮扶的老人开展志愿服务。房泽秋的愿望是再干10年,壮大志愿者团队,服务更多老人。三十五年如一日守住一个承诺,房泽秋的善举让老街上的这眼“善泉”喷涌而出,敬老爱老,房泽秋身体力行用小家传递大爱,也将爱心和善心传递到了更多地方。

■房泽秋一家和李玉柱老人

■房泽秋(左一)和她的志愿服务团
守着老街老院,守着一汪清澈的泉水,老街人也就守住了“官有清名,商有厚德,民有佳风”的济南人风骨。
不让泉眼干涸的方法,就是用心养护;不让心灵干涸的方法,就是用爱滋养。历经600多年风雨沧桑,老街依然保持着“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温和样貌。无论城市发展如何日新月异,这汪清泉从未染尘。它是济南的根脉所在,也是泉城人的心灵归处。
编 导:张 琳 赵 宁
撰 稿 人:梁子玉
指导撰稿:赵瑞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