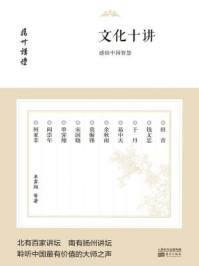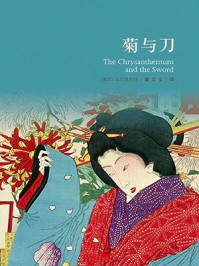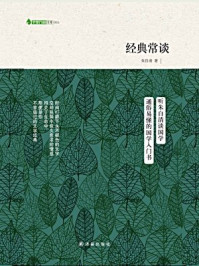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在外滩海关大楼,《东方红》的旋律破开了蒙蒙薄雾,开启了上海新的一天。渡轮、地铁、汽车,把人们送往城市的各个角落。这个时候,911路公交车,就会沿着布满梧桐树的林荫大道,掠过斑驳的树影,驶过高楼林立的热闹商区,抵达被人们称为“老城厢”的地方。
北临外滩,东望陆家嘴的“老城厢”,自元朝以来一直是上海老县城的所在地。这片只有两平方公里的老街区,曾经耸立着一圈高高的城墙,当时的人们把墙内称为“城”,墙外商业繁盛之地叫作“厢”,老城厢由此得名。

■上海老城厢
走进上海老城厢,仿佛有一种穿越历史、回到过去的感觉。不同于浦东新区的高楼林立、外滩街头的十里洋场,老街旧屋,沉淀下一代又一代上海人原汁原味的生活,蕴藏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底蕴。像一位年迈的母亲,老城厢用了数百年的时光,哺育出上海今天的繁荣。
红黑相间的砖瓦屋顶连绵起伏,演绎着繁华都市中最东方的传统景致;城隍庙和文庙里香火不断,延续着700多年的历史和文脉。江南传统民居、石库门里弄错落分布,近百条蜿蜒的小路延展着弄堂人家“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精致生活,还原着上海最初的模样。
老城厢的弄堂都是弯弯曲曲的,因为老城厢以前是传统的江南水乡,原先的弄堂都是小河,随着老城厢的发展,这些河都填了,所以形成了现在弯弯曲曲的狭窄街道。走在这样别致的巷道中,如同脚下的路也化身为蜿蜒的溪流,反倒增添了别样的意趣。
伴水而居的生活早已远去,但与水相关的故事,却在深深浅浅的巷弄中流传。
黄浦江是上海的象征,而黄浦之名,最早见于宋代。起先黄浦水域并不宽阔,到了元代,黄浦水量逐渐变大,渐成滔滔之势。至于明永乐年间,黄浦北部的吴淞江变得淤堵严重,吴淞江是太湖的主要泄水口,这一淤堵便使得整个苏松地区的排水灌溉变得困难,稻禾被淹没,房屋被冲毁,人民流离失所,江南地区水患成灾。时任户部尚书的夏原吉十分着急,开启了一项浩大的治水工程。
夏原吉做了很多的调查和走访,他多方打听别人的建议,先是采用了“掣淞入浏”的治水方案,即将吴淞江的水势分流,由夏驾浦将水向北导出至刘家港,吴淞江东段则暂弃不顾。
疏浚到上海这一段的时候,上海县的一个学人跟夏原吉提议,说疏浚吴淞江工程量特别浩大,或许可以直接疏浚范家浜。范家浜原是老城厢东北边的一条小河,夏原吉实地考察后,采纳了这个建议。
疏浚后的范家浜连通了吴淞江、上海浦和黄浦,形成了一条烟波浩渺的大河,就是今天的黄浦江。
“黄浦滩头水拍天,寒城如雾柳如烟。月沉未沉鱼触网,潮来欲来人放船。”明代王穉登的这首《黄浦夜泊》就写出了黄浦江当年已经出现渔船往来的景象。
黄浦江的疏通解决了太湖水患,由于河道变宽,水运兴起,上海逐渐成为往来商船最重要的中转码头,也为日后上海港的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福建的茶叶商和江浙的丝绸商等络绎不绝,商贸往来在这里逐步兴盛,此外,上海还出现了票号,就是今天的银行。水运畅通带来了商业繁荣,但也带来了困扰。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海上倭寇时常侵袭,老城厢人民为了抵御倭寇,筑起了城墙,并沿着城墙开掘了护城河。高高的城墙给人们带来了安全感,吸引了众多达官贵人入住,曾经的小县城逐渐发展成为了商贸重地。
商贸繁盛带来了财富,也使得老城厢诞生了一批批商界巨贾。
乔家路77号位于乔家路与巡道街相交处,这里曾是清代鼎鼎大名的船王郁松年建造的宜稼堂。郁松年的父亲郁馥山靠在上海经营沙船业发家,父亲去世后,他就帮兄长郁竹泉掌管家业,20余年后郁松年继承了父兄的事业,当时郁家已拥有近200条沙船和100余家钱庄、商号、典当等,时人称其为“郁半城”,郁松年也成为当时的上海首富,他在上海的航运、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均作出了不少贡献。
上海商船会馆是当时上海沙船业的同业组织,郁松年以会馆为核心,团结其他沙船商,打通了长江、运河航线,使南北货运流通更加顺畅,同时,他还积极组织开拓海上航线,使上海港能够转运南洋海外货物,沙船也因此成为联通上海港和外界的主力,为上海成为东方大港之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老城厢因水而兴,老城厢人的性格也像水一样,包罗万象,永不停止。南来北往的船只带来财富,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眼界变得开阔起来。他们接纳来自天南地北的文化,异乡人建起商馆会所,在舟楫相望、车辇声声中,开辟出一方包容开放的天地。药局弄因集中大量中药铺而得名,外咸瓜街是海货一条街,旧校场路是驻兵操练的地方。今天的人们,依旧可以从古老的街巷名称中,感受当年的繁盛景象。

■黄浦江
时隔数百年,黄浦江依旧是沟通南北的主要水路。每当夜幕降临,伴随声声汽笛,灯光就会扮靓这条流淌了600多年的上海母亲河。滔滔江水诉说着沧桑往事,也见证着老上海发展的历史。
明嘉靖年间,朝廷开始实行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人们为了抵御倭寇侵袭而围起的城墙,围起了小日子的安生,却也困住了发展的脚步。
徐光启是明末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他目睹了上海的兴衰,也见证了明王朝走向没落。忧国忧民之心,让徐光启有了“立身行道,治国治民”的远大抱负。就在他潜心苦学的时候,远在大洋彼岸的欧洲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当一艘艘满载着西洋钟表、仪器的轮船来到中国时,徐光启看到了一幅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就是著名的《坤舆万国全图》。
徐光启看到这幅图以后,视野有了非常大的扩展。山外青山楼外楼,原先他并不知道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幅图使他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明代末年的中国,社会空谈之风盛行,他很希望用这种先进的知识、先进的仪器、先进的意识,弥补自己国家不足的地方,他决定虚心学习、变革图新。
徐光启几经周折找到利玛窦,和他一起翻译完成了西方数学的经典之作——《欧几里得原本》前6卷。徐光启把《原本》中的数学理论译为“几何”,并料定“此书为益,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翻开如今的课本,“点、线、面”这些人们再熟悉不过的数学用语,都是在那次翻译中确定下来的。
徐光启的努力,没能延长明王朝的气数,但历史却没有辜负他的期许。今天,这位先驱者长眠的故乡——徐家汇,这片因徐氏后人聚居而得名的地方,已经成为上海最繁华的商圈之一。当年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开明思想,在随后的几百年中一直深深影响着这座以开放著称的城市。

■由徐光启和利玛窦共同翻译的《几何原本》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在这种危难时刻,1895年,康有为联合1300名举人发动了“公车上书”,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随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南下上海,筹划组建了上海强学会,该会明确表示“专为中国自强而立”。强学会的成立,使得上海在短期内成为维新运动的舆论宣传中心,既开启了民智,也使维新变法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民国初年,上海思想文化界在新思想的冲击下已展现出一些新的面貌,但封建思想依然潜伏在各处,禁锢着社会发展前进的脚步。在这种背景下,五四运动应运而生。1919年,陈独秀辞去北大教授之职,返回上海,《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也随之迁往上海。《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对封建专制主义发起了猛烈攻击,给上海文化界带来了极大的思想解放。
维新变法运动带来了新观念,却没能挽救中国;辛亥革命带来了政治变革,却没能使垂危的旧中国彻底走向新生;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思想冲击,但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依旧没有得到改变。20世纪20年代,上海已成为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当时上海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以及资本主义商人的盘剥,导致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罢工浪潮此起彼伏。被马克思主义思潮深深影响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上海工人阶级具有很强的斗争性,建党已经具备了一定条件。
离老城厢不远,有一处石库门房子,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参与会议的正式代表共有12人,其中上海代表为李达和李汉俊。这次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确定了党的性质和现阶段的基本任务。
从徐光启在封闭中眺望西方,到维新变法的思想启蒙,再到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的勇敢批判,直到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历史的选择绝非偶然。正是以老城厢为代表的上海,以其海纳百川的胸襟接纳外来文化的精髓,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才跨越千山万水,落脚在这片开放包容的土壤中,为中华民族探索出一条光明之路,奏响了国富民强、复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

■中共一大召开的石库门房子
对于很多上海人来说,老城厢承载着他们对于家的记忆,而散落在街边的茶楼和点心店则记录着他们的乡愁味道。“湖心亭”是上海市区现存最古老的一间茶楼,这里的常客大多是当地的居民,无须特地约定,如果遇到就坐在一起聊聊家长里短,独自一人也可以品尝一份特有的清闲。点一壶茶、一份点心,看看窗外的九曲桥,平淡的生活也就此有了滋味。
曲径通幽处,老城厢里藏着许多上海往事。
九曲桥连接湖心亭通往豫园,这座彰显江南文人诗情画意的园林始建于明代,是上海市中心唯一保留下来的古典园林。园林最初的主人将其取名为“豫”,意为平安、康泰,然而在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这个吉祥的名字却没有让它幸免于难。
鸦片战争第二年,上海被迫开埠。英、法等国在老城厢以北设立租界。当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中国大门后,爵士音乐在新建成的洋楼里响起,各色光怪陆离的西洋货物蜂拥而入,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转移到上海。站在东西方文明碰撞的最前沿,面对家园沦为半殖民地的悲凉,有人沉迷于“远东第一大都会”的喧杂与传奇,也有人开始思考如何才能“师夷长技以制夷”。上海,由此走向历史发展的巨大拐点。
1868年,一艘名为“恬吉号”的轮船带着一丝希望的曙光,划破这个东方大国在列强倾轧下长期沉闷压抑的氛围。它在黄浦江上缓缓驶过,引发了江岸万人围观,时人称“观者如堵”,这新奇的事物仿佛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启示,在踮着脚好奇张望的人群中播下一颗颗希望的种子,亟待长出新芽。它带给上海的不仅是生活方式的改变,更有思想深处的冲击。
东西方文化撞击之下,拥抱变化成为老城厢唯一的选择。1867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迁到了老城厢以南的华界。李鸿章派幕僚前往欧美学习机器制造。那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正席卷西方各国,改变着人们的生产、运输和生活方式。这一幕幕场景,给一位叫朱志尧的年轻人打开了新的思路。
朱志尧生于上海董家渡,儿时曾就读于徐汇公学。24岁时,他随三舅父马建忠赴英法美诸国,参观了许多机器厂,眼界大开。回国之后,朱志尧毅然放弃科举之路,取“器惟求新”之意,于1902年创办了“求新机器轮船制造厂”,研发各种新型机械。

■求新机器轮船制造厂旧址
那个时候,年轻的求新厂在上海滩崭露头角。但是一天早上,人们却惊讶地发现,用来制造机器的模具丢失了。大家没有想到的是,过了几天,竟然有同行来到厂里,向工人求教模具的使用方法。
这个事情让朱志尧知道了,他却很乐意提供帮助。“君子务知大者远者”,朱志尧明白,仅凭一己之力并不能改变这个国家的现状。在求新厂的产品图册里,他写道:“唤起我国同胞,不要迷信外国,谁说中国不及外国,嫉妒没有用,羡慕崇拜没有用,要自己动手做!”这句话掷地有声,仿佛一道钟声撞入人们的心灵。
城门与国门齐开,开明求变的思潮席卷而来。无数老城厢人怀揣实业救国的梦想,开办起电厂、水厂、电话局、电车公司,他们喊出“提倡国货,与洋货抗争”的口号,民族工商业逐步兴起。
民国年间,在这片五方杂处的土地上,有踌躇满志的实业家和银行家,有意气风发的文人墨客,也有更多在这里谋求一方生计的城市平民和流离失所的战争难民。老城厢以宽容的胸怀接纳一切,成为新“移民”的家园。
改革开放后,上海于20世纪90年代被确定为改革发展的中心,树立了“龙头”地位。1990年,国务院批准浦东地区开放计划,制定“十项优惠政策”,在中央政府的帮助下,上海经济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增长速度加快、产业结构重组,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现在的上海已经发展成一座世界性的经济金融大都市。
如今,老上海的痕迹大多已经在高楼林立的城市景观中消失,但作为大上海发源地的老城厢依旧保存完好,它是这座城市的根脉,它的文化底蕴与创新拼搏精神也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今天的老城厢居民依然延续着老上海的生活。巷弄不宽、房子不大,一栋楼里往往住着几十户人家。就在这看似杂乱无章的日常中,却有着远亲不如近邻的温情。
老城厢居民张国毅,每日都会从附近的烟纸店取上牛奶和钥匙,去郑忠阿姨家里照看,这件事情他和邻居们已经坚持了十几年。
郑阿姨年近百岁,儿女一直希望能把她接到身边赡养,但老人却一直没有答应。对于郑阿姨而言,上海一个世纪的变化都集中在了老城厢,她只想在这里慢慢老去。得好乡邻胜过亲,城市越来越大,人心越来越远。唯有老城厢里狭窄的巷弄,还能自然地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已经79岁的知名主持人陈铎带着妻子回到了老城厢。陈铎现在的家人都已搬离老城厢,老宅更换了主人,童年时最喜欢的天台也改作他用,但每次回来,陈铎都要去那里看一看。
陈铎儿时总爱爬到天台的墙上,看向远处,上海的高楼都在那边,高楼象征着一些什么东西,那时候他眺望着,想透过高楼大厦看清些什么,却觉得模模糊糊的。多少年之后,他在《文汇报》的大楼往这边看,想找他的家时,突然明白,一反方向,一倒回思索,原来他看的,向往的,或者说追求希望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种美好。
老城厢面积不大,却培育出一颗颗向往广阔天地的心,越过高高的围墙,陈铎把自己的声音传播到了五湖四海。而对于家乡的文化,他也有自己的理解。
陈铎说,上海走在全国很多城市的前面,不是偶然,尽管这么小的一条弄堂,远不是大草原大海边,但是这里也有这里的“海洋”。不管是南方北方,还是国内国外,只要他人有长处,我都吸取,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前进的脚步就会变慢。
数百年时光中,有人留下,也有人离开,还有人归来,老城厢始终是他们人生开始的坐标原点。在时代的发展中,这里从不曾被人们遗忘,新一轮的保护和改造正在加速进行,为上海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留住历史的根脉。
如同一位慈祥的母亲,老城厢孕育了上海最初的文化底蕴,给予了它不断前行的活力。如今的上海正在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曾经这里是“冒险家的乐园”,如今这里是人们追逐梦想的舞台。
从20世纪90年代被确立为改革开放的龙头开始,上海已经历了几十年风云巨变,在这几十年中,无数次激动人心的国内外盛大活动在这座勇于开拓进取的城市举行,其中有一场空前绝后的盛会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
2010年,在上海市中心的黄浦江两岸,位于南浦大桥和卢浦大桥之间的滨江地区,上海世界博览会在这里举行。此次世博会主要表达了两大理念:一是科技世博,倡导以低碳生活为主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模式;二是人文世博,倡导过去和未来完美融合的城市生活,这两大理念均着眼于当时全世界重点关注的问题。
在世博会展区的A片区,上海馆就矗立在这里,展馆以石库门造型为主,既显朴素大方又颇具现代时尚风格,正凸显了上海这座城市历史与现代交融的气质,以及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特征。其中展馆的外墙由5000块三棱镜组成巨大的像素墙,每块三棱镜上根据“永远的新天地”“上海祝福你”“世博之城”这3个主题放着3张冲印照片,随着这些三棱镜实时地旋转变换,站在墙外的观众们将会看到一出出绚丽夺目的精彩表演。
3个主题影片当中,“永远的新天地”显得尤为特别。整部影片以一个渔村女孩的视角,借助江河与海洋来展示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变换,演绎了上海百年间的沧桑巨变,也揭示了上海上善若水、海纳百川的城市特色。

■繁华的现代上海
上海世博会不仅是一次探讨新世纪人类城市生活的伟大盛会,更是人类文明的一次精彩对话。这次世博会的召开,使得上海的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基础设施建设获得了升级,同时就业机会也大大增加。上海世博会在更大的意义上还推动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参与度,提高了上海的知名度和区域辐射效应。
弹指一挥间,悠悠数百年。
如同过去的老城厢,先民们怀揣憧憬沿河而来,催生出一座城市的繁荣。今天的上海,承载着2400万人的梦想。海纳百川、大气谦和,不辜负每一个人的奋斗和坚持。
席慕蓉曾说过:“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当异乡人站在灯火阑珊处遥望故土,上海人的乡愁就隐匿在巷弄深处。老城厢的房子没有高楼大厦宽敞明亮,却为一代代人遮风挡雨,它是这座城市的根脉,记录岁月的变迁,深藏繁华背后的奥秘,并和今天的大上海一起,拥抱一个崭新的时代。
编 导:赵奕琳 吕 妍
撰 稿 人:黄晓宇
指导撰稿:赵瑞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