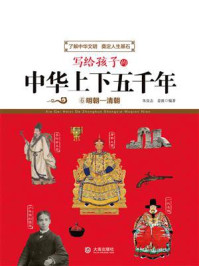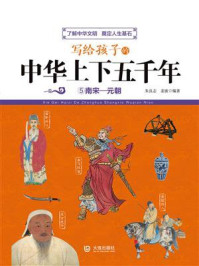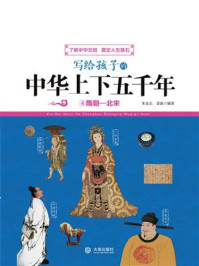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摇换大王旗。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忙举行了即位典礼,次日率大顺军撤出京城,计其在京时间,整整四十天。五月初二,清摄政王多尔衮率部分清军由朝阳门进入北京。
清军以“仁义之师”的面孔最初出现在京城,着实让臣民百姓吃了一惊。
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必不汝害。

这则出自大学士范文程之手的《安民告示》,是清廷宣传上的常用口号,其价值比李自成通过拷饷得来的“七千万”还重要,与刘邦初入关的“约法三章”有同等意义。清军在以每天40公里的速度进逼京师时,一再发布上面的告示。到达北京后,比它更为详细、具体的告示贴在了各处。

聪明的清朝统治者十分注重利用大顺的失误来赢得臣民的拥戴,总是处心积虑地把自己和大顺的形象对照起来。到达北京后,多尔衮让降服的故明群臣推出他们当中官爵最高的人。李明睿惊恐不安地来到多尔衮的面前,多尔衮宣布升任他为礼部左侍郎。李明睿稍有推辞,多尔衮说:“尔朝皇帝尚未收殓,明日即欲令京城官民人等哭临,无神主,何以哭临?无谥号,何以题神主?”李明睿听后感激涕零,叩首接受新命。多尔衮随后发布的命令一再煽动故明臣民对大顺的仇恨情绪,并说:“有志之士,正于功名立业之秋,如有失信,将何以服天下乎?”
 谕令一下,“官民大悦,皆颂我朝仁义”
谕令一下,“官民大悦,皆颂我朝仁义”
 。
。
从进京的次日起,清廷派官员在承天门登记所有原明朝官员的姓名,并按名单邀请他们复任原职。初六,多尔衮令原明朝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族官员一体办事。最初响应者寥寥无几,很多官绅纷纷南下,清吏部侍郎沈惟炳在上奏中忧心忡忡地说:“京官南去不返,似怀避地之心;高人决志林藏,似多避世之举。见在列署落落晨星,何以集事而襄泰运哉!”
 但多尔衮有的是耐心,前来投靠的人,他一一亲自接见,好语安慰,并立即任职,又让他们荐举。他还制定了极为宽大的用人原则,即清廷入京前,罪无大小,悉行赦免,给所有人以弃旧图新的平等机会。于是,任用一批,推荐一批;推荐一批,任用一批。仅当年一个月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推荐36人,户部左侍郎王鳌永推荐39人,兵部左侍郎刘余祐推荐9人。这仅是不完整的记载。
但多尔衮有的是耐心,前来投靠的人,他一一亲自接见,好语安慰,并立即任职,又让他们荐举。他还制定了极为宽大的用人原则,即清廷入京前,罪无大小,悉行赦免,给所有人以弃旧图新的平等机会。于是,任用一批,推荐一批;推荐一批,任用一批。仅当年一个月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推荐36人,户部左侍郎王鳌永推荐39人,兵部左侍郎刘余祐推荐9人。这仅是不完整的记载。
 多尔衮的用人政策收到良好效果,“于是诸名公巨卿,甫除贼籍,又纷纷舞蹈矣”
多尔衮的用人政策收到良好效果,“于是诸名公巨卿,甫除贼籍,又纷纷舞蹈矣”
 。顺治二年(1645年)初,吏科都给事中朱徽回忆说:“去岁五六月间,人心甫定,引避者多,寮署一空,班行落落。”由于多尔衮招纳成功,出现了“东西响应,多士云集”的局面,乃至他所在的吏部竟然出现了“人才不无壅积之虞”。
。顺治二年(1645年)初,吏科都给事中朱徽回忆说:“去岁五六月间,人心甫定,引避者多,寮署一空,班行落落。”由于多尔衮招纳成功,出现了“东西响应,多士云集”的局面,乃至他所在的吏部竟然出现了“人才不无壅积之虞”。

对于多尔衮宽泛甚至不讲原则的用人政策,汉官中有人表示反对。顺天巡按柳寅东就主张前明贪官以及投诚大顺政权的明官应一概排斥。
 多尔衮却不这样认为,他回答道:“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用人一事,我也颇下功夫。”
多尔衮却不这样认为,他回答道:“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用人一事,我也颇下功夫。”
 他表示国家用人之际,“不必苛求”。
他表示国家用人之际,“不必苛求”。
其后,多尔衮宣布废除明末弊政之极的三饷加派,又将都城从盛京迁往北京,以定人心。
这种种适时而正确的决策,都在向亡明的臣民证实:改朝换代的胜利果实已被满族贵族稳操在手。
然而,胜利只能说是初步的。随着军事征服节节推进,以及大批臣民归附新主,特别是控制区域的稳步扩展,清朝统治者颇有些自满,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气势,加之满族本身尚处于封建化程度很低甚至前封建化状态,这就使清朝的政策暴露出摇摆不定的特点来。清初的五大弊政——圈地、投充、逃人法、剃发、易服就是这样。
清朝定鼎北京后,随着征服战争的进行,大批满族贵族、将士及旗下人拥入关内。八旗诸王、贝勒及将士是清朝立国的基础,是完成武力征服的中坚力量。为确保其经济特权,清朝通过赤裸裸的剥夺来满足征服者的欲望。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廷开始圈占土地。户部派遣满族官员和地方官吏来到乡村田野,由两人骑马拉着户部颁发的绳子,不分有主无主,看好一块,四周一拉,田地就划归八旗。“圈一定,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
 被圈占的不仅是土地,连土地上的庐舍、场圃以及百姓妻室儿女全被其强行占有。
被圈占的不仅是土地,连土地上的庐舍、场圃以及百姓妻室儿女全被其强行占有。
随后,圈占的地区由近京扩大到其他各地。仅顺治四年(1647年)一次圈占,满族贵族便在京畿府州县掠夺了膏腴之地达到5 962 242亩。仅在直隶72个州县圈占土地达244 201顷,是原有土地364 886顷的67%。以后,又在山东、山西、苏北地区进行了大量圈占。

圈地只为八旗王公、贵族、兵丁解决了住房和庄园,而庄园耕种和日常服侍还需要大量人手。为此,清廷实行“投充”和“逃人法”。投充是将汉民逼迫成旗下奴仆,为其耕种。这是将落后的农奴制生产方式强行楔入中原地区。投充的汉民完全没有人身自由,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不仅本身受凌辱,而且世世代代子孙也要按照主奴名分,供满族贵族驱使。
为了摆脱非人的境况,汉民只有逃亡一途。为维护满族贵族的利益,清初统治者不惜制定惩处逃亡行为的法律。逃人与反逃人成为清初各种矛盾斗争的焦点。
逃人法是禁止已沦为满族庄园上的奴仆逃亡的法令,包括对逃人、窝主严加惩处。清廷把“捉拿逃人一款”列为“第一急务”,
 为此设置专门机构督捕衙门,制定异常严格的《督捕则例》。尽管如此,逃人仍很多。清初申涵光在《哀流民和魏都谏》一诗中描写了逃亡流民的惨状:
为此设置专门机构督捕衙门,制定异常严格的《督捕则例》。尽管如此,逃人仍很多。清初申涵光在《哀流民和魏都谏》一诗中描写了逃亡流民的惨状:
流民自北来,相将南去。问南去何处?言亦不知处。日暮荒祠,泪下如雨。饥食草根,草根春不生。单衣曝背,雨雪少晴。
老稚尪羸,喘不及喙。壮男腹虽饥,尚堪负载。早舂粮,夕牧马,妪幸哀怜,许宿茅檐下。主人自外至,长鞭驱走。东家误留旗下人,杀戮流亡,祸及鸡狗。日凄凄,风破肘。流民掩泣,主人摇手。

清初统治者强力推行圈地、逃人法等恶政,加重了汉族人民的负担,也侵害了汉族地主的利益。当时不少汉族官员挺身谏言,要求放宽民族压迫政策。多尔衮却下令:“有为剃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王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本章不许封进。”
 这是清初最早为言官划定的言事禁区,犯禁者也成为第一批受惩处的言官。
这是清初最早为言官划定的言事禁区,犯禁者也成为第一批受惩处的言官。
顺治十一年(1654年)正月,刚升任兵部督捕右侍郎的魏琯上《罢籍没定逃窝疏》,指出逃人法行至今日已十一年,“民之死于法,死于牵连者几数千百家。而究治愈力,逃者愈多”,认为今日之逃人,已不是自盛京而来,“自投充之门开,而所逃不皆东人”,逃者未必皆真逃,窝者未必皆真窝,请罢籍没之令,定逃窝之法。
 顺治帝命下部议,经大臣定议,对窝主“改斩为流,免籍没”。
顺治帝命下部议,经大臣定议,对窝主“改斩为流,免籍没”。
 魏琯因上疏取得初步成果,于是再次上疏,指出:窝主改为流徙,虽法外施恩,但窝主家属辗转随徙,于情不合。因此,他请求妻儿免流徙,田宅不必报。
魏琯因上疏取得初步成果,于是再次上疏,指出:窝主改为流徙,虽法外施恩,但窝主家属辗转随徙,于情不合。因此,他请求妻儿免流徙,田宅不必报。
顺治帝览奏后勃然大怒,说满族家人系先朝将士血战所得,故逃窝之禁甚严,近年屡次宽减,罪止流徙,且逃人多至数万,所获不及什一,督捕衙门屡经具奏,魏琯明知,何得又欲求减,显见偏私市恩,殊为可恨。顺治帝命议政诸王、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各官,会同从重议处具奏。魏琯随后被议绞,罪责是其统司缉捕一年之内,逃人至于数万,所获未及数千,又疏请宽逃人之禁,欲使满族家人尽数逃散。顺治从宽降三级使用。但几个月后,清廷借口魏琯与山东德州秀才吕煌私匿逃人案有牵连,将他革职,遣戍辽阳。从此,魏琯开始了“穷荒旅羁,饮食艰辛”“黄沙莽莽恶风吹”的谪宦生涯。不久,魏琯卒于辽阳戍所。

魏琯并非言官,但他是具体执行逃人法的汉族官僚。他目睹逃人法的暴虐无理,企图让清朝统治者改弦更张,自己却因此获罪,成为直谏的牺牲者。
“逃人法”是被清朝最高统治者明令宣布的言事禁区,而汉族言官却敢于屡次触犯这个禁区。顺治十一年(1654年)九月初三,福临驾临内院,召诸王及九卿、科、道等汉官,赐给他们上等好茶后,话题转到巡抚宜永贵上疏一事。宜永贵称,满族逃人甚多,捕获甚少,而汉官议隐匿逃人之罪,必欲轻减。说到这里,顺治帝顿时龙颜不悦,对在场的汉臣说:“尔等汉臣每每与满洲抵牾,蓄有贰心。朕以同德相期,而尔等多怀异念矣。今尔等之意欲使满洲家人尽皆逃亡,使满洲失其所业,可乎?今日面谕之后,若更持贰志,朕决不尔贷。”
 顺治帝一再用“贰志”“贰心”“异念”这样非常敏感的政治词语来警示、提醒、威慑汉官,并告知汉官:逃人法关系满族根本利益,是不能触碰的禁区。随即,由郑亲王济尔哈朗等议定隐匿逃人者正法、家产入官等十几项更为严厉的逃人法。
顺治帝一再用“贰志”“贰心”“异念”这样非常敏感的政治词语来警示、提醒、威慑汉官,并告知汉官:逃人法关系满族根本利益,是不能触碰的禁区。随即,由郑亲王济尔哈朗等议定隐匿逃人者正法、家产入官等十几项更为严厉的逃人法。
魏琯因谏逃人法而被革职遣戍,顺治帝又一再打预防针,并经清廷新订法律。但这些仍没有封住言官之口。兵科右给事中李裀,堪称前赴后继。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他目睹逃人法执行以来的种种弊端,上疏说立法过重、株连太多,使海内不论贫富良贱,都惴惴于性命朝不保夕之忧,即便大逆不道之罪,也不过如此,而破一家即耗朝廷一家之贡赋,杀一家即伤朝廷一人之培养,“法愈峻则逃愈多,学医犹曰人费,立法乃以人试乎”(李裀《谏辽东疏》),他提出逃人法“可为痛心者”有七。主要内容是:一是自逃人法实行后,官绅民皆不安,大有危在旦夕之感;二是因逃人法无休止地残杀,市井为空;三是流民失所,转为盗贼,国家则无安宁之日……
李裀并非不知上疏可能带来的结局,亲友得知他将上疏后,仓促间一再索要疏稿,当看到内容措辞后,惊讶咋舌,劝他修改文辞,以免获罪。李裀不为所动,说:“吾每见言官缄口不言,或以细琐无关者塞责。朝廷亦何贵有此阘茸赘员哉!心窃鄙之,何敢自蹈。且天子圣明,必不见罪;即罪,我死分耳!”李裀的意思是倘若不能直抒胸臆,即便安全一生,老死终日,那实在是有负君国,我将抱恨九泉。

李裀的上疏于正月二十八日上达,经过二十多天后,才交给议政王大臣会议。因上疏有“七可痛心,情由甚毒”,李裀被议为死罪,顺治改为“流徙尚阳堡”。

三月初九,顺治帝谕称:逃人一事,屡经详议,立法不得不严,昨颁谕旨,备极明确,若仍执迷违抗,偏护汉人,欲令满人困苦,谋国不忠,莫此为甚,朕虽欲宥之弗能矣,兹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
 顺治帝再次将逃人法划定为言事禁区。
顺治帝再次将逃人法划定为言事禁区。
李裀有谏言之责,他明知不可而为之,他被议罪后引起正直官员的普遍同情。在他告别京城,前往流放地时,人们夹道相送。毛腾蛟在《送别李龙衮奉诏诣尚阳堡》诗中写道:
朔风一朝起,严霜惨以冽。
君为秦廷哭,举国惊欲绝。
谁知今日泪,一字竟一血。

李裀带着满腔的悲愤踏上了陌生的土地,远离了让他充满希望而又失望的京师。当他的肉体经受残害时,他的精神也逐渐麻木。史书记载,李裀在戍所褐衣蔬食,虽手不释卷,但闭口“不及世事,若将终身焉”,不久死于戍所。

先期因文字狱被流放到这里的释函可,作有《哭李给谏》一诗,为他的死鸣屈:
山中愁未了,走马哭孤臣。
白发随江水,青云逐塞尘。
史留忠愤疏,天丧老成人。
幸有绨袍在,年年渍泪新。

清初直谏言官大多成长于明末,他们的血统中还流淌着明代士大夫的血液,敢于犯颜直谏,讽议朝政,虽罪不辞。朝廷对触及其根本利益的直谏者,尤其是触动满族贵族利益的直谏者,虽未直接杀戮,但或流放,或罢官,罪谴随之不绝。
赵开心是明朝崇祯七年(1634年)进士,清朝定鼎北京后,他官任御史时因敢于直谏而颇有声名,仕途也屡起屡仆。他得知礼部侍郎李若琳曾向多尔衮建议令官民剃发而愤怒至极,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他参劾李若琳“垂涎内院一席,辄借剃头为先资”,说:“李若琳忽传王上有官民剃头之旨,举朝闻之,争相错愕,谓我清朝主盟中夏,急当讲求帝王文物之理,方将进皇上、王上加衮冕,以隆郊祀,以示观仰,岂复令臣民去冠裳而伤发肤,且独不有煌煌之明旨在,乃倏而为反汗之号,使之疑功令之不信乎?”
赵开心的参劾疏与其说针对的是李若琳,不如说是针对摇摆不定的清朝最高统治者。因为“剃发令”时而雷厉风行般执行,时而停罢。疏中所说的“帝王文物”是指汉族中央王朝的制度,也自然包括衣冠服饰。上疏还谏言清廷不能出尔反尔,使得天下臣民不相信“明旨”。皇帝的谕旨颇有意味,说:赵开心这本既然说的是仁义之道,“但不知纱帽圆领即可为仁义否?今愿学本朝服制的反说谄佞,将欲使通国官民不遵清制而终为明朝人物乎?”“若不愿剃头者亦不必强,其情愿剃头者方且嘉许之不暇,何得反目为贪位固宠,指斥而非之耶?”

“将欲使通国官民不遵清制而终为明朝人物”,这顶政治大帽子实在不小。此时,多尔衮自以为南明弘光政权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都已被摧毁,乐观地认为天下已然大定,于是下令全国一律剃发。大学士洪承畴启奏摄政王,希望先从官员开始,百姓稍缓。多尔衮说他思考此事已经一年了,遂于顺治二年六月十五日通过礼部,向全国发布严厉的剃发令:
向来薙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薙发。
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
。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若有复为此事,渎进章奏,欲将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其衣帽装束,许从容更易,悉从本朝制度,不得违异。该部即行传谕京城内外并直隶各省府州县卫所城堡等处,俾文武衙门官吏师生一应军民人等,一体遵行。

剃发令颁布后,激起全国各地的强烈反抗。江阴人民守城八十一天,抵抗清军,表现出“头可断,发不可剃”的精神。次年三月,赵开心被革职为民。此后,汉官也不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博取直谏美名,也再没有为剃发令上疏者。
在因言获罪的流放者中,李呈祥是极少数生还的幸运者之一。出生于山东沾化的李呈祥少有才名,崇祯年间选庶吉士。降清后授编修,累迁少詹事。顺治十年(1653年)二月,他针对满族官员把持各部院政权、汉族官僚毫无权力的现状,上疏请求各部院应裁去满官,专用汉人。这无疑是对清朝“首崇满洲”国策的最尖锐批评。顺治帝对大学士洪承畴等说:“(李)呈祥此奏甚不当。昔满臣赞理庶政,弼成大业。彼时岂曾咨尔汉臣?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尔汉臣奈何反生异志?若以理言,首崇满洲固所宜也。想尔等多系明季之臣,故有此妄言耳!”
 顺治帝承认“首崇满洲”,但把汉官在清初打天下的作用一笔抹掉,这无论如何也说不通。在场的汉官洪承畴、范文程、宁完我、陈名夏等人自然心中不服气,向顺治帝表示:“臣等无以仰答圣谕矣!”顺治帝发怒,满官立即行动起来。都察院副都御史宜尔汉等人弹劾李呈祥“讥满臣为无用,欲行弃置,称汉官为有用,欲加专任,阳饰辨明,阴行排挤”
顺治帝承认“首崇满洲”,但把汉官在清初打天下的作用一笔抹掉,这无论如何也说不通。在场的汉官洪承畴、范文程、宁完我、陈名夏等人自然心中不服气,向顺治帝表示:“臣等无以仰答圣谕矣!”顺治帝发怒,满官立即行动起来。都察院副都御史宜尔汉等人弹劾李呈祥“讥满臣为无用,欲行弃置,称汉官为有用,欲加专任,阳饰辨明,阴行排挤”
 。顺治帝革去李呈祥的职官,交刑部议处。刑部议处李呈祥当死。顺治帝从宽改为流放盛京。
。顺治帝革去李呈祥的职官,交刑部议处。刑部议处李呈祥当死。顺治帝从宽改为流放盛京。
李呈祥追随前贤来到了流放者的土地。《仲冬一日》衬托出作者凄苦的心境:
饥鸦蹲不语,冻犬卧成团。
日出柴门晓,烟高大漠宽。
顺治十七年(1660年),在清理建言得罪诸臣中,李呈祥熬过了八年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煎熬,从流放地释归。可是,他再也不愿为皇家操心了,释归后徜徉林下二十余年。
多尔衮摄政时期,清廷处于武力征服全国阶段,对汉官虽曲意任用,但汉官还不能与满官争权。顺治亲政后,对汉官比较重视,内三院的满族大学士只有富察氏额色黑一人,而且汉官在六部的势力也有所增长。满汉官员的矛盾较为突出。往往议及一事,满官群起反对,汉官赞成;汉官反对,满官赞成。这自然不利于统治。因此顺治帝于十年(1653年)四月对汉官等宣谕说:
凡事会议理应画一,何以满汉异议?
虽事亦或有当异议者,何以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洲官,
此皆尔等心志未协之故也
。本朝之兴,岂曾谋之尔汉官辈乎?故明之败,岂属误于满官之言乎!奈何不务和衷,而恒见乖违也。自今以后,务改前非,同心图效,以副朕眷顾之意。不然,朕虽欲尔贷,而国法难容。至于都察院、科道等官,职司言路,见有如此乖戾者,亦当即行纠弹。

满汉官员之间“心志未协”是那个时代矛盾的产物,并非几次上谕式的劝诫就能化解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