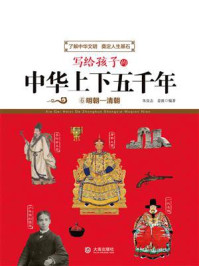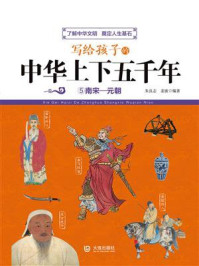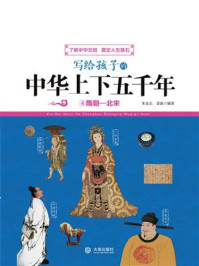甲申年(1644年)正月初一,正旦节,诸多不祥之兆笼罩着壁垒森严的京师。紫禁城主人崇祯帝的心绪烦乱如麻。连日来,李自成的农民军自南而北攻城略地,警报频传;地处一隅的满族贵族已统一东北,取道蒙古,长驱入内,国门为此多次紧闭。除夕,面对来自东西两方面日甚一日的威逼,大明王朝第十六代传人朱由检彻夜难眠。
正月初一,按惯例要在皇极殿(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改“奉天殿”为“皇极殿”)举行“大朝仪”。这种典礼与冬至大典完全相同,晨贺昼会,仪式相当隆重。照规定,文武大臣要先期而至,“待漏天子”,即等待天子圣驾。“待漏之时,鼓未严”,这是提醒朝臣们疾步入宫。“鼓初严”时,开始肃班,文武百官已经穿戴朝服,齐聚在午门外;“鼓次严”时,引班官引导百官,次第由左右掖门进入皇极殿,在丹墀序立;“鼓三严”时,肃班结束,开始鸣钟,钟声停止,天子圣驾缓缓升殿,东西四向鞭声齐响,文武两班大臣“有容无息,有意无声”,一齐仰瞻殿上,只见千百红袍,袖缨竖立,冠带相横。致辞官要高声朗语:“具官臣某,兹遇正旦,三阳开泰,万物咸新。”皇帝先致辞答谢,接着要训示一番,群臣随后山呼万岁。
 整个典礼高亢而不失庄重、紧凑而不失严肃,体现了新年新气象的进取精神。
整个典礼高亢而不失庄重、紧凑而不失严肃,体现了新年新气象的进取精神。
自开国皇帝朱元璋确定本朝仪制以来,岁月如梭,转眼已过去了277个春秋,其间继文守武,不乏英主,也不乏庸君。但只要条件允许,大朝仪就要照例举行。
也许是为了拂去多日来的晦气,也许是为了重温即位时的辉煌,甲申年的正月初一,朱由检来得格外早。一种希冀、一种重整河山的志向催促他疾步走向皇极殿。可是,空荡荡的大殿只有一名大金吾在当班。当时钟声已停,群臣按理早该肃班侍立。国家多事之秋,君不君,臣不臣,崇祯帝于少有的振奋中又平添了许多感慨。大金吾不等龙颜发怒,忙解释道:“群臣不闻钟鼓声,谓圣驾未出,来者益迟。令再鸣钟,启东西门,远近闻之,自皆疾驰。”崇祯帝也不再讲究礼仪,谕令鸣钟,而且不要停歇,朝门大开,永不关闭,以待群臣。
沉闷的钟声有气无力地撞击着,回荡在紫禁城的上空。皇宫里依然死一般寂静,许久也不见一人。崇祯帝是个情绪化的君主,他无法让漫长而久远的期待销蚀在这无奈的时间里,他不能让少得可怜而又弥足珍贵的振奋之情,随着这钟声飘向无际的远方。他提出要先谒太庙,到列祖列宗那里吸取先圣的元气,寻找一种精神力量,然后再接受那些各怀心中事、姗姗而来的大臣的朝贺。可是,圣驾銮舆与立仗马需要一百多匹,当时一无所备。一个小太监急中生智,提出将长安门外供朝臣们所乘的马全部牵到端门。崇祯刚要起驾,司礼太监奏道:“天子乃万乘之尊,乘用外臣马匹谒太庙,对祖宗不敬,也恐马有不驯,发生意外,请求免劳此行。”崇祯只好改为先受朝贺,后谒太庙,再次升殿以候。
原来,明朝的文武官员分东西二城居住,文臣寓西城,武臣寓东城,恰与朝班所列的文在东、武在西相反。此日崇祯帝先期而至,龙颜正视,文武大臣不敢过中门,从长安门入者各寻方便,文臣们从螭头下伛偻而入武班,武臣们躬身而入文班,朝班一时大乱。经过一番整肃后,大朝仪勉强成礼。
随后,崇祯帝往谒太庙。六品以下官不应陪祭,但因马匹全被征往端门,只好步行而归。这又为正旦节日增添了不祥之兆。

更奇异的是正月初一这一天,黄风刮得天昏地暗,咫尺之外看不见人。尽管十天前已立春,燕京的春天刮点风也不足为怪,但如此玄黄翻滚的狂风在这个季节是很少有的,尤其是又传来太祖的家乡凤阳地震的消息。占卜的结果是“风从乾起,主暴兵至,城破”。确是骇人听闻。

一连串的反常现象给神秘的皇宫蒙上了层层阴影。崇祯帝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他不甘心让大明几百年的基业丢失在自己的手中。他沐浴焚香,拜天默祷,在神坛面前虔诚而恭敬,口中喃喃低语:“方今天下大乱,欲求真仙下降,直言朕之江山得失,不必隐秘。”大仙降乩,崇祯帝一看,上面写着四句话:
帝问天下事,官贪吏要钱。
八方七处乱,十爨九无烟。
黎民苦中苦,乾坤颠倒颠。
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

崇祯帝见此回答,颓然地低下了头。大明气数已尽,朱由检的“振作”只能算作一种良好的愿望。
一个王朝的兴衰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更何况像明朝这样一个存在近三个世纪、在同期的世界史上曾处于领先地位的王朝。同样,看似相同的历史表象却掩盖着许多不同甚至相反的历史真相。因此,探究明亡之因,除了探究它与以往王朝末期相同的因素,更应到那个时代发展的“新征兆”中去寻找。
在以农立国尤其是小农经济占支配地位的王朝里,其他生产部门自会受到排斥、挤压,难以摆脱其从属身份。自上而下的权力正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被扩散为社会中无孔不入的唯一整合组织。因此,任何事物也不能成为缓解、平衡处于独尊地位的权力的筹码,社会呈现为一种封闭、有序的静止状态,社会价值系统有效地影响、左右人们的所有活动。嘉靖以前的明代社会就是这样。
隆庆、万历以来,导源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风尚、价值系统发生巨大变化,时人惊叹“僭分违常”“风教不施”,其对社会上层的影响尤为显著。郑恭王朱厚烷的世子、创十二平均律的朱载堉在万历十九年(1591年)坚辞王爵,以世子独居,平生愤世嫉俗。他在《山坡羊·钱是好汉》中形象地描绘了一幅金钱崇拜的景象:
世间人睁眼看见,论英雄钱是好汉。五湖四海逞威能,如今人敬的是有钱。拐子有钱,走路也合款。哑叭有钱,打手势好看。有了钱诸般如意,合家人喜欢。蒯文通无钱,说不过潼关。铜钱多,人为你走遍世间。铜钱(少),求人一文,跟后侧前。

在金钱至上的时代氛围下,大小官吏不廉不法,把权力作为一种政治钞票,随时抛售。“方今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贸易,计美恶,计大小,计贫富,计迟速”
 ,学子一旦为官,则忘掉平日朋友,而每天奔走其门的都是言利之徒。“或某处有庄田一所,岁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银几百两,岁可生息若干;或某人为某事求一覆庇,此无碍于法者,而可以坐收银若干,则欣欣喜见于面。”对于这些讲“生财之道”者,官吏们大为欢迎,引其为座上之宾,待之唯恐不谨。
,学子一旦为官,则忘掉平日朋友,而每天奔走其门的都是言利之徒。“或某处有庄田一所,岁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银几百两,岁可生息若干;或某人为某事求一覆庇,此无碍于法者,而可以坐收银若干,则欣欣喜见于面。”对于这些讲“生财之道”者,官吏们大为欢迎,引其为座上之宾,待之唯恐不谨。
 松江华亭人何良俊在慨叹风俗易人之快的同时,论述了官场风气的演变:成化、弘治(1465—1505年)以前,为官者尚大法小廉,家无余资;至正德年间(1506—1521年),官员竞相营产谋利,积资十余万者不乏其人,“自以为子孙数百年之业矣”,但仅仅五六年间,田宅皆已易主,子孙贫困乃至不能自存。至万历时发生巨大变化,初试县令,即买田宅玩好,为子孙计,被人谴责,也恬不为怪。
松江华亭人何良俊在慨叹风俗易人之快的同时,论述了官场风气的演变:成化、弘治(1465—1505年)以前,为官者尚大法小廉,家无余资;至正德年间(1506—1521年),官员竞相营产谋利,积资十余万者不乏其人,“自以为子孙数百年之业矣”,但仅仅五六年间,田宅皆已易主,子孙贫困乃至不能自存。至万历时发生巨大变化,初试县令,即买田宅玩好,为子孙计,被人谴责,也恬不为怪。

商品经济一旦生发为一种物质力量,它对传统社会,尤其是对权力的侵蚀、冲击必将是巨大而迅猛的。宫中的糜烂奢侈之风及万历帝对金钱的贪求仅从后者的性格等因素考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值得注意的是,万历帝之屡派宦官督办织造、陶瓷,一再增加贡品数量,要求款式新奇鲜艳华美,大量搜购金珠宝石,染指之处正是中国当时最繁富奢华之区。并且,自张居正去世后,尽管臣僚进谏相踵,但万历帝直到寿终正寝,依然沉迷于此。尤其有趣的是,万历十年(1582年)九月初二,云南省解进年例黄金迟限两天到达京师,万历帝精于计算,锱铢必较,当即命阁臣拟旨参劾。刚接替张居正为内阁首辅的张四维,觉得此事张扬出去“恐骇观听”,并解释说,云南距离京城万里之遥,江山隔远,中途又遇大雨,也就迟误两天,现在已经解进宫中,如果就其抵达京城算起,尚在八月之内。万历帝令收进金两,姑饶一遭。
 万历十三年(1585年)二月,抄没张居正家财的钦官将所谓赃物装成一百箧,运往京师内库,途中丢失一箧,万历帝得知后雷霆大作,颁旨罚官。
万历十三年(1585年)二月,抄没张居正家财的钦官将所谓赃物装成一百箧,运往京师内库,途中丢失一箧,万历帝得知后雷霆大作,颁旨罚官。
 可见其对财货的贪恋,连宾师良辅的情分也忘得一干二净。
可见其对财货的贪恋,连宾师良辅的情分也忘得一干二净。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万历帝派矿监税使对全国的搜刮。学者据《明神宗实录》《定陵注略》等材料估算,矿监税使每年向内库实际进奉白银171万两、黄金0.36万两,远远超出其内库每年120万两金花银的规定数目,而这些进奉只是实际掠夺的十分之一。
 按此估算,在矿监税使横行的十年间,实际从各地攫取了1.71亿两白银、36万两黄金。
按此估算,在矿监税使横行的十年间,实际从各地攫取了1.71亿两白银、36万两黄金。
矿监税使的掠夺激起全社会的公愤。市民、商人、手工业者以及地方官吏以各种方式予以抵制,山东、湖广、苏州、江西、辽东、福建,带有新时代气息的“民变”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此伏彼兴。从内阁大臣到科道言官,从地方大吏到低级末僚,整个社会的神经都系于此,劝谏的奏疏像雪片一样飞来。他们或从大明江山的长治久安角度,披肝沥胆,慷慨陈词;或从纯经济的角度,条分缕析,核本算利;或从万历帝贪财好色的角度,直言不讳,披鳞不避。更有的臣僚煞费苦心,把奏疏写成图说的形式,以便神宗阅读;还有的拟出标题,附以“贴说”,以便提纲挈领;等等。这些充分表达了他们的满怀忠诚和深远的政治眼光。
 对于这些赤诚中间杂激愤、情理中略带不平的千言万语,神宗只有一个办法,“即束高阁”“屏置勿阅”
对于这些赤诚中间杂激愤、情理中略带不平的千言万语,神宗只有一个办法,“即束高阁”“屏置勿阅”
 。
。
与对待臣僚进谏截然相反的是,对待矿监税使及其爪牙,神宗似乎幻化成另一个天子,他一改倦怠之态,精神为之大振,总是“朝入朝批,夕上夕发,应之如响”
 ,金钱司天子,神宗当之无愧。无怪乎户科给事中田大益说神宗“以金钱珠玉为命脉”。但这样的药石之言,只能充耳,即使比干剖心,皋、夔死谏,也不能解惑,因为神宗的贪婪已深入骨髓,“意迷难救”
,金钱司天子,神宗当之无愧。无怪乎户科给事中田大益说神宗“以金钱珠玉为命脉”。但这样的药石之言,只能充耳,即使比干剖心,皋、夔死谏,也不能解惑,因为神宗的贪婪已深入骨髓,“意迷难救”
 。
。
值得玩味的是万历三十年(1602年)初的一件事。这年二月,神宗得病,自以为行将离开人世,十六日巳时忽宣召大臣进宫,首辅沈一贯独自奉诏至神宗卧病的西暖阁。神宗说:“朕病日笃矣,享国已久,何憾!佳儿佳妇付与先生,惟辅之为贤君。矿税事,朕因殿工未竣,权宜采取,今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内监皆令还京。”沈一贯回到内阁,根据皇帝的谈话内容整理成谕旨草稿,而后又进呈宫中,等候批红。当天夜晚,他与部院重臣直宿朝房,以备不测。漏下三鼓,太监送出神宗审阅过的正式谕旨,内容与所拟一致,诸臣大喜,谓天下倒悬可解。可是,神宗次日病愈,立即反悔,令宦官二十余人前往内阁索要已审阅的谕旨,内阁大臣初不肯交,双方扭成一团,“搏颡几流血”,最后阁臣只好让步交出。司礼太监田义稍示异议,神宗大怒,“欲手刃之”。此后,廷臣尽管日有诤谏,但神宗我行我素,“矿税之害遂终神宗世”。

早在大明王朝行将就木的16、17世纪之交,朝野有识之士及敏锐的思想家们就在思考:起于草莽、深悉民间疾苦的太祖皇帝躬身创设的一代规制何以历久弊生?曾自由游弋海上数十年、执世界诸国之牛耳的大明王朝何以必定要走入垂暮之年?目睹天启六年(1626年)“七君子之狱”中父亲惨遭宦官杀害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善于从制度,尤其是从时代的高度,总结明亡之因,他写的传世之作《明夷待访录》是同时代对君主政体予以鞭挞批判最有力的大作。他指斥君主“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他认为,讲君臣之义的都是“小儒”,因为像夏桀、商纣王那样的君主,民众早应该起而推翻之,那些腐儒所奉行的君臣之义,是拿亿万百姓的血肉以供一家一姓之私。后世之君若没有做到如父如天,人民就有理由取而代之。他在《明夷待访录》的《原臣》篇中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桀、纣之亡,是天下大治的开始。
。他认为,讲君臣之义的都是“小儒”,因为像夏桀、商纣王那样的君主,民众早应该起而推翻之,那些腐儒所奉行的君臣之义,是拿亿万百姓的血肉以供一家一姓之私。后世之君若没有做到如父如天,人民就有理由取而代之。他在《明夷待访录》的《原臣》篇中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桀、纣之亡,是天下大治的开始。
 诸多论断,都是从总结明亡教训而发出的,振聋发聩,引人深思。他提出的种种拯救社会的方案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社会力量的声音,同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前瞻性。在以后的相关部分,我们会听到这位思想家的时代强音。
诸多论断,都是从总结明亡教训而发出的,振聋发聩,引人深思。他提出的种种拯救社会的方案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社会力量的声音,同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前瞻性。在以后的相关部分,我们会听到这位思想家的时代强音。
清朝入关后,历时近百年,经由亡国之痛的前明遗臣的广泛参与,并由康、雍、乾三代帝王发纵指示的官修《明史》,于乾隆初年问世。该书明确得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的结论,这一结论集中了晚明以来时人的思考,也最具代表性,影响所及,乃至今天的相关著作仍频繁出现上述字句。然而,明之亡何以亡于神宗?思想家们的论断见仁见智。
的结论,这一结论集中了晚明以来时人的思考,也最具代表性,影响所及,乃至今天的相关著作仍频繁出现上述字句。然而,明之亡何以亡于神宗?思想家们的论断见仁见智。
龚自珍无愧于最先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家,他透过封建政治衰世的表象,捕捉到了与以往朝代迥异的新气息,看到了新时代的朦胧发轫。他说:“俗士耳食,徒见明中叶气运不振,以为衰世无足留意,其实尔时优伶之见闻、商贾之气习,有后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跻者。不贤识其小者,明史氏之旁支也夫?”
 明朝中叶是中国传统社会酝酿重大变革的时期
明朝中叶是中国传统社会酝酿重大变革的时期
 ,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商人资本异常活跃,舍“本”逐“末”的人口比例急剧增加,士商合流所带来的“四民”新排序,
,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商人资本异常活跃,舍“本”逐“末”的人口比例急剧增加,士商合流所带来的“四民”新排序,
 以及政治生活中的党派政治分野,社会舆论对政治权力、政策决策的钳制和干涉,等等,都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的中国逐渐远离传统社会,正在走向新的时代。
以及政治生活中的党派政治分野,社会舆论对政治权力、政策决策的钳制和干涉,等等,都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的中国逐渐远离传统社会,正在走向新的时代。
万历帝及他所执掌的明朝政府,不能超然于时代而独存、远离社会而安居。时代的悄然变化及涌动的新世潜流与传统权力所承担的社会职能正在交汇、碰撞,表面看去乖张而怪异的现象正是二者间矛盾的结果。
神宗是中国古代庞大的帝王家族中创造“之最”最多的一位皇帝。他二十余年不上朝、不接见大臣、不御经筵、不阅奏章、不亲享太庙,他对“酒色财气”的全身心投入使万历后期的政府处于半瘫痪状态。南炳文、汤纲二先生在其所著《明史》中详列万历二十四年至四十八年间(1596—1620年)各衙门缺官状况,并认为“从中央政府到地方,从高级大僚到中下级官吏,概莫能外,而且几十年一直存在,政府机构几同瘫痪”
 。因缺官而误事的记载在史籍中随处可见。万历二十四年因吏部尚书缺员,竟废大选。
。因缺官而误事的记载在史籍中随处可见。万历二十四年因吏部尚书缺员,竟废大选。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六月,因吏科都给事中久缺,无人经手发放官员赴任的凭证,致使等待签发的多达七八百人,其中无财无势的“教官候凭日久,多有穷死者”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六月,因吏科都给事中久缺,无人经手发放官员赴任的凭证,致使等待签发的多达七八百人,其中无财无势的“教官候凭日久,多有穷死者”
 。次年五月,由于刑部久缺掌印官,“狱卒积至千人,莫为间断”
。次年五月,由于刑部久缺掌印官,“狱卒积至千人,莫为间断”
 。史书中往往将万历帝的怠政与政府瘫痪联系在一起,认为神宗“怠于政事,曹署多空”
。史书中往往将万历帝的怠政与政府瘫痪联系在一起,认为神宗“怠于政事,曹署多空”
 。实际上,这种状况是神宗有意为之,尤其是他厌烦官吏议论国政。明中叶以来,朝野官吏及士大夫议论国政已成风气,神宗对此颇感厌烦,不但限定议事人员,且对所议之事形成逆反行为,“论救忠良,则愈甚其罪;谏止贡献,则愈增其额”
。实际上,这种状况是神宗有意为之,尤其是他厌烦官吏议论国政。明中叶以来,朝野官吏及士大夫议论国政已成风气,神宗对此颇感厌烦,不但限定议事人员,且对所议之事形成逆反行为,“论救忠良,则愈甚其罪;谏止贡献,则愈增其额”
 。大学士赵志皋曾在催促补官时说:“皇上所以不即允部院考选之请者,岂因近日诸臣好发议论,欲于稽迟之中默寓裁抑之意?”
。大学士赵志皋曾在催促补官时说:“皇上所以不即允部院考选之请者,岂因近日诸臣好发议论,欲于稽迟之中默寓裁抑之意?”
 礼部的奏章说:“道路之口,妄相猜忖,以为皇上非忌其拜官也,忌其拜官之后言或激切逆耳,遂排抑至此。”
礼部的奏章说:“道路之口,妄相猜忖,以为皇上非忌其拜官也,忌其拜官之后言或激切逆耳,遂排抑至此。”
 一个拥有亿万臣民的皇帝以怠政的方式来对待祖先创下的基业,他“每晚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
一个拥有亿万臣民的皇帝以怠政的方式来对待祖先创下的基业,他“每晚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
 ,在用酒精麻醉自己的同时,也在为大明王朝注射一种慢性死亡的麻醉剂。
,在用酒精麻醉自己的同时,也在为大明王朝注射一种慢性死亡的麻醉剂。
诸多事实表明,万历时期统治者已很难照旧统治下去,它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四月,刑部左侍郎吕坤上《忧危疏》,开篇提出“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他说的四种乱民包括无聊之民、无行之民、邪说之民、不轨之民,都已如箭在弦。并且:
万历十年之后,无岁不告灾伤,一灾动连数省。近日抚按以赈济不可屡求,存留不可终免,起运不可缺乏,军国不可匮诎,故灾伤之报遂稀,催科之严如故。岂不哀民?势不可已也。臣久为外吏,熟知民艰。
自饥馑以来,官仓空而库竭,民十室而九空
。陛下赤子,冻骨皴肌,冬无破絮者居其半;饥肠饿腹,日不再食者居其半。流民未复乡井,弃地尚多荒芜。存者代去者赔粮,生者为死者顶役。破屋颓墙,风雨不蔽;单衣湿地,苫藁不完。儿女啼饥号寒,父母吞声饮泣。君门万里,谁复垂怜!

仅仅过了四年,吏部尚书李戴的上疏已表明全国处于极度的饥荒状态:“数年以来,灾儆荐至,秦晋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继之,民食雁粪矣,齐鲁继之,吴越荆楚又继之,三辅又继之,老弱填委沟壑,壮者展转就食,东西顾而不知所往。”
 普遍的贫困和饥饿,把全国同时推到了无法忍受的极限。这就不难理解明末农民战争何以在较短的时间里以摧枯拉朽之势埋葬了明王朝。
普遍的贫困和饥饿,把全国同时推到了无法忍受的极限。这就不难理解明末农民战争何以在较短的时间里以摧枯拉朽之势埋葬了明王朝。
“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历史有因果,也有大势。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七日攻陷大同,次日下宣府。明朝大势已去。崇祯帝先后三次颁罪己诏于天下,把所有罪责都揽于自己一身:所以使民罹锋镝,蹈水火,血流成河,骸积成山者,皆朕之过也;使民室如悬磬,田尽污莱,望烟火而无门,号冷风而绝命者,又朕之过也。他希望借重祖宗之厚德,与民更始,以挽回天心、民心。
 但岂不是太晚了吗?!与仅有太监王承恩一人从殉崇祯帝于煤山形成对比的是,李自成进京后,投顺新主的明臣挤破了皇宫的大门,因为人众拥挤,被守门长班用棍打逐。即便如此,穿着囚服立于午门外的百官,仍有四千多人。
但岂不是太晚了吗?!与仅有太监王承恩一人从殉崇祯帝于煤山形成对比的是,李自成进京后,投顺新主的明臣挤破了皇宫的大门,因为人众拥挤,被守门长班用棍打逐。即便如此,穿着囚服立于午门外的百官,仍有四千多人。
官员再一次用行动做出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