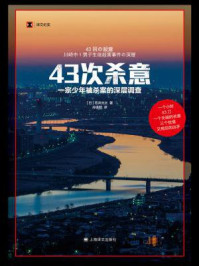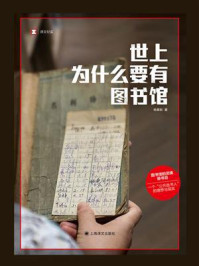20世纪30年代,宇宙学原理通过了一项重要的实证检验:公式(2.1)中红移—距离关系的均匀性的预测与第2.3节中讨论的严格测试相符。但是星系分布图并未表明均匀性。查利尔(1922)绘制了已知星云在天空中的分布图。在查利尔的分布图中,这些物体包括银河系中的星团,以及星光被尘埃云反射的区域,但大多数都是银河系外的星云,即其他包含着大量恒星的星系。查利尔指出,该图使人想到了分层星系团:星系以团块形式出现,而团块则存在于包含着很多团块的大团块中,依此类推,可能扩大到无限大的尺度。这在后来被称为“分形宇宙”。
10年后,哈佛学院天文台的哈洛·沙普利和阿德莱德·艾姆斯展示了1 249个已知的星系的星表,其光度超过 m =13(这是对在天空中明亮程度的度量)。图2.2展示了这些星系在银河系两个半球中角向位置的分布(Shapley and Ames,1932)。左侧分图显示了我们银河系北半球的星系,右侧分图显示了银河系南半球的星系。在银河系平面附近几乎没有星系,这是由于靠近我们银河系平面的星际尘埃吸收了光。银道面上方和下方的天空更加明晰。图2.2左侧的北半球展示了室女星系团(该星团因临近室女座而得名)及其周围的许多星系。德沃古勒(1953,1958a)将其命名为室女星系团,将其周围的星系聚集命名为本超星系团。周围星系的这种明显不均匀的分布已得到充分证实。

图2.2 沙普利-艾姆斯星系图(亮度高于表观星等13级,沃尔巴赫馆藏区,哈佛学院图书馆)
威廉·德西特(1917a,b)对爱因斯坦关于宇宙结构的思想做了讨论。由于德西特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天文学家,他本可以告诉爱因斯坦,这些星云主要都是河外星系以及这些河外星云根本不接近均匀分布的证据。但是我没有看到过任何资料表明,爱因斯坦考虑过这一观测,以及如果考虑过,这些是否影响了他的思考。
1917年的可能性是,尘埃的消光是一片一片的,很零散,甚至远离我们银河道面,或者观测到的星系分布根本不符合宇宙学原理的均匀性。到20世纪50年代,除了排除尘埃选项外,其他方面并没有太大变化。这种情况在颇有影响力且内容丰富的著作《经典场论》(Landau and Lifshitz,1951,1948年俄语版的英文译本)中得到了认可。这本书对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进行了令人钦佩的阐述,但这本书或他们这套理论物理学系列中的其他书对数据却很少提及。罕见的例外是朗道和利夫希茨(1951,332)对爱因斯坦的均匀性假定的评论:
尽管目前可获得的天文数据为该密度的均匀性的假定提供了基础,但该假定可能仅具有近似性质。此外,在获得更多新的数据后,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改变,哪怕是定性的改变,以及如此获得的引力公式解的基本性质在多大程度上与现实相符,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从图2.2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明智的说法,尽管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人们可能已经预见到一个警告:对广义相对论的检验不多。引力物理学的情况与他们著作的第一部分中的实证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后者基于的是经过充分检验和广泛应用的电磁学。
奥尔特(1958)在第十一届索尔维会议的一份报告《宇宙演化与结构》( La structure et l’évolution de l’univers )中以“宇宙最显著的方面之一就是其不均匀性”开头。作为证据,他展示了图2.2中沙普利和艾姆斯(1932)的图。他原本还可以加上阿贝尔(1958)星表中距离较远的富星系团,以显示它们像超星系团中的星系团一样,以分散的形式散布在天空中。但与沙普利和艾姆斯图中更近的星系的分布相比,阿贝尔图(1958,图7)中的星团的分布确实显得不那么成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