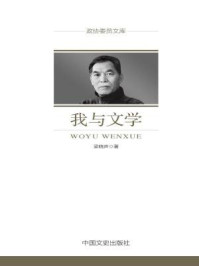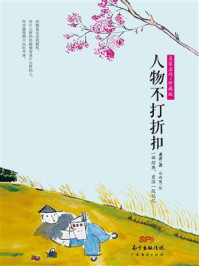“要是养我这么丢脸的话,当初我生下来就把我弄死算了啊!”我冲着洗衣池边上的母亲吼道。母亲背对着我没有再说话,水龙头下的水流声好像更大了。母亲什么也没做,但她每次都要收拾我和父亲“战斗”的残局。有时候我会成功点燃母亲的愤怒,把矛盾转移到她和父亲的夫妻关系上,不过多数时候她都像此刻这样,在听完我歇斯底里的发泄之后继续当个沉默者。
我非常厌恶我的父亲,我觉得他也不喜欢我,打我记事起,我们俩在家就一直是随时向对方“开炮”的状态。我从没见过哪个父亲会在教训孩子时用尽侮辱性词汇——“你是个残废你知道吗?”“真不知道你将来会有什么出息!”
“我这样还不是你喝酒害的。”“你就是条贱命,贱人自有天收的。”当然,我也没有见过哪个儿子回击父亲如此出言不逊。
父亲母亲是同龄人,二十八岁结婚,二十九岁有了我。在那个鼓励晚婚晚育的年代,可以说两个人都是“楷模”。“我生你那天晚上肚子开始痛,我就喊你阿爸带我去卫生所,你阿爸非倔,喊了你两个阿姑还有圩里那赤脚的老助产妇来家里,后来人家看情况怕不行,赶紧让叫车送到县医院。”很多年后母亲回忆道,“那医生说要剖,你阿爸坚持要顺产,在那里还跟人掰扯,后半夜你总算出来了。你这个仔出来大家都惊死了,什么声都出不来,那医生就往你的脚掌狂拍,你就是哭不出来,接着你阿爸也开始打啊,打了多久我也记不清,但你哇一声哭出来那一下,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母亲越说越激动,本来靠在沙发上突然端正坐起,“我以为哭出来就好了,那医生说你在胎里缺氧太久了,命是保住了,人会怎么样就另说了。我听完很心酸,你阿爸在外面跟人家医生干起来,整个走廊鸡飞狗跳的。”也是从那一刻起,我们这三口之家开始过上了不太平静的日子。
别的小孩一岁就开始“妈、妈”往外蹦,我到了两三岁嘴还是很严,按母亲的话说就是“有时你突然‘啊’一下,我都阿弥陀佛,各种感恩。那些亲戚过来看个个都说你应该是个哑巴,嘴脸表面看着是在可怜,我看背地里没少说闲话”。母亲不信邪,去新华书店买了两本《唐诗三百首》,天天把我放进外公专门做的竹椅子上就开始念,边念边拿着我的手摸着她的喉咙,就这样持续了三个多月。母亲说:“有一天我抱着你去菜市买菜,刚刚把钱拿给菜贩,你这个仔突然喊了声‘妈’。我还以为是听错了,然后你又喊了一遍,我当时在人家摊子上跟疯了一样,拿起菜就往家跑。我非常非常欢喜,但我没办法去跟菜市人斗阵
 分享,一个快四岁的小孩会叫‘妈妈’不应该吗?我怕太癫会被笑死。”我不清楚母亲的复述里会不会有失真的成分,但那两本皱巴巴的《唐诗三百首》一直被母亲珍藏到我们搬出政府大院。
分享,一个快四岁的小孩会叫‘妈妈’不应该吗?我怕太癫会被笑死。”我不清楚母亲的复述里会不会有失真的成分,但那两本皱巴巴的《唐诗三百首》一直被母亲珍藏到我们搬出政府大院。
本以为攻克了哑巴,日子就会好起来,但天公不仅疼憨仔
 ,天公也爱乱捉弄,我会讲话,却不会走路了。是大姑最先发现我走路有问题,怎么步步都走得瘸瘸拐拐,身体摇摇晃晃。她和母亲带着我上卫生所一看,那医师说:“坏了,是鸭母蹄
,天公也爱乱捉弄,我会讲话,却不会走路了。是大姑最先发现我走路有问题,怎么步步都走得瘸瘸拐拐,身体摇摇晃晃。她和母亲带着我上卫生所一看,那医师说:“坏了,是鸭母蹄
 ,这种是先天的,没药救。”“先天的”三个字总有致命一击的力量,它代表再怎么努力最后都是无果。消息一出,那些亲戚又很快跑到家里,这次也没有那可怜样了,也不委婉了,直截了当地劝母亲再生一个。按照当时的计生政策,每家每户只能生一胎,但如果第一个子女患有先天非遗传性残疾,就具备生二胎的资格。换言之,只要给我上个残疾证,母亲是可以再生一个的。
,这种是先天的,没药救。”“先天的”三个字总有致命一击的力量,它代表再怎么努力最后都是无果。消息一出,那些亲戚又很快跑到家里,这次也没有那可怜样了,也不委婉了,直截了当地劝母亲再生一个。按照当时的计生政策,每家每户只能生一胎,但如果第一个子女患有先天非遗传性残疾,就具备生二胎的资格。换言之,只要给我上个残疾证,母亲是可以再生一个的。
也许大人们天生没把小孩当回事,或者说没把我当回事,那些话都是当着四岁的我的面说的,就连父亲有天晚上都跑到床前跟母亲说:“我看,上幼儿园的事情可以缓缓,这仔也不一定要读书。”我侧卧在床边,面对着那纸片隔断墙,背后的一句一句都听得清清楚楚。
“那时候啊,谁来说我都没太大波澜,但你阿嬷也来劝我是真的有些顶不住,我自小最听你阿嬷我姨的话。”母亲说道。我们家管阿嬷和外婆都叫阿嬷,母亲和舅舅们也只用闽南语称呼外婆为“姨”,我一直很困惑,明明是妈妈,却得听一辈子叫姨。“那时你阿爸觉得丢脸,一天到晚出去找人喝酒,都是我自己在应付,人都麻了。还有些买体育彩票的人拿着一箩筐的号码球让你抓,说什么歹命仔身上都有玄机,我那时还笑笑相迎,现在想来实在晦气。”
说起来,我的命运掌握在那个四十二天大的女孩手里。千禧年前夕,计划生育政策还在有条不紊地执行着,在重男轻女思想比较严重的闽南,有些人家便投机取巧钻空子。就在那个所有人都劝父母再生一个的节骨眼儿上,有个刚生下四十二天的小女孩被放在了大院公厕的门口。小女孩被两层被子裹着,小脸被正月的寒风吹得通红,兴许是冻僵了,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女孩身上放了张红纸,上面写着出生时间,旁边有个白袋子,装着女孩的几件衣服。这下好了,都不用劝母亲生了,有个现成的在那,可能是时间紧迫,那两天家里总是一拨拨来人劝母亲把她抱回来。“这样老了才有人能指望,说不定这仔以后还得靠那妹妹养呢。”说着说着自己便笑起来,笑声真像电视里那些坏人,我当时心想。记得那阵子的某个晚上,母亲哄我睡觉时问道:“你想不想多个妹妹呀?”我愣愣地看了母亲几秒,投进她怀中,泪眼婆娑地回道:“阿妈,有妹妹你还会要我吗,不要我我去哪里啊?”母亲被我吓到了,急忙拍拍我的背安抚我。最后她还是没有把小女孩抱回来,当时父亲很心动,不管不顾就是要抱,母亲冲他嚷道:“你要是敢抱回来,那我就带着这仔走,你要再婚再生随你去。”到现在我都没见过几次母亲那么生气。父亲只好作罢。女孩第三天被人抱走了,就在隔壁乡里一户人家,有传言是儿子儿媳不孕不育,二老才将就着抱回来。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跟母亲说要二胎的事情。前些年,母亲对我的说辞一直是当时父亲工资不高,怎么可能再要一个孩子。去年有媒体去采访母亲时,我才知道了母亲的真实顾虑,她是这样说的:“办那什么证不就是打了个标签……我打这个标签,是关系到他一辈子的事情……说有补贴,社会对他有特殊的关照,我们都不需要这个,我不需要这个。要什么靠他自己去努力……我儿子再怎么样,在我们的心中,他就是正常人。”
20世纪90年代初,父亲是镇畜牧站的一名小职工,母亲是县服装厂的女工,两人是被做媒的介绍认识的。那做媒的好像背着KPI一样,使劲在外公外嬷耳边吹风,说这种在政府工作的铁饭碗可不多,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于是两人仅仅见了一面就被按头定下亲事,在那个只有一床双喜四件套当彩礼的年代。很多年后,我翻箱倒柜找到了当年母亲一封信的草稿版,信是写给远在福州读中专的小舅的。皱巴巴的纸上写着:“光弟,我见到了那个男的了,阿爹很满意,过不久也许我们就会成家,从没有跟男的一起过,想来还是紧张……也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幸福。”纸上字迹写写又涂涂,溢着母亲那颗悸动的少女心。我一边看一边露出“姨母笑”,母亲在旁说道:“当初有多期盼,日后就有多后悔。”
也许是因为我的出现破坏了这段感情,从小我就感受到父母的关系也如同我走路一般摇摇晃晃。他们俩只要一吵架,我就会是那个被丢来丢去的“炸药”。母亲责怪父亲在她孕期不顾家,天天酗酒;父亲则揶揄母亲没本事,产不出好卵。要是放在今天,遇到这样的男人不得有多远走多远,但是在那个年代,忍忍就过去了。有几次父亲甚至动手把母亲的脑袋往衣柜上砸,腥风血雨过后,父亲摔门而出,母亲抱着我坐在卧室花砖地上痛哭,一滴滴血落在母亲仅有的那双白色高跟鞋上,我用纸巾给母亲擦拭额头上的伤口。第二天放学回来,母亲不见了,父亲说:“你阿妈回你外嬷家,不回来了,不要你了……”我被吓得哇哇大哭,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才让这个家变成这样的。我躺在地上任由父亲怎么揍怎么骂,死活都不肯上学,父亲只好拨通外嬷家的电话,让我跟母亲说话。电话那头母亲声音一出来,我又绷不住狂哭,父亲就把电话挂掉了。大姑来家里把父亲责骂了一顿,父亲只回道:“咱爹不也是这样对咱娘的吗?”我们父子俩就这样单独相处了四五天,几乎零交流,他看电视,我自个儿玩自个儿的。要是家里剩我一个人,我就害怕地躲进衣柜里偷偷地哭,后来很多年我在难过时都喜欢躲进衣柜里,不用面对外界,也不用面对自己。
父亲家暴没有持续太久。我们搬到县城之后,母亲变成了一个新兴职场女性。有次挨了巴掌立马打电话给两条街外的大舅,大舅骑着摩托唰一下赶到我家,两百斤的大块头,进门就把父亲按倒,

 给了两拳,还嫌不够,又来了两脚。我拿了条热毛巾让他擦一擦伤口。家里后来集结了好多亲戚,大家轮番批斗父亲。从那之后,夫妻俩还是会吵架,但再也不动手了。也不能说我大舅有多正义,因为他也经常打老婆。
给了两拳,还嫌不够,又来了两脚。我拿了条热毛巾让他擦一擦伤口。家里后来集结了好多亲戚,大家轮番批斗父亲。从那之后,夫妻俩还是会吵架,但再也不动手了。也不能说我大舅有多正义,因为他也经常打老婆。
有很多年里几乎都是母亲一个人在管我,按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丧偶式育儿”。付出更多的一方,往往更容易出差错。我们住在政府大院时,上厕所得走到三四百米外的公共厕所。有一年冬天下着大雨,母亲图省事,便抱着我越过家后窗外的下水道想直接解决,不料泡沫拖鞋踩在石板路的青苔上,重重滑倒。我的后脑勺猛烈地撞上一块板砖,母亲顾不上自己额头上不断流血的伤口,抱起号啕大哭的我,骑着摩托车就往镇上卫生院赶。等我软趴趴地躺在手术床上进行消毒缝针时,母亲这才开始非常克制地默默抽泣。上着班的父亲和大姑前后脚赶到,都责怪母亲怎么照顾孩子这么不小心,母亲绷不住又哭了起来,这次哭出了声。针线一次次穿过头皮,特别特别疼,但我知道我不能再哭了。我望着母亲说:“阿妈,别哭,我没事了。”“阿妈,你疼不疼啊?”
回头看,生活总在试探母亲的底线。有次母亲发着烧,她怎么说我我都不听。母亲忽然沉默不语,靠近我,一把抓住我的头发,往厨房水池里那桶洗衣服遗留的肥皂水里摁。肥皂水没有味道,我的鼻腔瞬间被灌满。我呛得直咳嗽,母亲才松了手。我惊恐地望向她,她已转身离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梦到自己被淹没,多年后我问母亲还记得这件事吗,母亲却说忘了。
糟糕的家庭关系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性格。八九岁时我性格特别暴躁、偏执、敏感。有一次我阿叔说了我两句,我就觉得他在针对我,直接坐上他那没上锁的摩托车,踩动油门往他家门上撞。车是没啥事,我的膝盖破了一大块皮。回家后我被父亲要求下跪,还挨了他好几个巴掌。我知道这下玩大了,自觉理亏,不敢说话。还有一次,我表叔在影楼里拍婚纱照,影楼工作人员非让我在门外等着,我以为他就是把我当异类,直接堵在门口,谁来都不让进。后来表叔把父亲喊来,我一边被拉走一边朝着那工作人员臭骂。如今表叔都离婚了,我想来仍然愧疚。
我至今还会不自觉地观察别人投来的眼光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我特别怕理头发,因为小时候理头发时身体总会不由自主地晃动。那个理发先生就会和我母亲轻轻地怨叹一声,那一声到我耳朵里如同水波般炸开,我就晃得更加厉害。长大之后,我宁愿把头发留到流浪汉的长度,也不想去巷子口理发店修剪一下,我太害怕那种被上下打量的目光了,但是从未和谁提起过,所有人都只会告诉你该去剪头发了。从小到大,我最喜欢的季节是冬天,厚大衣、棉裤、棉鞋,加上双手插兜,我的四肢被盖得严严实实。被盖住的还有我的羞耻。
在学校里,我更是唯唯诺诺。上学第一天,母亲就交代我:“在学校受欺负就跟老师说,听到没有?”听到了,但第一个下马威就来自老师。因为作业没写完,我直接被老师喊到讲台上,她拿起竹鞭就往肉多的地方打,我两条小腿上都是伤痕。那个老师还是我小舅的初中同学,下手狠到我都感觉是我小舅以前欺负过她。要在今天,家长铁定得让她被停职甚至开除,但是在那会儿,父母都只会说:“为什么不写完,你这不是活该吗?”
一个老师带“好”头,学生们纷纷效仿。当时班级里都在集干脆面的卡,谁的最全谁就牛气。合理获得的方式是两人拿卡碰碰,谁的卡片朝上就能获得对方那张卡牌。但男生们拿我打趣,说给看一次小鸡鸡就给一张卡,说着手就往我裤头上摸。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交易里的恶意,刚开始还觉得不就是看小鸡鸡,也没啥损失。渐渐地大家开始上手弹,好疼好疼,我说不玩了,他们就开始疯狂地扒拉。后来我才知道那叫作霸凌,对我的霸凌,也是对女同学的霸凌。我谁都没敢说,也不知跟谁说、如何说。其实最早被后桌同学揪耳朵我还会跟母亲说,母亲告诉父亲,依父亲那性格就是火拼,直接带我到学校,等同学一来就疯狂揪着他的耳朵,问他还敢不敢。那同学说着不敢不敢,但父亲走了他就敢了。我觉得很丢脸,从此闭嘴。
我的童年相对孤单,在学校和在家都很沉默,每天说话最多的不是父亲母亲,而是我堂哥带来的老伙计——很多年前从河里抓来的红头龟。老伙计到去世都没有名字。它也不像其他饲料龟,它只吃生肉,还得是肉丝。每次扑通一声被掷到水里,它就立马朝我迎过来。它吃着肉,我说着话,都不耽误。它也不会审视我、教育我、取笑我。再后来我偶然发现它能吃蟑螂,就开始蹲守在厨房徒手抓蟑螂,它的大快朵颐是对我的劳动成果的肯定,而那时的我能得到的肯定并不多。老伙计活了十三年,在高考前一个月离开了我。母亲让我拿到垃圾堆丢掉,我责怪母亲太无情,偷偷把它埋在家门外的盆栽下面。隔了半年,盆栽要扔掉,我又偷偷挖开看看,尸肉基本腐烂了,只留下破碎的龟壳。我把碎片都拾起来,装在一个红包里面,夹进年少时的日记本里。母亲也不是第一次“无情”了,她好像对养宠物有天然的抗拒,我中学时提出想养狗,也被她断然拒绝。有一年冬天,一条土狗跑到我们家门口,坐下来不走,母亲拿着棍子怎么敲打它都不动弹,兴许是外面太冷了。我觉得这就是命运的安排,但母亲不同意,我带着哭腔祈求,让它哪怕待一晚上都好。最后大概被打疼了,它又独自走进冬夜里。它的无助困在了我的身上。
煌和凯,我为数不多的童年玩伴,将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了出来。小学三年级刚分班,“早餐进乡村”工程全面实施,学校会在课间二十分钟发放早餐。我的早餐经常被抢走,有时候会被吃掉,有时候被直接扔掉,我只能从起床挨饿到中午。凯有天实在看不下去,和那些欺负我的同学说:“你们再这样弄他,我就告诉老师去。”大家就没再继续了。不是因为凯的身材有多魁梧,而是因为他阿嬷就是学校的老师。煌在旁边,把他那份给了我。我们仨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看电视,有时我也攒下零用钱带他们去游戏机室玩。四年级读完,我要转学去县城,最留恋的就是他俩了。我们说一定要考上同一所初中、同一所大学,要永远做好朋友,只是后来渐渐都失联了。我很想他们。
跟同龄小孩的家庭条件相比,我对环境不应该有那么多抱怨。在政府大院长大,放学回家就可以看电视,有来自院里各种叔叔阿姨的投喂,每天母亲都会给我买五毛钱一颗的鸡仔胎,还不时能吃到阿公从山上猎来的鸟,但物质上的富足和精神上的苦闷相互映衬,就像开春的回南天,让我郁郁寡欢,时刻在等一个转机。
转机出现在我们举家搬往县城时。彼时房地产行业开始走在风口上,好学区好地段就是好投资。那些大院里的职工纷纷抢占先机,拿出毕生积蓄都要在县城拥有一套房。“今天一套房,明天花不完”这样的广告标语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虽然也没咋押韵。大院里家家户户都陆续搬走了,到最后整栋楼只剩我们这一户,走廊的风都吹得更为萧瑟。母亲也按捺不住,跟父亲商量着也买一套,可以把孩子转到县城更好的小学。父亲起初说啥也不同意,这种不要房租不要水电的公家房住着多舒服,一旁的姑父也帮腔道:“小孩在哪读不都一样,况且转学得花个大几千,这小孩将来有啥出息我把我耳朵割掉。”后来不到半年,父亲同事买的房子价格都开始噌噌上涨,他觉得面子上不能输,重新把买房的议题放到台面上。夫妻俩精打细算,终于在2003年年底花了五万出头买了套两层的二手楼房,后来我们仨在那一住就是十六年。
房子买完之后,母亲开始着手装修,那两个多月是我和父亲单独相处最久的时光。我回到家他已经做好饭菜,吃完之后我就在母亲那台缝纫机上写作业,他在一旁给我削铅笔,削完桌上所有铅笔后,他便阔步骑上他的嘉陵摩托出门去别人家泡茶或者喝酒了。我还是很自律,写完作业打开电视看到他回来,有时早有时晚,只要确保门打开那一刻我在床上就行了。有几个早上他睡过了头,就打电话跟老师说我生病了,去不了学校。那段时间他给母亲打电话都得意道:“我比你会管孩子多了。”是挺会管的,新房装修差不多,母亲也收获了一个成绩飞速下滑、作业潦草甚至换成左手写字的我。
大县城好繁华啊,处处是高楼,每天都有新的事物在冲击着我。我有专属的衣柜,连写作业都有专门的办公桌。家里两间卧房,我和母亲睡大的那间,父亲自己睡小间。父亲仍然在镇政府上班,每天早上会用摩托车载着我上学,完了再去镇里。每天放学出校门,我就可以远远看到父亲那满是粗糙褶皱的面孔。或许因为环境的变化,我们父子俩的关系也缓和了一点。母亲从服装厂下岗也已有两个年头,开始跟着我堂哥的女朋友卖起了保险。她领着我去她上班的地方,一排看过去都是电脑,那时我不敢想象每天玩电脑能有多快乐,若干年后体会到了。有一次她业绩达标,奖励是带我去市里面的游乐园一日游,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游乐园,什么海盗船、旋转木马、摇晃飞椅,所有项目都在冒着幸福的泡泡。
我很喜欢县城的学校,尽管我是插班生,被安排在最后一排,尽管我各科的成绩都数一数二(从后往前数),但这里的同学不会欺负我,甚至根本不理我,我只要安安静静做个角落里的人,就没有人会伤害我。我不是没想过在新环境里交朋友,当时我们班有个智力受损的同学,老师把他安排在讲台旁边,本是出于好意,却让他成为人群中更特殊的一个。据说他父亲是县里的企业家,有头有脸。他上课自己玩,下课被同学玩,无论别人怎么打,他都笑嘻嘻地不还手,直到被打疼了才会猛地一下哭出来。他哭得越大声,别人打得越起劲。打他的人不固定,尤其男孩子,看到有战局就会加入也踹上两脚。他们也招呼我一起玩。头几次我想要迎合,也变成施暴者,但每次“大显身手”时,我就感觉仿佛在欺负自己,我的良心极度不安,之后我便不再参与了。但我也没有去跟老师打小报告。
我上了小学六年级,母亲业务繁忙,对我的功课辅导开始有些吃力了,索性让我自力更生,也不盯着我学习了,就连学校都让我自己踩着单车去。那单车县城里的孩子骑起来如鱼得水,我愣是一蹬脚一个大扑街
 ,练了好久就是学不会,直到母亲说:“你要是能学会,我就带你去厦门。”当天晚上我就会了,神秘大城市的吸引力足以让一个小孩发挥所有的本能。这种小小的满足感后来越来越难有了。自从开始骑单车后,哪怕下雨天没带伞我都得自己骑回家,雨太大就找个旮旯等雨停。
,练了好久就是学不会,直到母亲说:“你要是能学会,我就带你去厦门。”当天晚上我就会了,神秘大城市的吸引力足以让一个小孩发挥所有的本能。这种小小的满足感后来越来越难有了。自从开始骑单车后,哪怕下雨天没带伞我都得自己骑回家,雨太大就找个旮旯等雨停。
一到周末,我第一时间写完作业之后就开始光明正大地看电视,从早上八九点看到下午五六点。母亲要是念叨,我就把写完的作业摆在她面前。在那个年代,作业写完就行,视力交给了课前的眼保健操。当时家里的电视装上了有线机顶盒,从以前的九个频道扩展到三十个频道。我也不看动画片,就爱看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我爱记歌词》《开心100》……一个个轮流看过去。看腻了我就踩着单车去我大舅家,他家天台上装了个“锅”,可以收到宝岛台湾的电视频道。胡瓜和张菲主持的《鲤鱼跃龙门》真的可以把我笑到胃痉挛。十岁出头的年纪,我对娱乐圈已经了如指掌,别人是三五结伴过家家,我是在房间里同时开三五个节目,假装周围有摄影机,假装有大明星在场,这些都是秘密。有次母亲开了我房间的门,我正在拿着根仙女棒对着空气讲八卦新闻。她肯定以为我疯了。
闽南这边一有喜事就会在家门口装上一个巨型的充气人,风机一开,充气人就会随风摇晃,不管怎么摇晃,它都屹立不倒。我人生的前十八年正如充气人一般摇摇晃晃,学着立稳。
如果说来县城的日子是让我人生摇晃得更自在一点,那初中班主任就是那个拿风机的人,她站在我前头说,摇起来啊摇起来。小学毕业我考的成绩不是很理想,只考上了县重点中学的非重点班。入学军训那一周,我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肢体,站军姿时扭来扭去,教官一个回旋踢直接落在我的腚上。当时同学们都在笑,教数学的班主任杨老师就在楼上看着,我心里嘀咕:这下完了,又要自己跟自己玩三年,指不定还要继续被霸凌,报纸上说中学霸凌都是直接动刀子的。我越想越害怕。军训结束后那天下午开班会竞选班长,杨老师说:“今天班长竞选我先提名一个人,他叫张佳鑫,就是军训屡屡被骂的那位,我觉得他能坚持特别不容易。这个班长选上了老师可能也不会让他当,但我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和他交朋友,如果有人欺负他,我们班的人都要保护他。”这番话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哪怕放眼我整个学生生涯都非常令人震撼,有时候一个渺小的人要的并不多,一点点就能超满足。最后我们班男生都投给了我,女生们都投给了另一个女生候选人,又因为女生数量比男生多,所以班长不是我。但是因为那节班会课,我从中学时代伊始就有了朋友。一年后,市里教育改革,把县城三所公立中学合为一体,我们也要重新整合分班,杨老师在我的学生报告手册上这样写道:“风没有方向,不能决定往哪吹,而你就是个追风的男孩,跑到哪里都是对的。”
杨老师给我更多的是勇气,面对生活的勇气。2023年10月,我第一次回老家漳州演出,邀请杨老师来看,杨老师应允了。她的鬓角微白,坐在台下听台上的我娓娓道来,时光瞬间拉回十五年前,她在台上,我在台下,我终于能表达那一声迟到了很多年的“谢谢”。
一个人成长的标志,就是开始想要有清晰的自我认知,比如孩童时不愿意别人动自己的玩具,比如在变声的青春期,我开始拒绝母亲到服装市场给我挑的衣服,又比如初三那年暑假的某天夜晚,我跟母亲说:“我想去市医院看看我的病。”没有由头,就是突然有种自己命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冲动。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正面地向母亲要个答案,因为她当时总拿“你这种情况只要多多锻炼总能好”来敷衍我。母亲大概被我的正经给惊到,脸上表现出丝丝不解和慌张,好在最后她答应了。
从县城到市医院那天是个下雨天,大巴驶过乡镇的土路时,车轮摩擦飞溅出点点泥巴,车身摇摇晃晃,车上烟味和汽油味混合令人作呕。我们挂的是神经科,医生听了情况,面无表情地说:“这小孩是脑瘫吧。”说罢往前握了握我的手,“这种病很难治,你在这里是没办法的,你去上海或北京那种大城市看看吧,不过可以开些药吃着。”短短几句话,讲的人云淡风轻,听的人却入了心。母亲察觉到我的反应有些颓,连忙补充:“但这个如果经常锻炼,是不是也能好,是吧医生?”医生看了眼母亲,再看看我说:“可能吧……十年八年的……哎,门口的,医院里不能抽烟,有没有点公德心。”我一瞥,是门外的父亲,此刻他已丢掉烟头,双手抱胸坐在走廊的长椅上。
出院后雨势更大了,我们在医院旁找了家德克士坐下吃东西等雨停,父亲又点起了一根七匹狼,没过一会儿,餐厅的一个女服务员走过来制止了父亲,父亲显然没有在医院掐得那么爽快,故作威风地问服务员:“哪里有写禁止吸烟啊,我怎么没看到?”“你让我把这根抽完嘛,刚点上。”我见不得父亲的跋扈,加上从医院出来的情绪使然,起身夺下父亲嘴里叼着的烟,扔在地上,用脚猛地踩了几下。父亲怒视着我喊道:“发什么神经!”我也瞪大眼睛看着父亲。母亲出来当和事佬,让我们快吃快吃。我坐下来拿出我的按键手机在QQ空间写道:“医院出来,我感觉天都要塌了。”同学还以为我得了什么绝症,都来关心我。
神奇的是,当我明确了自己的情况难以改变,我却开始学着和自己的身体和谐共处了。我以一种自得的姿态开启了我的高中生涯。每次回老家去姑丈家做客,我总当着他面开玩笑道:“阿丈,你以前说我要是有出息你把你耳朵割掉,你记得吗?”姑丈可能也没想到这事我能记这么久,忙摆摆手,说:“没有的事,你听错了听错了。”母亲面上不说话,一离开就在我耳边说道:“干得漂亮。”整个高中时代我的社交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经常主动认识新朋友,甚至被我班主任叫到了办公室挨批,说我的成绩太差,让我别下课就去找女孩聊天。我现在才意识到他真实的意思可能是“差归差,别去影响别人”。那时候的我可以说非常虚荣,总感觉有很多朋友才能证明我这个人有价值。高二那年母亲同意叫同学来家里过生日时,我高兴坏了,利用课间一层层楼地跑,遇到稍微面熟的就问:“你下周日有空吗,来我家……我生日,你电话多少,我给你发家里地址。”就这样成功地招募到十四个朋友,他们有些根本互相不认识,场面略显尴尬,再怎么热场都没用。第二年生日时我就想着这回谁也不告诉,看看那十几个人有没有人记得,结果一个都没有,连母亲都是我说了她才想起来。那时候别提多失落了,现在想想真有趣。
当然有时候敏感脆弱玻璃心还是会反复横跳。高中文理分班后我的班主任教英语,有次她在教“disabled”(残疾的)这个单词时,当着全班的面拿我举例子:“像我们班的佳鑫就是disabled。”那句话铁锤般重重敲在我自认为足够坚强的心灵上,我起身离开教室去操场大哭了一场,暗暗发誓再也不上英语课。第二天班主任约我聊聊,我以为她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都准备好接受她的道歉,没想到她说了句:“你身体有缺陷这件事,纸是包不住火的。”“纸是包不住火的”这句话当时给了我二次暴击,我写了封信给学校教务处,要求老师道歉,但不了了之。多年后,我站在舞台上重新咀嚼这句话时,才悟到或许它是个人生真谛,有些事情藏着掖着,总是躲不过的。
文理分科时我毅然决然选了文科,因为觉得自己记东西快,周围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语文都不及格了,政史地要写的题不得要了你的命。其实总体来说我成绩还可以,高三模考成绩一直在二本线上,但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卷子是自己学校老师改的,大家都是耐心地从准确性入手,而高考改卷的人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我的卷子和千千万万卷子一样被一扫而过,我也从二本线被扫到了专科线。现在我每次和朋友提起这件事,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发出提问:“你不是应该有什么特殊政策之类的吗?”当然有,刚上高三那会儿,班主任就问我要不要申请,申请成功的话可以延长考试时间,我没有犹豫地回答,不太需要。我脑海里的画面就是所有人离开考场时,我继续留下来答卷,那局面该有多狼狈,他们出了考场就不是先对答案了,而是议论我。现在回头想想,肠子都悔青了,年长的自己总要为年少的自己买单。
高考那两天,父亲骑着摩托车载我去考场,我坐在车后座,他的背影小小的、颓颓的,我们父子俩早已不那么针锋相对,更多时候只是相视无言。车到考场门口,我往里走,父亲突然喊住我:“东西带全了吧?好好,尽力加油就好,接下来的路要你自己走了。”他的眼神透着过往十八年里我未曾见过的柔软,我有些不知所措,示意他快回去吧。
高考结束后,我和表弟去市区的一家包装厂打工,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直面社会。厂子很大,但是舆论环境却很逼仄。刚入职第二天,厂里面的人看到我笨拙地装箱,都要议论一番,当着我的面问表弟:“你哥是不是脑子有问题?”表弟看我表情尴尬,回击道:“我哥正常得很,他们家在厦门有三套房呢。”不说不知道,说完大家更认为我是那种有钱人家的“二傻子”了。和我同小组的那个大婶一直在工作,没有参与其中,本来犹存些温暖,直到快下班时她突然拿出两枚五毛钱的硬币,说道:“我考考你聪不聪明,你说这两个加起来是多少钱?”我天天给母亲打电话想回家,母亲说:“你忍一忍,等隔两天有新人来,你的风头就过了。”母亲深谙这个道理,果然没过两天,大家就开始讨论起机械组的某某跟某某的婚外情。在厂里的两个多月我没有赚到多少钱,但让我对成年之后的生活有了基本的认知。高考成绩出来,母亲问我要不要复读,我想了想拒绝了,重来挺难的,不管是高考还是人生。
我的成长跌跌撞撞,普普通通,甚至有些细碎,像是六七月台风天过后,空气中弥漫的霉味,不难闻但涩涩的。闽南语常把长大称作“大汉”,和普通话的“成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人只有远行离家、奔赴远方,回头看双亲时,才开始成为一个立体的人,一个男子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