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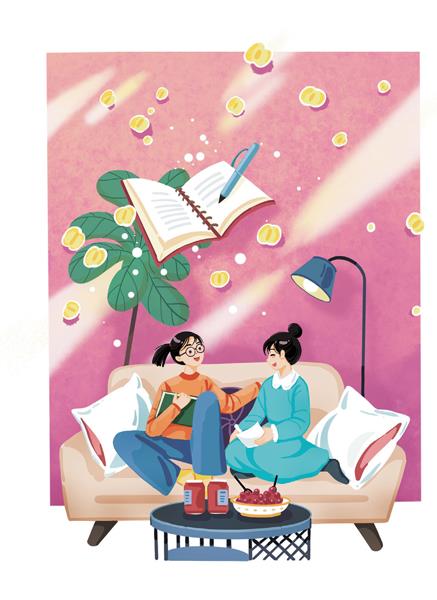
乌鲁木齐的初夏总比秋天更枯黄。
那天,走在通往初中教学楼的路上,燥热的风卷着一树树成熟的榆钱纷飞而下,漫天金色,宛如午后太阳为旧时光落下的眼泪。
许久未见的初中政治老师拈去我发梢上的榆钱,笑着收下我“二模”全市第八的消息,然后问:“李宇洁怎么样?”我愣了愣,告诉老师她“二模”是全市前五十。
老师说,她觉得我情绪很稳定,而李宇洁似乎常有情绪起伏。“她太有自己的想法了,个性也太强——这时候需要没有杂念,还有23天就要高考了!”
我回道:“她一直都是那样的呀。”
但仔细回想,四五年前情绪更稳定的明明是她呀。原来时光荏苒,真的会物是人非。
初一的某个傍晚,我因听写没过,被教英语的宋老师留下背单词。宋老师还是初一(3)班的班主任、教研室主任,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我只好守在3班门口,百无聊赖地看着浓黑的天。
就在这时,李宇洁走了过来。她扎着松散的短马尾,戴着黑框眼镜,镜片后沉静的目光中有温和的笑意。已经不记得我们是如何打招呼的了,但听到她的名字,我觉得有些耳熟,便问:“你是上次期中考试的年级第三吗?”
她点点头:“比你低了5分。”
那是升初中后的第一次期中考试,考7门,每门100分。我考了672.5分,她考了667.5分——这两个分数,我至今都记得。
我们互留了QQ号,回家后就加上了好友。13岁的年纪,交朋友总是轻易又快乐。我们聊诗歌,聊科幻小说,聊学校的晚霞和白杨。不记得是谁先说了“拜拜”,但后来翻看那长串的聊天记录时,我想起一个词,叫“倾盖如故”。
我们成了挚友。我活泼、张扬、炽热又坦率,她温和、镇静、幽默又宽和。她渊博的学识之下藏着睿智和冷峻,而我炽热的表达里尽是敏感与天真。
我们像两块不规则却又严丝合缝的拼图一样契合。她正如我梦寐以求的知音一般,美好得有些不真实。
那是我迄今为止最美好的时光。
自童年起,我一直享受着,也忍受着一种深切的孤独。幼年时和院子里的小伙伴捉迷藏,我被遗忘在草丛中;小学当班长,我在质疑声中恪守着那时被我奉为圭臬的准则;初中我依然做班长,在不尽然友好的目光中坚持着所谓的“以身作则”。
而孤独,不止这些。从“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中隐约感到的痛苦,从科幻小说字里行间触摸到的温情,从刚刚开始的人生里尝到的真切的酸涩——那些无人可以诉说的生命瞬间,积攒着沉甸甸的寂寞。
直到她恰如其分地走进我的青春。
我们畅聊各自倾慕的诗人,也分享彼此都犯过的错;我们一起去书店读书,席地而坐,偶然抬头相视一笑;我们一起去看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隔着一个座位牵着手,哭成两个泪人,偏偏谁也没带纸巾……
那天看电影,其实是为了庆祝我的14岁生日。她送的礼物是半部手抄的《飞鸟集》。我们在她家吃过午饭后,窝在沙发上看一档有点吓人的综艺节目,她修长的手臂搭在我的肩上,我昏昏欲睡。
23天后是她的生日,我准备的礼物里有一个笔记本,里面写满了100天的碎碎念和从各处摘抄的美丽诗句。
后来她告诉我,她笑着翻过了每一页。
我们常给彼此写小作文。她写道,“你像站在黎明和永夜交点的人,伸出手企图触碰光明,却害怕被光明灼伤”;我回她,“你是我的启明星,引我到一片光辉灿烂的黎明”。
还有互相鼓励的“凡是过往,皆为序章”,还有我努力学来唱给她听的《送你一朵小红花》……还有她不顾我的班主任苛责的眼神,在我放声大哭时将我搂进怀中时身上的温度。
那时我以为,我们的友谊一定地久天长。
可她从来不是我幻想中的模样——这不怪她,她是具体的、真实的她自己,而非我心中投射的幻象。是我该学着剪掉我梦中的虚影,去触碰真实的她。
只是这个道理太深刻。那个14岁幼稚、尖锐又鲁莽的夏一丹不理解,只好由18岁长大了一点、温和了一点且谨慎了一点的夏一丹吞下苦果。
不仅如此。我们对待这段友情的态度也始终不同——我总是格外投入和热烈,而她始终保持着冷静和克制。还有很多习惯上的细微差异:我守时而她随性;我想和她独处,她却喜欢带上更多朋友;我想和她合影留念,她却总说不喜欢拍照……
这一切细微的矛盾在一场争执中被推至顶点。我希望她亲笔给我写一封回信,她之前答应了,却迟迟没有动笔。在我三番五次询问之后,她发了一条说说:“我本以为数次彻夜长谈足以抵过一封薄薄的信。”
我生气了,质问她:“你应该当初就拒绝我,为什么答应了又毁约,还要说我不好?”她道了歉,我说“就到此为止吧”。她问:“什么东西到此为止,是这件事还是我们的关系?”我回道:“这件事。”
但感情上的裂痕已生,分崩离析只是时间问题。直到有一天,她提议终止这场名存实亡的友谊,我爽快地答应下来,像个赌气的孩子。
为这一次的爽快,我品尝着缓慢的凌迟——在她和她的新朋友谈笑嬉闹时,在老师不经意提起她时,在她托人送我一沓写着“人生海海”的书签作为我15岁生日的礼物时,我都感到一种钝痛从心底向全身蔓延。
就这样,我在孤独和压抑中,度过了黯淡的初三时光。
在初升高预科班,我和她有过一段回光返照般的时光。我们偶尔交谈,一起活动,不时对视。击剑课上,她帮我穿剑衣,神色温和而专注。那天我穿着薄底休闲鞋,在剑道上踉跄了一下,她下意识地问“没事吧”,语气中带着久违却熟悉的关切。我站稳后仓皇摇头,她才举起剑来。
其实我的脚扭到了,只是当时没有发作,之后几天才隐隐作痛。一如我和她之间的这场分离,看似潇洒,实则化作我生命中漫长的潮湿。
中考成绩出来后,都没考好的我们,又分享了“深恩负尽”的苦涩。
而后,我们渐行渐远,最终形同陌路。
我的高中生活乏善可陈。我因为讨厌物理逃一般地选了文科,又因为脑子一热做了学生工作,甚至结交了一些并不真正契合的朋友。
选择文科后,我常因外界的声音而苦闷。我和她仍坐在一间教室里,我会在转身时望向她伏案的身影。我坚定地相信她的选择,并以此作为自证正确的、稀薄的慰藉。就像我在和我那些“朋友”争吵后怀疑自己时,想起我和她曾经的对话。
那次我问她:“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她回道:“热烈真诚,世所罕见。”
如今高考成绩已出,一切尘埃落定。我有幸被北京大学录取,将步入燕园研读我热爱的中文系。她也如愿考上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专业。
于我而言,我们之间或许称得上“故事鲜艳而缘分太浅”。那段短暂的友谊是我生命中绚烂的焰火,照耀着我理想主义的那部分。
“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书中这么说。
但是没关系。
榆钱早已落尽。
翠绿的盛夏永远等着我们呢。

(本刊原创稿件,豆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