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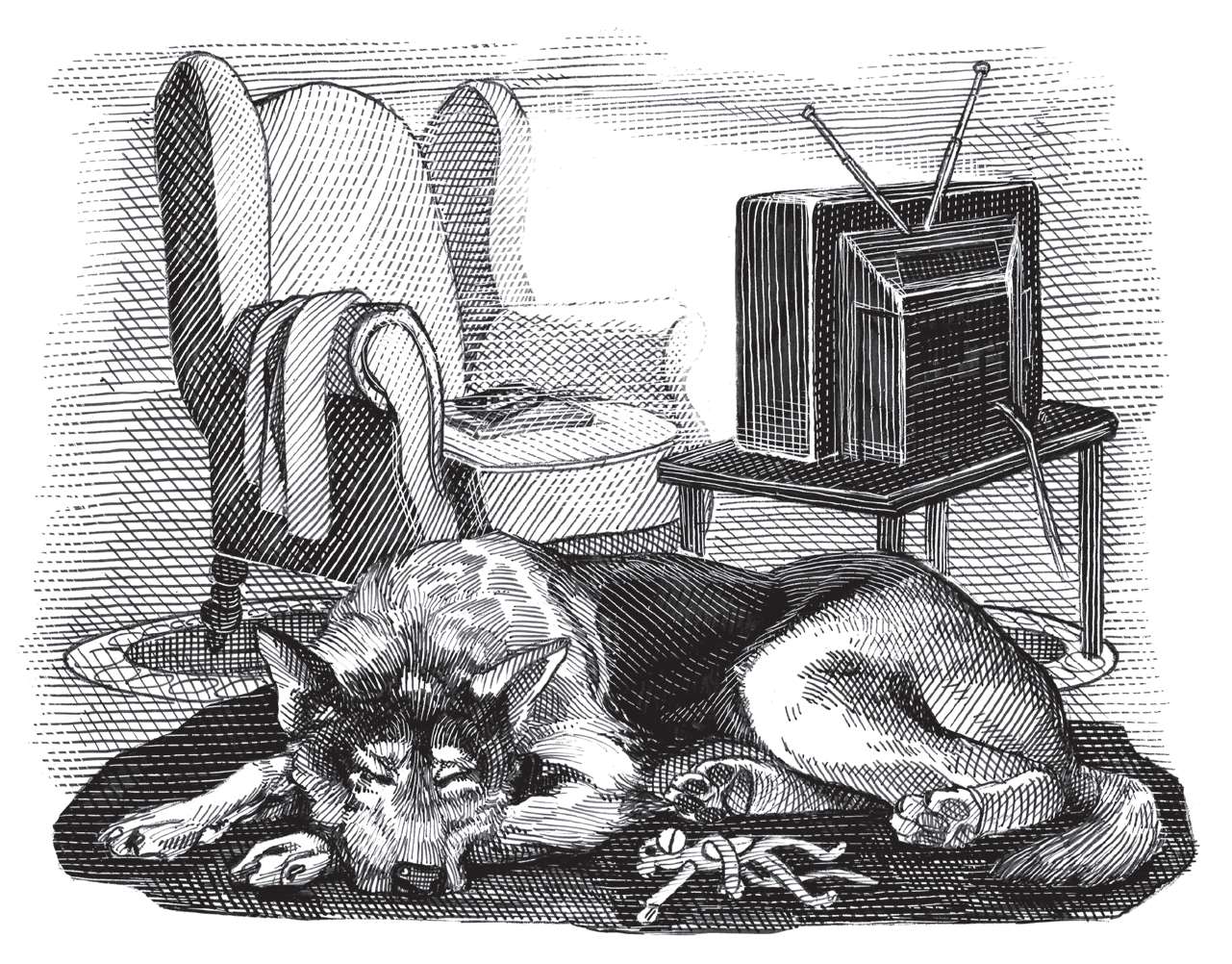
刚开始,我每周用海绵给鲍迪奇擦三次身,因为楼下的小卫生间里没有淋浴。他接受我的帮助,但坚持自己洗私处(我当然没问题)。我帮他擦洗瘦弱的胸部和更瘦弱的背部,有一次他在缓慢地走向小卫生间的途中出了一次不幸的意外,我还帮他擦洗了瘦弱的臀部。那次他说脏话既是因为尴尬(难堪的那种尴尬),也是因为生气。
等他重新穿上睡裤,我说:“别在意。我在后院给雷达捡了不知道多少次屎了。”
他又用他标志性的“你是不是天生这么傻”的眼神看我:“那是不一样的。雷达是狗,要是你不管,她会在埃菲尔铁塔前面的草坪上拉屎。”
我觉得有点好笑:“埃菲尔铁塔前面真有草坪吗?”
现在轮到他标志性的翻白眼了:“我怎么知道?我只是在举例子。能给我一个可乐吗?”
“没问题。”自从老爸带来那六听可乐之后,鲍迪奇先生家里的可乐就没断过货。
我拿着可乐回来,发现他已经从床上起来,坐在他喜欢的那把安乐椅上,雷达蹲在他身旁。“查理,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为我做的这一切——”
“你每周会给我一张非常好看的支票,我真的很感激,但我总是觉得我做得不够多,配不上你给我的薪水。”
“就算免费你也愿意。我在医院里的时候听你说过,我相信你说的是真话。所以为什么呢?你是想争取成为圣徒,还是在为某些事情赎罪?”
这是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我想到我的祈祷(我和上帝的交易),但我也想到了打电话到史蒂文斯小学谎称有炸弹。伯蒂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玩的恶作剧,但那天晚上我听着醉鬼老爸在隔壁房间打鼾,我却只想到了我们吓得很多人魂不附体,其中大部分是小孩。
与此同时,鲍迪奇先生一直在专注地看着我。“赎罪,”他说,“为了什么呢?”
“你给了我一份好工作,”我说,“我很感谢你。我喜欢你,哪怕是你发脾气的时候,尽管我承认那些时候不太容易喜欢你。除此之外的一切,你就当它是桥下的流水吧。”
他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话。也许因为我妈死在桥上时我就是史蒂文斯小学的学生,也许只是因为这句话对我来说很重要——直到今天也依然重要。
“时间是流水,查理。生命只是它流过的那座桥。”
时间一天天过去。做理疗的时候,鲍迪奇先生依然骂骂咧咧,偶尔惨叫,吓得雷达坐立不安,后来梅利莎不得不在理疗开始前把雷达请到院子里去。弯曲膝盖依然很疼,疼得厉害,不过到了五月,鲍迪奇先生能弯到十八度了,而六月就快到五十度了。梅利莎开始教他怎么拄着拐杖上楼(更重要的是如何不在下楼时酿成惨剧),于是我只好把奥施康定药瓶转移到了三楼。我把药藏在一个积灰的旧鸟舍里,鸟舍顶上蹲着一只木雕乌鸦,我每次看见都会起鸡皮疙瘩。鲍迪奇先生发现拄着拐杖行动更自如了,于是开始自己用海绵擦身(他称之为“婊子澡”)。我再也没得到机会帮他擦屁股,因为他再也没在去厕所的路上出过意外。我们在我的电脑上看老电影,从《西区故事》到《满洲候选人》(我和他都很喜欢)看了个够。鲍迪奇先生说要买一台新电视,我觉得这无疑是他想重新参与生活的证据。然而等我说完有了新电视就必须接入有线电视或安装卫星天线,他就改变了主意(看来参与的程度还很有限)。我每天早上六点来一趟,由于不练棒球也不打比赛了(哈克尼斯教练每次在走廊里碰到我都会恶狠狠地瞪我),大多数时候我每天下午三点就会回到梧桐街1号。我做各种家务事,以打扫卫生为主——我并不介意。二楼和三楼真他妈脏,尤其是三楼。我建议清理一下檐沟,鲍迪奇先生瞪着我,眼神就像在说我是不是疯了,他叫我去雇人来干活。于是我请来了哨兵住宅维修公司,等檐沟清理到鲍迪奇先生满意的地步(他站在后门廊上看他们干活,他拄着拐杖,探出身子,包着固定器的睡裤随风翻飞),他叫我请他们维修屋顶。鲍迪奇先生看了一眼他们的估价单,命令我去和他们讨价还价(“打穷苦老人牌”)。我和他们讲价,让他们打了八折。住宅维修公司的人还给前门廊安装了无障碍坡道(鲍迪奇先生和雷达都从来不用,雷达见到它就害怕)。从铁门到前门廊的小径石板高低不平,歪七扭八,他们说也可以帮忙重铺,但我拒绝了,自己动手解决问题。我还更换了前后门廊翘曲和劈裂的台阶(在YouTube的DIY视频帮助下)。那年的春夏就像梧桐街山顶的清理-修复季。这给了里奇兰夫人很多热闹看,她也确实看得很开心。七月初,鲍迪奇先生去医院拆除固定架,比梅利莎最乐观的估计还早了几个月。她对鲍迪奇先生说她为他感到非常骄傲,紧紧地拥抱他,老先生难得一次地没词儿了。我爸每周日下午来做客(应鲍迪奇先生的邀请,我没有提示过他),我们三个玩金拉米纸牌游戏,鲍迪奇先生几乎每把都赢。非周末的其他日子,我先给他做饭,然后下山和老爸一起吃饭,再回鲍迪奇家洗他屈指可数的碗,遛雷达,和他一起看电影。有时候我们吃爆米花。拆掉固定架之后,我不再需要做骨针护理,但必须给以前穿骨针的伤口消毒,让它们尽快愈合。我用红色的宽橡皮带帮他练习踝部,逼着他练习弯曲双腿。
这几周过得很快乐,至少大多数时候很快乐。当然也不是一切都好。雷达散步的距离越来越短了,她经常走不了多远就开始瘸,然后转身往回走。她上门廊台阶的动作越来越艰难。有一次鲍迪奇先生看见我抱她上台阶,叫我别这么做:“等她没法自己上台阶再说。”鲍迪奇先生撒尿所用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候他上过卫生间,我会在马桶边缘看见星星点点的血迹。
有一次我在卫生间门外听见他说:“快点,没用的东西,快给我尿出来。”
无论利普卓应该有什么样的效果,事实上都不怎么好。我尝试过和他谈这件事,问他为什么费了这么大的力气重新站起来,却放任“他真正的问题”(我的委婉说法)自由生长,他叫我别多管闲事。最后要了他的命的也确实不是癌症,而是心脏病发作。不过这么说也不确切。
真正的原因是该死的棚屋。
有一次(我记得是六月),我再次提起黄金的话题,但我拐了个弯。我问鲍迪奇先生担不担心那个瘸腿的德国矮胖子,尤其是我为鲍迪奇先生支付医疗费做了一笔巨额交易之后。
“他不会害我的。他在里屋做过数不清的生意,据我所知,他从没引起过执法机构的注意,也没惹上我觉得更有可能找他麻烦的美国国税局。”
“你不担心他告诉别人吗?我是说,也许他确实帮盗贼之类的人销赃,处理烫手的钻石,对此他肯定会保持沉默。但要我说的话,六磅金豆就完全是另一个层次的事情了。”
他嗤之以鼻:“拿他和我做交易的可观利润冒险?那可就太蠢了,威利·海因里希有很多缺点,但他肯定不蠢。”
我们在厨房里,用高脚杯喝可乐(加了屋子靠松树街一侧院子里长的薄荷叶)。鲍迪奇先生从桌子对面用狡黠的眼神打量我:“我看你想说的其实不是海因里希。我猜你一直在想那些黄金和它们的来路。”
我没有回答,但他没说错。
“告诉我,查理,你是不是偶尔会去楼上?”他指了指天花板,“看黄金?或者更确切地说,欣赏黄金?你去过,对吧?”
我的脸红了:“呃……”
“我担心,我不会责备你。对我来说,那仅仅是一桶金属,和螺母螺钉没什么区别,我毕竟老了。然而这不等于我不明白它的魔力。告诉我,你有没有把手插到桶里去过?”
我想撒谎,但觉得没这个必要,他肯定已经猜到了。“有过。”
他依然狡黠地看着我,眯着左眼,挑起右边的浓眉,但同时他也在微笑。“把双手插进桶里,让金豆流过指缝?”
“对。”我的脸烧得发烫。我不只是第一次拿黄金的时候这么做过,后来还偷偷地做过好几次。
“黄金的魔力不只在于值多少钱。你知道的,对吧?”
“对。”
“只是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假设海因里希从他的店里出来,走进同一条街上的那家恶心的小酒吧,然后灌了一肚子酒,把不该说的话全告诉了一个居心叵测的陌生人。我敢用这座屋子和它底下的地皮打赌,老瘸子威利这辈子都没喝多过,甚至很可能滴酒不沾,但我们就这么假设好了。假设听他说话的那个人——也许一个人,也许还有同伙——某天夜里等你离开,然后闯进我家,命令我交出金子。我的枪在楼上。至于我的狗,它曾经是条猛犬……”他摸了摸在身旁打盹儿的雷达,“现在比我还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我会怎么做?”
“我觉得……你会把金子给他们?”
“正是如此。我不会祝他们好运,但我会给他们的。”
于是我不得不问了:“霍华德,你的黄金是从哪里来的?”
“以后我也许会告诉你。我还没有下定决心。因为黄金拥有的不只是魔力,它也会带来危险。另外,它是从一个危险的地方来的。我好像在冰箱里看见了羊排。家里有菜丝沙拉吗?蒂勒的菜丝沙拉做得非常好。你应该吃一点。”
换言之,谈话结束。
七月末的一个晚上,我和雷达去松树街散步回来,雷达爬不上后门廊的台阶了。她试了两次,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喘着气看我。
“算了,把她抱上来吧,”鲍迪奇先生说。他出来迎接我们,只拄着一根拐杖,另一根已经差不多退休了。我抬头看他,想确定他是不是说真的。他点点头,“到时候了。”
我去抱雷达,她气呼呼地叫了两声,朝我龇出牙齿。我把一条胳膊向后移动,托住她的腰腿部,尽量远离疼痛的位置,然后把她抱了起来。我没费什么力气。雷达瘦了,鼻子几乎全白了,眼睛总在分泌黏液。我把她轻轻地放在厨房的地上,刚开始她的后腿甚至撑不住体重。她咬牙坚持(我能看见她在用力),一瘸一拐地走向食品室门口她睡觉的那块地毯,她走得很慢,最后几乎瘫倒在地毯上,发出一声疲惫的叹息。
“她需要去看兽医。”
鲍迪奇先生摇摇头。“她会害怕的。没有任何意义,我才不会让她去白受罪呢。”
“但是——”
他重新开口,音调非常轻柔,我吓了一跳,因为这非常不像他:“任何兽医都帮不了她。雷达的时候快到了。现在她需要的只是休息,而我需要思考。”
“我的天,思考什么!”
“思考怎么做才是最好的。你该回家了。吃你的晚饭。今晚别来了。我们明早再见吧。”
“你的晚饭怎么办?”
“我吃沙丁鱼和苏打饼干。好了,去吧。”然后他重复道,“我需要思考。”
我回到家里,但没怎么吃东西。我没胃口。
从那天以后,雷达再也没有吃完过早饭和晚饭,尽管她还能自己下台阶,但上台阶都要靠我抱了,而且她偶尔会在家里大小便。我知道鲍迪奇先生说得对,任何兽医都帮不了她……除了最后送她一程,因为她显然很痛苦。她大多数时候在睡觉,有时候会朝着自己的后腿怒吼,甚至会上嘴咬,仿佛想赶走正在伤害她的隐形怪物。现在我需要照顾两个病患了,一个在好转,另一个在恶化。
八月五日,周一,我收到了蒙哥马利教练的电子邮件,其中列出了橄榄球训练的日程安排。在回复前,我先把我的打算告诉了我爸:最后一年我决定不打球了。我爸显然很失望(我本人也很失望),但他说他能理解。前天他去过鲍迪奇家打金拉米纸牌,看到了雷达的状况。
“那里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呢,”我说,“我想收拾一下三楼的破烂。另外等我觉得可以让霍华德去地下室了,还有一整个拼图等着他去完成。我觉得他已经完全忘掉了。哦,我还要教他使用我的笔记本电脑,他可以上网,还可以看电影,还有——”
“够了,小土豆。其实是因为狗,对吧?”
我想到抱着她上后门廊的台阶,想到她在家里大小便后的羞愧表情,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我小时候养过一条可卡,”老爸说,“她叫潘妮。眼看着一条活泼的狗变老,确实会让人很难接受。尤其是到最后的时候……”他摇摇头,“感觉就像撕心裂肺。”
就是这样。我就是这个感觉。
听说我打算在最后一年退出球队,生气的不是老爸,而是鲍迪奇先生。他气得暴跳如雷。
“你疯了吗?”他几乎在吼叫,布满皱纹的面颊涨得通红,“我是说你他妈是脑子进水了吗?你是球队里的明星!你可以进大学校队,也许能拿到奖学金!”
“你又没看过我打球。”
“《太阳周报》虽然狗屁不是,但我还是会读他们的运动版。去年该死的火鸡碗能赢,靠的就是你!”
“那场比赛我们打出四个达阵。只有最后一个是我打出来的。”
他降低嗓门:“我会去看你的比赛的。”
我震惊得一时间说不出话来。这个人哪怕在受伤前也主动闭门不出,现在说出这样的提议,简直像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我上不上场你都可以去,”我最后说,“我陪你去。你买热狗,我买可乐。”
“不。不。我是你的老板,真该死,我付你工资,我说不行。这是你高中最后一年的橄榄球赛季,你不能因为我而缺席。”
我也是有脾气的,尽管我从没让他见过我的这一面。但那天我生气了。说是暴怒也未尝不可。
“和你没关系,不是每件事都和你有关系!她怎么办?”我指着雷达说,雷达抬起脑袋,不安地呜呜叫,“你能抱着她上下台阶,让她在后院拉屎撒尿吗?你自己走路都还很困难!”
他好像被我吓住了。“我……她可以在屋里解决……我把纸铺在地上……”
“她不喜欢这样,你知道的。也许她只是一条狗,但她也有她的尊严。这也许是她的最后一个夏天,最后一个秋天……”我能感觉到眼泪快要夺眶而出了,除非你从没养过狗,从没爱过狗,否则你就不会认为我的反应很荒唐,“……我不希望她去世的时候我正在训练场上扑该死的假人!我会去上学,学是不能不上的,但剩下的时间我都想在这里陪她。你要是还不满意,那就解雇我好了。”
他一言不发,双手握在一起。等他再次抬头看我,他的嘴唇抿得只剩下了一条几乎不存在的缝,有一个瞬间,我以为他会真的解雇我。过了一会儿,他说:“假如我出的钱足够多,你觉得会有兽医愿意上门吗?而且假装不知道我的狗没登记过?”
我长出一口气:“让我去问问看吧。”
我找到的不是有照的兽医,而是一名兽医助理。她是单亲母亲,有三个孩子,安迪·陈认识她,介绍她和我认识。她来检查了雷达的情况,给了鲍迪奇先生一些药,她说这是实验性药物,但比卡洛芬好得多。药效更强。
“我们先把话说清楚,”她对我们说,“药能提升她的生活品质,但很可能会缩短她的寿命。”她犹豫了一下,“不,肯定会缩短。你们别等她死了来找我,说我没告诉过你们。”
“有效的时间能有多长?”我问。
“未必一定有效。我说过了,只是实验性的。我手上的药是皮特里医生做完临床试验后剩下来的。补充一句,他参加临床试验,药厂给了他不少钱,但我一分钱都没见到。要是真的有效,你们的雷达也许能度过很有品质的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三个月就很难了。她不会变得像小狗那么充满活力,但肯定比现在强。然后有一天……”她耸耸肩,蹲下,撸了几下雷达皮包骨头的身体,雷达甩了甩尾巴,“总有一天,她会走的。要是她能活到万圣节,我会非常惊讶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鲍迪奇先生知道,再说雷达是他的狗:“足够好了。”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话,我当时不明白,但现在明白了,“也足够久了。应该。”
她离开后(带着两百块钱),鲍迪奇先生弯下腰,爱抚他的狗。等他重新抬起头看着我,他脸上多了一丝坏笑:“警察不会因为买卖非法狗药逮捕我们吧?”
“应该不会,”我说,但万一有人发现了他的黄金,引来的麻烦恐怕会大得多,“还好你做了决定。换了是我,肯定没法下定决心。”
“霍布森选择
 。”他还在爱抚雷达,手从脖子慢慢地撸到尾巴,“说到底,与没有品质可言的半年相比,我觉得高品质的一两个月显然更好。当然了,前提是药真的管用。”
。”他还在爱抚雷达,手从脖子慢慢地撸到尾巴,“说到底,与没有品质可言的半年相比,我觉得高品质的一两个月显然更好。当然了,前提是药真的管用。”
药确实很管用。雷达又开始能吃完饭了,也恢复了上下门廊台阶的能力(有时候需要我帮个小忙)。尤其好的是,她晚上又能玩几轮游戏了——追猴子,把玩具咬得叽嘎响。但是,我仍旧认为她会走在鲍迪奇先生的前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是诗人和音乐家口中所谓的“休止”。雷达持续……怎么说呢,我不会说这是好转,但她越来越像鲍迪奇先生从梯子上摔下来那天我遇到的那条狗了(尽管每天早晨,她还是必须挣扎一阵才能爬起来,缓慢地走向她吃饭的盘子)。鲍迪奇先生确实在好转。他减少了奥施康定的用量,把自从八月就在使用的单拐换成了他在地下室角落里找到的手杖。说到地下室,他又开始拼他的拼图了。我去上学,花时间陪老爸,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梧桐街1号上。豪猪队的赛季首战打了个零比三,我以前的队友再也不理我了。这固然让人不开心,但我脑子里的事情太多,才不会被这种事打倒呢。对了,我又打开过几次保险箱(通常总是趁鲍迪奇先生在沙发床上打瞌睡的时候,为了多陪陪雷达,他现在依然睡在楼下),把双手插进那一桶黄金,感受它每次都会使我惊讶的重量,让金豆像小溪似的从我指缝间流过。我每次都会想到鲍迪奇先生说的黄金的魔力,甚至可以说我在黄金的触感中冥想。梅利莎·威尔科克斯现在每周只来两次,她对鲍迪奇先生的恢复啧啧称奇。她说肿瘤科的帕特森医生想见他,鲍迪奇先生拒绝了,说他感觉挺好。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不但因为我信任他,更是因为我想相信。现在我知道了,会拒绝承认现实的不仅是患者本人。
一段平静的时光。休止。然后所有事情几乎同时发生,而且没有一件是好事。
吃午饭前我有一段空闲时间,我通常会去图书馆做作业或读一本鲍迪奇先生家的地摊小说。九月末的那一天,我沉浸在《这个游戏叫死亡》的世界里,这本书血腥得非常带劲,作者名叫丹·J. 马洛。十一点四十五分,我决定把高潮留给晚上不受限制的阅读时间,随手抓起一份报纸。图书馆里有电脑,但报纸的网络版都需要付费。另外,我喜欢拿着真正的报纸看新闻,这会带来一种迷人的复古的感觉。
假如我拿的是《纽约时报》或《芝加哥论坛报》,那我就会和这篇报道失之交臂了,然而放在报纸堆最上面的是《埃尔金每日先驱报》,因此我拿起来的正是这份报纸。头版头条的大新闻是关于奥巴马决定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和华盛顿特区造成十三人死亡的大规模枪击案。我匆匆扫了一眼,抬头看看时间(离吃午饭还有十分钟),然后开始往后翻,寻找漫画版。但我并没有能够翻到那么后面的地方,第二版本地新闻的一篇报道让我停下了。更确切地说,让我愣住了。
斯坦顿维尔珠宝商死于谋杀
昨天深夜,斯坦顿维尔的一名长期居民兼商人被发现横尸于其经营的卓越珠宝行内。报警者称店门开着,但挂着“打烊”的牌子。詹姆斯·科齐温克尔警员前去调查,珠宝行里屋的门也开着,而威廉·海因里希死在房间里。在被问及犯罪动机是不是抢劫时,斯坦顿维尔警察局局长威廉·亚德利称:“尽管警方还在调查,但看起来,动机无疑就是抢劫。”在被问及有没有人听见扭打或枪击的声音时,亚德利局长和伊利诺伊州警察局的伊斯雷尔·布彻警探都表示无可奉告,只说自从镇外的购物中心开业后,斯坦顿维尔主街西端的大多数店铺都处于空置状态,而卓越珠宝行是个众所周知的例外。亚德利和布彻都承诺会“迅速解决此案”。
午餐铃声响了,但我坐在图书馆里没动地方。我打电话给鲍迪奇先生,他的开场白和平时一样:“假如你是电话推销员,请从你的名单里删掉我。”
“是我,霍华德。海因里希先生被杀了。”
好一阵沉默,然后:“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看看四周。图书馆里禁止饮食,这会儿只有我一个人,于是我把报道念给他听。文章很短,没多久就念完了。
等我念完,鲍迪奇先生说:“该死,现在我该去找谁兑换黄金呢?我找他帮忙已经快二十五年了。”听不出任何同情,甚至没有惊讶,至少我能听出来。
“我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
“当心!注意保密!”
“那是当然,我会尽可能谨慎的,但我认为这不是重点。你和他做了一笔大交易,甚至称得上巨大,然后他突然死了。要是有人从他嘴里问到了你的名字……要是他受到拷打,或者对方保证只要他老实交代,就会饶他一命……”
“查理,我那些老地摊小说你看得太多了。你是去年四月替我兑换六磅黄金的。”
“是去年四月,又不是中世纪。”我说。
他没有理睬我:“我不喜欢责怪受害者,但他就是不肯离开那个破烂小镇和他的破烂商店。摔断腿之前四个月,我最后一次和他当面交易,那次我说:‘威利啊,你再不关店搬到购物中心去,迟早会被人抢劫。’现在终于有人动手了,顺便取走了他的老命。简单的解释往往更正确。”
“但要是你把枪拿到楼下来,我还是会感觉安全一点。”
“要是能让你感觉安全一点,那我就拿下来吧。放学后过来吗?”
“不,我打算去一趟斯坦顿维尔,看看能不能搞点白粉。”
“年轻人的幽默感总是太粗俗,很少会好笑。”鲍迪奇先生说,挂了电话。
我赶到食堂的时候,买饭的队伍已经排了一英里,等排到我,今天供应的热餐多半已经凉了。不过我无所谓。我脑子里只有黄金。鲍迪奇先生说在他那个年代,那不过是一桶金属。也许确实如此,但我觉得他不是在撒谎就是在诡辩。
不然他为什么存着那么多黄金呢?
那天是周三。我付了《埃尔金每日先驱报》的订阅费,这样我就可以在手机上看新闻了。周五,他们又刊出一篇报道,这次登在本地新闻的头版上:斯坦顿维尔的一名男子因珠宝店抢劫杀人案被捕。被捕的人名叫本杰明·德怀尔,现年四十四岁,无固定住所(我猜这就是无家可归的意思)。报警的是斯坦顿维尔典当与借贷行,因为德怀尔企图典当一枚“价值可观”的钻石戒指。来到警察局后,警察还在他身上发现了一只镶翡翠的手镯。一个无固定住所的人持有这些珠宝,警方自然有理由认为他非常可疑。
我给鲍迪奇先生看这篇报道,他说:“你看,我没说错吧?一个蠢货做了蠢事,企图用更蠢的方法把贼赃换成现金,结果被警察抓住了。写成悬疑小说都让人看不下去,你说呢?就算是地摊读物也不能这么糊弄人。”
“我看也是。”
“你似乎有心事。”我们在厨房里看雷达吃晚饭,“喝个可乐也许能治好你。”他起身走向冰箱,几乎一点也不瘸了。
我接过可乐,但可乐治不好我的心病:“他的里屋塞满了珠宝。甚至有一顶钻石头冠,就像公主在舞会上戴的那种东西。”
鲍迪奇先生耸耸肩。对他来说,这个案件已经告破,这件事已经尘埃落定:“你太多疑了,查理。现在真正的问题是该怎么处理我手上的黄金。集中精神考虑一下。但——”
“必须谨慎,我知道。”
“谨慎比勇气更重要。”他睿智地点点头。
“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都没有。”鲍迪奇先生咧嘴笑笑,“我只是想这么说。”
那天晚上我在推特上搜索本杰明·德怀尔,得到的结果虽然很多,但说的都是一位爱尔兰作曲家,于是我把搜索关键词改成“谋杀嫌犯德怀尔”。这一网捞到了五六条小鱼。一条推文是斯坦顿维尔警察局局长威廉·亚德利发的,大体来说就是恭喜自己这么快就抓到了嫌犯。还有一条来自一个ID叫“女朋克44”的人,她和推特上的很多人一样充满“同理心”:我在斯坦顿维尔长大,该死的烂地方。要是德怀尔杀光那里的所有人,那就是帮了世界一个大忙。
真正引起了我的注意的推文来自“牛头人19”:本吉·德怀尔是杀人嫌犯?别逗我笑了。他在屎城维尔待了能有一千年,脑门上应该刺上“村中傻瓜”四个字。
我打算第二天把这条推文拿给鲍迪奇先生看,顺便提出我的看法:假如“牛头人19”说的是真话,那么本杰明·德怀尔就是完美的替罪羊了。然而事与愿违,我没有得到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