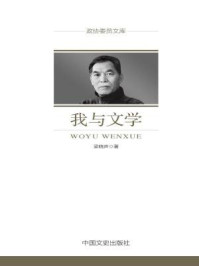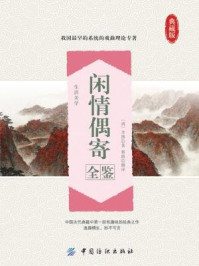贵州盘县两河乡(现为盘州市两河街道),山险地高。如果逢着雨季,路就泥泞不堪。这是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乡民们一辈子的愿望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走出这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许多年过去了,愿望似被山压着,难以实现。
雨季的某一天,四个城里来的大男孩放弃了都市绚烂的霓虹灯,投入山的怀抱。不是旅游,不是新奇地探险,而是实实在在地生活。他们将在这里度过一年或是两年的时间,以自己的热情和学识为山里孩子上课,做孩子们小学、初中乃至高中年级的老师。
一年、两年,于一个人漫长的一生实在算不得什么。但为了这一两年,他们将放弃高薪舒适的工作——外资企业里不允许停薪留职,他们只有辞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原来的工作。还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在山里教书,工资低得可怜,为了给孩子们订阅报纸杂志,他们实际上用的是父母寄来的钱。
在这一两年里,他们同时担任几门课的老师,不仅教孩子们知识,也让孩子们渐渐养成文明卫生的好习惯——贫穷可以没有鲜艳时髦的衣服,但贫穷不是黑黑的指甲不剪,不是拖着鼻涕不擦,不是满脸汗渍污垢不洗……周末的时候,他们也不让自己闲着,踩着泥泞的路,爬几个小时的山去学生家家访。他们觉得老师有责任了解学生更真实的一面,这样才能更好地教孩子们知识。
这几个男孩都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志愿者。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凭一时冲动,而是有组织的行动——志愿者行动。
我是在一个很偶然的场合,看到中央电视台播放这个“志愿者行动”的故事的。就这么偶然的相遇,屏幕上的四个男孩形象竟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且以一种朴实的方式,直达我的灵魂。
是的,灵魂,我们很久不谈灵魂了。灵魂是什么呢?
山里其实也有老师,可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就这几位,也算是山里的“秀才”了。他们有的只小学毕业,就来教小学;有的刚初中读完就教初中;最高的也仅有高中学历。他们本来是可以继续念下去的,说不定念完高中还可以上大学,从此可以告别乡村。可他们终于没有舍得离开,乡亲们一次次真心的呼唤挽留住了他们。乡亲们说:“你们走了,谁来教这些孩子们哪?大家都盼着娃们出息……”
他们就这样义不容辞地留下了,从此吃住在简陋的临时校舍,做着孩子们的“王”。张老师既是两河乡小学、中学的教师,又是孩子们的校长。当四个城里男孩不远万里来到学校的时候,张老师正在教学生们念一首诗。见到新来的老师,他憨憨地笑笑,表示对新老师真切的欢迎。城里男孩问张老师:“你住哪儿?”张老师又是憨厚地一笑,指指教室后面搭出来的木棚。城里男孩提出能否到里面看看,张老师带着歉意,说:“里面很乱,没有灯。”围在一旁看热闹的孩子们听了开心地大笑,说:“张老师房间隔壁是猪棚,白天猪常常要拱进来。”
……
镜头闪回。一个女孩正在教训三个比她小的小男孩。小男孩似乎并不买账,无所谓地向远方茫然斜视。女孩很生气,对站在一旁了解情况的城里老师解释:“你看,他们三个多次不交作业,而且还撒谎……”女孩其实自己也只有十七八岁,扎着两条小辫,刚初中毕业。
就是这么几位放弃继续升学的机会,全身心投在孩子们身上的乡村教师感动了城里来的四个大男孩。男孩们决定以自己的行动为孩子们做点儿什么。一年、两年,也就一两个三百六十五天,对他们却可以用分秒来计算。在这片贫瘠的土壤里,他们要用爱心为孩子们播撒精神的种子;他们要让孩子们明白,有书读是一个人的幸福,为了对得起这份幸福,不应该向老师、父母敷衍;他们还要让孩子们懂得,山区的贫困可以用知识来改变,因此一旦学有所成,首先想到的不应该是走出大山,而是带着知识回到大山……
志愿者在行动。一两年后,又一批志愿者会加入前任志愿者的行列。无数个贫困地区的学校因他们的加入,散发出新的希望与亮光。
于是我扪心自问:倘若我也有资格、有能力成为一名志愿者,我会舍下一两年的城市生活,去山区教书吗?
能!——还是不能?我在心灵两端徘徊,竟迟迟不敢做出选择。在那一刻,当我的灵魂受着四个男孩的牵引、震颤时,我的确不假思索选择了能。而当我再冷静地回想初始的选择时,我竟犹犹疑疑地开始放不下眼前的一切:父母、亲朋、工作。到底还是抛不开生活中的种种杂念,否则,我怎么这么瞻前顾后?
似乎很久没有这样让自己的灵魂痛苦了。在记忆深处,灵魂这个词渐渐被我们遗忘。灵魂在我们的脑海里,究竟以怎样一种形式存在?它能左右我们的思想、意志吗?西藏的一位年轻僧人曾对作家马丽华说:灵魂像气,也像风,实际存在而无形……
倘若灵魂真是这样一种存在,那么我们会不会因为它的无形而懈怠了对它的追求和关注?我想我们的确是在渐渐改变。那些曾经感动过我们的人、事、物,因阅历和年岁的渐长,我们慢慢对之报以习以为常的不屑或者干脆视而不见;而那些曾经让我们唾弃的尘世的红红绿绿,有时竟成为眼前一份实实在在的诱惑。生活的实质有时常让我们将心底的一点儿温暖、一点儿感动失落于红尘,我们变得现实和迟钝,时时忽略了其实和我们同在的美好。
此刻,久违了的灵魂竟像梅檀香风,怡悦我心。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个“志愿者行动”还只有不多的大学生参与。又若干年,一个更专业的组织——“西部阳光行动”在北京十几所大学中兴起。从2004年暑期,第一批志愿者支教开始,“西部阳光行动”仅一年间,就组织了近四百名大学生走进西部,深入偏远乡村支教、支农。
一生关注教育的北大学者钱理群感慨道:“当这些北京的大学生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西部山区,以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周围的一切时,恐怕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他们人生旅途中的重要时刻,对于当下中国社会变革,也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他们正在参与历史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