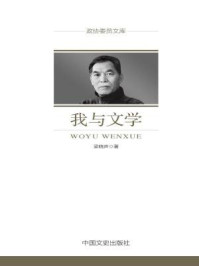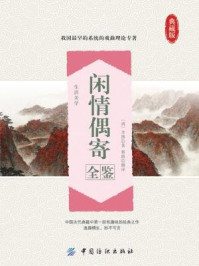因为要给家乡的孩子做一堂演讲,关于文学和人生、阅读和成长——如此辽阔的主题,我几辈子的人生都不够!我在书架前徘徊。指尖滑过一本本有温度的书,那些书,因着共通的气息——洁净的笔墨,幽微的人与事,平静白描中的忧伤和哀怜,敏锐的心灵和孩童清澈的眼光,而一次次惊醒着我的阅读记忆和经验。
关于阅读,我能够说什么呢?
“有一本书的晚上,就是一个在天堂里的晚上,书带来一个很广大的世界。一个十几岁的中国孩子,在晚上可以去十九世纪的法国,可以去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可以去美国……”
多年前的秋天,陈丹燕第一次走进上海七宝中学高中部教学楼的阶梯教室,连着六年,每年都有一个下午,她和那一届高一的学生一起度过。她讲她的求学时代,讲她的阅读记忆,讲一个人在青春期的时候,“最好的安慰——比友谊都好的安慰,最大的乐趣——比恋爱还大的乐趣,就是读一本质量上乘,既有故事又有思想的小说,跟着书去漫游幻想的世界”。
那些演讲,来自现在立在我书架上的《梯形教室的六个下午》。炭笔素描的黑白封面,几个女孩的背影,背着大大的书包,站在走廊的窗口窃窃私语——每次拿起这本书,我总要琢磨,这些女孩背后的包里装着什么?
我曾经听说一个很小的小孩,走在大街上,手里拖着个拉杆书包,肯定是包太重了,她爸爸妈妈给她备了个有滚轮的书包。我猜想这样的包里肯定装着很多东西,但就是没有一本书。我指的是闲书。陈丹燕讲,“只有闲书才叫作书,不是闲书的都不是书”。我们都这么认为——所有视书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人都这么认为。
写过《昨日的世界》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对书发出过由衷的礼赞——
“一个人和书籍接触得愈亲密,他便愈加深刻地感到生活的统一,因为他的人格复化了:他不仅用他自己的眼睛观察,而且运用着无数心灵的眼睛观察,由于他们这种崇高的帮助,他将怀着挚爱的同情踏遍整个世界。”
另一位我喜爱的作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生在意大利乡村的卡尔洛·斯戈隆,在小说《木头宝座》里借主人公朱利安诺之口说过一段话:“我对世界的了解完全来自书本,那是因为我不厌其烦地阅读各种书籍,就像一个打捞海绵的渔民不停地潜入海底一样……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等我看完最后一页,心满意足地丢下书时,脑子里却充满了那本书的情节及其延续……我的想象力被激发起来了,一时难以恢复与现实世界的联系。”
我相信童年的朱利安诺的讲述就是斯戈隆自己的体验。斯戈隆出生的乡村,遍地是山峦和丘陵,生活贫困,但也远离工业喧嚣。斯戈隆的童年浸润在丰厚的民间文化传统中。偏僻、纯朴的乡村生活,悠久、深厚的乡土文化,是朱利安诺,也是斯戈隆生长的世界,属于童话和故事、游记和传奇的世界。这个世界,恰如一张宝座似的木头椅子,给了斯戈隆源源不断的写作营养。
还是茨威格,有一次坐船旅行。船上乘客很少,茨威格经常和一位意大利年轻水手聊天。有天水手收到一封信,他扬着信要茨威格读给他听,信是意大利文的,茨威格立刻恍然——这个“像画中人一般漂亮的,聪明的,具有天真的伶俐和真纯的娴雅的”年轻人,是个文盲。
茨威格很痛苦。他无法想象,曾经当作朋友交谈过的人,一旦与一切书写的东西隔绝——拿起报纸,不能了解;拿起一本书,书之于他,是一件全然无用的东西——那么,世界在他眼里会是怎样?
事实上,阅读已愈益引起重视。我们对书的礼赞,也从来怀着虔敬。可是,悖谬的是,如陈丹燕对少年时代的感叹——“像我,有时间,想看书,却没有书可以看;像你们,有很多很多可以看的书,又没有时间。”陈丹燕说:这就是生活。
那么我想说,亲爱的小孩,还来得及,在你的书包里放一本书吧!读书,这么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