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自古钟灵毓秀,不仅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自然资源,同时又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这样的文化交汇之地,为陶瓷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沈阳的地理位置正好处于长白山脉,大、小兴安岭和渤海、黄海的中枢,是辽东与辽西、辽东半岛与东北大平原的连接点。正如《大清一统志》所言:“盛京形势崇高,水土深厚。长白峙其东,医闾拱其西,沧溟鸭绿绕其前,混同黑水萦其后。山川环卫,原隰沃饶。洵所谓天地之奥区也。”又如《盛京通志》所记:“盛京沧海朝宗,白山拱峙。浑河绕其西南,混同环其西北。缔造鸿规,实基于此。”还如乾隆皇帝在《盛京赋》中所说:“左挟朝鲜,右据山海,北屏白山,南带辽水。”整个沈阳地区地势由东北向西南缓缓倾斜,西南部属于辽河、浑河的冲击平原,地势平坦,土质肥沃。山地丘陵集中在东部和北部,东北部的石人峰和辉山等山地丘陵,林深树茂,花光锦簇;东南部的马耳山周边山地与丘陵,槲树森森,花果累累;北部康平、法库两县的山丘之地则草树繁荫,古木苍然。与山丘形成对映的河流,则有辽河、浑河及其支流蒲河、秀水河、柳河、沙河、养息牧河等。
今天,我们如果运用现代航拍手段在空中俯视沈阳城,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北而南,辽河、蒲河、浑河,三水环绕;自西向东,千山和长白山余脉,从南北接近城市,犹如两个臂膀,拥这一方水土入怀。从沈阳城向南,这一对臂膀支配洪荒之力,将绸缎般的千里沃野,铺陈到大海……
这样优越的地理形势,或许只是因为洪荒时代的一次偶然。19亿年前,一场声势浩大的陨石雨,降落在还没有沈阳之名的沈阳地面上。直到今天,一块形似王冠的巨大陨石,仍气魄非凡地矗立在沈阳东南部的馒首山上。它长160米,宽54米,高42米,重量约200万吨,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体积最大、陨落时间最早的陨石,也是茫茫宇宙带给沈阳地区的厚重礼物。古人将陨石称为“圣石”,把它们当作神或者上天的使者。现代人不再迷信,他们清楚这些石头的来历,但19亿年前这些不速之客的光临,仍然赋予它们落脚的土地以奇妙与神圣。世间常见陨石雨,唯独沈阳有陨石山,19亿年前这场轰轰烈烈的陨石群撞击,让沉寂几十亿年的土地发生巨大改变。有专家认为,正是这样剧烈的撞击所带来的地质结构巨变,才让辽南地区出现了丰富的镁菱矿与滑石矿。更有专家大胆假设,这次撞击形成了巨大的陨石地貌,才给沈阳留下了今天的河流、平原和山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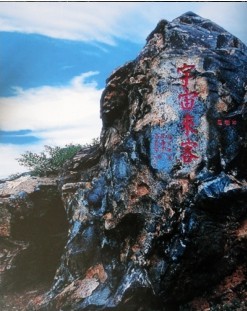
沈阳陨石山

沈阳农业大学后山11万年前古人类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陨石雨过后,经过漫长时期,沈阳终于步入了旧石器时代。到了距今11万年的时候,这里有了人类居住,那是沈阳最早的先民。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会经常听到“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这两个表述。为了弄清楚这两个表述的关系,我们首先应当了解其上位概念即属概念“石器时代”。“石器时代”是考古学家假定的一个时间区段,为考古学上的术语,即早期人类历史分期的第一个时代。时间段从出现人类到青铜器的出现,大约始于距今200万年,止于距今5000至2000年左右。称这一段为“石器时代”,顾名思义,即这一时代的人类主要使用的工具是石器,但也并不代表那个时候的人类只会使用石器。“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距今约200万年—1万年前,“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万年—3000年前。如果说“旧石器时代”人类的主要工具还是石器,那么“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在使用石器的同时,已开始步入制陶、纺织、稻作、冶铸等文明时期。
沈阳地区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起步较晚。18世纪末19世纪初,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和八木奘三郎曾在沈阳地区做过考古学和人类学考察,这在《鸟居龙藏全集》和八木奘三郎《东北地方的人类学旅行》等文献中略有记载。20世纪30年代,梁思永先生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他到东北进行考古调查,由于缺乏资料,只是将沈阳地区作为东北地区考古文化南北分界线,认为此地区之南为农耕文化区,其北为游牧文化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新乐新石器遗址的确立为契机,沈阳地区的考古发现进展很快。2011年,沈阳考古工作者在康平、法库两县进行考古调查,共发现以康平县王立岗窝堡东山遗存为主的旧石器地点14处,采集到石器1029件,其中包括石片、石核、石锤、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年代跨度为距今3万年至1万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过渡阶段。2012年,考古工作者对沈阳农业大学后山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到2014年,在该遗址中发现了多个连续分布的旧石器文化层,发掘出一组古人类在野外搭建的窝棚式建筑遗迹,出土了620余件古人类加工和使用的打制石器,包括尖状器、雕刻器、砍砸器、刮削器、石核、石片、断块、砾石等。证明了早在11万年前,沈阳这片土地上就一直有人类繁衍生息,他们不但能制造石器工具,而且能利用这些工具改造生存和居住环境。沈阳农业大学后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中更新世至晚更新世时期,沈阳乃至东北亚地区古人类的迁徙与融合、旧石器文化的交流与演变、现代人起源与发展等重大学术课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进入21世纪的沈阳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不仅填补了沈阳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空白,同时也将沈阳先民的活动史提前了10万多年。由此,沈阳先民和华夏古人类就形成这样一个清晰的序列:
——距今200万年的重庆巫山龙骨坡人。
——距今170万年的云南元谋人。
——距今100万年的陕西蓝田人。
——距今70万年的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
——距今50万年的辽宁本溪庙后山人。
——距今28万年的辽宁营口金牛山人。
——距今11万年的沈阳农大后山人。
——距今3万年的北京山顶洞人。
——距今3万年的沈阳康平王立岗窝堡人。
直到从距今7200年的新乐人开始,沈阳开启了以陶器为主的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沈阳文化是从20世纪50年代偏堡子考古揭开序幕的,史学家定名为“偏堡子文化”。
为了研究那些古代的遗存,考古学界将分布于一定范围,延续了一定时间并有着共同特征的考古发现称为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称谓是一种考古学意义上的特指文化,而非通常的一般意义的文化。这种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命名,习惯上使用最早发现这种文化的地点来称呼。如长江流域的彭头山文化、河姆渡文化,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西北地区的老官台和大地湾文化、齐家文化,山东的后李文化,内蒙古的赵宝沟文化,辽宁的兴隆洼文化,沈阳的新乐文化、偏堡子文化等,都是新石器时代最典型的文化遗存。

沈阳农大后山考古发掘出土的11万年前古人类使用的打制石器
沈阳偏堡子文化遗址是1956年东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经过实地调查,在新民县偏堡子村所发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过考古发掘,发现了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等,并出土了大口深腹罐、陶钵、四耳罐等,是一处“易于区别而有特殊性”的文化遗存。
 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队在沈阳铁西区肇工街试掘中,发现郑家洼子青铜时代遗址之下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并与偏堡子文化属于同一类型。
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队在沈阳铁西区肇工街试掘中,发现郑家洼子青铜时代遗址之下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并与偏堡子文化属于同一类型。

1973年6月,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在沈阳市北陵乡新乐电工厂宿舍院内考古调查,并通过试掘,发现了“新乐下层文化”。这是一种新的沈阳地区的早期文化,与辽西红山文化相比,不见彩陶与石犁,表明其社会生产的原始性和单一性,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

1978年5月,考古部门对新乐遗址F2房址进行了发掘,出土陶器40件,各种石器如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等数百件,玉器5件,骨器22件,煤精制品10余件,木雕制品2件。其中鸟形木雕最为知名,全长38.5厘米,宽4.8厘米,厚1厘米。由嘴、头、身、尾、柄五个部分组成。除柄外,全身双面雕刻,阴刻纹饰基本一致,通体设计图案化,刀法娴熟流畅,线条刚劲细腻,其形宛如一只振翅欲飞的鸟,栩栩如生。考古学家认为木雕鸟很像是权杖,直柄以上的雕饰图案可能是图腾徽帜。权杖为氏族首领统帅族人所用,说明当年新乐地区为鸟图腾氏族。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新乐出土的炭化木柱进行碳14测定,新乐遗址下层文化距今有7200多年。其中“大量的炭化物和磨盘、磨棒等加工工具的出土,说明当时这里的人们已出现农耕并开始定居生活。陶器普遍饰有压印纹,还有原始木雕艺术品,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美的生活的追求。”
 1980—1982年,新乐遗址博物馆与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又在新乐遗址区域进行了抢救清理发掘。这次发掘主要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多座房址,大量石器和陶器以及煤精制品,还有石墨、赤铁矿石、榛子壳、山里红子等,尤其是在房址火塘边发现了多件陶制斜口器。同时明确了新乐遗址在原新乐上下层文化之间还有一种文化:“新乐中层文化”,距今约4000—5000年,即偏堡子文化类型。此次发掘根据新乐下层出土的大量房址,正式确认新乐遗址是新石器时代原始氏族聚落遗址。“目前为止在沈阳地区史前考古方面具有重大突破性意义。因此称之为‘新乐文化’。”
1980—1982年,新乐遗址博物馆与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又在新乐遗址区域进行了抢救清理发掘。这次发掘主要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多座房址,大量石器和陶器以及煤精制品,还有石墨、赤铁矿石、榛子壳、山里红子等,尤其是在房址火塘边发现了多件陶制斜口器。同时明确了新乐遗址在原新乐上下层文化之间还有一种文化:“新乐中层文化”,距今约4000—5000年,即偏堡子文化类型。此次发掘根据新乐下层出土的大量房址,正式确认新乐遗址是新石器时代原始氏族聚落遗址。“目前为止在沈阳地区史前考古方面具有重大突破性意义。因此称之为‘新乐文化’。”
 沈阳在辽时有“乐郊”之称,当代又有了新乐遗址。这个遗址的发现,对于沈阳来说,确实是一种“新乐”。
沈阳在辽时有“乐郊”之称,当代又有了新乐遗址。这个遗址的发现,对于沈阳来说,确实是一种“新乐”。

新乐遗址博物馆景观
1982年—1988年,在新乐保护区内,为配合基建,先后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发现大量遗迹遗物,其中个别陶钵的口沿凹带内发现了黑色彩绘条纹,证实了新乐文化彩绘陶的存在。

1991年—1993年,相关部门对新乐遗址重点保护区进行了连续性发掘,新发掘出新乐下层房址18座和大量各类遗物。

通过对沈阳新乐这一新石器时代最重要遗址的数次考古发掘,我们对新乐文化有了更加完整的认识。最终新乐遗址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新乐遗址博物馆也成为沈阳的文化地标。
继偏堡子文化和新乐文化考古发现之后,1973年,沈阳考古工作才又在新民高台山发现了以“之”字压印纹为代表的新乐下层文化,早于以素面陶三足器为代表的新乐上层文化。1979年—1980年,再次对高台山遗址进行发掘,在地层关系上明确了在新石器时代“东高台山一期类型”早于偏堡子类型,年代应在距今6000年以上。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沈阳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康平、法库、辽中等地考古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1980年春,在康平西部、北部和东部地区发现了敖力营子、李家北坨子、刘家店后岗三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遗址,与红山文化极为相似。
 1980—1986年,在辽中大黑北岗和白家村后沙岗两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别属于新乐下层文化和偏堡子文化类型。
1980—1986年,在辽中大黑北岗和白家村后沙岗两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别属于新乐下层文化和偏堡子文化类型。
 1983—1988年,法库县文物普查,发现了属于新乐下层文化的佘家堡遗址、蛇山沟遗址;属于偏堡子文化的黑山下遗址;属于红山文化系统的叶茂台遗址、羊泉遗址、王家店遗址、泉眼沟遗址、李贝堡遗址。1988年,在康平县赵家店发现白沙沟遗址,出土有新石器时代陶器,纹饰具有红山文化风格。
1983—1988年,法库县文物普查,发现了属于新乐下层文化的佘家堡遗址、蛇山沟遗址;属于偏堡子文化的黑山下遗址;属于红山文化系统的叶茂台遗址、羊泉遗址、王家店遗址、泉眼沟遗址、李贝堡遗址。1988年,在康平县赵家店发现白沙沟遗址,出土有新石器时代陶器,纹饰具有红山文化风格。
 1990年,在康平县郝官屯乡老山头村发掘一处从新石器时代到魏晋时期遗址。
1990年,在康平县郝官屯乡老山头村发掘一处从新石器时代到魏晋时期遗址。

20世纪的考古发现,终于让沈阳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类型有了一个系统而完整的体系,那就是新乐下层文化类型、偏堡子文化类型、红山文化类型,并各具特点。

根据新乐遗址出土的木雕鸟所制的太阳鸟雕塑,原立于沈阳市政府广场,后迁至新乐遗址博物馆内。
新乐下层文化类型所反映的社会发展阶段为母系氏族公社的鼎盛时期,其房址有规律地分布,房址内的窖穴以及大量的陶器和石磨盘、石磨棒、炭化谷物,陶塑猪头、狗头等动物形象和猪、羊骨,已证明此时的新乐人正过着以原始火耕农业为主体的定居生活。而数量众多的精制石镞和网坠的存在,也表明新乐人广泛的渔猎活动也是原始农业经济不可或缺的补充。
 与物质生产相一致,新乐下层文化类型的精神生活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出土的栩栩如生的木雕鸟,大量造型丰富的煤精制品,磨制精美的玉石球,花纹规整而式样多变的陶器纹饰,都表明这一时期已经有了图腾崇拜和原始艺术欣赏。这些都证明新乐下层文化与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早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绝对年代定为距今7000年左右。
与物质生产相一致,新乐下层文化类型的精神生活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出土的栩栩如生的木雕鸟,大量造型丰富的煤精制品,磨制精美的玉石球,花纹规整而式样多变的陶器纹饰,都表明这一时期已经有了图腾崇拜和原始艺术欣赏。这些都证明新乐下层文化与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早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绝对年代定为距今7000年左右。
考古发现,新乐文化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中原的裴李岗文化、华北的磁山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大致处于同一历史发展阶段的母系氏族社会。“因此,新乐人可能过着财产公有、集团劳动、平均分配的社会生活。他们‘知其母,不知其父’,母系血缘在维系氏族制度、确定世系和财产继承权诸方面,都起着决定作用。”
 新乐遗址的发现不仅将沈阳地区人类部落居住和活动历史上溯到7000年前,同时也为东北地区史前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填补了辽河下游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空白。
新乐遗址的发现不仅将沈阳地区人类部落居住和活动历史上溯到7000年前,同时也为东北地区史前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填补了辽河下游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空白。
偏堡子文化稍晚于新乐下层文化。其陶器以夹砂或夹滑石褐陶为主,烧成温度比新乐下层陶器要高,素面较少,多数有纹饰。石器与新乐下层文化相似,有打制、磨制和细石器三类。这一文化类型在新民高台山、前当堡、沈阳新乐遗址里同时存在。与大连小珠山中层的器物存在相似之处,因此绝对年代距今有4000—5000年左右。
沈阳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类型主要集中在康平、法库两县境内。这一类型的陶器以泥质红陶或夹砂红陶为主,彩绘花纹多为黑彩,以平行带状纹为主,也有几何纹、斜带纹和涡旋纹。生产工具以打制、磨制和细石器为主。磨制石器中,带有扶手的石磨棒比较特殊。考古学家一般认定这些遗存属红山文化晚期,其绝对年代应在距今5000年左右。
新石器时代沈阳历史文化的多元类型,为沈阳陶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让新石器时代沈阳的陶器制作进入一个丰富而多彩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