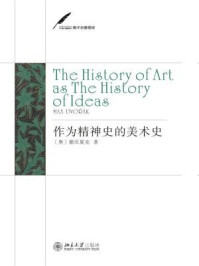中国自古有“礼仪之邦”的美称,“礼”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南宋哲学家陆九渊《大学春秋讲义》云:“圣人贵中国,贱夷狄,非私中国也。中国得天地中和之气,固礼义之所在。贵中国者,非贵中国也,贵礼义也。”
 钱穆先生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得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
钱穆先生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得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
 《礼记·礼运》篇云:“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礼记·礼运》篇云:“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就生命个体来说,“礼”是自别于禽兽,修身成人的基本要素;就社会群体来说,“礼”是齐家治国,安定社会的方法和手段。中国传统经典中,《周礼》《仪礼》《礼记》并称“三礼”,构成古代中国礼仪制度和礼义思想的总汇。其中,《周礼》是三礼之首,通过官制构建起理政治国的理想体系,内容丰富、结构缜密,是一部以人法天、天人同构的皇皇大典。
就生命个体来说,“礼”是自别于禽兽,修身成人的基本要素;就社会群体来说,“礼”是齐家治国,安定社会的方法和手段。中国传统经典中,《周礼》《仪礼》《礼记》并称“三礼”,构成古代中国礼仪制度和礼义思想的总汇。其中,《周礼》是三礼之首,通过官制构建起理政治国的理想体系,内容丰富、结构缜密,是一部以人法天、天人同构的皇皇大典。
《周礼》一书,据《史记》《汉书》《汉纪》记载,初名《周官》或《周官经》。《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克商之后的周代历史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周公)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
 《史记·封禅书》也记载:“《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
《史记·封禅书》也记载:“《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
 《汉书·艺文志》曰:“《周官经》六篇。王莽时刘歆置博士。《周官传》四篇。”颜师古注:“即今之《周官礼》也。”
《汉书·艺文志》曰:“《周官经》六篇。王莽时刘歆置博士。《周官传》四篇。”颜师古注:“即今之《周官礼》也。”
 《汉纪》云:“歆以《周官》十六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
《汉纪》云:“歆以《周官》十六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
 而《周官》的面世,当在西汉初年,汉武帝时期。贾公彦《周礼注疏·序周礼废兴》篇记载:
而《周官》的面世,当在西汉初年,汉武帝时期。贾公彦《周礼注疏·序周礼废兴》篇记载:
《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周礼》后出者,以其始皇特恶之故也。是以《马融传》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

按照马融的说法,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法家思想施行统治,与周公之道不合,直到汉惠帝四年(前191)废除秦朝挟书之律(按:马融云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误),广开献书之路,《周官》才得以被世人所知。《汉书·景十三王传》则记载:“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
 《周官》是河间献王从民间征集到的“古文先秦旧书”,在武帝广开献书之路时,河间献王将其献与官方。《经典释文序录》则进一步记载了《周官》一书的来源:“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
《周官》是河间献王从民间征集到的“古文先秦旧书”,在武帝广开献书之路时,河间献王将其献与官方。《经典释文序录》则进一步记载了《周官》一书的来源:“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
 《周官》是河间献王从李氏处所得,但史籍并未记载李氏的姓名、身份等详细信息。关于《周官》最后一部分补入的《考工记》,郑玄《三礼目录》则云:“《司空》之篇亡。汉兴,购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识其事者,记录以备大数,《古周礼》六篇毕矣。”
《周官》是河间献王从李氏处所得,但史籍并未记载李氏的姓名、身份等详细信息。关于《周官》最后一部分补入的《考工记》,郑玄《三礼目录》则云:“《司空》之篇亡。汉兴,购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识其事者,记录以备大数,《古周礼》六篇毕矣。”
 这里叙述的《周官》面世过程,众说有异,并未达成一致的认知。但基本可以认同的是,《周礼》被世人所知的时间是在汉惠帝除挟书之律后,大致在景、武之际。在当时,《冬官》篇已经缺失,时人取《考工记》补之。
这里叙述的《周官》面世过程,众说有异,并未达成一致的认知。但基本可以认同的是,《周礼》被世人所知的时间是在汉惠帝除挟书之律后,大致在景、武之际。在当时,《冬官》篇已经缺失,时人取《考工记》补之。
《周礼》之“周”,既可以指朝代,指其内容是周代的礼法、官制;也可是周密、周普之意,指“周天之官”,或其所创立的官制体系,上下四旁,无所不周。相对于《周礼》面世过程的不同说法,《周礼》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更是经历代学者长期争论,仍未取得一致的结论。正如《四库提要》所说:“(《周礼》)于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
 其主要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
其主要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周礼》为周公所作
周公是周初儒学的奠基者,也是西周典章制度的创制者,《尚书大传》云其“一年救乱,二年伐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刘歆认为《周礼》是周公所作,并云:“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
。刘歆认为《周礼》是周公所作,并云:“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
 郑玄注《周礼·天官·冢宰》“惟王建国”也认为“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
郑玄注《周礼·天官·冢宰》“惟王建国”也认为“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
 。在此之后,历代名家大儒多宗此说。朱熹云:“《周礼》是周公遗典也。”
。在此之后,历代名家大儒多宗此说。朱熹云:“《周礼》是周公遗典也。”
 孙诒让认为,《周礼》是周公对西周之前经世大法的总结:
孙诒让认为,《周礼》是周公对西周之前经世大法的总结:
粤昔周公,缵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然非徒周一代之典也,盖自黄帝、颛顼以来,纪于民事以命官,更历八代,斟汋损益,因袭积累,以集于文武,其经世大法,咸稡于是。

周公作《周礼》虽在六年,其班行则在致政时,故《明堂位》孔疏亦谓“成王即位乃用周礼是也”。

因此,《周礼》也被认为是最理想、最有效的典章制度。王安石《周礼义序》云:
惟道之在政事,其贵贱有位,其后先有序,其多寡有数,其迟数有时。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盖其因习以崇之,庚续以终之,至于后世,无以复加。

孙诒让也说:“此经建立六典,洪纤毕贯,精意眇恉,弥纶天地,其为西周政典,焯然无疑。”
 可见,《周礼》为周公所作的说法出现最早,影响最广,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元吴澄《周礼考注》,明王应电《周礼传》,清惠士奇《礼说》、江永《周礼疑义举要》等均宗此说。
可见,《周礼》为周公所作的说法出现最早,影响最广,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元吴澄《周礼考注》,明王应电《周礼传》,清惠士奇《礼说》、江永《周礼疑义举要》等均宗此说。
(二)《周礼》作于西周但未必出于周公之手
《周礼》通过官制阐述治国方略,内容极其丰富,几乎涉及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周礼》作于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其东迁以前三百余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损益,除旧布新,不知凡几。其初去成、康未远,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于是以后世之法窜入之,其书遂杂。”
 有研究者将《周礼》的成书年代定位在西周时期。蒙文通《从社会制度及政治制度论周官成书年代》一文认为:“(《周礼》)虽未必即周公之书,然必为西周主要制度,而非东迁以下之治。”
有研究者将《周礼》的成书年代定位在西周时期。蒙文通《从社会制度及政治制度论周官成书年代》一文认为:“(《周礼》)虽未必即周公之书,然必为西周主要制度,而非东迁以下之治。”
 不同于汉代得以重新问世的其他经典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周礼》使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称为“古文经”。朱谦之《〈周礼〉的主要思想》一文通过文字考订《周礼》的成书年代:“此书中所用古体文字,不见于其他古籍,而独与甲骨文金文相同,又其所载官制与《诗经·大雅》《小雅》合,可见非在西周文化发展的时代不能作。”因此,得出“《周礼》是西周宣王中兴时代之书”的结论。
不同于汉代得以重新问世的其他经典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周礼》使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称为“古文经”。朱谦之《〈周礼〉的主要思想》一文通过文字考订《周礼》的成书年代:“此书中所用古体文字,不见于其他古籍,而独与甲骨文金文相同,又其所载官制与《诗经·大雅》《小雅》合,可见非在西周文化发展的时代不能作。”因此,得出“《周礼》是西周宣王中兴时代之书”的结论。
 陈汉平也说:“笔者倾向于《周官》成书在西周之说。”
陈汉平也说:“笔者倾向于《周官》成书在西周之说。”
 日本甲骨学先驱林泰辅著有《周公及其时代》(《周公及其时代》)一书,认为《周礼》作于西周末期的厉王、宣王、幽王时代。
日本甲骨学先驱林泰辅著有《周公及其时代》(《周公及其时代》)一书,认为《周礼》作于西周末期的厉王、宣王、幽王时代。
(三)《周礼》作于春秋
从所载官制的角度,刘起
 《〈洪范〉成书时代考》一文认为:“《周礼》一书所载官制材料,都不出春秋之世周、鲁、卫、郑四国官制范围,没有受战国官制的影响。”
[1]
其《〈周礼〉真伪之争及其书写成的真实依据》进一步补充道:“《周礼》的成书有一发展过程。第一步只是一部官职汇编,至迟成于东周春秋时代,它依据的是自西周以来逐渐完备的周、鲁、卫、郑四国的姬周系统的官制,初步还记录了一些官职的职掌。后来逐渐详细补充,写成了各官职的职文,除主要保存了春秋以上资料外,还录进了不少战国资料,所以全书的补充写定当在战国时期。到汉代整理图书时,又有少数汉代资料掺进去了,但不影响这部书原是周代的旧籍。”
[2]
金景芳认为:“《周礼》一书是东迁以后某氏所作。作者得见西周王室档案,故讲古制极为纤悉具体。但其中也增入作者自己的设想。例如封国之制、畿服之制一类的东西,就是作者自己设想所制定的方案。这个方案,具有时代特点,不但西周不能为此方案,即春秋战国时人也不会作此方案。原因是春秋战国时,周室衰微已甚,降为二、三等小国,当时不会幻想它会复兴。而在西周的历史条件下,则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设想。”
《〈洪范〉成书时代考》一文认为:“《周礼》一书所载官制材料,都不出春秋之世周、鲁、卫、郑四国官制范围,没有受战国官制的影响。”
[1]
其《〈周礼〉真伪之争及其书写成的真实依据》进一步补充道:“《周礼》的成书有一发展过程。第一步只是一部官职汇编,至迟成于东周春秋时代,它依据的是自西周以来逐渐完备的周、鲁、卫、郑四国的姬周系统的官制,初步还记录了一些官职的职掌。后来逐渐详细补充,写成了各官职的职文,除主要保存了春秋以上资料外,还录进了不少战国资料,所以全书的补充写定当在战国时期。到汉代整理图书时,又有少数汉代资料掺进去了,但不影响这部书原是周代的旧籍。”
[2]
金景芳认为:“《周礼》一书是东迁以后某氏所作。作者得见西周王室档案,故讲古制极为纤悉具体。但其中也增入作者自己的设想。例如封国之制、畿服之制一类的东西,就是作者自己设想所制定的方案。这个方案,具有时代特点,不但西周不能为此方案,即春秋战国时人也不会作此方案。原因是春秋战国时,周室衰微已甚,降为二、三等小国,当时不会幻想它会复兴。而在西周的历史条件下,则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设想。”
 洪诚《读〈周礼正义〉》认为,《周礼》起于周初,历经累积,成书最晚不在东周惠王后。
洪诚《读〈周礼正义〉》认为,《周礼》起于周初,历经累积,成书最晚不在东周惠王后。
(四)《周礼》作于战国
与郑玄同时的林孝存、何休并不认同《周礼》为周公所作的观点,林孝存认为《周礼》是“末世渎乱不验之书”
 ,何休认为《周礼》是“六国阴谋之书”
,何休认为《周礼》是“六国阴谋之书”
 ,顾颉刚将阴谋解释为私下的计划。清崔述《丰镐考信录》云:“(《周礼》)条理详备,诚有可观,然遂以为周公所作周一代之制,则非也。”其对《周礼》所论方里、建国大小、税制等进行考察,比较《周礼》与《孟子》《春秋》《尚书》在封国、赋税、朝觐、立法方面的诸多不同,认为《周礼》盖“撰于战国之时”。
,顾颉刚将阴谋解释为私下的计划。清崔述《丰镐考信录》云:“(《周礼》)条理详备,诚有可观,然遂以为周公所作周一代之制,则非也。”其对《周礼》所论方里、建国大小、税制等进行考察,比较《周礼》与《孟子》《春秋》《尚书》在封国、赋税、朝觐、立法方面的诸多不同,认为《周礼》盖“撰于战国之时”。
 毛奇龄《经问·周礼问》认为:“《周礼》为周末之书,不特非周公所作,即战国孟子以前皆未曾有。……《礼记》杂篇皆战国后儒所作,而《仪礼》《周礼》则又在衰周之季、吕秦之前。”
毛奇龄《经问·周礼问》认为:“《周礼》为周末之书,不特非周公所作,即战国孟子以前皆未曾有。……《礼记》杂篇皆战国后儒所作,而《仪礼》《周礼》则又在衰周之季、吕秦之前。”
 近现代学者的研究中,郭沫若《周官质疑》择取金文中的职官与《周礼》进行比较,认为这些职官“乃彝铭中言周代官制之卓著者,同于《周官》者虽亦稍稍有之,然其骨干则大相违背。……如是而尤可谓《周官》必为周公致太平之迹,直可谓之迂诞而已”,“考其(《周官》)编制,以天地四时配六官,官各六十职,六六三百六十,恰合于黄道周天之度数,是乃准据星历智识之钩心结构,绝非自然发生者可比。仅此已足知其书不能出于春秋以前矣”,“《周官》一书,盖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袭其师‘爵名从周’之意”。
近现代学者的研究中,郭沫若《周官质疑》择取金文中的职官与《周礼》进行比较,认为这些职官“乃彝铭中言周代官制之卓著者,同于《周官》者虽亦稍稍有之,然其骨干则大相违背。……如是而尤可谓《周官》必为周公致太平之迹,直可谓之迂诞而已”,“考其(《周官》)编制,以天地四时配六官,官各六十职,六六三百六十,恰合于黄道周天之度数,是乃准据星历智识之钩心结构,绝非自然发生者可比。仅此已足知其书不能出于春秋以前矣”,“《周官》一书,盖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袭其师‘爵名从周’之意”。

钱穆《周官制作时代考》认为《周官》书出战国晚世,当在道家思想转成阴阳学派之后,而或者尚在吕不韦宾客著书之前。杨向奎《〈周礼〉内容的分析及其制作时代》判定《周礼》可能是一部“战国中叶左右齐国的书”
 。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认为,《周官》一书和《管子》相似,是齐人关于组织人民、充实府库,以求达到统一寰宇的目的而设计的一套制度。《周官》出于齐国或别国的法家而托之于周,与周公和儒家没有关系。沈文倬《略论宗周王官之学》认为:“《周礼》成书确实较晚,成于晚周(但决非汉初);而且其书散乱,是在秘府的乱书堆里发现的。……残存三百四十五官(《考工》是记,当别议),基本上取诸于两周实制(周初创建和晚周更制)。”
。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认为,《周官》一书和《管子》相似,是齐人关于组织人民、充实府库,以求达到统一寰宇的目的而设计的一套制度。《周官》出于齐国或别国的法家而托之于周,与周公和儒家没有关系。沈文倬《略论宗周王官之学》认为:“《周礼》成书确实较晚,成于晚周(但决非汉初);而且其书散乱,是在秘府的乱书堆里发现的。……残存三百四十五官(《考工》是记,当别议),基本上取诸于两周实制(周初创建和晚周更制)。”
 吕友仁《〈周礼译注〉前言》,钱玄《三礼通论》,杨天宇《郑玄三礼注研究》,沈长云、李晶《春秋官制与〈周礼〉比较研究——〈周礼〉成书年代再探讨》,以及张舜徽、范文澜等人均认同《周礼》成书于战国。
吕友仁《〈周礼译注〉前言》,钱玄《三礼通论》,杨天宇《郑玄三礼注研究》,沈长云、李晶《春秋官制与〈周礼〉比较研究——〈周礼〉成书年代再探讨》,以及张舜徽、范文澜等人均认同《周礼》成书于战国。
(五)《周礼》作于周秦之际
宋时,魏了翁提出《周礼》为秦汉间所附会之书,清毛奇龄《经问》卷二认为《周礼》系周末秦初儒者所作。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写道:“(《周礼》)总是战国秦汉之间,一二人或多数人根据从前短篇讲制度的书,借来发表个人的主张。”
 金春峰《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将《周礼》所记制度和社会行政组织置于时代的宏观背景之下,发现其与秦的历史环境与文化背景相符,认为《周礼》是战国末年入秦的学者所作。《周官》的官职设置和制度设计的蓝图与指导思想,是为新的统一王朝服务的。陈连庆《〈周礼〉成书年代的新探索》认为“《周礼》制作年代的上限,不早于商鞅变法”,“下限也不会晚于河间献王在位之时”,“成书年代的最大可能,是在秦始皇帝之世”。台湾学者史景成《〈周礼〉成书年代考》认为《周礼》作于《吕氏春秋》之后,秦统一天下之前。
金春峰《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将《周礼》所记制度和社会行政组织置于时代的宏观背景之下,发现其与秦的历史环境与文化背景相符,认为《周礼》是战国末年入秦的学者所作。《周官》的官职设置和制度设计的蓝图与指导思想,是为新的统一王朝服务的。陈连庆《〈周礼〉成书年代的新探索》认为“《周礼》制作年代的上限,不早于商鞅变法”,“下限也不会晚于河间献王在位之时”,“成书年代的最大可能,是在秦始皇帝之世”。台湾学者史景成《〈周礼〉成书年代考》认为《周礼》作于《吕氏春秋》之后,秦统一天下之前。

(六)《周礼》作于汉代
胡适《论秦畤及〈周官〉书》因为《周礼》时常出现“祀五帝”,认为《周礼》“为汉人所作之书似无可疑”
 。彭林也认为《周礼》成书于汉初。日本学者池田温认为:“《周礼》基本上为战国时代思想家的构想,至汉代始以如今日所见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书。在其内容中,作为素材的那些被认为是从周至春秋战国的诸制度和诸事物,乃是经过种种加工而收入进去的。”
。彭林也认为《周礼》成书于汉初。日本学者池田温认为:“《周礼》基本上为战国时代思想家的构想,至汉代始以如今日所见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书。在其内容中,作为素材的那些被认为是从周至春秋战国的诸制度和诸事物,乃是经过种种加工而收入进去的。”

(七)《周礼》为刘歆伪造
北宋时,王安石借《周礼》经义施行变法,胡安国、胡宏通过抨击《周礼》来抨击王安石以《周礼》乱宋,称《周礼》是“王莽令刘歆撰”
 的,认为《周礼》“附会王莽,变乱旧章,残贼本宗,以趋荣利”,是“假托《周官》之名,剿入私说,希合贼莽之所为耳”。
的,认为《周礼》“附会王莽,变乱旧章,残贼本宗,以趋荣利”,是“假托《周官》之名,剿入私说,希合贼莽之所为耳”。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认为,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伪造群经,《周官》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徐复观《〈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认为:“《周官》乃王莽、刘歆们用官制以表达他们政治理想之书。”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认为,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伪造群经,《周官》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徐复观《〈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认为:“《周官》乃王莽、刘歆们用官制以表达他们政治理想之书。”
 侯家驹认为:“《周礼》是集体编著,刘歆为其总提调,其所用底稿乃是战国时代人士所撰,为河间献王于武帝时所献而藏于秘府之《周官》原文或残本,再予以损益。”
侯家驹认为:“《周礼》是集体编著,刘歆为其总提调,其所用底稿乃是战国时代人士所撰,为河间献王于武帝时所献而藏于秘府之《周官》原文或残本,再予以损益。”
 洪迈《容斋续笔》、廖平《古学考》、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均认同这一观点。但刘歆伪造《周礼》的主张,在四库馆臣时已有反驳。《四库全书总目》云《周礼》之改易、兴废“亦如后世律令条格,率数十年而一修,修则必有所附益。特世近者可考,年远者无征,其增删之迹,遂靡所稽,统以为周公之旧耳。……如斯之类,与二礼多相矛盾,歆果赝托周公为此书,又何难牵就其文,使与经传相合,以相证验,而必留此异同,以启后人之攻击。然则《周礼》一书,不尽原文,而非出依托,可概睹矣”
洪迈《容斋续笔》、廖平《古学考》、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均认同这一观点。但刘歆伪造《周礼》的主张,在四库馆臣时已有反驳。《四库全书总目》云《周礼》之改易、兴废“亦如后世律令条格,率数十年而一修,修则必有所附益。特世近者可考,年远者无征,其增删之迹,遂靡所稽,统以为周公之旧耳。……如斯之类,与二礼多相矛盾,歆果赝托周公为此书,又何难牵就其文,使与经传相合,以相证验,而必留此异同,以启后人之攻击。然则《周礼》一书,不尽原文,而非出依托,可概睹矣”
 。
。
从西周到汉,《周礼》成书及作者的争论前后跨越一千余年,在没有新的佐证材料的情况下,也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但可以获得一致意见的是:《周礼》记载的职官、礼制、名物多与先秦古籍相合,保存了先秦时期的制度和思想,对后世政治制度、治国方略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周礼》面世时,《冬官》已经缺失,故以《考工记》补之。关于《考工记》的作者和成书年代,贾公彦《考工记》疏云:“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知在于秦前,是以得遭秦灭焚典籍,《韦氏》《裘氏》等阙也。”
 宋林希逸《考工记解》云:“《考工记》须是齐人为之,盖言语似《穀梁》,必先秦古书也。”
宋林希逸《考工记解》云:“《考工记》须是齐人为之,盖言语似《穀梁》,必先秦古书也。”
 均认为《考工记》是先秦时期作品。清江永《周礼疑义举要》也记载:
均认为《考工记》是先秦时期作品。清江永《周礼疑义举要》也记载:
《考工记》,东周后齐人所作也。其言“秦无庐”“郑之刀”;厉王封其子友,始有郑;东迁后,以西周故地与秦,始有秦:故知为东周时书。其言“橘逾淮而北为枳”“
 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皆齐、鲁间水;而“终古”“戚速”“椑茭”之类,郑注皆以为齐人语,故知齐人所作也。盖齐、鲁间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辞者为之。
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皆齐、鲁间水;而“终古”“戚速”“椑茭”之类,郑注皆以为齐人语,故知齐人所作也。盖齐、鲁间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辞者为之。

钱玄认为,《考工记》也是先秦古籍,成书约在东周时期;刘洪涛认为《考工记》多是周朝遗文;郭沫若、贺业钜等认为《考工记》是春秋末年齐国所记录的官书;杨宽、王燮山等认为《考工记》成书于战国初期;梁启超、史景成等认为《考工记》成书于战国后期;夏炜瑛认为,《考工记》就是《周礼》的一部分,即《冬官》,是战国年间齐国的阴阳家所作;沈长云认为《考工记》成书于秦汉。由此可见,《考工记》和《周礼》的其他篇章一样,可能也并非一时一人所作,其内容在长期流传中进行了不断增益或修订。但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考工记》的记载大体可以与战国初期的出土文物相互印证,基本保存了战国及其之前的科技和手工艺发展成果,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
《周礼》全书约四万五千字,体大事繁,结构严密,原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因《冬官》亡佚,后补入《考工记》以代之,六个系统的职官构成一部宏大的建国规划和官制系统。这种职官体系的布局,蕴含着时人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春、夏、秋、冬,对应东、南、西、北四方,四官各管一方,时空相合,加上天地,六官即宇宙。每官之下各辖六十属官,总数三百六十,恰好与周天三百六十度、一年三百六十日相吻合,构筑了一幅天人同构、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的蓝图。其立意并非实录某朝某代的典制,而是为千秋万世立下法则。
天官冢宰为治官,职掌治典,也就是国政。冢宰,即太宰,为六官之首、百官之长,大致相当于后世宰相,起到职掌天下政务的作用,其所属从“大宰”到“夏采”,计六十三种职官,分别掌管国家法典和王宫戒令、寝舍、饮食、车服、医药、财货、府藏等宫廷事务。蒋伯潜认为:“天官一方统摄六官,一方兼掌杂务,恰似现代各机关中之总务处焉。”

地官司徒为教官,职掌教典,相当于后世的大司农、户部。其所属从“大司徒”到“槁人”,计七十八种职官,分别掌管国家山林川泽及其出产、户口及人民、农业、政教、赋税、市政、地方力役、赈济、祭祀等。此外,还有为民调解仇怨的调人,掌民婚姻的媒氏等。
春官宗伯为礼官,职掌礼典,相当于后世太常、礼部。其所属从“大宗伯”到“神仕”,计七十种职官,分别掌管吉、凶、宾、军、嘉五礼,包括礼仪规范的实施,礼器、服饰的使用,与礼相关的宗庙祭祀、乐、卜、筮、祝号,以及星象、天文历法、车旗、教育、历史文献等事务。
夏官司马为政官,职掌政典,相当于后世的兵部。其所属从“大司马”到“家司马”,计六十九种职官,主要掌管军队的编制、军事防御、出师征伐、民兵训练、部队校阅、军赋征收、军需军械管理等军政事务,以及与此相关的马政、戎事和田猎。
秋官司寇掌刑法、司法、治安等,相当于后世的刑部。其所属从“大司寇”到“家士”,计六十六种职官,分别掌管国家刑法、狱讼、监管役使罪犯和战俘、接待宾客,以及与刑法狱讼有关的盟约、禁令等事务。司寇属官中的“大行人”以下数职还从事与诸侯四夷的外交和礼宾工作。
天官到秋官,共计三百四十六种职官,地官司禄,夏官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掌疆、司甲,秋官掌察、掌货贿、都则、都士、家士等十一种官职职文缺。
由于《周礼·冬官》原文亡佚,冬官具体职掌已无法考证,据推测,冬官司马为“事官”,相当于后世的工部。补入的《考工记》是我国最早的手工艺技术汇编,其将社会职业分为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等六种,主要叙述百工及土木建筑之事,包括攻木、攻金、攻皮、设色、刮摩、抟埴之工的详细分类,各种工种所负责的工艺过程和制作器物的原理,不仅详其尺度、要求、要领,且善于总结经验和规律。“轮人”到“弓人”,计三十种工种,因“周人尚舆”,车工之事尤详,其次则详于弓矢,段氏、韦氏、裘氏、筐人、楖人、雕人等六种工种职文缺。
从各官职作用发挥上来看,《周礼》六官虽各有职属,官职间仍“联事通职”,需要既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六官的宗旨均是希望邦国和谐、百官团结、万民和乐,是一幅治国理政、安定民心的理想蓝图。
汉武帝之后的很长时间,《周礼》并未广泛流传。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进入秘府校理群书,《周官》被列入学官,著于《七略》,更名为《周礼》。《汉纪》云:“歆以《周官》十六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
 《隋书》云:“至王莽时,刘歆始置博士,以行于世。”
《隋书》云:“至王莽时,刘歆始置博士,以行于世。”

东汉初,刘歆门人杜子春设席授业,传授《周礼》之学,作《周官注》,一时注家蜂起,郑众、贾逵等鸿儒均仰承其说。《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云:“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河南缑氏杜子春受业于歆,还家以教门徒,好学之士郑兴父子等多往师之。贾景伯亦作《周礼解诂》。”
 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征引马融《周官传》曰:“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仓卒,兵革并起,疾疫丧荒,弟子死丧。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众、逵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记转相证明为《解》,逵《解》行于世,众《解》不行。”郑玄《周礼注疏序》云:“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
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征引马融《周官传》曰:“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仓卒,兵革并起,疾疫丧荒,弟子死丧。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众、逵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记转相证明为《解》,逵《解》行于世,众《解》不行。”郑玄《周礼注疏序》云:“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

《后汉书·儒林列传》云:“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
 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综览前儒,博综兼采,括囊大典,网罗众家,择善而从,著成《周礼注》,《周礼》始居“三礼”之首。就郑玄经学研究的成绩,王粲曰:“伊、洛已东,淮、汉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阙,郑氏道备。”
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综览前儒,博综兼采,括囊大典,网罗众家,择善而从,著成《周礼注》,《周礼》始居“三礼”之首。就郑玄经学研究的成绩,王粲曰:“伊、洛已东,淮、汉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阙,郑氏道备。”
 贾公彦认为“《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是以《周礼》大行,后王之法”。
贾公彦认为“《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是以《周礼》大行,后王之法”。
 孙诒让赞誉云:“郑注博综众家,孤行百代,周典汉诂,斯其渊棷矣。”
孙诒让赞誉云:“郑注博综众家,孤行百代,周典汉诂,斯其渊棷矣。”

在郑玄之后,王肃学贯古今,遍注群经,著有《周官礼注》十二卷。但王肃在经义说解上与郑玄立异,出现了《周礼》学史上的“郑王之争”。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虽政局动荡,但《周礼》研究著作仍不在少数,朝廷制定国家典章礼仪也以“三礼”为主要参考依据。且这一时期声韵学成就突出,《周礼》音义之作有较多涌现,干宝、刘昌宗、徐邈、李轨、聂熊等都撰有《周礼音》。
唐朝重视教育和人才,对西汉以来流传的经传进行整理、研究。为扭转六朝以来经说歧义的局面,颜师古奉命撰成五经定本,完成五经文字的统一;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人奉敕撰述五经义疏,完成《五经正义》;贾公彦奉敕撰《周礼疏》,全文刻入开成石经,列为十三经之一。贾公彦《周礼疏》是继郑玄《周礼注》之后又一部学术价值高、影响深广的《周礼》学著作,其疏解“极博核,足以发挥郑学”
 ,“发挥郑学最为详明”
,“发挥郑学最为详明”
 。在此之前,陆德明《经典释文》有《周礼音义》上下卷,是解释《周礼》经文读音、字义的重要著作。
。在此之前,陆德明《经典释文》有《周礼音义》上下卷,是解释《周礼》经文读音、字义的重要著作。
伴随宋学的兴起,《周礼》研究呈现繁盛局面。宋代研究整理《周礼》的著作见于《宋史·艺文志》的有:王昭禹《周礼详解》四十卷,杨时《周礼义辨疑》一卷,史浩《周官讲义》十四卷,郑谔《周礼解义》二十二卷,黄度《周礼说》五卷,徐焕《周官辨略》十八卷,陈傅良《周礼说》一卷,徐行《周礼微言》十卷,易祓《周礼总义》三十六卷,刘彝《周礼中义》十卷,胡铨《周礼传》十二卷,俞庭椿《周礼复古编》三卷,林椅《周礼纲目》八卷,郑伯谦《太平经国书统集》七卷,郑氏《周礼类例义断》二卷,魏了翁《周礼折衷》二卷、《周礼要义》三十卷等。
 宋熙宁八年(1075),朝廷将王安石所撰《书》《诗》《周礼》三经新义颁于学官,作为试士标准。有宋一代,王安石《周官新义》影响较大,学者望风披靡,效仿颇多。王与之《周礼订义》八十卷,采旧说五十一家,征引宋人之说达四十五家,对宋代《周礼》研究的成绩进行了总结。此外,龚原《周礼图》十卷、郑景炎《周礼开方图说》一卷、聂崇义《三礼图集注》二十卷、项安世《周礼丘乘图说》一卷等以图解形式注释《周礼》,是宋时《周礼》研究的特点之一。
宋熙宁八年(1075),朝廷将王安石所撰《书》《诗》《周礼》三经新义颁于学官,作为试士标准。有宋一代,王安石《周官新义》影响较大,学者望风披靡,效仿颇多。王与之《周礼订义》八十卷,采旧说五十一家,征引宋人之说达四十五家,对宋代《周礼》研究的成绩进行了总结。此外,龚原《周礼图》十卷、郑景炎《周礼开方图说》一卷、聂崇义《三礼图集注》二十卷、项安世《周礼丘乘图说》一卷等以图解形式注释《周礼》,是宋时《周礼》研究的特点之一。
元明时期,研究整理《周礼》的著作也达百部之多,但相较宋儒,创见不多。其间可称道者,元毛应龙《周官集传》十六卷,参考诸家训说,引据颇博;明王志长《周礼注疏删翼》三十卷,立足郑《注》贾《疏》,间采宋以后之说,时有发明;明王应电《周礼传》十卷、《图说》二卷、《翼传》二卷“于《周礼》之学,用力颇深”,“论说颇为醇正,虽略于考证,而义理多所发明”。

清代是中国传统学术集大成的时期。乾隆年间开三礼馆,接续康熙时的经籍编纂计划并纂修《三礼义疏》,参与者超过一百五十人。其中,《钦定周官义疏》四十八卷为《三礼义疏》第一部,但此书学术水平较宋明未见较大提升。清时,《周礼》研究著作宏富,名家辈出,或对《周礼》重新阐释、考辨名物,或对前人《周礼》研究的著作进行校勘整理、汇集刊刻,著作超过二百五十部。李光坡《周礼述注》二十四卷、惠士奇《礼说》十四卷、江永《周礼疑义举要》七卷、沈彤《周官禄田考》三卷、王鸣盛《周礼军赋说》四卷、戴震《考工记图》二卷、段玉裁《周礼汉读考》六卷、阮元《考工记车制图解》二卷等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孙诒让《周礼正义》凡八十六卷,约二百三十万言,征引宏富,博采众长,详密审慎,对历代研究《周礼》的重要成果几乎甄录无遗,代表清人经学新疏的最高成就。章太炎誉之为“三百年绝等双”
 。梁启超也说:“这部书可算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
。梁启超也说:“这部书可算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

伴随近现代学术发展,《周礼》研究新著大量涌现,郭沫若的《金文丛考·周官质疑》,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钱玄《三礼名物通释》《三礼通论》,钱玄、钱兴奇《三礼辞典》,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周礼引得附注疏引书引得》,野间文史《周礼索引》等均是影响较大的《周礼》学著作。
孔颖达《毛诗正义》云:“汉初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三传》之文不与经连,故石经书《公羊传》皆无经文……及马融为《周礼》之注,乃云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
 在《周礼》的流传过程中,一直到马融为《周礼》作注,注文才开始分条附在经文之下,也改变了汉初经典流传经注别行的情况。在这之后,即经注并行。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云:“考六朝以后,行世者只有经注本,无单经本。唐石经虽单刊经文,其所据亦经注本。如《周易》前题‘王弼注’,《尚书》题‘孔氏传’,《毛诗》题‘郑氏笺’,《周礼》《仪礼》《礼记》均题‘郑氏注’……是石经祖本本有注文,但刊时病其文繁,故存其序例,刊落其注耳。”
在《周礼》的流传过程中,一直到马融为《周礼》作注,注文才开始分条附在经文之下,也改变了汉初经典流传经注别行的情况。在这之后,即经注并行。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云:“考六朝以后,行世者只有经注本,无单经本。唐石经虽单刊经文,其所据亦经注本。如《周易》前题‘王弼注’,《尚书》题‘孔氏传’,《毛诗》题‘郑氏笺’,《周礼》《仪礼》《礼记》均题‘郑氏注’……是石经祖本本有注文,但刊时病其文繁,故存其序例,刊落其注耳。”

王国维提到的唐石经,即唐开成石经,因其开成二年(837)刊刻完成而得名,内容包括《周礼》在内的儒家十二部典籍。广政元年(938),后蜀主孟昶命宰相毋昭裔以开成石经为蓝本,增刻注文,刻《周礼》等十经于石,立于成都府学文翁石室(今石室中学);北宋时,增补为十三经;南宋时,晁公武又刻《石经考异》于诸经之后。此石经被称为蜀石经,又名广政石经,首次汇集儒家十三经,是我国古代唯一附有注文的石经,也是《周礼注》首次和唯一一次刻于石碑。但在南宋末,广政石经就已经被毁,现仅存七块,其中一块《仪礼·特牲馈食礼》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余六块均藏于四川博物院。1926年,刘体乾将其收藏宋拓广政石经《公羊传》《周礼》等残本影印发行,“丙寅(1926)四月,庐江刘健之以自藏本付印,发行处上海北河南路图南里本宅,定价银币陆拾元”
 。书题为《蜀石经残本》,版权页钤有“蜀石经斋”之印,全书共八册,一、二、三册为《周礼》。
。书题为《蜀石经残本》,版权页钤有“蜀石经斋”之印,全书共八册,一、二、三册为《周礼》。
五代后唐长兴年间,始议雕版刻印经书。《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云“(长兴三年二月)辛未,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从之”。《旧五代史·汉书隐帝纪》云:“(乾祐元年)五月己酉朔,国子监奏,《周礼》《仪礼》《公羊》《穀梁》四经未有印板,欲集学官考校雕造。从之。”
 《玉海》云:“周广顺三年六月丁巳,十一经及《尔雅》《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板成,判监田敏上之。”
《玉海》云:“周广顺三年六月丁巳,十一经及《尔雅》《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板成,判监田敏上之。”
 这个版本被称为五代监本,是目前所知《周礼注》的最早刻本。
这个版本被称为五代监本,是目前所知《周礼注》的最早刻本。
北宋时,因群经刻板时间日久,字体漫漶不清,于是以五代监本为依据,重新翻刻。《玉海》记载:“先是,国子监言群经摹印岁深,字体讹缺,请重刻板,因命崇文检讨杜镐、诸王侍讲孙奭详校,至是毕。又诏(邢)昺与两制详定而刊正之。”
 太宗端拱元年(988)到淳化五年(994),刻完《五经正义》;太宗淳化五年(994)到真宗咸平四年(1001)刻完《七经疏义》,其中包括《周礼疏》。《玉海》记载:“咸平三年三月癸巳,命国子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礼》……四年九月丁亥,翰林侍讲学士邢昺等及直讲崔偓佺表上重校定《周礼》……七经疏义,凡一百六十五卷。赐宴国子监。昺加一阶,余迁秩。十月九日,命摹印颁行。”
太宗端拱元年(988)到淳化五年(994),刻完《五经正义》;太宗淳化五年(994)到真宗咸平四年(1001)刻完《七经疏义》,其中包括《周礼疏》。《玉海》记载:“咸平三年三月癸巳,命国子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礼》……四年九月丁亥,翰林侍讲学士邢昺等及直讲崔偓佺表上重校定《周礼》……七经疏义,凡一百六十五卷。赐宴国子监。昺加一阶,余迁秩。十月九日,命摹印颁行。”
 真宗景德二年(1005)至大中祥符七年(1014)补刻讹缺经板。真宗天禧五年(1021)开始,再次对书印板进行重刻。宋室南渡后,依北宋监本翻刻群经注疏,称南宋监本。《玉海》云:“(绍兴)二十一年五月,诏令国子监访寻五经、三史旧监本刻板。……经籍复全。”
真宗景德二年(1005)至大中祥符七年(1014)补刻讹缺经板。真宗天禧五年(1021)开始,再次对书印板进行重刻。宋室南渡后,依北宋监本翻刻群经注疏,称南宋监本。《玉海》云:“(绍兴)二十一年五月,诏令国子监访寻五经、三史旧监本刻板。……经籍复全。”

除以上所述外,宋代可见的《周礼》经注本还有宋婺州唐宅刻本、宋刊巾箱本、残蜀大字本等。宋婺州唐宅刻本《周礼》总十二卷,卷三后有“婺州市门巷唐宅刊”牌记,卷四、卷十二末镌“婺州唐奉议宅”牌记。《中国版刻图录·周礼注》根据避讳情况推断其为南宋初期刻本。清杨绍和《楹书隅录》评价此本云:“盖宋时刊书多出坊贾,俗文破体,大抵类然。此本字学独极精审,几于倦翁所谓偏旁点画不使分毫差误。故宋讳之缺避较他本颇详,可知此本非特今世为罕见之珍,即宋椠各本亦莫与之京矣。”堪称“宝中之宝”。书中劳健跋亦赞云:“此则郑氏单注,完帙仅传,且为黄顾诸老所未见,真稀世秘籍矣。”此本曾经明代周良金插架,清代又经何绍基、英和收藏,之后入藏汪氏问礼堂,后入聊城杨氏海源阁,位列其所藏宋本“四经”之首。杨氏海源阁书散后,1934年,周叔弢收得此书,入藏自庄严堪,后捐献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宋刊巾箱本《周礼注》十二卷。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记载:“《周礼注》十二卷,汉郑玄注,存卷七至十一。宋刊巾箱本,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注双行十八字,细黑口,四周双阑,版心上方记字数,左阑外上方有耳记篇名。版匡高三寸,宽二寸一分。”
 王锷《郑玄〈周礼注〉版本考》认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与“傅氏所载者,款式、残缺卷数吻合,疑即为一书耳”
王锷《郑玄〈周礼注〉版本考》认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与“傅氏所载者,款式、残缺卷数吻合,疑即为一书耳”
 。
。
残蜀大字本,仅存《秋官》二册,一般认为是宋代孝宗时期的刻本,由清吴县杨偕时所藏,后赠予同窗黄丕烈,历汪士钟、陆心源等人收藏,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库,被列为“日本重要文化财”。
唐陆德明善言玄理,精通音义、校勘、目录之学,其采摭汉、魏、六朝音义之作二百余家,考证诸本异同,编为《经典释文》。宋代开始将《经典释文》中的内容附于《周礼注》。宋绍熙间闽刻本《周礼注》十二卷,附陆德明《释音》一卷,有清费念慈跋,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有1934年文禄堂影印本。金刻本《周礼》十二卷,附陆德明撰《周礼释音》一卷。书中避讳至宋高宗赵构止,当刻在南宋初年。《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定为宋刻本,赵万里先生根据刊刻字体和刀法特点,定为金刻本。此本经明项笃寿收藏,后钤“乾隆御览之宝”“太上皇帝之宝”诸印,清嘉庆年间入藏清宫天禄琳琅,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南宋时,为阅读方便,开始出现将经注与疏合刻的版本,南宋建州刻《附释音十三经注疏》因将陆德明《经典释文》音释部分附入注疏,故书名前冠以“附释音”,因其每半页十行,故又称“十行本”。清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以扬州文选楼旧藏建刻十行本为底本。但阮元所依据的并非宋世建刻原本,而是元代建刻坊本,存在较多讹误,是较大的遗憾。
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周礼疏》五十卷,经、注、疏合刻,共存世三本,分别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存二十七卷)、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图书馆。2019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全十二册,《序言》记:“八行本《周礼疏》用以缀合的经注与义疏,其文本源自北宋国子监刻经注本与单疏本,无俗本牵合变乱之弊;又以一地官府之力编校刊刻,不惜成本,其校勘精良、文字优胜,远非十行本及后世诸本可比。清阮元《周礼注疏校勘记》曾利用‘惠校本’,纠正十行本及闽、监、毛本大量讹误,此‘惠校本’主要体现的即八行本异文。但阮元所据仅为辗转传校之本,未能亲见原本,故多失校及误校。今日研读《周礼》郑注贾疏,八行本《周礼疏》实具有无可取代的价值。”
 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彭林教授点校整理的《周礼注疏》也是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为底本,参校唐石经、蜀石经及历代善本,是《周礼》研究的重要参考。
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彭林教授点校整理的《周礼注疏》也是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为底本,参校唐石经、蜀石经及历代善本,是《周礼》研究的重要参考。
明嘉靖中,李元阳在闽中据十行本重刻《十三经注疏》,称“闽本”;万历中,北京国子监据闽本翻刻,称明“北监本”;崇祯中,常熟毛氏汲古阁又据北监本翻刻,称“毛本”;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重新校刻《十三经注疏》,称“殿本”;嘉庆二十年(1815),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在南昌府学开雕,其中包括《附释音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本,称“阮本”或“阮刻本”。
今有林尹《周礼今注今译》、杨天宇《周礼译注》等,也是《周礼》研究的重要成果,可为阅读提供帮助。
《周礼》以职官系统为基本框架,构筑起严整完备的职官制度及政治和礼仪制度,体大思精,系统条贯,内涵极为丰富。钱玄《〈三礼辞典〉自序》云:
今试以《仪礼》《周礼》及大小戴《礼记》所涉及之内容观之,则天子、侯国建制、疆域画分、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役财用、冠昏丧祭、服饰膳食、宫室车马、农商医卜、天文律历、工艺制作,可谓应有尽有,无所不包。其范围之广,与今日“文化”之概念相比,或有过而无不及。是三礼之学,实即研究上古文化史之学。

《左传》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礼记》也记载:“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
《礼记》也记载:“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
 《周礼》作为周代官制和政治制度的记述,与当时的礼乐仪式、器物、道德法度一起,共同构筑了中华礼乐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千载,传承不息,中华文明之所以从未中断,原因就在于礼乐制度和仪式在文化碰撞、交流和融合中历经沧桑而不衰。在千载之后,继续研读《周礼》,依然有助于了解中华文化的高度与深度。
《周礼》作为周代官制和政治制度的记述,与当时的礼乐仪式、器物、道德法度一起,共同构筑了中华礼乐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千载,传承不息,中华文明之所以从未中断,原因就在于礼乐制度和仪式在文化碰撞、交流和融合中历经沧桑而不衰。在千载之后,继续研读《周礼》,依然有助于了解中华文化的高度与深度。
第一,《周礼》一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周礼》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为纲,详细记录了三百六十多种职官,对官员的级别、人员构成和职责范围做了精细的规定,其中既有六官的属官,也有地方官和职事官,内容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可以囊括国家治理实践,构成了由中央到地方基层组织以及各个行政机构之间层层相因、彼此制约、相互依存、井然有序的国家政权模式。官制体系之层级分明且职能完备,宏大而详密,为上古文献所仅见。虽然不排除有理想化的成分,但依然反映出当时的官制实际和设想。孙诒让盛赞《周礼》说,自黄帝、颛顼以至西周文、武二王的“经世大法,咸稡于是”
 ,对研究周代历史、官制、政治制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周礼》之后,历代官制往往遵循《周礼》的职官体系。从隋代开始实行“三省六部制”,吏、户、礼、兵、刑、工构成中央官制的主体,即仿照《周礼》六官设置,之后历代沿用。
,对研究周代历史、官制、政治制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周礼》之后,历代官制往往遵循《周礼》的职官体系。从隋代开始实行“三省六部制”,吏、户、礼、兵、刑、工构成中央官制的主体,即仿照《周礼》六官设置,之后历代沿用。
历史上,逢朝代更迭等重大变革,或政治、经济制度的革新,《周礼》往往是重要的援引和借鉴对象。王莽改制、西魏宇文泰任用苏绰改革官制、王安石变法等重要的革新都参考《周礼》,吸收其有益成分,对缓和社会矛盾、改善官民文教、富国强兵起到了关键作用。历朝修订典制,同样参照《周礼》。唐代开元十年(722),唐玄宗下诏书命徐坚等人依据《周礼》制定官制,成《唐六典》三十卷。之后,宋《开宝通礼》、明《大明集礼》都是在《周礼》的基础上有所损益。朝鲜的《经国大典》《经世遗表》也是以《周礼》为蓝本。
《周礼》“大宰”之职“八法”有“官成”“官计”,即各级官府年度工作总结和对官员政绩进行定期考核,“小宰”有“六计”之制——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即规定了从官员的声誉、办事能力、工作态度、道德品行、守法与否、辨别是非能力等六个方面考察官员政绩的制度,这对于秦汉以来历代官吏考核都很有影响。
 直到晚清八国联军入侵,慈禧挟光绪帝外逃,国难当头时,孙诒让在盛宣怀、费念慈的建议下,以《周礼》为据,撰写《周礼政要》,介绍西方国家的有关情况,阐述改革变法的必要性,并提出革新吏治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改革举措。《周礼》在两千年后,依然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
直到晚清八国联军入侵,慈禧挟光绪帝外逃,国难当头时,孙诒让在盛宣怀、费念慈的建议下,以《周礼》为据,撰写《周礼政要》,介绍西方国家的有关情况,阐述改革变法的必要性,并提出革新吏治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改革举措。《周礼》在两千年后,依然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
 研读《周礼》对研究历朝政治制度、典章规范及其沿革有重要作用。
研读《周礼》对研究历朝政治制度、典章规范及其沿革有重要作用。
第二,《周礼》一书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天官·冢宰》篇记载“掌建邦之六典”“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则治都鄙”至“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以九两系邦国之民”,详密严谨,宏纤毕载,呈现了诸侯拱卫王室的政治格局和儒法兼容、德主刑辅、礼法相济的治国方针;“官联”制度下六官互相协调、合作处理国家事务,显示了相当成熟的政治智慧,也为官员管理和协作提供范本;国家府库的管理、各类财务的收纳严密细致,相互制约,体现了高超的运筹和理财智慧。同时,《周礼》的职官设置虽然基本遵循“由天定人”,但以“得民”为安邦定国的基本旨归,反映了早期的民本思想。《周礼》以礼乐化民、治民,处处体现“仁政”精神,对稳定社会、促进休养生息有重要作用。
从《周礼》的流传和传播来看,自西汉末期由刘歆、王莽提倡,取得合法的官学地位,到成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列“三礼”之首,《周礼》对儒家经典文献的形成和儒家学说的传播也功不可没。
第三,《周礼》一书还具有重要的科技价值。因《冬官》遗失而补入的《考工记》书写了车轮、兵器、青铜器、玉器、农具等的制造,包含了当时物理、数学、化学、天文、生物、建筑、冶金、水利、纺织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上承殷商、西周青铜文化之遗绪,下启后代手工业制造之先河,对秦汉之后城市建筑、手工业生产等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考工记》在记述国都营建原则时写道:“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元世祖忽必烈入主北京后,刘秉忠参照《考工记》的这一记载,设计成元大都棋盘式的街巷,也奠定了之后明清两朝乃至今天北京城的基本格局。如故宫太和殿南面是皇帝治政之朝,北面是皇后掌管的市,是为“面朝后市”;左面是太庙(今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右面是社稷坛(今中山公园),是为“左祖右社”。明、清两朝沿用元大都建制,又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也基本遵循了《考工记》的设计原则。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多次引用并解释《考工记》,可见《考工记》不仅对我国古代科技发展影响深远,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考工记》在记述国都营建原则时写道:“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元世祖忽必烈入主北京后,刘秉忠参照《考工记》的这一记载,设计成元大都棋盘式的街巷,也奠定了之后明清两朝乃至今天北京城的基本格局。如故宫太和殿南面是皇帝治政之朝,北面是皇后掌管的市,是为“面朝后市”;左面是太庙(今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右面是社稷坛(今中山公园),是为“左祖右社”。明、清两朝沿用元大都建制,又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也基本遵循了《考工记》的设计原则。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多次引用并解释《考工记》,可见《考工记》不仅对我国古代科技发展影响深远,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
刘起
 :《〈洪范〉成书时代考》,《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第168页。
:《〈洪范〉成书时代考》,《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第168页。
[2]
刘起
 :《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650页。
:《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6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