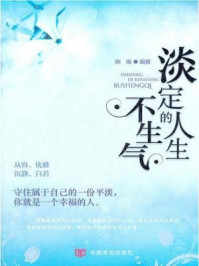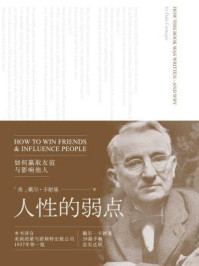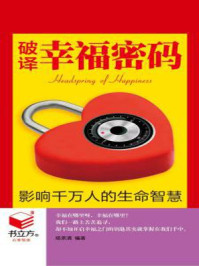曾有人对我说:“你应当全面清晰地认识自己。”
“然后呢?”
“爱自己。”
莉姐在高校就职,每每提起工作,总说和朝气满满的学生们相处,自己仿佛永远不会老去。可有一天她踌躇难言,犹豫了半晌方道:“你说,我是不是老了?思想落伍,不能体会现在的学生们的心思了?”
原来,这一届学生中有一名家境不佳而学习努力的孩子,经历如同“寒门出贵子,贫困生逆袭”的标准事例模板。
师者之心,看到一名试图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孩子,总会忍不住多关注几分。莉姐对这名学生颇多照顾,主动帮他申请勤工助学岗,时常留心他的动态,开导他、帮助他。
但人与人的思想和情感有时犹如篝火与寒冰般迥异,火焰在剔透的坚冰上映出耀眼的花朵,但这份温暖却难以穿透寒冰的冷漠。
莉姐的另眼相待最终没有酝酿出师生和乐的琼浆。以莉姐为师为长的心思看来,那名学生虽家贫然上进,必有作为,稍逊于人的出身更凸显其可贵;而学生有着敏感心思,只觉得旁人的目光都在自己的困顿处聚焦。
其实类似的“助人者和被助者”的故事并不罕见,莉姐平日行事也尽可能顾及学生的自尊心,唯恐表达善意却揭破孩子的疮疤。可惜,按照现在的流行说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雷点”,谁也不能摸清别人的“雷区”究竟是什么。
倾诉过这段以遗憾收尾的师生故事后,莉姐最终无奈地说:“这孩子要强,如果以后也一直这样敏感,日子会过得多累啊。”
美国心理治疗专家露易丝·海在《每一天爱自己》中写道:“生命从来不会卡死、停顿或腐朽,因为每时每刻都是崭新的。”
在漫长又匆匆、平凡且充满波折的人生路途中,如莉姐的这位学生那样敏感的人,可能在某段岁月中,无法爱上没有余钱买课外读物也不敢花费时间休闲娱乐的自己。但是,人生的河流滚滚向前,无论是否能将痛苦遗忘,是否能与苦难和解,总得学会给予自己的伤疤和缺陷更多温柔耐心的目光,才有机会看见新生的嫩芽。
听罢莉姐和学生的故事,我思潮翻涌回溯往昔,想起老家一位来往不多的妹妹。这位妹妹出身殷实之家,物质上并不缺少什么,却有一副消极自伤的性子。亲朋好友怕冒犯她,每与她交往多小心慎重。
前年春节我诸般事忙,未曾走亲访友,无意中发现她发了一条朋友圈:“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来不及细看,已被她匆匆删去。
我对着手机屏幕呆了片刻,思忖既然瞧见了她的动态,又值年节,或许该关怀一番,权当亲戚间的走动,遂发了条微信问候。
我们互道了声“和顺安乐”,聊了几句近况,她说起自己谈的朋友,似不经意般发过来一句:“不耐烦我是正常的,毕竟我也挺不耐烦自己的。”
朋友圈里流星般消失的“我与我周旋久”从我的眼前闪过,我和这位妹妹的亲近是乡邻间的相熟,而非长久相交相知,见她这般说,我一时拘谨起来,不知该以怎样的态度回她。
输入框里的文字飞速落下又被快速删除,我斟酌着写下:“你已经够好了,处不来的人大概就是没缘分。”
她在那边沉默了一阵子,接连发来一串消息:“我有时候怀疑自己有抑郁症,但有没有的,现在谁的心理没点毛病?我也懒得去查。”“我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我自己也不喜欢自己。”“像我这样的人,就算一开始别人愿意搭理我,时间长了,也被磨得不愿理我了。”“世上那么多好相处的人,干吗花那么多心思和精力在我身上?”
忆及从前与她相处的光景,联系她这番话语,我逐渐理解了她……
“我真是挺矫情的,大过年和你说这些,让大家的心情都不好了。”她又发来一句。
如果说一般人的心绪是一条河,那些幽怨愤懑纵掀起一时波涛,也终流去了;而这位妹妹的心绪却是一泊湖水,沉沉郁气淤积在心,难以泄去。
在许多长辈和同龄人看来,这样的孩子无疑是一个“净想些没用的”“别扭扫兴”的不合时宜之人,更糟糕的是,就连她本人也嫌恶这样的自己。
“郁结——自厌——更郁——更厌”,我在这位妹妹身上看到了一个难以脱身而出的怪圈,耳中恍惚听见她细微的呼救声。
想不起那天花了多少心思疏导安抚她,我想或许有些原本与她亲厚的人也在一次次帮她“消除内耗”中与她渐行渐远,而我也许有一天也会承担不起倾听者和安抚者的责任,任其往“自怨自伤”的泥沼中又下沉一些。
她唯有爱自己,才能完成自救。我这样想着,也反反复复在话语中传达这样的信息:“你得尽量爱自己。”
我没有从事法务工作的打算,却因这句话喜欢上了罗翔老师的刑法课程——“请你务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千次万次,毫不犹豫地救自己于这世间水火。”
想来,社会公众需有行为法度,每个人的心里也应有自理自治之法,那就是审视自己、规划自己、保护自己。
有人会觉得单一的个体太过渺小而不重视,因而自轻又不肯包容自己。那么,我们不如将自己视作一个国度,将躯体之康健比作军力,将一己之操守等同风气,以更加宏大的视角赋予自己更浓烈的色彩,以更细化的自我梳理发现所有在枯败的枝叶和落红的滋养下萌发的新芽,以欣欣向荣的心灵气象来宽容我这一“国度”的破碎和阴霾。
在充满成与败、聚与散、热闹与孤单的人生征程中,所有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提升都应当以“爱自己”为力量源头。
一个名为“焦糖”的网友曾分享自己的一些经历。
她说,她从小就是“讨好型”人格,认为所有的不足和错误都是自己的,“把自己踩到深渊中,看每一颗石子、每一株杂草都带着耀眼的光,而自己只敢迎光落泪,却不敢心生向往”。
后来她经历了很多分别,与朋友,与恋人……每一次她都会暗暗地想,是自己不够好,所以别人离开她是理所当然。
于是她愈发沉迷于网络,不愿意在现实世界中用自己的真实面目与人交际。直到一天,她偶然看到了这样一句话:“你有没有认真喜欢过自己,就像在一座废墟之中,千方百计搜寻并珍藏一块带花纹的断砖残瓦?”
“焦糖”说,她讨厌过自己超过一米七的身高,讨厌过自己不敢拒绝别人的请求,讨厌过自己看俄国文学的时候把一群“斯基”记混……“我就像一块酥糖,不仅一碰就掉渣,还黏糊糊的,不能如一粒干爽的灰尘一样被人轻松拂去。”她辛辣地点评自己,转而又道,“只敢辣评自己,可不敢议论别人。”
在本该潇洒恣意的年华,“焦糖”一心宽容他人却苛待自己,所幸她终于找到了自救的良方。
“我那时以为,拼命爱别人,别人才能向我伸出手,让我变得更好;后来发现,若我不爱我,我就不会爱人,别人也不会稀罕我的爱。”
读过“焦糖”的故事,我想起了和朋友看过的名为《深海》的动画电影。有过短暂幸福童年的女孩参宿,在生母断联、生父继母更关照新生幼子的家庭中逐渐丧失勇气、厌恶自己。在幻想的深海世界中,参宿的潜意识一次次向自己发动攻击,认定自己是招致“丧气鬼”的灾星。
朋友同我讨论,影片看起来是一个“拯救与被拯救”的故事,幻想世界中深海大饭店的南河船长、现实世界中为救参宿而共同坠入汪洋的“小丑”南河,无疑是她的救星。但细细想来,这也是一个女孩自救的故事。在象征着潜意识的幻想深海中,她曾做出追寻的努力,曾尝试抗击心中的“丧气”,她最终认可了被忽视的自己,成长为一颗能够承载他人愿望的星星。
王尔德说,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或许我们疲惫、沮丧,是有裂纹的茶杯或缺了瓣的花朵,但这不妨碍我们珍视自己,爱自己身上那些“毛茸茸的小问题”以及所有使我们与众不同的缺口。
不惧人言,不自我伤害,做自己,然后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