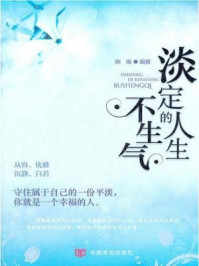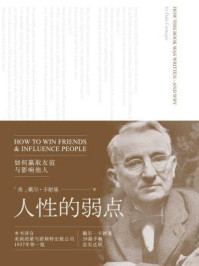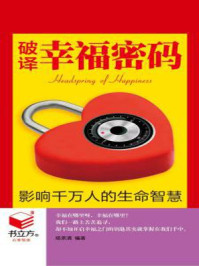从起点至终点,
每个人生命的轨迹似乎大同小异;
然而总有什么令生活不同,
那就是——我们自己。
偶尔路过地下商场略带斑驳的招牌,就会想起从前上学时“非主流”盛行的那几年。那会儿我和雯雯两个不爱交际的人是饭搭子,也约着在课余逛了几回商场。一次,她忽然在一排排亮闪闪的帽子前停住了脚步,毫不迟疑地掏出了自己的零花钱。
老实说,我的审美大概是不太“流行”的,可以随时撕拉掉的美甲片、搓一搓就掉的文身贴等“很不学生”的小饰品都是雯雯带我认识的,她无疑是我眼中的时尚达人。
彼时的我看着时尚达人雯雯拿着从午餐费中省出来、攒了大概三个星期才攒出的钱,买了密布铆钉、挂着链子的鸭舌帽,困惑地求问道:“究竟要怎样比较,才能看出哪一款铆钉更好看呢?”
孰料雯雯竟略带吃惊地看了我一眼,按着自己头上的“新宠”含糊地说:“都可以,反正就是这个样子的,大家都会喜欢的这种就行。”
我先是惊讶于不爱交际的雯雯做这些竟是为了合群,后又恍然明白了:人有的时候追寻与众不同,却又怕被集体排斥,是以苦苦追求的未必是自己喜爱的,装点自己的也未必是自悦的。
后来,我开始不自觉地留心起雯雯的真正喜好,发现美甲片是她喜欢的,文身贴是她不喜欢的,铆钉帽子也是她不喜欢的……等到“复古”流行自编水晶绳手链时,晶莹剔透的浅粉色、浅金色是她喜欢的,但她常买的水晶绳却是酷酷的深色系。
倘若是现在的我,一定会用很多话告诉她“做自己”“你喜欢才重要”,可惜那时终究笨口拙舌,不能漂亮而清晰地将“生活是自己的”理念吐露。
杨绛在《一百岁感言》中发自肺腑地说:“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生活在人群中的我们,有时候在乎“他人眼中的我”更甚于在乎“我”本身。
一件自己喜爱的衣服,想穿出门却要反复斟酌是否会招来他人的议论;一次普通的玩乐,想要发朋友圈却又担心引来一通“教育”……我们如履薄冰地聆听人群中抛来的只言片语,却听不到自己心灵深处的呼声。
从年少青葱到成熟干练,再到有一天垂垂老矣,我们一些并未言明的心思仍会从一次次选择、一次次应对中体现出来。而他人的视线,岂不是就像凸透镜后聚拢的光,初时是亮且暖的,后来变得炽热,有可能将我们焚烧?
都说“一千个人的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一千个人眼里自然有一千种对你我人生的不同看法。我们要是一直迎合他人的看法,就只好让自己疲于奔命。
或许,我们可以少问一句“他怎么看我”,多想一下“我怎样看待自己”;少听一语“你应当如何”,多思一番“我应当追寻什么”……
我们可以徜徉在阳光下,也可以奔跑在风雨中,唯独不应该战战兢兢地活在他人的眼光里。
曾在网络上看到一段很喜欢的文字:“你一定记得,不要做借光的月亮,而要做自己的太阳。”
生命历程中,他人的夸赞和支持如同燃烧的火把,随时都可能熄灭;只有我们的心中燃起的火焰,才能拥有恒久的光热。
大学做兼职时认识的学妹凌凌一直和我保持着不温不火的关系,有一天无意中发现我们俩的工作单位离得很近,这段重逢于茫茫人海的缘分让我们的往来频繁了些。
一天中午,凌凌和我相约于公司楼前小广场上。刚毕业没多久的她风中微醺,忍不住向我吐了一汪苦水。末了,她自嘲地说:“姐,我现在这样是不是很烦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也拿出来说一说。有的是比我难得多的人!”
我本打算柔声细气地好生安抚一番,但转念一想,空洞苍白地安慰一番又能有什么用呢?我没有和她在同一场雨中淋湿,怎么知道那场雨是不是冰凉刺骨、令人狼狈?于是我和她一条条分析起来。
是因为没有得到心仪岗位的内推,所以难过吗?——凌凌说,是因为自以为稳操胜算,结果却没得到那个岗位,在辅导员和几个知情同学面前失了面子。
是因为被信任的同学和实习单位的前辈在背后议论,所以难过吗?——凌凌说,是因为突然发现在很多人眼中,自己可能并不像原本以为的那样受欢迎。
是因为前途迷茫,面对理想和现实左右为难,所以难过吗?——凌凌说,是因为怕被人说有了工作还不珍惜,辞职考研变相啃老,做兼职插画师不过是小孩子的玩意儿。
问题已如白雪上的煤灰一样明显了,凌凌畏惧的不是生活中的琐碎麻烦,而是别人的指指点点。很多人都听过萨特《禁闭》中的名言“他人即地狱”,不能正确对待他人的目光,生活便将一片沉郁。凌凌显然正处于“他人目光的地狱”中。
我和她聊了许久,最终劝她:“不要去向别人索要力量,你自己才是力量的源头。”
后来,凌凌没有选择立刻辞职,而是先经营了一番做插画师的副业,有了一点名气后才走上了“边学习边画画”的路子。她和我视频连线时说,自己做着喜欢的事,有养活自己的底气,还能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不管最终有没有进入理想的院校,都不会为了这段经历而后悔。
“感觉自己就像一堆柴火,自己燃烧起来,不用别人给我光和热。”凌凌虽身上仍萦绕着疲惫,眼神中却有着灼灼的光亮。
偶然听到一句话:“人的情感,往往是孤独的。”
人生路漫漫,大部分路程是自己走的。我们身寄天地之间,不必与他人一样,也不必符合他人的心意,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太阳,源源不断散发着热气,将光芒洒落在前路上。
自然,人往往“当局者迷”,我有时也会因为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而陷入苦闷之中。
比方迁居他城那回,我那挂牌为“曼珠沙华”,有着充满神秘气息的别名“彼岸”,实则是一株普通石蒜的“室友”又因水土不服秃了叶子。当初搬家时,我恐它路上有个三长两短,便揣着花盆上了公交,上了火车,上了大巴。
有不少人好奇地问我:“你怎么带一盆土?”
当我试图给“室友”正名后,人们的好奇转变成各种各样的声音,“不吉利”说、“小年轻爱出风头”说、“白费力气”说纷至沓来。
我早已不是初出茅庐的“小菜鸟”,但一路被“热心人”指点过来,只觉得哪里都有人在对着我们这对组合嘀嘀咕咕。
如果我种的是兰草或茉莉,是不是就不会引发这么多的议论?
如果我把花盆包裹起来托运,是不是就不会被围观?
是不是我心里确实藏着“标新立异”的念头,所以才固执地带着我的“彼岸”来出风头?
很多时候,人能够对别人指点江山,却唯独看不到自己已处于陷阱当中。
当我坐在通往新住所的车上,和“室友”相顾无言之时,坐在旁边的一位女士——她看起来年轻如“大姐”,神色中又显露出“阿姨”才具有的阅历和智慧——向我搭话了:“装着土可沉呢,不然你把这盆放在我们中间吧,我给你挪点地方。”
自然而然地,她最终还是问了“室友”的出身来历,然后实心实意地赞叹起来:“听起来怪有意思!它开的花是网上图片里那种大红色的吗?”
惭愧!我“室友”的历史成绩只有小花一朵,也不是正统“彼岸红”的红,但在邻座女士的捧场下,我还是借着“室友”打开了话匣子。
听罢我这一路的遭遇,邻座女士不由笑了:“你喜欢这一盆花,喜欢了就是喜欢,有什么标新立异的?我喜欢兰花,难道还要怕别人笑我装模作样、故作风雅?”
她的一番话让我豁然开朗。
汪曾祺《人间草木》中的一篇,写到路遇的一对老夫妇一边散步,一边时不时到草丛里去寻觅,原来是捡拾枸杞子玩。他们完全不理会别人的打量和揣摩,遇到人搭话也坦荡自若且意兴盎然地回应,鹤发如雪却有着孩子般的烂漫之心。
不知这对伉俪是否遭受过疑惑乃至嘲弄的目光,但想来他们应当不似我怀抱石蒜时这般如芒在背、如坐针毡,因他们是那样沉浸于闲趣,将生活酿成了仅供自己酌饮的甘醴。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风露是我们自己的,花果也是我们自己的,与他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