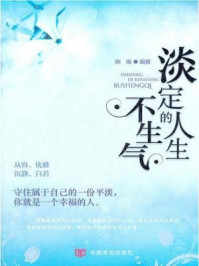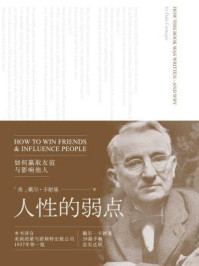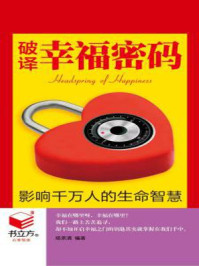纵然无数次经历自我怀疑,我仍然会重新爱上自己。
因为我很好,并将变得更好。
前段时间,沉寂许久的小学同学群突然活跃起来,大家纷纷倡议聚会。有人提议“找回从前的感觉”——从前班级有班服,这回聚会要穿差不多的衣服;从前班级纪律要求统一喝白开水,这次聚会也要统一饮品。
想法很有趣,但操作起来实在是有点困难。比方说饮品,就引发了一场“热议”。有人表示:“不理解爱喝茶的人,茶水究竟有什么好喝的?”有人当即反驳:“我还不理解你们喝咖啡的呢!”结果唯有普普通通的白开水最能获取同学们的一致认可,毕竟大家还不至于质疑“谁要喝白开水,人怎么会喝白开水”。
这番探讨使我想起此前另一批同学聚会时一位老同学的故事。
这位老同学从小就有一颗只给自己打工的雄心,自主创业几年后,公司经营得比较稳定了,需要扩大队伍,拓展新业务。
那天酒至半酣,老同学对我吐槽,说有个岗位在团队里相当于“黏合剂”,但这个岗位的员工因家里有事离职后,再招来的偏偏接二连三都是些“刺头”,团队老班底总反映与之磨合困难,最后好不容易留住了一个,能力也还算可以,但总感觉和原来的员工比起来不够出彩。
我安慰他说:“人才总有棱角。而且现在这位新员工的能力、性情等各方面都可以,是一位均衡型选手,谁说就不算是一种人才呢?”
我并不清楚老同学的那个岗位究竟需要怎样一个人,但若仅从“让多数人说可以才可以”这一点来看,或许只有既无与众不同的观点,也无鲜明脾气的“普通人”才能胜任吧。
在网上看到一个问题:“当你能理解所有人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你失去了自我认知?”
我忍不住反过来想:如果你能被所有人理解,是不是意味着你拔去了刺、磨掉了棱角、擦除了色彩,消除了一切可能招致非议的地方,掩埋了真实的自我?
骨头太硬,早晚会硌了别人的手;能发光,难免会刺了别人的眼。
并非人心皆狭隘,见不得他人的锋芒,只是人的立场不同,认知也不同,便使得那些绵软无刺的人往往更能避免批判意见。
初入社会的年轻人棱角尚存,往往被前辈们评价“锋芒毕露”。
彬彬是个很有个性的人,有话就要说,有事就要做,干脆利落。我与她曾一起合租过一段时间。
一天,彬彬很晚回来,发消息问我睡了没有,说自己没带钥匙。我听她的语气有异,飞奔出去打开大门一看,果然她喝了酒,额头顶着墙壁,似乎要睡着了。
好不容易把她拖进屋里,用养生壶煮点花果茶给她喝下去。过了一会儿,她清醒了点儿。
原来,她的小组里有个资历老的同事一直不太喜欢她,经常阴阳怪气地和她说话。不过其他组员都还算好相处,领导对她也算和气。但小组今天聚餐竟然没有一个人叫她,不小心被她发现了,他们才顺势邀请了她,还说当作团建了。
组里只有她一个人是新来的,老同事们想自行聚一聚也正常。她一开始推辞了,但大家热情洋溢地一再邀她,她也就跟着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心里有了意见,她再看组员们感觉不一样了。那个资历老的同事又在饭桌上阴阳她,其他人也只是和稀泥、拉偏架,甚至原来看起来很器重她的领导也说出“年轻人有的是机会,不要忙着出风头,沉淀自己才有更稳健的核心”这样的话。
领导不理解她,那么和家人倾诉呢?
“领导的话有道理,以后长点记性,别急着抢风头。”彬彬复述了妈妈对此事的回应。她嗓音干涩地说:“可我并没有刻意在组里揽活;而且谁帮了我,我从来都写得明明白白;觉得自己没做太多工作的时候,我会感到不好意思,让他们别带上我的名字。”这一刻,义愤填膺的她感觉仿佛全世界都不理解自己。
周国平《人与永恒》中有这样一句话:“被人理解是幸运的,但不被理解未必不幸。”
以他人的反应来判断自己的价值,只会使自己陷入可悲的境地之中。比起尽力争取被更多人理解,不如努力去做应做的事,成为一个无法被轻易替代的人。
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活成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样子。
和彬彬不一样,杳杳——我曾经的“City Walk(城市漫步)搭子”——是我见过的同龄人中少有的有锋芒又稳得住的人,我们称其为“长刺的水豚”。
大学毕业后,杳杳选择去大城市打拼,周围人都劝她留在老家,没必要这么辛苦要强,但她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几年后,繁忙的工作侵蚀了她的健康,她决定带着积蓄去一座三线小城,过简单的生活。这个决定又招致了身边亲友的一番批判,认为她没本事才被公司淘汰,不听人劝才熬坏了身体。
细细碎碎地听了杳杳的这些“家事”,我替她感到压抑和无奈。可杳杳的脸上始终挂着温暾的笑,她说:“没有谁能始终理解别人,也不可能所有人都理解你。”
杳杳所听过的这些话,大概很多人都曾听过。
品行、能力、梦想追求,只要有一星半点与旁人的认知不符,便可能迎来劈头盖脸的质疑声,原本的热情、鲜活、个性被这些质疑声所消磨。而杳杳面对这些,总是会沉静地说:“我觉得我自己很好。”
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莫与弹。
就像有人说的,没必要让所有人都知道真实的你,也没必要让每个人都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懂你的人自然会懂,信你的人自然会信。
何必试图争取所有人的理解?我们大可以将那些因认知不同而生出的质疑声当作过耳清风,心中坚定地认为“我很好,我不怕做个有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