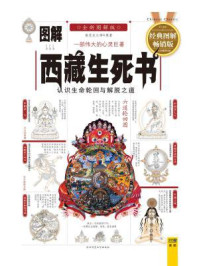精神分析学是一门庞大的话语,拥有数量庞大的专门概念。在这些概念之中,毫无疑问,无意识(the unconscious)是最为基本的概念,精神分析学就是关于无意识的科学。自弗洛伊德创建精神分析学以来,精神分析学家对无意识的理解都与弗洛伊德不尽相同,比如分析心理学派的荣格(C.Jung),社会文化学派的沙利文(H.S.Sullivan)和弗洛姆(E.Fromm),自我心理学派的哈特曼(H.Hartmann)和埃里克森(E.H.Erikson),对象关系学派的克莱因(M.Klein),拉康学派的雅克·拉康,等等。其中,以荣格为代表的分析心理学派和以沙利文与弗洛姆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学派最为背离弗洛伊德的理论,因为他们剥除了无意识的内核性本能。最为忠实于弗洛伊德的则是拉康,因为他创造性地重新阐释了无意识,从而复兴了精神分析学。因此,本文将着重阐述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以及拉康借助现代语言学对这个概念的重新阐释,他们二人对无意识的解释至今仍然是理解这一概念最为重要的资源。
在弗洛伊德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无论他探讨的是梦、症状、失误动作,还是欲望、自我和人格,抑或是艺术、宗教和文化,无意识始终是他的事业核心。为了探索无意识,弗洛伊德先后提出过三种观点,即地形学的、动力学的、经济学的观点,这三种观点构成了他的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的枢轴。然而,无意识既是精神分析学大厦的基石,也是弗洛伊德毕生拼搏但又最终未能圆满解决的难题。
作为元心理学的三大枢轴之一,地形学观点(the topographical point of view)是弗洛伊德最早提出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弗洛伊德认为精神机器(the mental apparatus)由不同的心灵区域构成,不同的心灵区域受不同程序支配。早在《科学心理学方案》(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1895)中,弗洛伊德就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心理地形学理论。在此,他将精神机器区分为意识(the conscious)、前意识(the preconscious)和无意识(the unconscious)三个区域。处于意识区域之内的乃是各种能够直接为主体所觉知的观念,处于前意识区域之内的乃是那些虽然暂时不在意识区域之内,但随时可以被主体感知的观念,而处于无意识区域之内的则是那些因为受到压抑而不可能被主体感知的观念。弗洛伊德提醒我们,这三个区域不是存在于人的身体结构之中,而是存在于人的心理结构之中。这就是人们熟知的第一个地形学观点。
随着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弗洛伊德发现这一地形学不足以对付病态的自恋,因为它无法把自我安置到任何一个心灵区域,因为自我既是意识的,也是无意识的;它也无法安置主体在个体发展过程中内化的那些社会价值与道德法则,因为主体虽能明确意识到这些法则的存在,但对这些法则的服从又是无意识的。因此,在《自我与本我》( The Ego and the Id ,1923)中,弗洛伊德提出了第二个地形学观点,把精神机器分为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根据这个观点,无意识不再被当作精神机器中一个单独的区域,甚至在性质上也不尽相同,因为无意识不仅存在于本我之中,同时也存在于自我和超我之中。第二个地形学观点充分考虑到了无意识的复杂性,尤其有助于心理人格的分析。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无意识的核心地位,不利于精神分析的深化。此外值得指出的是,第二个地形学观点并未取代第一个地形学观点,而是与之构成一种相互补充的辩证关系。
作为元心理学的枢轴之二,动力学观点(the dynamic point of view)研究的是运行于精神机器之中的各种力量对抗、结合和相互影响的方式。其实,这种研究无意识的观点从弗洛伊德开创精神分析学之初就存在,并贯穿其学术生涯,只是到他写作《压抑》(Repression,1915)时这一观点才得到集中表述。动力学观点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的基础之上:心灵之中运行着各种不同的力量,心灵就是这些不同力量相互冲突的场所。为了减少或者消除这些冲突引发的不快,精神机器使用了一些不同的机制,而压抑(repression)就是所有机制中的原型。借助压抑,精神机器改变了各种驱力(drive)的观念代表所处的地形学位置。由此,通过使某些驱力或者驱力的某些方面(驱力总是包含三种要素:驱力、驱力的观念代表、与驱力相应的情感)成为无意识,它保护主体不因一些相互冲突的欲望而感到痛苦。除了压抑之外,与动力学观点密切相关的还有投射(projection)、否认(disavowal)和排斥(foreclosure)等许多概念。
投射原本是光学和几何学中的一个术语,意指将某一影像投射到一个屏幕上,或者将某一形状投射到另一个平面上。在精神分析学中,投射主要指驱力的观念代表在主体内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位移,比如在恐惧症中,主体将引发恐惧的内部的力比多冲动投射到外在的马、公鸡或者广场、集市之上;还有一种心理投射表现为主动与被动之间的位移,主体将自己的欲望、思想或者感情投射到另外一个主体身上,比如,一个对伴侣不忠的人通过指控其伴侣不忠来保护自己免受背叛伴侣所引发的道德谴责。否认是另一种防御机制,它是一种心理行为,其特征在于拒绝接受某种知觉到的现实,因为这一现实会对主体产生一种创伤性效果。比如,幼儿发现女孩没有阴茎但拒不承认,相反,他会认为女孩和男孩一样具有阴茎。否认就是对阉割的否认,性变态与否认密切相关。值得指出的是,弗洛伊德在探索狼人病例时提醒我们,否认阉割与承认阉割是密切相关的,或者说任何否认都伴随着承认。主体一方面在自我的意识区域中接受象征阉割和性别差异,另一方面在自我的无意识区域中却拒不接受象征阉割和性别差异。这两种对立的态度互不干扰,对自我几乎没有影响。对阉割的否认之所以能在性变态中发挥重要作用,就是因为它伴随着承认。与动力学观点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排斥,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和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共同主编的英文版《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将Verwerfung翻译为repudiation,但拉康将其译为 forclusion ,与后者对应的英语则是foreclosure。这个词语的本义是指因逾期而丧失权利,就精神分析学而言,就是指主体因为没有按期接受“父亲的名字”(name-of-the-Father),从而彻底丧失了进入象征秩序(symbolic order)的能力。弗洛伊德在研究防御时提出了这个概念,但并没有详细阐述它,只是扼要地解释道:“自我拒绝了某个不兼容的观念及情感,表现得就像这个观念根本没有被自我想到过一样。” [1] 弗洛伊德后来在研究施瑞伯(Schreber)的病例时认为,施瑞伯的症结在于他拒不接受父亲的权威,甚至决不接受父亲的存在。“排斥”这一概念后来获得它在精神分析学中的分量,要感谢拉康的改造。拉康认为,排斥不是对某种知觉现实或者某种外在事物的拒绝认可,而是对“父亲的名字”这个能指的彻底排斥。也就是说,“父亲的名字”从未被引进主体的象征秩序,从一开始它就被排斥了。排斥是一种原始的防御机制,因为被排斥的能指并不是先被铭刻进了能指链或象征秩序,然后才被排斥出去的;排斥是对这种铭刻本身的排斥,因此“父亲的名字”这个能指从未进入主体的象征秩序。 [2] 正如否认是性变态的核心机制,排斥是精神病的核心机制。精神病的本质就在于“父亲的名字”被排斥了,以致能指链进入了一条德里达所谓的无尽的延异之路,意义彻底失去了可能性。
经济学观点在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中同样出现得很早,至少在《性学三论》(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1905)中就已经基本形成,十年之后在《本能及其变迁》(Instincts and Their Vicissitudes,1915)
 中趋于成熟。无意识的经济学观点根据贯穿并激发心理事件的那些力量(forces)的强度来对付这些事件。这种观点基于这样一种假设:精神机器被投资了一些为驱力所特有的力量,这些力量在强度上或者天生不同,或者因为驱力的变迁而受到不同的投资。弗洛伊德提出这种观点既是为了根据运行于心理事件之中并激发心理事件的那些能量的强度,以对付个体成长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些心理事件,也是为了描述原始能量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这些能量由此而改变的强度。1920年以后,经济学观点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经济学观点密切相关的概念是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和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以及贯注(cathexis)、取消贯注(decathexis)、反贯注(anticathexis)、超级贯注(hypercathexis)和宣泄(discharge)等。
中趋于成熟。无意识的经济学观点根据贯穿并激发心理事件的那些力量(forces)的强度来对付这些事件。这种观点基于这样一种假设:精神机器被投资了一些为驱力所特有的力量,这些力量在强度上或者天生不同,或者因为驱力的变迁而受到不同的投资。弗洛伊德提出这种观点既是为了根据运行于心理事件之中并激发心理事件的那些能量的强度,以对付个体成长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些心理事件,也是为了描述原始能量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这些能量由此而改变的强度。1920年以后,经济学观点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经济学观点密切相关的概念是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和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以及贯注(cathexis)、取消贯注(decathexis)、反贯注(anticathexis)、超级贯注(hypercathexis)和宣泄(discharge)等。
鉴于人们对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尽管掺杂着许多误解),这里姑且只简单介绍一下贯注、取消贯注、反贯注和超级贯注这几个概念。贯注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癔症研究》( Studies on Hysteria ,1895)和《科学心理学方案》中。贯注指的是精神机器将精神能量(主要是力比多)投注到某一对象身上,这个对象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身体部分,或者甚至是某种精神元素。精神冲动(impulses)的组织、症状和退化之间的相互作用都与贯注有关。观念的产生必然是能量贯注的结果,没有贯注就不会有观念。同样,情感如果不能得到能量贯注,或者只得到很少的能量贯注,就不会被固定在意识之中。取消贯注指精神能量从贯注对象撤回或者撤回的结果。在《哀悼与忧郁症》(Mourning and Melancholia,1917)中,弗洛伊德认为忧郁症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主体不能正常地将力比多能量从一个业已失去的对象身上撤回来。因此,取消贯注主要是一种自我保护措施。反贯注最早出现在《释梦》(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1900)中,后来在《无意识》(The Unconscious,1915)和《抑制、症状和焦虑》( Inhibitions,Symptoms,and Anxiety ,1926)中得到更为深入的阐释。反贯注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误解的概念,主要是因为弗洛伊德给出的解释过于含蓄和简略,非常容易让人将其视为一种防御机制。受到反贯注的对象自然是与社会法则不兼容的观念,但实施反贯注的代理是谁?如果把反贯注与防御混同,那就会让人认为实施反贯注的代理就是自我。果真如此,那么反贯注和压抑就无法区分了。事实上,反贯注的动力不是来自自我,而是来自原始压抑形成的无意识内核。如果说贯注的目的是将本能的某些观念代表(思想、形象、记忆)努力向外推进到意识之中,那么反贯注的目的则是由于原始压抑而形成的无意识内核将这些观念代表重新向内吸引回来。至于超级贯注,弗洛伊德在《无意识》中明确指出,它是意识得以形成的机制,其基本特征就是物表象(thing-presentation)被赋予了与之匹配的词表象(word-presentation)。
纵观这三种解释无意识的观点,地形学的观点有助于确认无意识的存在及其在精神机器中的位置,但不能解释无意识的运作机制;动力学的观点有助于解释无意识的运作动力,但不能解释其运作机制;经济学的观点有助于解释驱力之变迁以及原始能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但不免有堕入生物学主义的危险。也许是因为这三种观点各有利弊,所以弗洛伊德从来不曾认为它们可以彼此替代,而是将其当作探索无意识的三种共存的视角。正因如此,弗洛伊德指出,当我们在地形学方面、动力学方面和经济学方面成功描述了一个精神过程时,我们才能说这样的描述够得上是一种元心理学的表达。这三种观点在弗洛伊德思想中产生的时刻并没有可以清晰分别的先后顺序,这一事实也可以证明它们的确不存在互不相容的关系。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无论是地形学的观点、动力学的观点,还是经济学的观点,都和压抑密切相关,不理解压抑,就不可能理解无意识。这就不难理解,虽然弗洛伊德有一篇名曰《压抑》的单篇论文,但他对压抑所做的最深刻的探索却出现在同年写作的论文《无意识》中。所谓压抑,就是指主体将一些令人不快的观念代表(思想、形象、记忆)驱逐并使之与意识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这些观念代表与自我不相容。一般而言,人们认为无意识源于压抑,起初弗洛伊德也是持这种观点;但随着研究逐渐深入,他发现事情绝非如此简单。弗洛伊德认为,本能的唯一使命就是得到满足,因此单纯依靠压抑是不可能将那些与自我不相容的观念代表排除出意识的;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在主体的心灵深处还必须要有一个原始内核,这个内核不是为本能的观念代表提供冲进意识的动力,而是将这些观念代表吸引回无意识中来。如果没有这个发挥内吸作用的内核,压抑根本不可能实现其目的,让主体获得基本的宁静。因此他说:“我们有理由假定,存在着一种原始压抑(primal repression),它是压抑的第一阶段,表现为本能的某种精神(观念)代表不能进入意识。由此就形成了固定(fixation);这个精神(观念)代表从此就不再改变,本能一直隶属于它。” [3] 主体为了避免痛苦,实现与现实的和解与平衡,必须将与自我不相容的那些本能的观念代表驱逐出去,然而尽管他为此调动了原始压抑和正常压抑,但是被压抑者依然会竭尽全力回到意识中来。正是被压抑者的回归导致了梦、各种神经症和失误动作。因此,压抑在结构上分为三个阶段:固定(原始压抑)—压抑—被压抑者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尽管弗洛伊德就无意识提出了地形学的、动力学的和经济学的观点,并探索了压抑和原始压抑与无意识发生的密切关系,让它们共同为解释无意识服务,但他终其一生仍然未能对无意识做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这三种观点都不能揭示无意识的存在论身份,也就是说,不能告诉我们无意识究竟是什么。这三种观点无疑对揭示无意识的存在、运作动力和运作机制具有至关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它们无一能够揭示无意识的本质。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需要另一种新的方法,一种语言学的方法。事实上,在弗洛伊德开创其精神分析事业的全部历程中,他一直都在和语言打交道。他独辟蹊径开创的自由联想诉诸的是语言,他不辞辛苦地解释梦的内涵以及梦的工作诉诸的也是语言,他研究诙谐与无意识的关系诉诸的还是语言,他探索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诉诸的更是语言。
如果说语言学的观点早已以一种实践形态存在于弗洛伊德的事业中,那么除了上述理由之外,下面两个事实与此更为相关。其一,早在《释梦》中,弗洛伊德就已经指出,无意识系统的运作机制是两种基本程序(primary processes),即压缩(condensation)和移置(displacement);而意识系统的运作机制则是次要程序(secondary processes),即普通语言采用的隐喻(metaphor)和换喻(metonymy)。基本程序和次要程序的区别在于,精神机器在无意识系统中受快乐原则的支配,将承载力比多的观念代表随意进行压缩和移置;而在意识系统中,精神机器受现实原则的支配,只能按照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来表达自己。在无意识系统中,观念和观念代表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偶然的、任意的、临时的、个人的,力比多与任何观念代表之间没有约定的关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压缩和移置不是自我为了逃避稽查而采取的策略,它们是无意识系统固有的运作机制。在意识系统中,所指(signified)和能指之间的关系只是在初始时刻才是任意的,此后便确立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稳定关系,力比多在进入这个系统或进入这种语言时,必然会受到约束和限制。其二,在1915年完成的论文《无意识》中,弗洛伊德甚至确信自己发现了区分意识与无意识的标准:“我们现在似乎突然知道了意识表象和无意识表象的区别。不像我们以前想的那样,二者并不是相同的内容被各不相同地登记到了不同的心理位置,也不是贯注在同一个地方有两种不同的功能状态;而是意识表象包含了物表象和属于这一物的词表象,而无意识表象只有物表象。无意识系统包含了对对象的物-贯注,这是最初且真实的对象-贯注;意识系统则来自这一物表象因为和与之对应的词表象被联系在一起而被过度贯注。” [4] 虽然弗洛伊德在此明确将无意识排除出语言,但他借助物表象与词表象的离合来区分无意识与意识的思路深刻地启发了拉康根据语言学来思考无意识的性质。
由于历史局限,弗洛伊德未能明确指出,压缩其实就是隐喻,移置其实就是换喻,无意识的运作机制已然是语言学的机制了。拉康认为,压缩之于隐喻,正如移置之于换喻,它们都是话语的基本运作机制,因此无意识本质上就是一种话语,只不过是一种不同于一般话语的话语。拉康能够更进一步,要感谢罗曼·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雅克布森发现,任何语言符号都涉及组合和选择两种结构模式:“组合:任何符号都是由一些(更小的)构成性符号构成的,并且/或者只有与其他符号结合在一起时才能出现。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语言单位都既是更简单的语言单位的语境,同时又在一些更加复杂的语言单位中寻找自己的语境。因此,语言单位的真实聚合把它们结合为一个更高级的语言单位——组合和编织是同一种运作机制的两个方面。选择:选项之间的选择意味着存在用一个选项代替其他选项的可能性,各选项在某一方面等值,在另一方面则不同。因此,选择和替代是同一种运作机制的两个方面。” [5] 的确,正如雅克布森承认的那样,索绪尔(F.de Saussure)对这两种活动在语言中发挥的基本作用具有清楚的认识,但由于屈从于传统观念,索绪尔只注意到了语言的线性特征,因此只有时间序列上展开的组合原则得到了他的认可。雅克布森将针对共时而不在场符号的选择原则和针对历时而在场符号的组合原则相提并论,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成就,因为语言的结构法则正是由这二者共同构成的,缺一不可。
拉康立刻发现,雅克布森的组合和选择正好对应了语言最为根本的两种结构法则,即换喻和隐喻;而弗洛伊德发现的梦的两种最为根本的运作机制——移置和压缩,从语言学上说,其实也就是换喻和隐喻。拉康指出,换喻的基础就是从词语到词语的连接。就精神分析学来说,换喻不仅只是一种避开社会稽查的力量,它本身就是无意识的运作机制。但这种给无意识提供领地的机制同时也让解读无意识变得不可能,因为在从能指到能指的移置过程中,所指(无意识)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拉康为换喻给出的公式是:

在这个公式中,括号中的“-”表示的是,在从能指到能指的移置过程中,隔离能指与所指(无意识)的栅栏始终没有被穿越。这个公式表明:“正是能指到能指的连接使那种省略得以存在,凭借这种省略能指将存在之欠缺安置到了对象-关系之中,并利用意义的指引作用为它(能指)赋予了针对这一欠缺的欲望,而这个欠缺是由能指支撑的。” [6]
与换喻不同,隐喻的创造性火花并不来自两个形象的并列,也就是说,并不来自将两个同等实现的能指并列起来。所指(无意识)闪现在两个能指之间,但其中只有一个能指显现,另一个能指并不出现在能指链中,这个被隐藏的能指以其与能指链中其他能指的联系而存在。一个词语取代另一个词语,这就是隐喻的公式:

在隐喻的公式中,括号中的“+”表示隔离能指和所指(无意识)的栅栏被穿越了,破译隐喻就可以揭示能指的无意识内涵。这个公式表明:“正是在能指对能指的替代中,某种诗意的、创造性的意义效果被生产出来了,换句话说,这种替代使得当前谈论的意义现身存在了。” [7]
但是,当拉康言简意赅地断言“无意识就是大他者的话语” [8] 时,他的这一箴言似乎与弗洛伊德的论断直接对立,因为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本能的观念代表被意识拒绝,是因为它只有物表象,而没有与之相应的词表象。如果拉康真的如其所说,要让精神分析“回到弗洛伊德”,如果“无意识就是大他者的话语”,那么如何理解无意识只有物表象?一言以蔽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能指?
拉康并不认为自己背叛了弗洛伊德的教导,在他看来,无意识中的物表象本身就是一种能指。在弗洛伊德积极建设精神分析学的时代,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的成果还没有辐射进语言学之外的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弗洛伊德似乎也只是把语言笼统地当作指示事物或者观念的符号。而当拉康着手改造精神分析学的事业时,索绪尔的语言学已经渗透进了几乎每一个人文学科,精神分析学更不例外。拉康不仅借鉴了索绪尔的语言学,还改造了它。首先,拉康认为,语言不是一个由符号(symbols)构成的系统,而是一个由能指构成的系统。其次,他颠倒了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将能指放到优先地位,因为所指只是能指相互区分的产物(这一点其实已经是索绪尔的题中应有之义)。最后,拉康改造了能指这个概念本身的含义。在索绪尔那里,能指就是符号的音响或形象所造成的心理效果,与所指构成对应关系。拉康的能指不再与所指构成对应关系,而且能指表达的也不是所指;拉康认为,能指就是“替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的东西” [9] 。也就是说,虽然所有能指都指向主体,但能指表达的只是另一个能指。最为重要的是,拉康完全超出了一般语言符号的范畴去理解能指,认为自然和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作为能指对主体起作用。也许正因如此,他说:“每一个真实的能指就是什么也不表示的能指。能指越是什么也不表示,它就越是不可摧毁。” [10] 基于这种认识,拉康认为,一切事物,只要它开始按照语言的基本法则(隐喻和换喻,也就是压缩和移置)运转,它就已经是一个能指了,就此而言,弗洛伊德所谓的物表象本身已经就是能指了。拉康认为,弗洛伊德早就肯定了“梦的运作遵从的是能指的法则”,可惜“从一开始,人们就忽视了在弗洛伊德以最精确、最明白的方式立刻为无意识指派的身份中,能指的建构作用” [11] 。
无意识话语与意识话语的区别不仅在于一者服从快乐原则,一者服从现实原则,还在于二者使用的能指大为不同。作为一种话语,无意识使用的能指看似是一般能指,其实不然。在无意识系统中,精神机器凭借压缩和移置,随意地把一些基本能指(观念代表或记忆痕迹,比如音响和形象)整合进普通语言既有的一般能指中,但其所指已经完全不同了。拉康认为,无意识不是只有物表象,没有词表象;恰好相反,构成无意识的物表象本身就是能指。无意识借以表达自己的能指当然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能指,也就是约定俗成的词语;但是,无意识还有一些更为基本的能指,一些在字典里面查询不到的能指——因为这些能指不是约定俗成的,也不具有特定的所指与之对应。无意识的基本能指是一些音响和形象,是物表象本身,也就是拉康所说的最不具有能指特性的东西。
1960年在博纳瓦尔(Bonneval)召开的关于无意识的研讨会上,拉康的第一代学生拉普朗什和勒克莱尔提交了他们合写的论文《无意识:精神分析学研究》。拉普朗什和勒克莱尔写作此文原本是为了阐发拉康的学说,但拉康并不领情,因为他明显感到两位作者对无意识的理解与自己并不一致。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二者对语言和能指的理解仍然没有达到拉康的高度,以致最后竟然得出了一个与拉康直接对立的结论:“无意识是语言的前提。” [12] 而拉康认为,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是语言作用于主体的效果。尽管事与愿违,但拉康的另一个学生安妮卡·勒迈尔(Anika Lemaire)认为,拉普朗什和勒克莱尔在论文中分析的菲利普(Philippe)的梦,对我们理解拉康所说的能指,也就是无意识的基本能指,仍然具有非常适切的启发意义。 [13] 菲利普是一个30岁左右的神经症患者,下面就是他的“独角兽的梦”:
在一个小镇荒凉的广场( place )上,很奇怪,我在寻找某种东西。莉莉安( Liliane )——这个人我并不认识——出现了,她光着脚,对我说:“我好久没有看见这么好的沙滩( plage )了。”我们在森林里,那些树木的颜色看上去很奇怪,带有鲜艳而简单的阴影。我想森林里一定会有很多动物,正当我想说出这个想法时,一只独角兽( licorne )越过了我们的小路;我们三个一起,向一块林中空地走去,我们觉得空地就在下面不远处。(梦醒后,我口渴难耐。——菲利普叙述这个梦时所做的补充) [14]
根据弗洛伊德的教导,我们知道,梦的材料有两个来源:最近的生活细节和幼年的愿望。与菲利普的梦有关的最近的生活细节是:菲利普曾和他的侄女安妮( Anne )在森林里步行。当时他们做了一个跟踪游戏,并在一个山谷的底部发现了鹿和雌羚的踪迹,山谷里有一条小溪,表明有动物曾在某处饮水。当时安妮说:“我好久没有看到这么鲜艳的石南花( bruyère )了。”借助自由联想,菲利普提供了与这个梦有关的三个童年记忆:(1)大约三岁时,菲利普曾经在一个外省小镇度过了一个夏天,那个小镇的广场上有一处独角兽喷泉。当时,他曾用双手从翻涌的泉水中掬水喝。(2)他曾在瑞士山中行走,那里森林茂密,到处是鲜艳的石南花。当时他曾努力模仿一个比他大的孩子,将双手合成海螺形状吹口哨。(3)三岁时,他曾和母亲的表姐妹莉莉( Lili) 在大西洋的海滩( plage )上玩耍。整整有一个月,他都在用一种严肃而且坚持不懈的语气对她说“我渴”,以致莉莉戏称他为“菲利普-我-渴”( Philippe j'ai-soif )。
仅凭这个梦本身,其含义不易理解。但菲利普在讲述完这个梦后立刻补充说,梦醒之后,他感到口渴难耐。当我们把这一细节和他在自由联想时回忆起的上述三个童年事件联系起来时,这个梦与指向莉莉的口腔驱力之间的关系就一目了然了。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再把这种口腔驱力与梦中出现的独角兽联系起来,也许这个梦的深层含义就得到了揭示:拒绝阉割。如果这个梦表达的是菲利普追求口腔驱力的满足和拒绝阉割,那么这个话语是如何表达出来的呢?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使用何种方法又借助何种能指来表达的呢?
无意识话语使用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能指,不是普通的语言符号。就菲利普的这个梦而言,我们仅凭这个梦的明显内容(the manifest content),也就是构成这个梦的文本,是不可能把握到它的潜在内容(the latent content),即无意识含义的。甚至即使我们求助于围绕这个梦的自由联想,也不可能达此目的。因为无论是小镇广场上的独角兽喷泉,还是瑞士山中鲜艳的石南花,抑或是小镇荒凉的广场;无论是从泉池中合手掬水畅饮,还是在瑞士山中学吹口哨,抑或是追着莉莉说“我渴”——这些都不可能将我们最终指引向这个梦的无意识话语本身。总之,仅凭由这些普通语言符号构成的能指链或者话语,我们终将一无所获。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博学、不够敏锐,不能发现这些词语(普通能指)的深层含义,而是因为梦的潜在内容根本不在其明显内容之中,它根本不是由通常意义上的普通能指来表达的,而是由一些迥异于普通语言符号的特殊能指来表达的。就能指的一般定义来说,这些特殊能指根本就不被我们视为能指。比如,梦中出现的陌生女子莉莉安,菲利普之所以不认识她,是因为梦者将莉莉和安妮这两个人压缩成了一个人。莉莉安本身是无解的,因为菲利普的生活中根本没有这样一个人。梦中的独角兽( licorne )也是压缩的产物,这个词语的第一个音节“li”不仅来自莉莉( Lili ),还来自他自己的名字 Philippe 。至于“独角兽”这个词语的第二个音节 corne ,不仅表示动物的角,对年幼的菲利普来说,它也是阳具的代表。这个梦同样使用了移置。比如,梦中荒凉的广场( place )其实是对与莉莉安密切相关的沙滩( plage )的替换,而森林中颜色奇怪的树木则是瑞士山谷中鲜艳的石南花的替代,而在鲜艳的石南花背后,则是将双手握成海螺状吹口哨,而这一动作又是口欲的隐喻表达。从以上分析可知,无意识话语的能指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符号,而是一些以音响或形象出现的记忆痕迹;就这个梦而言,这里的音响就是[li]和[plas],其形象则是荒凉的广场、喷水的独角兽、赤脚的莉莉安、美丽的沙滩、颜色奇怪的树木和独角兽。值得指出的是,在梦中,这些形象纯粹是视觉性的存在,它们只是在菲利普对梦的叙述中才获得语言描述。这些音响或者形象按照压缩和移置法则被随意组装起来,以便让主体的无意识话语得到表达。即使无意识话语中的能指以一般能指的形式出现,比如广场、沙滩、独角兽和石南花,它们的意义也完全不是这些词语的普通意义所能表达的。也就是说,在语文学的层面上追溯这些词语的无意识含义,永远都不会有任何结果。
无意识的基本能指绝非一般意义上的词语,而是一些记忆痕迹,这些痕迹或者表现为一些音响,或者表现为一些纯粹的视觉形象。作为实在之物,这些音响和形象本身毫无意义,但是,因为它们和主体的某种本能建立了非常偶然的关系,于是主体根据压缩和移置两种基本程序对其加以利用。一旦这些音响和形象开始服从压缩和移置的法则,它们就获得了能指的性质。虽然主体在构筑各种无意识文本(梦、症状和失误动作)时也会利用一般意义上的词语,但无意识的基本能指永远都是这些记忆痕迹。所以安妮卡·勒迈尔说:“词语在其最根本或者最基本的无意识中没有任何地位。 构成基本无意识的毋宁说是一些音素 或者音素群,这些音素或者音素群后来会进入词语的构成中,然后再进入 无意识幻想 的构成中,这些无意识幻想的综合结构建构了那些更加容易分析的无意识地层。基本无意识本身根本上是不可抵达的。” [15]
其实弗洛伊德已经发现了无意识借以表达自己或者构建自己的能指不是普通的词语,而是一些特殊的能指,因为他在《释梦》中已经指出:“(潜在的)梦-思想(the dream-thoughts)与(明显的)梦-内容(the dream-content)就像同一个主题用两种不同语言写成的两种版本。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梦-内容就像以另一种表达模式出现的梦-思想的抄本,通过比较原文与译本去发现这个抄本使用的字符和句法正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16] 在此,弗洛伊德明确指出了无意识和意识是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写成的,这两种语言有不同的文字和句法。这至少已经暗示我们,一般的意识文本就其本身而言,无论如何解读,都无法解读出其无意识含义。普通文本当然会有言外之意,会有象征意义,但这些象征意义仍然是相应的词语在象征秩序或文化传统里的含义,而无意识能指的含义却绝不是由象征秩序建构的,而是由个别主体自由建构的,虽然并非与象征秩序绝对无关。一个梦文本的无意识含义必须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才能被揭示。
因此,无意识不是一个由一般意义上的词语构成的文本的言外之意或者加密信息,而是另外一个由特殊能指写成的特殊文本。这个特殊文本之所以难以释读,不仅是因为它使用了一些特殊能指,还因为这个文本已经被抹除了、擦掉了。拉康说,无意识是为了书写意识文本而被擦掉的文本,就像古人把羊皮纸上原有的文字擦掉书写新的内容;但这个文本没有被彻底擦除干净,而是留下了痕迹,然而我们只有透过意识文本的空白、节点和裂缝,才能发现和辨认这些残留的痕迹。无意识是双重铭刻的结果,是一种双重铭文(double inscriptions)。为了辨认无意识,我们只能依赖由一般意义上的词语书写的文本,但无意识并不在这种文本之中;让无意识得以表达的文本从一开始就被抹除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透过普通文本的空白、节点和裂缝,去努力辨认那些依稀残留的痕迹。如果我们只停留在普通文本上,那么无论我们如何博学多识,无论我们如何洞幽烛微、钩沉索隐,即使对文本的每一个词语都做穷形尽相的语义学分析,也不可能捕捉无意识的蛛丝马迹。只有当我们从普通文本的空白、节点和裂缝中发现另一个文本残留的只鳞片甲时,在精神分析学的指导下,才有可能捕捉无意识。正因如此,拉康说无意识是一种双重铭文,释读无意识不是在一个印版(上面印有一棵树,树中暗藏拿破仑的头像)上寻找拿破仑的头像的问题。如果无意识是一则铭文,那么这则铭文就来自知识(意识)的印版对真相(无意识)的印版之抹除。关于无意识,拉康自己给出了最为精确的描述:
无意识是我的历史的一章,以空白标示的一章,或者被谎言占据的一章:它是被查禁的一章。但真相可以被重新发现;通常它已经被写在了另一个地方。即:
在一些遗迹之中:这些遗迹就是我的身体,换句话说,就是神经症的癔症内核,在这个内核中,癔症显示了语言的结构,并且像一则铭文那样被破译;一旦这则铭文被复原,就可以被轻松摧毁;
也在一些档案文件之中:这些文件就是我的童年记忆,它们和那些我不知道其出处的文件一样难以理解;
在语义演变中:与此对应的是由我自己的特殊词语构成的词汇及其意义,正如它对应了我的生活风格和性格;
也在一些传统之中,甚至在一些传说之中:这些传说以一种夸张的形式表达了我的历史;
最后,在一些痕迹之中:这些痕迹不可避免地被保存在一些歪曲之中,这些歪曲是必需的,因为要把那被掺假的一章插入周围的章节之中,但是其意义可以被我的解释重建。 [17]
拉康的上述论断自然非常深刻,但不无晦涩,对此我们不妨借鉴勒克莱尔的阐释来帮助理解:
无意识不是用来为某幅图画增加光芒和深度而准备的底色:它是被抹除的早先的素描,因为这张画布后来要用来画另一张画。
如果我们用音乐来做比喻,那么无意识并不是赋格曲的对位乐曲,或者一个旋律的和声:它是人们在听海顿的四重奏时听到的爵士乐——可能因为收音机的调频出了问题或者调频不准确。
无意识不是一个信息,甚至不是写在一张古老的羊皮纸上需要人们费力破译的奇怪信息或者加密的信息:它是写在表层之下的另一个文本,要想解读这个文本,必须将这张羊皮纸对着光然后从背面去看,或者借助显像剂去看。 [18]
因为无意识是主体历史中被查禁的一章,是写在另一个场景中的话语,因此拉康说,无意识不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而是我们不可能知道的东西,这就意味着无意识只在被分析的时候才存在。要理解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有一个长期而且普遍存在的误解,那就是认为无意识是一种被压抑的观念——似乎主体先有某种观念,然后发现这种观念违背一般的道德法则,于是将其压抑下去。在某种程度上,弗洛伊德要为这种无解负责,因为在他的第一个地形学观点中,他把无意识比喻为海面下的冰山。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一种事先存在的无意识,等待着精神分析学家去发现或揭示它。如果无意识是能指结构的产物,那么它当然只能在无意识话语被分析之时才真正存在。正如解释学指出的那样,文本只有在被接受和解释时才具有意义,这一原理同样也适用于无意识话语。无意识不是一些被压抑的观念,而是一些只有在被分析时才被建构出来的观念。无意识只是在解释时才产生。 [19] 就此而言,无意识首先不是一种意义,而是一套文字。
正如前文所说,弗洛伊德已经发现最初的无意识并不产生于压抑,而是产生于原始压抑。原始压抑表明,早在自我产生之前,早在社会法则内化为超我之前——一句话,早在俄狄浦斯情结发生之前,主体或者前主体就已经有了无意识。但是,弗洛伊德只是假定了原始压抑的存在,至于原始压抑产生的原因则付之阙如。拉康发现了这个空白,并在现代语言学或者语言哲学的启发下,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回答。
拉康认为,语言这个大他者是造成原始压抑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原始压抑是主体或前主体进入语言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压抑的动因是超我,那么原始压抑的动因则是语言本身。超我起源于俄狄浦斯情结(3~5岁),但幼儿进入语言(1岁半左右)要远远早于俄狄浦斯情结。棘手的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发生与进入语言都和父亲有关,这就让人难以区分二者。但是,二者的差别还是明显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核心是主体对父亲或母亲的认同(identification),而幼儿在进入语言时尚且没有这种认同,进入语言的关键是“父亲的名字”之介入。在“父亲的名字”介入之前,幼儿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封闭在一个想象的完美状态之中,与母亲合二为一,无所欠缺。他不仅自己(其实他还没有自我意识)无所欠缺,因为他拥有母亲,而且母亲也无所欠缺,因为母亲拥有他。如果始终封闭在这样的状态中,他将无法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无法进入“世界”,因为他没有进入语言。“父亲的名字”就是打破母子合二为一的状态,将其引进语言的关键。拉康的这个公式表示的就是这个意思:

“父亲的名字”的基本功能就是打破母子合二为一的想象的完满。在这种想象的完满中,前主体只有一个对象,即满足自己快感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前主体不仅没有主体性,甚至也没有一个“世界”。“父亲的名字”炸裂了这个封闭的想象界,将前主体从中解放出来,将其引进一个三元的象征界。在这个三元的象征界中,不仅有母亲与自己,还有父亲,最重要的是,还有父亲禁止的东西。虽然这种东西因为“父亲的名字”而被禁止,并永远失落了,但正因如此,主体不会甘于丧失它,而是竭尽全力去捕捉它,但他现在唯一的工具就是语言:主体只能借助语言去捕捉那从未拥有但已经永远失去的东西。正是在永无止境地追逐这个永远失落的物的过程中,主体进入了语言,并因此拥有了一个世界。世界不是由实在的事物构成的,而是由“空虚的”能指构成的。象征界本质上是一个意义的世界,其中没有任何实在之物。然而语言不是万能的,如果语言是一张网,总有一些东西是这张网所无法捕捞的。语言既是一座桥,引领我们进入意义的世界;语言也是一面墙,阻止我们真正抵达实在之物。究其根本,就在于语言发生的基本前提就是欠缺。也就是说,总有某些东西与语言不兼容,语言必须将其排除才能正常运转。这就是原始压抑产生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无意识产生的根本原因。
无意识不仅是一种话语,具有语言的基本结构,服从语言的基本法则,而且是“大他者”的话语。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大他者呢?拉康还有一句类似的箴言:“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那么这两个“大他者”是一个意思吗?如果说“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中的“大他者”就是拉康所说的象征秩序,那么针对无意识而言的“大他者”也可以如此理解吗?在笔者看来,虽然这两个“大他者”不无关系,但它们在内涵上并不完全相同。诚如拉康所说,针对欲望而言的“大他者”指的是象征秩序本身,是一个处所、一个位置,而非某个人。针对无意识而言的“大他者”首先指的是与主体绝对异质的语言。主体是一个鲜活的生命,而语言则是一套象征符号,二者没有任何共同性,但这个鲜活的生命、这个实实在在的存在者却要受到语言这个完全异质的符号系统的支配。其次,无意识借以表达自己的语言与一般语言根本不同,因为它发生在“另一个场景”(another scene)之中,使用的能指也不是普通的语言符号,而是一些实实在在的音响或者形象。再次,这个大他者虽然与象征秩序不无关系,但更多情况下指的是某个或某些具体的个人,主体的无意识其实是对某一或某些特定个人的无意识的回应。总之,当拉康说“无意识就是大他者的话语”时,他要强调的是语言——普通语言和无意识语言——对主体至为深刻而又难以察知的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当拉康说“无意识就是大他者的话语”时,他所理解的无意识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是完全不同的。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是直接针对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而来的,他认为,集体无意识是现实的一个地层,它们并不来自个人经验,也不是由个人获得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普遍存在的,在不同文化和所有人中都基本相同。荣格首次提出这个概念是在其论文《无意识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the Unconscious,1916)中。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充满了本能和原型:古老的原始符号,如伟大的母亲、智慧的老人、阴影、塔、水和生命之树。他用集体无意识来支撑和包围无意识思维,并将其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个人无意识区分开来。他相信,集体无意识这个概念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类似的主题会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神话中。他认为,集体无意识对个人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通过它的象征,并通过他们的经历赋予其意义。分析心理学的心理治疗实践围绕着检查病人与集体无意识的关系展开。集体无意识的确存在,但集体无意识并不像荣格理解的那样,是与生俱来的,与个人经验无关;如果不同文化中的个体表现出了相同的无意识,那不是因为集体无意识是全人类由遗传而来的共同心理内容,而是因为不同的文化具有基本相同的结构。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背离了弗洛伊德的基本教义:无意识与性的发展密切相关。当荣格以集体无意识去解释各种文化现象时,他不仅远离了精神分析学,而且堕入了某种神秘主义的陷阱。正因如此,荣格的精神分析学始终不能成为精神分析学中的主流。
虽然弗洛伊德一开始就将精神分析定义为一种谈话疗法(talking cure),虽然他始终基于被分析者的自由联想(述说)去解释梦、症状和各种失误动作,虽然他早在《释梦》中就已经发现梦的工作的基本机制就是压缩和移置,但是,由于他对语言的本质还缺乏一种科学的认识,还将语言粗略地理解为一套符号系统,因此他未能发现压缩和移置就是隐喻和换喻,未能发现物表象本身就是能指,未能发现无意识完全按照语言的基本法则在运作。正如阿尔都塞说辩证唯物主义已经以一种实践形态存在于马克思的文本中,拉康可能会说无意识的语言学也以一种实践形态早已存在于弗洛伊德的文本之中了。因此,当拉康一方面宣称要引领精神分析学“回到弗洛伊德”,另一方面又毫不迟疑地宣布“无意识就是大他者的话语”时,他并不自相矛盾,因为在他看来,弗洛伊德的实践早已证明了无意识就是一种话语。拉康既没有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背离了弗洛伊德,也没有强行用自己的理论将弗洛伊德改造为一个拉康主义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始终是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他的使命就是引领精神分析学回到弗洛伊德。
[1] Sigmund Freud,“The Neuro-Psychoses of Defence”,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3,London:Hogarth Press,1981,p.58.
[2] Jacques Lacan, Écrits ,trans.Bruce Fink,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7,pp.386-387.
[3] Sigmund Freud,“The Unconscious”,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14,London:Hogarth Press,1981,p.148.
[4] Sigmund Freud,“The Unconscious”,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14,London:Hogarth Press,1981,pp.201-202.
[5] Roman Jakobson,“Two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wo Types of Aphasic Disturbances”,in Selected Writings:Word and Language ,Berlin:De Gruyter Mouton,1971,p.243.
[6] Jacques Lacan,“The Instance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onscious”,in Écrits ,trans.Bruce Fink,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7,p.428.
[7] Jacques Lacan,“The Instance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onscious”,in Écrits ,p.429.
[8] Jacques Lacan,“The Instance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onscious”,in Écrits ,p.436.
[9]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trans.Alan Sheridan,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98,p.20.
[10]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The Psychoses:1955-1956 ,trans.Russell Grigg,New York:W.W.Nordon & Company,1993,p.185.
[11] Jacques Lacan,“The Instance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onscious”,in Écrits ,p.426.
[12] Jean Laplanche,Serge Leclaire,“The Unconscious:A Psychoanalytic Study”,trans.Patrick Coleman,in Yale French Studies ,1972,No.48,p.151.
[13] Anika Lemaire, Jacques Lacan ,trans.David Macey,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1,pp.139-152.
[14] Jean Laplanche,Serge Leclaire,“The Unconscious:A Psychoanalytic Study”,in Yale French Studies ,p.136.
[15] Anika Lemaire, Jacques Lacan ,p.142.黑体强调形式为原文所有。
[16] Sigmund Freu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trans.James Strachey,New York:Basic Books,2010,p.295.本文参阅了孙名之的中译本(弗洛伊德。释梦。孙名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77),但英译本似乎更加彰显了无意识和意识是两种不同的符号这一意思。
[17] Jacques Lacan,“The Function and Field of Speech and Language in Psychoanalysis”,in Écrits ,p.215.
[18] Serge Lecalire,“La réalité du désir”,in Écrits pour la psychanalyse ,Paris:Editions du Seuil,1998,p.143.
[19] 无意识只在被解释和分析时才存在,这种观念很难被一般人理解。对此本书未予展开,更深入的阐释,请参阅:Juan-David Nasio, Five Lessons On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Jacques Lacan ,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