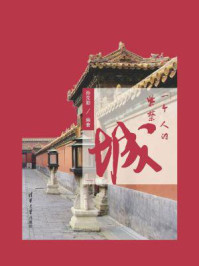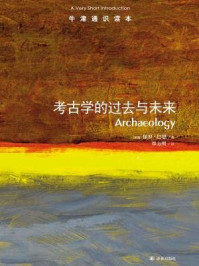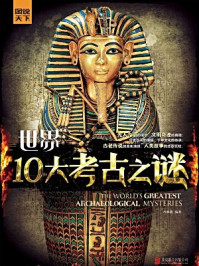战争威胁是美索不达米亚早期城邦居民长期面临的风险。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必然制约着这些早期城市居民的生活体验。常年存在的恐惧之一就是战争或者围城之困,这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叙事文本及城市挽歌中就有反映。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历史叙事文本(约公元前2450年)就是在战争之中诞生的。各种物品上的铭文描述了拉伽什城邦统治者安纳图姆(Eannatum)与来自乌玛的敌人争夺一块被称为古埃德纳的农田。
 其中一座被称为秃鹫石碑的刻有铭文的纪念碑,以图画的形式描绘了文本中叙述的事件,石刻秃鹫的喙叼住敌人被砍下的头颅,翱翔在战场上空的画面令人难忘。虽然这些作品在当时是具有高度感染力的国家宣传品,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获取到历史信息(George 2013)。文本中还描述了将死者堆放到乱葬坑中的做法,这种举动可能是额外的羞辱或亵渎,因为没有举行常规的丧葬仪式和祭品供奉。可以说,偏离常规的丧葬习俗(Richardson 2007)会让个体来世也不得安宁,下文将对此进行更加详细的讨论。
其中一座被称为秃鹫石碑的刻有铭文的纪念碑,以图画的形式描绘了文本中叙述的事件,石刻秃鹫的喙叼住敌人被砍下的头颅,翱翔在战场上空的画面令人难忘。虽然这些作品在当时是具有高度感染力的国家宣传品,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获取到历史信息(George 2013)。文本中还描述了将死者堆放到乱葬坑中的做法,这种举动可能是额外的羞辱或亵渎,因为没有举行常规的丧葬仪式和祭品供奉。可以说,偏离常规的丧葬习俗(Richardson 2007)会让个体来世也不得安宁,下文将对此进行更加详细的讨论。
早期的城市居民创造了各种技术来应对生活中的灾难,烽火信号就是其中之一,这种做法能在危险的时刻照亮黑夜(Earley-Spadoni,2015a,2015b)(见第9章)。古代近东最早的烽火传信的历史和考古证据来自青铜器时代中期的叙利亚,约公元前1800年。玛里王宫的书信档案记录了国家统治者及其官员的事务。
 王宫档案中还发现了数十封与烽火台有关的信件(Dossin 1938),其中有几封值得详述。在一封信中,高级官员班纳姆(Bannum)写信给国王说,他从玛里出发,向北旅行时,在特尔恰城(Terqa)附近看到亚米尼特人(Yaminites)的城镇正逐个点燃烽火
王宫档案中还发现了数十封与烽火台有关的信件(Dossin 1938),其中有几封值得详述。在一封信中,高级官员班纳姆(Bannum)写信给国王说,他从玛里出发,向北旅行时,在特尔恰城(Terqa)附近看到亚米尼特人(Yaminites)的城镇正逐个点燃烽火
 (Dossin 1938,178)。他并不知道点燃烽火的原因,但他许诺会再写信提供更多的细节。同时,他建议增强防御,这说明烽火具有警示系统的作用。在另一封信中,一位公职人员就燃烧烽火让国王担忧而道歉,并解释说亚米尼特人仍然处于叛乱之中。然而在另外一封上书给国王特尔恰的信里说附近一场袭击就要爆发,萨米塔将军已经在该地集结了部队,以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袭击。写信人对国王保证,虽然写信时并不知道烽火何时会被点燃,但是一旦烽火在事发地燃起,他会在第一时间进行救援。在另一封信中,一位叫作津德里亚(Zindria)的人回复了国王对烽火信号含糊不清的抱怨。津德里亚写道,为了避免出现混乱,今后只有在看到两处而非一处烽火点燃时,他才会召集部队,并向其他驻军发出信号。这表明烽火传信在当时是个不完善的系统,并且信号的含义可以根据情形事先商定。最后,如果综合考量这些公务信件,就可以看出部队集结是对点燃烽火的常规反应。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情况下,点燃火焰都意味着危险降临,但点燃烽火是为了从远方寻求援助。
(Dossin 1938,178)。他并不知道点燃烽火的原因,但他许诺会再写信提供更多的细节。同时,他建议增强防御,这说明烽火具有警示系统的作用。在另一封信中,一位公职人员就燃烧烽火让国王担忧而道歉,并解释说亚米尼特人仍然处于叛乱之中。然而在另外一封上书给国王特尔恰的信里说附近一场袭击就要爆发,萨米塔将军已经在该地集结了部队,以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袭击。写信人对国王保证,虽然写信时并不知道烽火何时会被点燃,但是一旦烽火在事发地燃起,他会在第一时间进行救援。在另一封信中,一位叫作津德里亚(Zindria)的人回复了国王对烽火信号含糊不清的抱怨。津德里亚写道,为了避免出现混乱,今后只有在看到两处而非一处烽火点燃时,他才会召集部队,并向其他驻军发出信号。这表明烽火传信在当时是个不完善的系统,并且信号的含义可以根据情形事先商定。最后,如果综合考量这些公务信件,就可以看出部队集结是对点燃烽火的常规反应。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情况下,点燃火焰都意味着危险降临,但点燃烽火是为了从远方寻求援助。
对叙利亚青铜时代中期遗址的考古调查也表明,这些烽火地点的布置是刻意为之,方便相互可见。“叙利亚北部干旱边缘项目”(Rousset et al.2017)对叙利亚西部100多个青铜时代中期的遗址进行了编目,以便对这一时期防御网络建设的可见性增强进行调查。项目记录了一个多层级的区域防御网络,其中包括要塞、堡垒、大塔楼、小塔楼和构筑了防御工事的村落。其结论是,在研究的目标区域内,有规律的间距和通视性是建筑布局的关键因素。建筑间固定的间距(约20千米)不仅确保了沿路旅行者的安全,还能提供良好的能见度和通视性,这使夜间传递烽火信号成为可能,比如所描述的玛里烽火系统就是这样。民族志研究表明,天气良好的情况下,一座小型烽火台的可见距离是50千米。
 除了青铜时代中期的叙利亚,在黎凡特(Levantine)遗址中,有大量文字和考古证据表明该地区有使用瞭望台和有意为之且可以通视的建筑设施(Burke 2007),这表明这种做法在公元前2000年早期之前就已普遍存在,领先于青铜时代。在米诺斯克里特岛工作的考古学家们(Panagiotakis et al.2013)记录了一个比玛里档案文献稍晚的视觉通信系统,他们发掘了一个叫作索罗伊(soroi)的可互见系统,其中包含信号燃料堆,可作为大型的独立烟火装置。
除了青铜时代中期的叙利亚,在黎凡特(Levantine)遗址中,有大量文字和考古证据表明该地区有使用瞭望台和有意为之且可以通视的建筑设施(Burke 2007),这表明这种做法在公元前2000年早期之前就已普遍存在,领先于青铜时代。在米诺斯克里特岛工作的考古学家们(Panagiotakis et al.2013)记录了一个比玛里档案文献稍晚的视觉通信系统,他们发掘了一个叫作索罗伊(soroi)的可互见系统,其中包含信号燃料堆,可作为大型的独立烟火装置。
美索不达米亚文字资料中描述最为生动的烽火台实例之一来自萨尔贡二世(Sargon II)的“第八次战役”,该战役的传统断代为公元前714年。这篇复杂的文学作品描述了新亚述军队深入敌国领土(今伊朗境内)与劲敌乌拉尔图遭遇的过程。到达乌尔米亚湖(Lake Urmia)附近的桑吉布特地区(Sangibute)后,亚述人试图与乌拉尔图人交战,但没有成功:
为了防范该地区的敌人(?),他们在山峰上修建了塔楼,并提供了[发信号用的木柴]。当他们看到(250)篝火燃起,预示着敌人的来临,[为此]火把日夜[就位(?)],宣告[],他们恐惧我那摧枯拉朽的攻击,从未有过如此的攻击,恐怖在他们中间蔓延,他们惊[恐万状难以抗衡]。都无暇一瞥自己无数的财产,他们放弃了强大的堡垒,消失了。(Foster 2005,804)。
除了描述乌拉尔图精细而有效的烽火系统外,这段文字还暗示了烟雾信号的使用,因为燃料的储备(可能湿柴和干柴都有)是为了不分日夜随时使用的。烽火台是夜间使用的系统,而烟雾信号则可以在白天使用。
考古证据证实了亚述资料中关于乌拉尔图烽火通信能力的说法。亚美尼亚塞凡湖(Lake Sevan)附近,公元前1000年早期的铁器时代早期遗址(EI)和乌拉尔图聚落区呈现出为了实现通视而有意规划的布局(Earley-Spadoni,2015b)。在亚美尼亚塞凡湖以南也观察到了密集的通视性遗址网络,该网络一直是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社会网络分析研究的对象(Earley-Spadoni,2015b)。在铁器时代早期和随后的乌拉尔图人吞并期间,密集的遗址相互连接形成了刻意为之且显得冗余的网络,这意味着即便一个信号装置出现故障,信息仍然可以传递出去。上述网络折射出现代电信网络也同样存在的不同层面的冗余现象。研究中使用的统计验证方法表明,要塞和堡垒网络并不是国家有机发展的结果。相反,这些遗址是作为一个综合、刻意的通信系统而建造的,它需要该地区的古代居民之间进行通力合作。例如,有些遗址充当中继站的作用,即作为中间站点将其他遗址发出的信号转发出去。
除了亚美尼亚,还有大量证据表明防御工事遗址之间存在通视性,如伊朗,特别是乌尔米亚湖以西的平原上,那里独立的塔楼在遗址内部的通信网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伊朗进行的地区调查中发现了各种独立瞭望塔的例子,如调查人员发现的查拉特加瞭望塔(Qalatgah Gipfelkastel),它位于规模可观的查拉特加堡垒上方约350米处,一条蜿蜒小路的顶端(Kleiss and Kroll 1977,71)。这座建筑能够俯瞰下方的平原,而堡垒本身却不大容易被发现。那座20米见方的瞭望塔是一个辅助设施,主要功能是侦察功能,并在视觉上将查拉特加堡垒与其周边诸如哈桑鲁(Hasanlu)和耶地亚要塞(Yediar)这样的地方连接起来(图3-1)。沃尔夫拉姆·克莱斯(Wolfram Kleiss)注意到了瞭望塔在地区视觉通信网络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他认为该遗址可能是一座兼具烽火和烟雾信号发送功能的优良中继站。伊朗主要的乌拉尔图要塞巴斯塔姆(Bastam)(1979,1988)也有信号塔的记载;而在古代近东地区的其他铁器时代遗址中,肯定也有瞭望塔存在(Edwards,2020)。
总之,烽火传信广泛用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夜晚。可以说,烽火台传递信号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活动,人们试图通过这种活动在不可预知的世界中获得一些微薄的力量。塔楼、堡垒和烽火台,虽然坐落在城市之外,却有助于保卫城市居民的安全,并成为安保基础设施的一部分。烽火台属于达里尔·威尔金森的“信号基础设施”(Wilkinson 2019),我们在第1章中曾有讨论。本节中,我讨论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是如何在黑暗中发出危险警告的,但是,接下来我将对历史和考古证据进行分析,以了解对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来说“黑夜”究竟代表着什么。

图3-1 以查拉特加瞭望塔为观察点的地区通视性。地图来源:Tiffany Early-Spado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