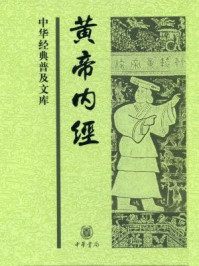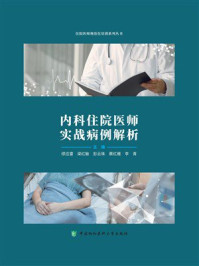根据Drummond等 [119-120] 的研究,卫生健康项目的经济学评价主要有四种类型: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用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和最小成本分析。Drummond等 [121] 对上述卫生健康项目的相关定义进一步优化,具体如下。
●最小成本分析:在效果、效用和效益没有差别的条件下,选择成本低的方案,该分析只考虑成本,代表经济学评价的部分形式。
●成本-效果分析,主要评价使用一定数量的卫生资源(成本)后的个人健康产出,这些产出表现为健康的结果,用非货币单位表示,包括“延长的生命年”或“正确诊断的病例数量”。
●成本-效用分析:是成本-效益分析的一种发展,根据健康状况偏好评分或效用权重来测量项目效果,通常采用质量调整生命年或失能调整生命年来表示。成本-效用分析最常见的衡量指标是质量调整生命年。
●成本-效益分析:在评价临床方案效果时,采用货币值分析和评估项目的实施效果。它是应用最广泛的分析形式,确定项目实施效果,进而验证成本是否合理。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经济学评价议程强调,对预防和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经济效益关注不够 [59] 。
2016年,一篇关于社区高血压患者干预经济学评价的系统综述显示 [122] :从1995—2015年,我国只有4项针对上述专题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两项采用了成本-效果分析法 [38,75] ,另外两项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 [18,123] 。2010年,Huang [124] 和Ren [123] 的研究评价了以社区为基础的脑卒中预防项目,结论是节省了疾病成本。但是,如前所述,该研究只考虑了脑卒中,而这仅仅是高血压的其中一个并发症。此外,该研究也未分析未来的成本和效益,没有明确解释该方法在经济学评价中的应用。Wang等 [17] 的研究仅通过对北京市140名高血压患者随访一年的基础上分析高血压管理节约的成本。整体上,这两项成本效益研究并不能够为我国高血压患者管理的经济学评价提供具有代表性的证据,因为上述研究使用的方法不够全面,不完全符合经济学评价对成本-效益分析法的基本标准 [120] 。
为改进我国经济学评价方法,本研究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框架,其中将效益定义为卫生健康项目效果的货币价值 [121] 。
延长生命年对于个人是有益的,因为他们可以活更久,享受更好的生活质量。与此同时,社区也能够受益,主要体现为降低了患者的治疗费用或者挽救的生命为社会和经济做出贡献。对于生命年的价值和医疗卫生服务干预措施的效益研究很多。Drummond等 [121] 在《卫生保健项目经济学评价方法(第4版)》中指出,人们通常采用支付意愿法来估算健康效益。该方法通过测量潜在的消费者需求和对非市场化的社会商品价值进行估算,其中社会商品包括卫生健康项目。不过,Drummond等 [121] 也指出,包括支付意愿法在内的每种效益估算方法都存在优缺点。支付意愿法虽然得到普遍使用且发展得较为完备,但仍然存在两方面的主要缺陷:一是该方法基于假设,二是通过支付意愿法将质量调整生命年用于效益估算时可能不包括社会效益 [121] 。美国的一些研究估计,一个生命年的价值等于15万美元 [125] ,但针对该问题的观点和方法分歧较大。
为解决上述缺陷,Stenberg等 [45] 开发了一个用于计算妇女和儿童健康项目的投资回报率的衡量指标,为卫生健康项目效益评估开辟了新的路径。在该模型中,卫生健康效益被认为由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组成。根据每个性别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和生产率,估计了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力参与卫生健康项目增加的经济效益。其社会效益主要来源于更长、更健康的预期寿命,其估算方法是分配一定比例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测算 [44-45] 。与支付意愿法的效益估算框架相比,这种效益估算方法解决了基于偏好的方法产生的偏倚,为效益估算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和可衡量的工具。
然而,该方法尚未应用于我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干预中。因此,在Stenberg等 [44-45] 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将该创新性模型应用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干预措施,即我国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患者管理。
国际上,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患者干预或管理措施的经济学评价研究较多。本研究回顾了几项国际研究。
在不丹,Dukpa等 [126] 对世界卫生组织出台的基于初级卫生保健提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基本干预包 [48] 进行了经济学评价,应用的模型包括决策树和马尔可夫模型。研究比较了3种情境下终身干预成本和避免的失能调整生命年,3种情境分别为无筛查、利用当前WHO提出的基本干预服务包和全人群筛查。高血压的马尔可夫模型包含4种健康状态:高血压未得到控制、高血压得到控制、脑卒中和死亡。队列人群的年龄范围在40岁或以上,每个周期为一年。使用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方法计算失能调整生命年。Dukpa等 [126] 研究结果表明,初级卫生保健机构开展筛查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在孟加拉国,有研究从社会角度对国家高血压治疗项目进行了成本-效益分析,分别计算了到2021年和2030年为60%的高血压患者提供降压药物干预措施的投资回报率 [127] 。研究结论是,如果政府积极主动地开展高血压患者管理,到2021年,年投资回报率可能达到12.7∶1;到2030年,年投资回报率可能达到8.6∶1。
在希腊,Athanasakis等 [128] 采用成本-效益分析的马尔可夫模型对2014年高血压患者控制进行了经济学评价。研究建议将促进血压控制的干预措施作为重点卫生健康政策。
在荷兰,研究者采用马尔可夫模型评估了对轻度高血压采取心血管疾病初级预防干预的经济学效果。研究发现,在10年期限和终身干预两种情况下,降低收缩压都具有成本效果 [129] 。
上述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方法学和国际实践经验基础与参考。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初级卫生保健一级干预或筛查措施都具有较好的成本效益或性价比。同时,大多数经济学评价均利用马尔可夫模型开展。例如,荷兰的研究建立了马尔可夫模型,确定心血管疾病进展的5种状态包括健康但有高血压、急性非致命性心血管疾病、稳定的非致命性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死亡和非心血管疾病死亡 [128] 。这与Gu等 [38] 采用的方法类似,为高血压控制的马尔可夫建模提供了准确的参考。
我国对患者健康管理的经济学评价研究存在三个方面的差距。首先,几乎所有的研究均采用成本-效果分析或成本-效用分析,但缺乏成本-效益分析。例如,2000年开展的一项对我国脑卒中干预的评价未包含成本-效益分析 [130]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研究对社区高血压患者管理进行了经济学评价,但未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131-132] 。其次,一些研究虽然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高血压患者管理进行了成本-效益分析,但未进行方法学讨论和深入分析。例如,一项针对糖尿病筛查项目的经济学评价研究,使用蒙特卡罗模型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但研究只考虑获得的质量调整生命年和治疗成本,未考虑货币形式的效益,因此这种评价是不完整的 [133] 。另一项研究分析了社区卫生服务管理模式下高血压患者的治疗效果和成本效益,但没有进行敏感度分析 [134] 。最后,在经济学评价过程中,很少考虑个体对社会的经济影响 [135] 。
2015年,顾东风等学者的研究部分解决了上述差距 [38] 。但是,依然还有两方面的研究空白需要填补。一是目前尚没有研究证据提供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更不用说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的投资回报研究证据。二是多项研究表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级干预措施将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高回报 [9,136] ,但Gu等 [38] 研究发现加强高血压治疗在我国的成本效益并不明确。从这个角度看,本研究将开展更加深入、完整的分析,提供成本-效益分析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