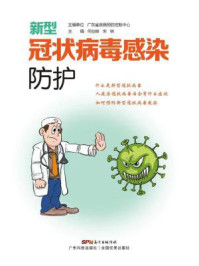到了宋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已经形成,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进一步成熟,源自孟子的天人观的宋明理学和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二程”的理论都进一步发展了孟子和董仲舒的“天人”理论,其主要观点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并且引入博爱思想,在此基础上同时肯定了天道与人道的同一。朱熹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将天理、人欲发展到极端,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
纵观儒家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发展,可以看出,“天人合一”思想已成为儒家的核心思想。儒家的“天”具有道德的含义,也就是道德之天。“合一”也就是“统一”,是指双方相互联系且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当然“合”不是简单地“天”“人”相加,是超越这种简单相加之和,是一种整体的概念。
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完整说法最早是由张载提出来的,他认为“太极”生万物,人的生命存亡就是太虚之气的聚散,且属天地间自然而然。据此,万物和人都是由气构成的,气中所固有的神也就构成了人物之性。因此,张载的气包括“虚而神”的气之性,具有本体的意义。尽管也提到了理,但理只是气运动的条理或法则,并不具有本体的性质。“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乾称》)。张载在此明确提出了从分裂的世界中必须把握天与人二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认为只有这样,学才可入圣,进入到天人一体而“得天而未始遗人”的最高境界。
宋代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在其代表作《太极图说》指出:“无极而太极……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朱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在《朱子语类》卷九十四中指出“圣人谓之太极者,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谓之无极者,所以大一作著夫无声无臭之妙也”“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他认为太极包含理、气,理、气相依而不分离,并以理为宇宙本原,强调“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理在气中”“若气不结聚时,理亦无所附著”。气流行生化为物,太极之理化为万物之理。万物之理、气,不同于作为其本原而无生无灭的太极理、气。
程颢、程颐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二程遗书》),他们认为天与人本是一个东西,不存在“合”的问题,否认这二者的差别性和对立性,强调天人本就相通,把世界的统一推到了绝对化的地步。他们将理上升到本体的高度。程颢云:“天者,理也。”认为天理是宇宙的本原,理生气,气生天地万物;程颐认为“所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二程集(上)》)在二程看来,万物都有理,理是万物的本原,而且是永恒存在的。二程的思想是对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更高程度上的“天人合一”。
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对“天人合一”的认识又赋予了新的思想,他提出“天人一理”说。朱氏视“天理”为“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朱子语类》)明确规定了天理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地位,确立了“理在事先”的基本原则。他认为理是天地万物生成的先决条件和必然基础,“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故必得是理,然后有是物”(《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理以气为中介,构成具体事物,人作为万物中之一物,自然也是理的体现者,故而天人一理。
理学家建构和提出了一个前人所未及的“天人合一”理论,使“人天同构”思想得到了理论上的升华。“天”和“人”两个范畴为“天人合一”奠定了理论基石,使理学天人关系真正升华为哲学形式,而“天人合一”使“天”和“人”真正融为一体,使人与世界成为和谐的统一整体。“天人合一”是理学天人关系理论体系组成的最核心的部分,是理学天人关系理论的原点,天人关系即是“天”与“人”相融相合的关系。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代天人合一整体观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基本、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整体观则是建立在整体性方式基础之上的,即从整体的角度出发,把宇宙视为生生不息的无限过程和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着眼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对于具体事物,不能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实体或元素去进行分析,而应着重于对它功能的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的哲人们一般把世界概括为天与万物或天与人两个最基本的部分。这个天(天道、天命、天理)不是实体,而是宇宙整体性的代表。它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弥漫一切,贯通一切,统摄万物,主宰化生。人与万物也不具有独立实体的意义,它们被天道所统摄,又以自己的独特功能体现天道,包含天道。同时,它们亦处在生灭循环的过程中,彼此相连而存在,相通而变化。因此宇宙万物之间、人与万物之间不存在绝对界限,而是相互映现、相互感应、相互贯通、相互联系成为一体,整体体现部分,部分体现整体。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朱子语类》)。而人与草木瓦石的区别,不在于形体或具体属性的不同,而在于人能够自觉地体认天道,效天法地,从而“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原善》),达到天地万物一体的境界。“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它具体表现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它认为人与天不是一种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而是处在一种部分与整体、扭曲与原貌或为学之初与最高境界的关系之中。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儒家、佛教、道家思想都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功能性,强调时空形神的多维联系。“万物一体”“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整体观的最集中体现。这种从相互联系的角度理解事物,从总体上把握宇宙的思维方式,更易于接近世界的真实面貌,也符合现代系统论的某些原则。中国古代的哲人们以这种方式把握宇宙,在社会政治、伦理、美学等方面发展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理论,推动了我国早期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在某些领域取得了领先的地位。
但是,如果说中国古代整体性思维的缺陷,可能就是其不易量化,不能解释系统内部组成成分及其动态变化过程,具有不可讳言的主观性。“天人合一”思想强调宏观规律,忽视微观认识。注重自然伦理道德的意义,而缺乏对自然规律的深入探索。
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合一”整体模式认为人与其他万物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人是万物之灵,最能体悟天道。儒家孟子提出“万物皆备于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等。这种人与天地万物同体的观念将人与天地并提,相信人只要充分发掘自己的本性,“修身养性”,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体认天道,便可赞天地之化育,辅万物之自然。因而它并不追求外在世界,偏重对人的自身内在价值的探求,强调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这种主体性原则赋予了中国人积极进取的精神,推动着人们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形成了重视社会人伦、道德修养与致思实用的倾向。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技术、医学、天文历法、数学等都曾居世界的领先地位,四大发明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此基础上本应提升出科学理论和体系,而科学思维却长期停留在经验水平上,没有实现突破性飞跃,这其中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整体观思维方法虽然有无可替代的优点,但也有不足。它对中国古代辉煌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可能也是造成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因素之一。应实事求是地对其积极和消极的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不能采取全盘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或全盘肯定的唯我独尊的国粹主义态度。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才能赋予整体观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