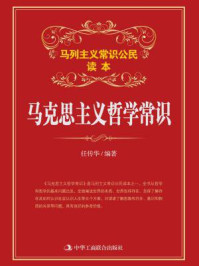在第一节中,我们通过对价值形式(交换价值)的分析,发现了价值实体,进而又研究了商品的价值量。在这一节中,我们将通过商品交换和价值形式的发展过程,揭示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进而说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揭示货币之谜。
在商品交换中,商品本身不能走进市场,它是由商品所有者带入市场的,所以,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从表面上看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却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经济关系。
商品所有者之间进行商品交换有其必然性:
第一,一切商品对其所有者来说具有非使用价值,对非所有者来说具有使用价值。
商品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体,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对他人有用的使用价值,而对商品生产者本人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如果生产者直接加以使用,那么商品就不成其为商品了。一切商品都是对他人有用的,这就产生了交换的必要性。一切商品又都具有共同的价值实体,使商品交换能够在量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对于商品所有者来说,他的商品只不过是一种交换手段,通过交换,各个商品所有者使自己商品的价值得以实现,并从对方处获得自己需要的使用价值。
第二,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有在商品交换中才能得到证明。
任何商品首先必须证明其具有使用价值,然后才能作为价值来实现,最后进入他人的消费过程。没有使用价值,就不会有价值,当然就更谈不上价值的实现。
怎样才能证明这个商品对他人有用呢?只有在商品交换中,才能证明这一点。只要发生商品交换,就表明这个商品是有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得到了证明,价值也就得以实现了。
商品交换的发生,归根结底是由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决定的,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但是商品生产者不能既取得商品的价值,又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卖者,生产者可以得到商品的价值,但要以放弃它的使用价值为前提,即他在得到其他价值的同时,必须放弃它的使用价值;作为买者,生产者得到他人手中商品的使用价值,但要以放弃自己手中商品的价值为前提,即在得到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同时,必须放弃自己手中商品的价值。于是,一个商品内部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表现在分裂的两个商品上,一个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出现,另一个商品作为价值出现。
在商品交换中,商品经济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表现为买者和卖者外部的对立,这种对立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货币。
货币是商品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商品交换过程一方面是个人的过程,每一个商品的所有者所要交换的是他所需要的特殊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商品交换过程又是一个社会的过程,每一个商品所有者都要使他的商品价值得以实现,而价值的实现需要得到社会的承认,这就是社会的过程。商品交换过程是个人过程同一般社会过程的统一,但问题在于现实生活中二者往往难以统一,从而使商品交换无法进行。例如,作为个人的过程,麻布所有者想把自己的麻布同上衣相交换,但是上衣所有者并不一定需要麻布,当上衣所有者不需要麻布时,麻布就不能实现它的价值,社会的过程不能完成,个人的过程也无法进行,于是,商品交换产生了困难。
商品交换产生困难的原因,或者说,个人的过程和一般的社会过程往往不能统一的原因在于,为了实现自己商品的价值,每个商品所有者都把所有的其他商品当作是自己商品的特殊等价物,为了取得他人商品的使用价值,又把自己的商品当作是一般等价物。又因每个商品所有者都把自己的商品看作是一般等价物,结果却是任何商品都不是一般等价物,造成了商品交换的困难。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这一矛盾会越来越突出。经过商品交换的不断发展,会自然形成一个公认的一般等价物,由物物之间交换变为以一般等价物商品为中介的间接交换,所有商品都把自己的价值统一表现在这个以贵金属为代表的一般等价物上面,这个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就成为大家都乐意接受的货币了。上衣生产者虽不需要麻布,但当麻布被换成货币之后,就会被上衣生产者接受,麻布交换上衣的过程也得以完成。
这种为大家所乐意接受的一般等价物,不是由人们的头脑想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自发产生出来的。它不是自封的,也不是由个别商品的行动造成的,而是由商品世界中的社会行动造成的,即通过商品的社会活动,把某一种商品作为一般等价物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
货币是由商品转化而来的,商品又是从劳动产品转化而来的,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的过程是从劳动产品进入交换过程开始的,但是,劳动产品最终转化为商品,是在货币出现以后才完成的。因此,在交换过程中,一方面是劳动产品逐渐完成向商品的转化过程,另一方面又是商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在商品转化为货币的同时,劳动产品也最终转化为商品。马克思说:“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

货币的形成过程,或者说,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的过程,共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直接的产品交换阶段,即物物交换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价值形式表现为简单的价值形式和扩大的价值形式。第二阶段,是通过中介物进行的商品交换阶段,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一般的价值形式和货币形式。
直接的产品交换或物物交换,是劳动产品在满足生产者的直接需要之后还有剩余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直接消费而不是交换,因而生产者不是把这种产品作为商品来生产的,只是在消费不了、有所剩余时才拿去市场交换其他商品,这时候他的产品才作为商品出现。
这种产品具有双重性质,在进入交换过程之前,即在生产过程中,它仅仅是作为产品而不是商品而存在,进入交换过程后,它才开始成为商品。由于这时还没有形成一般等价物,进入交换过程的各种产品就没有共同的价值表现,因而除直接交换的产品双方互相以商品看待之外,其他产品相互之间都不是作为商品看待的。马克思指出:“没有一个商品是一般等价物,因而商品也就不具有使它们作为价值彼此等同、作为价值量互相比较的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因此,它们并不是作为商品,而只是作为产品或使用价值彼此对立着。”
 劳动产品没有从生产过程直接进入消费过程,而是进入了交换过程,这只是由劳动产品向商品转化的第一步。
劳动产品没有从生产过程直接进入消费过程,而是进入了交换过程,这只是由劳动产品向商品转化的第一步。
在直接的产品交换阶段,商品价值的表现最开始出现的是简单的价值形式,进而发展为扩大的价值形式。
20码麻布=1件上衣
早在人类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之前,处于原始社会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甚至更早的蒙昧时代的中高级阶段中,就出现了这种价值形式。
当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虽已懂得用火和制造陶器,但主要生产工具仍然是弓箭和石器,以捕鱼狩猎为主。偶尔有些剩余产品,这一方面使交换有了可能,另一方面又决定了交换是一种偶然发生的现象。
“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能采取直接的物物交换形式进行交换活动的地区非常有限。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能采取直接的物物交换形式进行交换活动的地区非常有限。
由于交换行为是偶然发生的,决定了“20码麻布=1件上衣”这种价值形式也是偶然出现的,产品之间交换的量的比例也是偶然确定的。价值的表现形式非常简单,一个商品的价值只是通过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形式表现出来的,或者说,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是表现另一个商品的价值。
简单价值形式“20麻布=1件上衣”的两端,一端是麻布,另一端是上衣。麻布的价值通过上衣的使用价值形式被相对地表现出来,处于相对价值形式的位置上,由于麻布是价值被表现的商品,在价值形式中起主动作用;上衣是作为表现麻布这一商品价值的材料,是表现价值的商品,处于等价形式的位置上,起被动作用。
一方面,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是相互依存的,如果没有相对价值形式,即没有需要被表现价值的商品,也就不会存在用来表现这一商品价值的商品,即等价形式。反之,如果没有用来表现价值的商品,即等价形式,另一种商品的价值就不能被表现出来,因而也就没有相对价值形式。
另一方面,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又是互相排斥的,同一个商品在同一个价值表现中不能同时具有两种形式,因为一个商品同时出现两种价值形式只会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发生。第一种情况:20码麻布=20码麻布,这个公式是不能成立的。第二种情况:20码麻布=1件上衣,1件上衣=20码麻布,在这里“麻布”和“上衣”虽然先后处在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位置上,但在同一个价值表现中,“麻布”或“上衣”只能以一种价值形式出现。
相对价值形式的内容是物化了的抽象劳动,它是通过另一商品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一认识是由“20码麻布=1件上衣”这种价值形式告诉我们的,麻布和上衣相等,说明二者都是同质的一般人类劳动;麻布把上衣作为自己的价值形式,这又告诉我们,麻布的价值不能由麻布自身表现出来,而要由另一商品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
相对价值形式量的规定有它的规律性。由于商品A (麻布)的价值量是相对地表现在另一个商品B (上衣)的使用价值上,因而商品A (麻布)的相对价值量不仅取决于商品A (麻布)本身的价值量(二者成正比),也取决于商品B(上衣)的价值量(二者成反比)。按照前面的论述,商品A (麻布)和商品B(上衣)的价值量,是随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而变动的。
相对价值形式量的具体规定有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商品B (上衣)的价值量不变时,商品A (麻布)的相对价值量和商品A (麻布)本身的价值量变化成正比。例如,原来20码麻布和1件上衣的价值量相等,均为1小时,二者相交换时,20码麻布=1件上衣。现在麻布价值量提高一倍,20码麻布价值量为2小时,而上衣的价值量未变,仍为1小时,二者相交换时,20码麻布=
 件上衣,麻布的绝对价值量增加一倍,麻布的相对价值量也增加一倍。
件上衣,麻布的绝对价值量增加一倍,麻布的相对价值量也增加一倍。
第二种情况,商品A (麻布)的价值量不变时,商品A (麻布)的相对价值量和商品B(上衣)的价值量变化成反比。仍按照上例,现在上衣的价值量增加1倍,1件上衣的价值量为2小时,麻布的价值量未变,仍为1小时,二者相交换时,20码麻布=
 件上衣,或40码麻布=1件上衣,麻布的实际价值量虽未发生变化,但是它的价值表现即相对价值量却因上衣的价值量增加1倍而减少一半。
件上衣,或40码麻布=1件上衣,麻布的实际价值量虽未发生变化,但是它的价值表现即相对价值量却因上衣的价值量增加1倍而减少一半。
第三种情况,商品A (麻布)和商品B (上衣)的价值量按照同一方向和同一比例同时进行变动,商品A (麻布)的相对价值量不变。再按照上例,现在麻布和上衣的价值量同时都减少一半,20码麻布和1件上衣的价值量都由1小时减为半小时,二者相交换时,仍然是20码麻布=1件上衣,麻布的实际价值量变了,它的相对价值量却不变。
第四种情况,商品A (麻布)和商品B (上衣)的价值量按照相反方向变动,或者按照同一方向但不同比例变动,商品A (麻布)的相对价值量可按上述情况推算,进而得出各种更具体的结果。
根据上面的分析,除第一种情况外,可知道相对价值形式量的规定不能准确地反映商品价值量的变化,而第一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是极为少见的,即使出现了,也会由于各种情况混杂而难以辨认。这种缺点是由商品经济本身决定的,只要存在商品经济,这一缺点就不可避免。
处于等价形式上的上衣之所以能够表现出麻布的价值量,是因为上衣本身具有价值和价值量,但是上衣一旦处于等价形式的位置,其价值量就不会被表现出来。首先,上衣的价值量不能由处于相对价值形式位置的商品麻布来表现,这是因为麻布是价值被表现的商品,它本身的价值都有赖于上衣来表现,又怎么能表现上衣的价值呢?其次,上衣的价值也不能由上衣自身来表现,上衣如果能用其自身来表现它的价值,同样,麻布也能用麻布自身来表现它的价值,因而也就不会存在处于等价形式位置上的上衣了,可见,商品的等价形式不包含价值的量的规定。
商品的等价形式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以它的使用价值作为另一个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在20码麻布=1件上衣的等式中,上衣之所以能够以它的使用价值表现麻布的价值,是因为上衣本身也有价值。由于商品的等价形式不包含价值的量的规定,上衣的价值量没能表现出来,从而不能用上衣的价值量去表现麻布的价值量。等价形式的这一特点使人产生错觉,误以为上衣能够表现麻布的价值,不是由于上衣的价值,而是由于上衣的使用价值及自然属性,麻布的价值量取决于上衣的使用价值量,麻布的价值被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见了,产生了等价形式之谜,货币之谜即由此发展而来。
第二,以它的具体劳动作为另一个商品的抽象劳动的表现形式。在20码麻布=1件上衣的价值形式中,上衣以它的自然形式充当麻布的价值形式,证明了麻布和上衣一样是人类劳动的凝结物。但是生产上衣的劳动是具体劳动,于是,上衣就以自己的具体劳动,表现了生产麻布的劳动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生产上衣的具体劳动成为凝结在麻布中的抽象劳动的表现形式。生产上衣的劳动之所以能够成为商品麻布抽象劳动的表现形式,是因为上衣也和麻布一样是一般人类劳动,这一点是通过20码麻布=1件上衣的等式表现出来的。在价值的生产上,是抽象劳动,但在价值的表现上,却是具体劳动,这使人误以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具体劳动决定的。
第三,私人劳动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的表现形式。在20码麻布=1件上衣的价值形式中,麻布由于得到上衣的承认而使生产麻布的私人劳动成为一种社会劳动,这时作为生产上衣的私人劳动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的表现形式。这一特点告诉我们,任何商品的生产,不仅仅是私人的事情,商品生产者必须通过交换使商品取得社会的承认,但是这种社会承认却表现在另一私人的购买上。
简单价值形式使商品价值开始取得独立的表现形式,商品内部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开始表现为外部对立。在20码麻布=1件上衣的例子中,麻布作为使用价值出现,上衣作为价值出现。简单价值形式20码麻布=1件上衣成为后来货币形式20码麻布=X量黄金的萌芽形式。
在简单价值形式中,一个商品的价值只表现在另外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因而商品的价值性质与价值量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和证明。

在原始社会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发生了人类社会第一次大分工,出现了畜牧业,牲畜及其肉乳皮毛等剩余产品增加了,参加交换的产品无论从数量上或品种上看都增多了。现在,某一种商品,例如麻布,不仅和上衣相交换,还和其他许多商品相交换,这时,简单的价值形式就为扩大的价值形式所替代。
从简单的价值形式发展到扩大的价值形式,价值形式有了重大的变化。
从相对价值形式方面来看,原来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上,相对价值形式是简单的,现在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在一系列商品的使用价值上,相对价值形式是扩大的。这一变化的意义,从质的方面看,现在由于一个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由一系列的商品来表现和证明,并且可以由任何使用价值来表现,商品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与具体的使用价值形式无关,真正表现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从量的方面看,商品麻布和其他商品均以劳动为尺度,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交换,表现出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交换价值量,而不是交换价值量决定价值量。
从等价形式方面来看,原来一个商品的价值只通过另外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表现,等价形式是个别的,现在一个商品的价值通过一系列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表现,等价形式是特殊的。
扩大的价值形式也有它的缺点。从相对价值形式方面看,处在相对价值形式上的商品的价值表现始终是未完成的,因为随着新的商品不断出现,它的价值表现材料也不断增加。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也是杂乱无章的,每个商品都各自有其价值表现系列,它们交织在一起,拼成一幅五颜六色的镶嵌画。从等价形式方面看,一个商品的价值有无数特殊的等价形式,却没有一个统一的等价形式,因而许多商品都处在等价形式上,互相却不以等价形式相对待,也正因如此,在商品交换中经常发生这样的困难:如麻布生产者需要上衣,上衣生产者却不要麻布而要茶叶,茶叶生产者又不要上衣而要小麦,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交换难以进行。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这种矛盾越来越突出,要求有新的价值形式来解决矛盾。
随着生产的发展,交换行为越来越频繁,劳动产品越来越多地转化为商品,有些产品甚至在生产过程开始时就作为商品来生产,出现了以交换为直接目的的商品生产。由于劳动产品逐渐固定下来,分为直接消费的产品和用来交换的产品,对于生产者来说,交换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不再是由他个人意志决定的事情,而是一种有规则的社会行为,越来越成为社会的迫切需要。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形成了一般等价物,其他商品都把自己的价值表现在这个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上,在交换过程中,不仅发生交换的双方产品互相作为商品,所有一切进行交换的产品都互相作为商品,都表现为在价值上相同,在价值量上可以互相比较。
随着商品生产的出现和价值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逐渐转化为货币,与此同时,劳动产品也最终转化为商品。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进行交换的产品无论从数量上或品种上看都越来越多,交换行为越来越频繁。在交换过程中,有的商品如麻布逐渐成为大家所乐意接受的产品,经常用其他各种商品与之交换,形成一定的比例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商品都把自己的价值表现在麻布上,用麻布的价值表现来确定其他各种商品交换的比例。于是,麻布这一商品成为公认的一般等价物,扩大的价值形式演变为一般的价值形式。
在此之前,商品交换比较困难,比例关系也难以确定,现在由于麻布成为一般等价物,商品交换就比较容易进行,交换的比例也容易确定。例如,当麻布成为一般等价物后,上衣生产者虽不需要麻布,但仍会乐意和麻布生产者相交换,因为他获得麻布后,立即可换回他真正需要的茶叶。上衣和茶叶的交换比例也是比较容易确定的,因为现在各种商品都把自己的价值表现在麻布上,1件上衣的价值表现为20码麻布,10磅茶叶的价值表现为20码麻布,上衣和茶叶的交换比例很容易被确定下来。
一般价值形式的出现,使价值形式又一次发生质的变化。在此之前,无论是简单的价值形式或扩大的价值形式,都是直接的物物交换,表现为:1件上衣=10磅茶叶,1夸特小麦=40磅咖啡。商品的价值表现总是和所要交换的使用价值结合在一起,没有一个独立的价值形式,从而没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表现形式。现在由于形成了一般等价物,各种商品有了一个独立的、共同的价值形式,以这个一般等价物为中介进行间接的商品交换,表现为:1件上衣—20码麻布—10磅茶叶,1夸特小麦—20码麻布—40磅咖啡。在直接的产品交换中,买和卖是同一个行为,因而买和卖在同时同地进行,现在,买和卖分裂为两个行为,先卖后买,因而买和卖的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上会发生分裂。
一般价值形式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范围比较狭窄,如在这一小块地区的一般等价物是麻布,在另一小块地区的一般等价物是茶叶。不仅在地区上很不统一,在时间上也很不固定,如现在一般等价物是麻布,过些时候又会变成其他商品来充当一般等价物。第二阶段,形成比较固定和统一的一般等价物,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提到了牲畜这种商品。在种植业发展起来以前,肉类是人们最主要的食物,对于非游牧部落来说,牲畜是最重要的外来商品,这样一来,牲畜越来越成为人们经常与之交换的商品。货币是一种固定而又统一的一般等价物,此时牲畜开始拥有这种货币的职能。第三阶段,一般等价物固定在贵金属上,形成了货币。

在原始社会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人类社会发生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形成了全部或大部分产品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突破了地方的限制,甚至出现了海外贸易,用牲畜这一类商品充当一般等价物越来越不能适应商品交换的需要:质地不均匀,不能随意分割与合并,难以表现和计算其他商品的价值;体积大,价值小,又是鲜活商品,难以保存和携带。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最终落在黄金或白银等贵金属身上,它的天然属性使它具有任何其他商品难以具有的种种优点:第一,体积小,价值大,便于携带;第二,不易腐烂变质和熔解,便于储存;第三,质地均匀,可随意分合,能够准确表现商品的价值量。于是,原来作为普通商品的贵金属,一旦时机成熟,就从商品群体中脱颖而出,成为具有特殊地位的一般商品,即货币。
货币形式也是一般价值形式,二者并无质的区别。不同在于,在货币形式中,一般等价物由贵金属担任,因而在时间上固定了下来,在广大地区范围内统一了起来。
这种变化使商品经济矛盾有了一个新的发展,在商品世界中形成了两极对立现象,一极是普通商品,以使用价值形式出现在购买者面前;另一极是货币,以价值的体化物出现在卖者面前。商品内部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从此表现为商品和货币的外部矛盾,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两极对立由此固定下来。
货币是固定由贵金属充当的一般等价物,也是一种商品,和普通商品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般商品。
货币来自于商品,它也和其他商品一样,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体。从价值上看,对于作为货币材料的贵金属的开采,不论劳动形式有何差别,和其他商品一样,都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物。从使用价值上看,货币也和其他商品一样,有它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只是货币的特殊使用价值不是用来吃穿,甚至也不是用来作为金银首饰,而是用来充当一般等价物。
但是货币又不同于普通商品。第一,由于货币能够充当一般等价物,使它成为一般商品,其他商品不论其使用价值如何特殊,都不能处在这一特殊地位上。第二,普通商品不论其使用价值如何特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它们都是各种具体劳动的产物,而货币的使用价值却是由交换过程赋予的。
货币首先是商品,我们从价值形式的发展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货币名目论却认为货币是一种单纯符号,它的价值是人们在交换中想象出来的。
货币名目论的错误在于:
第一,作为货币材料的贵金属,它的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就已经形成了的,在交换过程中,贵金属只是得到特殊的价值形式,而货币名目论却误认为贵金属的价值是人们在交换过程中随意确定的,否定货币本身具有内在的价值。
第二,货币在发挥它的流通手段职能时,可以由完全没有价值的纸币来代替,货币名目论又误认为货币是一种单纯符号,把货币担负流通手段的这一具体职能看作是货币的本质,把作为货币符号的纸币和它所代表的货币混为一谈。
货币金属论就是把货币看作是金银的天然属性。如果说货币名目论不懂得货币是商品,货币金属论则不懂得商品是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
货币金属论的产生是由于处在等价形式上的商品用它的使用价值即自然形式去表现其他商品的价值,处在等价形式上的商品虽说包含价值量,却不表现出来,使人们误认为处在等价形式上的商品之所以能够表现其他商品的价值,是由它的自然属性决定的。这种假象到了货币形式时,就更使人迷惑了,因为这时的一般等价物和贵金属的自然形式完全融合在一起,金银从地下开采出来后,就作为一般等价物发生作用,货币形成的历史过程不见了,金银似乎天然就是货币。
货币金属论是一种货币拜物教,比之于商品拜物教,更使人着迷,更“光辉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