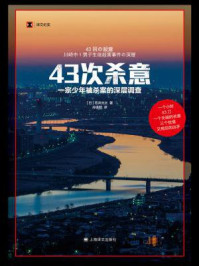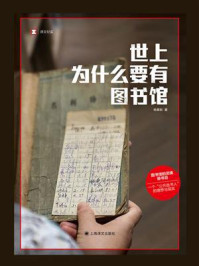《汉书·艺文志》中关于总结形法数术的形气关系有:“犹律有长短而各徵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中关于叙述精气同类相感的有:“气同则会,声比则应……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而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数自然也。”可见,精气说与鬼神论没有必然关系;同时可知,有些数术与鬼神论无关,有些与鬼神论有关
 。与数术有关的神人关系观念,也是两汉数术的基础理论之一。
。与数术有关的神人关系观念,也是两汉数术的基础理论之一。
在两汉文献里,“命”或“天命”的含义有两种。
一种指个人性命。《论衡·骨相》曰:“命谓初所禀得而生者也。”又,《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郑玄《注》曰:“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
另一种指帝王天命,即帝王有天下之命。《汉书·高帝纪》载刘邦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帝王天命也可以看作是个人命运的一种,《汉书·高帝纪》中载老父对汉高祖曰:“君相贵不可言。”这里的“贵”,是对刘邦个人性命的判断,而实际上指刘邦得天命有天下。
汉朝人以为,每个人的一切都受命于天,无论个人性命还是帝王天命。《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曰:“天令之谓命……人受命于天……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这是指个人性命。对于《诗·大雅·文王》,毛氏《传·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郑玄《笺》曰:“受命者,受天命王天下也。”这是指帝王天命。
个人性命包括生命、性情、命运等。《周易·乾》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孔颖达《疏》曰:“性者,天生之质,若刚柔迟速之别;命者,人所禀受,若贵贱夭寿之属也。”“夭寿”指生命,“天生之质”即人的性情,“贵贱”指人的命运。
两汉乃至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天子受命于天的观念,不能简单地归为“君权神授”这一看不出东西方区别的、看不出历史区别的抽象表述。在两汉,天子“受天命王天下”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第一,“受天命王天下”,是指某一姓受天命有天下。
天子有天下,《诗·小雅·北山》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又,《吕氏春秋·异用》谓周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
天子要有天下,必须得到天命,人为是不可能取得的,《汉书·董仲舒传》引董仲舒曰:“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汉书·叙传》曰:“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尚书璇玑钤》(《纬书集成》收)曰:“天子之尊也,……天之爱子也。”《潜夫论·释难》曰:“皇天无亲。帝王……父事天;王者为子,故父事天也。”《后汉书·李固传》载李固曰:“臣闻王者父天母地,宝有山川。”
得天命的不是某一人,而是某一姓。天子有两种:一种是始受命之君;另一种是继体之君。《汉书·匡衡传》载匡衡曰:“盖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继体之君”也是受命之君,《汉书·外戚传》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白虎通·爵》曰:“帝王……所以俱称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继体之君是始受命之君的同姓后代,之所以也承天命,是因为天命不是只给某一人,而是给某一姓的。《春秋繁露·楚庄王》曰:“受命于天,易姓更王。”《史记·历书》曰:“王者易姓受命。”《白虎通·三正》曰:“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
第二,天子受天命有天下,是天命其治理天下万民,而不是个人享受。
《白虎通·爵》曰:“帝王之德有优劣,所以俱称天子者何?……”《尚书》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曰:“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者,指王,《白虎通·号》曰:“王者,往也。天下所归往。”又,《汉书·贡禹传》载贡禹曰:“王者受命于天,为民父母。”天子为民父母,就是治理人民,《〈春秋〉左传·文公十三年》中载邾子曰:“天生民而树之君。”又,《潜夫论·班禄》曰:“太古之时,烝黎初载,未有上下,而自顺序,天未事焉,君未设焉。后稍矫虔,或相陵虐,侵渔不止,为萌巨害。于是天命圣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四海蒙利,莫不被德,佥共奉戴,谓之天子。”又,《易纬乾凿度·卷上》曰:“天子者,继天理物;……父天母地,以养万民。”
第三,天子受天命有天下,没有与天命无关的私情、私事、私德;其为人、做事、行政无一不与天命有关。《汉书·文帝纪》载宋昌曰:“王者无私。”
第四,天命无常,不专属于某一姓。
《尚书·康诰》曰:“天命不于常。”又,《诗·大雅·文王》曰:“天命靡常。”又,《史记·陈涉世家》载陈胜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汉朝人通行的观点。《潜夫论·贤难》曰:“天命数靡常。”又,《春秋繁露·楚庄王》曰:“受命于天,易姓更王。”又,《汉书·谷永传》载谷永曰:“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又,《汉书·眭孟传》载眭孟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受命。’”这是说继体守文之君可能失天命,凡夫可能受命为圣王。
如果天子违背了天命,为所欲为,天对其轻则警告,重则降灾,直至更改天命,改朝换代。《汉书·文帝纪》载诏曰:“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又,《汉书·成帝纪》载诏曰:“盖闻天生众民,不能相治,为之立君以统理之。君道得,则草木昆虫咸得其所;人君不德,谪见天地,灾异娄发,以告不治。”又,《汉书·谷永传》载谷永曰:“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顺天地,博爱仁恕,恩及行苇,籍税取民不过常法,宫室车服不逾制度,事节财足,黎庶和睦,则卦气理效,五徵时序,百姓寿考,庶草蕃滋,符瑞并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穷奢极欲,湛湎荒淫,妇言是从,诛逐仁贤,离逖骨肉,群小用事,峻刑重赋,百姓愁怨,则卦气悖乱,咎徵著邮,上天震怒,灾异娄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溃,水泉踊出,妖孽并见,茀星耀光,饥馑荐臻,百姓短折,万物夭伤;终不改寤,恶洽变备,不复谴告,更命有德。”
可见,天下易姓更王,改朝换代,取决于是否有德。旧王朝是否失天命,取决于治民是否有德;新一姓是否得天命,取决于是否有德治民。《汉书·公孙弘传》载公孙弘曰:“臣闻尧遭鸿水,使禹治之,未闻禹之有水也。若汤之旱,则桀之余烈也。桀、纣行恶,受天之罚;禹、汤积德,以王天下。因此观之,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又,《汉书·叙传》曰:“虽其遭遇异时,禅代不同,至于应天顺民,其揆一也。”又,《汉书·刘向传》载刘向曰:“孔子论《诗》,至于‘殷士肤敏,裸将于京’。”颜师古《注》曰:“此《大雅·文王》之篇。……言殷之臣有美德而敏疾,乃来助祭于周,行裸鬯之事。是天命无常,归于有德。”又,《汉书·叙传》曰:“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
鬼神与人异道,是指鬼神的世界不是人可以知道的,人不能根据人的世界来想象鬼神的世界。这是春秋至两汉的儒家观念。
汉朝人常讨论鬼神是否有知的问题,汉儒都认为,这个问题不可回答。如,《汉书·刘向传》载刘向曰:“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安用大。”又,《汉书·外戚传》载班倢伃曰:“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诉;如其无知,诉之何益?”不置可否的态度,可以追溯到孔子那里去,《说苑·辨物》曰:“子贡问孔子:‘死人有知无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孔子说,死后是否有知这个问题,死了再知道也不迟,实际上不置可否。
不置可否,是既不能说有知觉,也不能说无知觉,究其理由,就是鬼神与人异道,人不能以自己的世界猜测鬼神的世界。《礼记·檀弓上》载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郑玄《注》曰:“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这是说,人死后什么也没有,所以没有任何明器随葬,这是对死者不仁,是不对的;但认为人死后像生人一样,也是不对的。因为人不可能知道死后的世界。所以,明器要有,但既要与生人所用的相似,又不能真的有用。这里,孔子提出一个原则:生人不知鬼神的世界。实际上,孔子说“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也是因为生人不知鬼神的世界,因为如果认为人死后什么也没有,就说明生人是知道鬼神的世界的。所以,前文所引《说苑·辨物》,孔子既不说人死而有知,也不说人死而无知。
《礼记·檀弓上》郑玄本《注》又曰:“神与人异道则不相伤。”郑玄将孔子这种对鬼神世界“不知而不可为”的态度解释为鬼神与人异道。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因为生人与鬼神不在一个世界,所以生人不可能知道鬼神世界,不能用生人世界去想鬼神世界;如果将生人世界的做法用到鬼神世界,就是对鬼神世界的侵害。
 鬼神与人异道的理论,派生出种种观念,其中以下两种直接影响到数术。
鬼神与人异道的理论,派生出种种观念,其中以下两种直接影响到数术。
第一,关于天命里的“天”。
无论个人命理还是天子承命,都是天命。这个能够命令人的天,不是指具体的天地万物,而是指具有总领意义、抽象意义的天,《春秋繁露·郊祭》曰:“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又,《论衡·辨别祟》曰:“天,百神主也。”但“天”究竟具体是什么,是否有人格,或者是否有神格,如果有又是什么神,春秋以来,语焉不详。这似乎并不是想说而未能说清楚,而是没必要说,《论语·述而》曰:“子不语怪、力、乱、神。”《庄子·齐物论》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之所以没必要说,是因为鬼神与人异道,人不能按人的世界想象天的世界。
第二,关于人与鬼神沟通。
人应听命于天,这是承认鬼神作用;承认鬼神作用,就应该承认鬼神与人可以沟通。但是,先秦对于鬼神与人是否真的可以沟通、如何沟通、机制如何,同样语焉不详。《论语·八佾》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朱熹《集注》曰:“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于孝,祭神主于敬。愚谓此门人记孔子祭祀之诚意。”这是说,祭祀本身是不是与鬼神沟通的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态度。祭祀是在庙里进行的,但并不是说在庙里就可以与祖先沟通,也不是说庙祭是与祖先沟通的通信机制;祭祀于庙,主要是态度问题、仪式问题。这正是人神异道的观念使然:人是不可能知道鬼神世界的,所以,不可能按人所理解的方式即人与人的沟通方式与鬼神进行沟通。祭祀时人与鬼神究竟如何沟通,没必要说清楚;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不能按照人与人的沟通方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