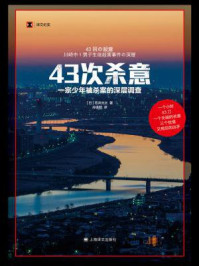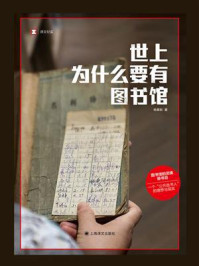不管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还是乡村和城市,山区和沿海,它们都各不相同。但这些地方的不同不仅在于它们的地理位置,或者说物理空间;也同时在于它们的心理图景,或者说群体意义空间。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关于幸福和自我的土地。
——Plaut,Markus & Lachman,2002
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社会性的动物(Aronson,2011),他强调了社会影响的重要性。如果从更广阔的意义来看,人也是一种生活在特定地理空间的生物,正如Sample(1911)认为,“人是地球表面的产物……(自然)已经进入他的骨和组织,进入他的心灵和灵魂”。笔者并不是要论证这种环境决定论的正确与否,而是希望借此说明:人类的心理与行为有不可避免地带上地域特征烙印的可能。事实上,心理学的跨国实证研究证据的确发现,人格存在地理分布特征(Allik & McCrae,2004)。尤其是近些年网络技术手段的发展和应用,使得测量国家内不同地区大规模人群人格特征的研究成为可能。区域水平的人格研究发现,人格在国家内区域水平也存在显著的地理差异(Rentfrow,Gosling &Potter,2008)。目前的一些初步证据表明,区域人格还与一系列重要社会指标之间存在着关联(例如,Rentfrow,Jokela & Lamb,2015)。
健康问题作为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变量,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探索的核心话题之一。那么各地区居民群体的人格特征,与该地区的健康(包括积极心理学关注的积极面,即幸福感,以及传统健康领域的寿命/死亡率、心理疾病率、物质滥用和健康行为等)是否存在特定的关联?即某种人格特质突出的地区是否与特定的健康特征相关联?如果更进一步考虑人格与健康关系的作用机制问题,在不同的文化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下,地区的人格特征与健康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即具有不同人格特征的地区在不同的环境(包括文化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下,是否会因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潜能实现程度、风险暴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最终导致在健康结果上呈现出一些系统性的差异和规律?例如,神经质对幸福感的消极作用在集体主义高的地方相比集体主义文化低的地方会更弱吗?即集体主义文化能缓冲神经质对幸福感的消极作用吗?基尼系数的高低会影响宜人性与预期寿命之间的关系吗?等等。本书将围绕以上问题展开实证研究和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