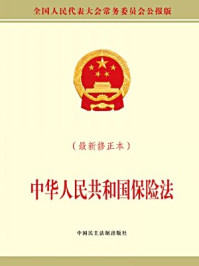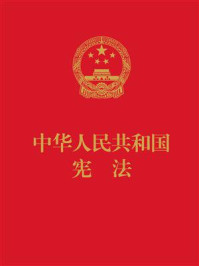在国际层面,“冲突”一词的运用频率似乎格外地高,武装冲突、外交冲突等都是新闻中频繁出现的组合。在国际法的领域内,“冲突”也在多种场合被使用着,法律冲突、冲突法、规则冲突、制度冲突等在不同的意义上展现了国际法上冲突的存在。然而,目前“权利冲突”这一词汇在国际法领域内还较少见及。为了明确国际法上权利冲突的内涵,建立对权利冲突在法理学上含义的分析与理解的基础,还有必要对国际法上“冲突”一词的使用情况加以分析、区别与借鉴。
当我们将目光放在国际法上各主体间的权利冲突问题上时,有必要将这里所要讨论的冲突与国际私法上的法律冲突相区别。法律冲突是指由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实质不同但却可适用于相同或相似事实的规则,适用二者将得出相反的裁决,所以必须要从中作出选择的情况。 [24] 国际私法上所说的法律冲突一般是指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即“所涉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民商事法律对同一民商事关系或同一民商事问题的规定各不相同,对它们却又都有加以适用的立法管辖权,从而造成法律适用上的相互抵触的现象”。 [25] 也就是说,国际私法要处理的是由于各国民商事法律对同一问题规定的不同,在解决某一涉外民商事争议时适用不同国家的相关法律会产生不同结果的问题。本书所要讨论的国际法上的权利冲突与国际私法上的法律冲突的区别在于:首先,这里讨论的是由国际法规则所赋予的具体权利的冲突,而不是规则的冲突,更不是法律适用的冲突;其次,这些冲突的权利来源于国际法各渊源,而非来自各国国内法;最后,这些权利的冲突也不仅限于民商事领域,国际法各分支上的权利都可能出现矛盾的状态。所以,国际法上的权利冲突,与国际私法上的法律冲突也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
在国际法领域内,原本规则冲突的概念没有受到太多关注,但是在鲍威林关于国际公法规则冲突的专著出版以来,关于规则冲突的讨论开始频繁出现。最初的规则冲突概念总是与两种相互排斥的法律义务逻辑上的不一致相联系。第一位对国际法上狭义的“冲突”概念作出界定的学者是詹克斯(Wilfred Jenks),他认为:“在直接不一致的严格意义上,冲突只会在两个条约的同一缔约国无法同时履行这两个条约的义务时才会产生。” [26] 1984年,卡尔(Wolfram Karl)表达了实质相同的看法:“当两个条约所规定的义务无法被同时履行时才会产生条约间的冲突。” [27] 阿克哈维(SadatAkhavi)也指出:“规则冲突是在不可能同时遵守两项规则的所有要求时才产生。” [28] 这些对于国际法上冲突概念的传统理解都是将规则冲突限定在狭义的范围之内,即认为“冲突”的概念仅仅指义务相互排斥的情况。凯尔森、克莱恩(Klein)和威尔丁(Wilting)等学者都接受这种对“冲突”概念的严格界定。 [29]
有些学者对“冲突”的界定较为宽泛。比如,1965年,佩雷尔曼(Perelman)在界定规则冲突时就没有强调义务冲突,他认为规则冲突就是“两个人为的法律规则同时按各自规定之适用的不可能性,这两个规则各自足以适用,而且没有一个强制法律条款使一个规则从属于另一个规则。” [30] 其实在这个界定中,“规则同时按各自规定之适用的不可能性”就可以涵盖规则规定的权利无法同时行使的情况,即权利冲突的问题。但原作者并没有将规则具体化,没有提及权利冲突的问题。
在最近发表的国际法文章中,对“冲突”的狭义界定遭到了批评。受到批评的方面:一是,在界定规则冲突时,我们会自动地倾向于要求与禁止,而不是允许的事项;二是,传统的规则冲突的界定倾向于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一个主体的法律义务都是与其他主体的权利相对应的。这就意味着,在分析法律规则时,对于某一法律规则表达了哪些禁止、要求或者许可,根据我们所持主体角度的不同,答案也会不同。 [31] 对一方主体来说,某一规则表达的是禁止,而对于与该义务相对的权利主体来说,同样的规则就可能被看作是对该主体某项权利的认可。
在对狭义的冲突界定持批判态度的基础上,有学者主张“冲突”应该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界定,这种主张实质上更支持佩雷尔曼的界定方式。有学者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类似的宽泛界定,“如果主张两个规则R1、R2相冲突,就等于说,根据R1,某种法律关系SS应当按照φ这种方式来组织,但根据R2,同样的法律关系应当按照-φ的方式来组织”, [32] 其中的法律关系可以指两项义务的安排,也可能涵盖权利的安排。这些宽泛的界定方式都给从规则冲突界定中将权利冲突具体化提供了可能。还有学者在对“法律冲突”一词,在一般意义上而非国际私法意义上使用的情况下,捕捉到了WTO专家组在“欧共体香蕉案Ⅲ”中对“冲突”的宽泛界定,可以理解为“如果实现一个规则(无论是命令性的规则还是仅仅是一项权利)将引起对另一个规则的违反时,冲突就会发生”。这一界定不仅涵盖了“一方无法同时遵守不同协定”时产生的冲突,即义务之间的冲突,还包括了如果一方自由选择行使某项权利或协议中的某个例外而引起的对其他协定的违反的这种潜在冲突。 [33] 鲍威林也指出:“当谈到规则的冲突时,‘冲突’和‘不一致’可以替换使用。两者都可以概括为一种规则的存在状态,即一项规则已经引起或潜在引起违反另一项规则。” [34] 鲍威林的观点一方面肯定了“冲突”是一种状态,另一方面也将潜在的规则冲突涵盖了进来,给了权利冲突存在的空间。与之相似地,最近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国际法上冲突的认识更倾向于“不仅指不能同时被遵守的规则,还包括追求不同目的的规则”。 [35] 这样的宽泛界定在持传统观点的学者对“冲突”进行狭义界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涵盖了一项规则确立义务,另一项规则赋予权利的情况,在规则冲突中考虑进了权利的因素,使对“冲突”的界定向前推进了一步。
然而,这种比狭义的冲突界定较为宽泛的认识仍然存在观察角度等方面的局限性。这些界定大多将冲突的产生限定在一个主体无法同时满足两项规则规定的情况,前面对于冲突的狭义界定也均是如此。这种“一个主体”的理解可以解释为什么学者们在定义冲突时会纠结于是否将赋权性条款涵盖进来,因为对于同一主体,相对于必须履行的义务来说,它的确可以选择不行使权利来避免这一冲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关注规则冲突或者一般意义上的法律冲突的学者,没有提到权利与权利的冲突的原因,因为在对同一主体的分析中,不可能出现权利之间的冲突,那最多是一种“选择困难”。然而,当面对两个或者更多的主体各自依据不同的规则行为时又会出现怎样的冲突状况呢?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视角就给了权利与权利之间冲突存在的空间。具体来说,当不同的主体各自依据不同的赋权规则而行为,而这些权利存在客体上的重叠却又无法同时实现时,权利冲突就此发生。在规则层面上,这就是两个许可性的规则在逻辑上的矛盾之处,就是这样两个规则之间潜在的冲突。国际法领域同样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隆端寺地区领土主权的争端就是这类冲突的典型表现。因而,对国际法上的权利冲突,在认识上要突破从一个既定的主体出发来审视规则的视角,这样才能避免前文述及的从义务冲突的角度认识权利冲突可能陷入的误区。
笔者之所以在这里用较大的篇幅介绍国际法学者们对规则冲突的认识,是因为在法学领域内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在国内各部门法及法理学的研究中,对权利冲突的直接研究较为多见,谈及规则冲突的文章则很少;而在国际法学的研究中刚好相反,很多文章都以规则冲突为研究对象,却极少有人谈及权利冲突。所以要对国际法上的权利冲突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就离不开对国际法上规则冲突研究的基础。而要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我们既要认识规则与权利的关系,又要对国际法的体系状态有所了解。
对于法定权利来说,规则是权利的主要载体。 [36] 鲍威林指出:“规则之冲突可以概括为一国或几个国家的权利和/或义务的冲突……更确切地说,是这些适用于特别国家之间的规则所确立的权利和/或义务的冲突。” [37] 正如笔者在前文所论述的,广义的规则冲突应当反映具体的权利相冲突的情况。由于规则中既包括使主体承担义务的规则,也包括使主体享有权利的规则,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权利冲突是规则冲突的表现方式之一。鲍威林总结四种冲突情形所列的表格有助于我们理解规则与权利的关系(见表1)。
表1 [38]

表1中,鲍威林将前两种冲突的情形视为必然的冲突,后两种冲突的情形视为潜在的冲突。在笔者看来,若“规则1”是一项规定主体权利的授权性规则或者是免责性规则,根据“规则1”A国可以做X行为;而“规则2”同样是一项规定权利的规则,根据“规则2”B国可以做Y行为,在X行为与Y行为由于涉及同一客体而无法同时实现的时候,就会出现第5种即便是潜在的也是可能出现冲突的情形(见表2)。
表2

若将表2附于表1之后,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权利及权利冲突在规则冲突中的位置。但需要明确的是,虽然我们可以从规则之间潜在冲突的角度去理解权利冲突,权利冲突却并不能被认为是一种规则冲突,权利一旦被规则所认可,就成了独立于规则的存在。规则之间的冲突可能导致权利之间的冲突,有些权利冲突也可以被看作是规则冲突的表现,但二者终究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权利都来自法律规则的认可,有些权利是以法律原则为依据的,国际法上更是存在以习惯甚至是自然法理论为依据的权利。所以,在我们所探讨的范围之内,可以通过规则的冲突去认识权利的冲突,也可以从规则冲突的角度去分析权利冲突的原因甚至探寻解决冲突的方法,但不应将两个概念混用。
造成国际法与国内法上对规则冲突与权利冲突的研究侧重不同的情况,本质上来说是由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在体系结构上的差异所决定的。在国内法体系内,法的各种形式之间有着明确而稳定的地位和效力。就我国目前的法的形式来看,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在体系中居于最高的、核心的地位,在其之下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法律形式的地位和效力依次递减。 [39] 于是,分属不同形式的法的规则之间等级关系明确。对于同一级别的规则,也可以通过“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方式辨别优先顺序。因此,在国内法的体系内,规则冲突的发生概率很小,而权利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会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而产生冲突,在国内法领域内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而国际法体系则不同。由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特点,国际法的规则大都是由国家之间以国际条约等契约的方式形成的,从整体上来说,并不具有严整的规则体系与层级。的确有学者试图以一定的标准为国际法律规则分类。比如,根据霍夫曼(Hoffmann)的理论,“在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中可以区分出三种国际法:(1)关于政治构架的国际法——如界定基本状况、某些基本准则和国家间开展政治博弈规则的一揽子协定;(2)关于互惠的国际法,它规定在各种具体问题领域中形成和发展国际关系的条件与规则,一般受关于政治构架的基本法规限定;(3)关于共同体的国际法,它处理那些不能以相互分离的、处于竞争状态的各个国家在利益上的互惠为基础,只能以其行动超越了狭隘的国家利益的共同体为基础才能得到最佳解决的问题”。 [40] 也有学者结合国际法的历史与发展趋势,将国际法分为“三代”,即共存国际法、合作国际法和国际人权法。 [41] 但这些分类方法毕竟无法在实然的国际法中区别出规则的等级。这样,在国际法的领域,各规则之间发生冲突的频率就较国内法大大增加。所以,在国际法的研究中,规则本身的冲突就很吸引眼球,这导致了权利冲突被相对忽视。
综合以上分析,对国际法上规则冲突的研究与法理学上对权利冲突的研究同样都是国际法上权利冲突的研究基础。无论在目前的概念界定阶段,还是后文的分类、原因探究与冲突解决的部分,都离不开对这两个研究基础的融会贯通。
有的学者在研究国际法上的冲突问题时,将冲突分为“表面冲突”与“真实冲突”。“表面冲突”是指那些“可以轻易地通过像条约解释这样的方法就能解决的分歧”,在这些学者看来,这样的情况“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冲突,其实它不属于冲突”。 [42] 这样的“冲突”也不需要解决,只需要通过条约解释等方法避免即可;而只有当所有避免冲突的方法都被证明无效时,才会产生“真实冲突”。然而,这正如同前面提到的以状态来界定权利冲突还是以结果来界定权利冲突一样,既然我们已经将权利冲突界定为一种状态,那它就是作为一种未经处理的客观存在而存在,它可能存在于法律逻辑之中,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有事实的表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条约解释等方法已经是在对冲突存在给予肯定的基础上,对该冲突的解决方法。况且,国际法与国内法不同,条约的解释,即便是由国际法院等国际裁判机构作出,也不像国内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那般有普遍的约束力。采用不同条约解释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不同,不同的主体以各自的理解作出的解释也可能相异,而且即便某种对规则或原则的解释经过国家的反复实践与确信而形成习惯国际法规则,仍可能因为某个国家的一贯反对而对其不具有约束力。所以,在一方主体看来经过解释而不复存在的冲突,在另一方主体看来很可能仍处于冲突的状态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区分哪些才是“真实冲突”是很难找到明确的界限与标准的。因此,区分“表面冲突”与“真实冲突”的意义不大。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的确有一种表面看起来是冲突而实际上并非冲突的情况,这就是当某一规则作出了一项原则性的规定,而另一个规则则明确规定了该原则的例外。 [43] 实际上,这样的两个规则无论是赋予权利还是规定义务,都是不可能同时适用的,因为一旦符合例外规定的条件,原则性的规定对于该具体情况就将不再适用。所以,这样的两个规则,以及其中的具体权利和义务之间是不会产生现实的冲突的。GATT第3条与第20条的关系就类似这种“虚假冲突”,前者作出的是原则性的规定,而后者则是规定了例外情况。但在法律的规则中,这种对例外的规定有时却不符合“明确”这个标准,这样的现象在国际法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此时,即便规定有例外,但由于主体对模糊规则的理解可能不同,仍会造成依据原则而主张的权利与依据例外规定所主张的权利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其实在GATT的原则性规定与一般例外之间就存在这样的真实冲突。所以,在辨别某一权利冲突是否真实存在时,对例外规定是否“明确”的考量是必要的。
国际法上的制度冲突研究对象更加抽象和概括,对于权利冲突原因的分析和解决有更大的启示作用,对概念界定部分作用不大,故在此不展开论述。
综合上述对国际法上权利的界定,法理学中对权利冲突的界定,以及对国际法上规则冲突的认识,对国际法上权利冲突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第一,相冲突的权利都必须是被国际法所承认和保护的权利;第二,相冲突的权利必须分属于不同的权利主体,这里的权利主体并不限于确定的国际法的主体;第三,这里的冲突指的是一种矛盾的、不和谐的状态,具体来说是指由于权利客体的重叠而使两个或多个国际法上的权利无法同时实现的状态;第四,国际法的规则冲突与制度冲突都是国际法上的权利冲突在法律逻辑上的成因,而权利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现实化的冲突是负载该权利的规则、原则与制度的冲突在现实中的表现。
在第三章中,笔者将尝试探究具体在哪些国际法上的权利之间可能产生冲突,并对冲突在法律逻辑上和现实中的表现加以简要分析,以期对国际法上的权利冲突问题有更直观、更系统的把握。
[24]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Fragmentation ofInternational Law : Difficulties Arising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International Law ,UN Doc.A/CN.4/L.682(Apr.13,2006)(finalized by Martti Koskenniemi),pp.23-25.
[25] 屈广清、李双元:《国际私法》,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8页。
[26] Wilfred Jenks,“The Conflict of Law-Making Treaties”, British Yearbook ofInternational Law 30,1953,p.426.
[27] Wolfram Karl,“Treaties,Conflict Between”, Encyclopedia of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Vol.4,2000,p.936.
[28] Ali Sadat-Akhavi, Methods ofResolving Conflicts between Treaties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3,p.5.
[29] 参见[比]约斯特·鲍威林:《国际公法规则之冲突——WTO法与其他国际法规则如何联系》,周忠海、周丽瑛、马静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页。
[30] 参见[比]约斯特·鲍威林:《国际公法规则之冲突——WTO法与其他国际法规则如何联系》,周忠海、周丽瑛、马静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
[31] See Ulf Linderfalk,“Normative Conflict and the Fuzzin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ius cogens Regime”, ZaöRV 69,2009,p.967.
[32] 同上,第969页。
[33] See Tim Graewert,“Conflicting Laws and Jurisdiction in the Disputes Settlement Process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nd the WTO”, Contemporary Asia Arbitration Journal 1(2),2008,p.292.
[34] [比]约斯特·鲍威林:《国际公法规则之冲突——WTO法与其他国际法规则如何联系》,周忠海、周丽瑛、马静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页。
[35] Erich Vranes,“The Definition of ′Norm Conflict′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Legal Theory”, Europe an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Law 17,2006,p.396.
[36] 除规则外,法律原则也是权利的载体。参见熊静波:《真实世界中的权利冲突》,《时代法学》2004年第3期,第47—48页。
[37] [比]约斯特·鲍威林:《国际公法规则之冲突——WTO法与其他国际法规则如何联系》,周忠海、周丽瑛、马静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5页。
[38] 同上,第208—209页。
[39] 参见张文显:《法理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97—99页。
[40] See Stanley Hoffmann,“International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Law”,In Klaus Knorr and Sidney Verba,(ed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p.205-237,Also reprinted in Falk and Hanrieder 1968,pp.89-120.转引自[美]熊玠:《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余逊达、张铁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226页。
[41] 参见李春林:《国际法上的贸易与人权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页。
[42] [比]约斯特·鲍威林:《国际公法规则之冲突——WTO法与其他国际法规则如何联系》,周忠海、周丽瑛、马静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43] 同上,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