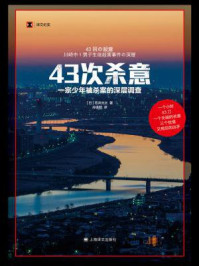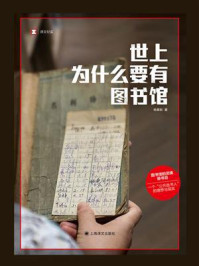城市与乡村是现代人类的主要居住形态,作为城与乡的联结点,县域在城镇化进程中有城市建成区扩大和农业转移劳动力两个主要特征。在大国大城的涌现和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在县域中出现了小县大城的现实样态。
新中国成立以来,县域人口变迁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展现着国家发展的脉络和人民生活的变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城乡二元结构下农业人口占据了绝大部分。1978年后,沿海地区县域人口密度急剧攀升,而内陆地区和一些偏远山区的人口密度则相对较低,这是当时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真实写照。进入21世纪,县域人口不断流向东部沿海与大城市。中国县域户籍人口数量由2016年的9.15亿人减少至2019年的8.97亿人,2019年中国县域户籍人口数量占全国户籍人口总数的63.9%。就区域分布来看,县域户籍人口的分布在空间上较为均衡,东部地区(含东北)占比为36.6%,中部地区占比为33.0%,西部地区占比为30.4%。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沿海地区的县域人口密度略有下降,而中西部地区和一些资源丰富的省份人口密度则逐渐上升,这是中国县域发展的新趋势。
由图2-1可见,决定未来县域发展格局及城乡关系变迁的根本力量在于人口迁移,核心在于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民分化与代际变化。随着城镇化的高歌猛进,农民群体发生高度分化,农二代的经济社会行为特征已经发生革命性变化,但鉴于城市权利视角下农二代权利滞后的严峻事实,伴随着农民进城的同时,在农二代、农三代相继离土难进城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回县的客观事实不容忽视。

图2-1 各年龄段人口的省内流动参与率和跨省流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1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每个年龄段的流动参与率为该年龄的流动人口数与该年龄段的人口总数的比值。
在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代际间的职业发展、家庭婚育与养老流向是三个重要选择窗口。由图2-2可见,在家庭生命周期的形成期,经历早期城镇化阶段的农一代是否选择非农就业影响了后续的家庭代际选择,农一代进城务工将面临农二代教育与自身置业的进一步选择,如果农一代选择农业就业,农二代择业时将面临父辈同样的选择。在家庭生命周期的成长期,如果农一代选择了非农就业,那么在城镇化中期的农二代面临着与父辈不同的职业分化选择,进而影响农三代能否实现市民化的选择。在家庭生命周期的成熟期,伴随着农三代的人口市民化,农一代的养老选择更加多元,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农一代既能够选择留在城市照料家庭,也能够选择回乡回县养老。

图2-2 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农民市民化代际选择
在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农业劳动力转移与人口市民化对小县大城成为未来县域城镇化的趋势有着重要影响。首先,随着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村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农业人口非农就业使得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的同时,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农一代的进城务工及农二代的教育和就业选择,农村人口的流出是大趋势,而大城市无法承接跨区域流入的大量人口,小县大城成为未来县域城镇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就地村镇化和就近市民化推动了县域城镇化的发展。其次,人口市民化也在家庭生命周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农民的非农化就业使其家庭逐渐融入城市生活,家庭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最后,人口市民化还带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升,使得小县大城更具吸引力,这进一步推动了县域城镇化的进程。因此,在农业劳动力转移与人口市民化的双重影响下,未来小县大城将成为县域城镇化的主要趋势。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县域城镇化将更加深入,县域的规模和功能将不断扩大,这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关系的变迁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乡劳动力活跃流动为县域城镇化提供了可能。农村劳动力纷纷涌入城市,部分流入县域为小县大城模式提供了人力基础。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县域为非农业人口就地就近就业提供了新选项。农民工的涌入,带动了小县城的建设和发展,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为小县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使得县域焕发出城乡融合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非农就业的增加也是小县大城模式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县城逐渐发展起了多样化的产业体系,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和投资者。制造业、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行业的兴起,为县城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吸引了乡村人口流入和县域人口就业。
刘守英基于国家统计局7万抽样农户数据发现,中国经济在2010年前后总体上到达刘易斯拐点。同时,他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仅仅意味着农村富余劳动力被消耗完毕,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劳动力成本会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是短缺的。此外,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存在区域的先后,将呈现出由东至西的逐次到来,支撑传统增长方式的富余劳动力亟待转型。春江水暖鸭先知,小县大城的县域将会最先迎接拐点,并寻找转型出路的窗口,这将为解决单向城市化导致的城市病和乡村衰败提供解决方案。
近20年来,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农业人口的非农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伴随着农民工流动数在2018年达到顶峰后,劳动流动人口在省内流动数超过跨省流动数并将成为未来的趋势(见图2-3)。这表明,农业人口非农就业的去向由跨省域、大城市转变为省域内、县域内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在县域内实现人口市民化,小县大城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图2-3 劳动流动人口数与跨省/省内流动数的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2022年)。
县域是一个城乡间的地理空间、经济活动空间、公共和社会关系空间的集合,也是联结城乡、促进城乡融合的载体。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配置活跃,城乡之间的分工与互联互通增强的进程中,县域在城乡之间的作用和地位凸显。继而周其仁、刘守英等提出“城乡中国”、杨华提出“县乡中国”等概念,我们在一步步地告别城乡二分法的同时,将城乡融合的载体一步步地指向县域。对此,县域将会成为理解转型中国结构形态的重要窗口。
迈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城乡融合格局不仅是中国城乡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成了推动小县大城模式的重要动力之一。首先,城乡融合促进了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和利用。随着城乡融合的深入,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资源、资金、技术等要素流动更加便捷,这有利于将城市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引入县域,推动县域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从而助推小县大城模式的发展。其次,城乡融合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在城乡融合的进程中,政府加大了对县乡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使得县域居民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当甚至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为小县大城模式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物质基础。最后,城乡融合带动了城乡居民的交流与互动。随着城乡融合的不断推进,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城市居民对县域的投资和消费增加,乡村居民也更多地参与到县域的生产和生活中来。这种城乡互动的加强有助于促进城乡居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小县大城模式的创新性发展。
如图2-4所示,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尽管在过“紧日子”的情况下,国家财政对县域发展支持的力度不断加大,以增长率作为衡量标准,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率较为平稳,但事关县域公共服务供给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资金和事关乡村振兴基础设施投入的农林水事务支出的增长率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率。

图2-4 国家财政对县域发展的支持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历年财政收支情况和财政部《中央财政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管理办法》的数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