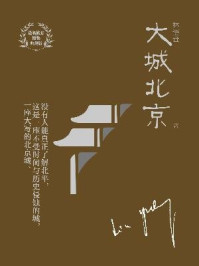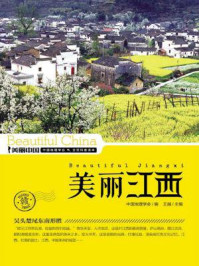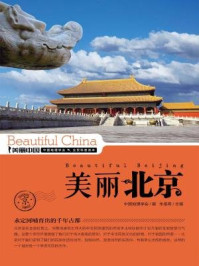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部挺叫座的电影,叫《雅马哈鱼档》,演个体户的,扑面而来的岭南风味。我对南国的想象,之前由小说《三家巷》《香飘四季》推动,之后就由这电影打底。“个体户”当主角,解放后的电影里没见过,随伴而来的,是浓浓的“改开”气息。“改开”不等于烟火气,但这部电影里二者却是混而为一,好似在提示,“改开”的一个面向,乃是日常生活的回归。
内容已模糊,片名分明说的是鱼档,印象中却是男主角等几个人赤着膊在卖烧鹅。有此记忆,当然是因为烧鹅列阵高挂的画面,不然就是当时与人有过“烧”“烤”之辩。广东得风气之先,个体经营早已风起云涌,内地要慢半拍,不过南京的烤鸭店也一家一家冒出来了。起初有不少还不是固定的门面,街边巷口支个摊就卖。我有个小学同学就是这样发起来的,有次在珠江路小粉桥那一带遇到,他脖子上、手腕上戴着粗粗的金链,说都是24K的,我头一次知道金子还有多少K的分别。南京第一拨的万元户,据说有不少就是卖鸭子起家。
到这时候,南京烤鸭对我来说,才算浮出水面。父母不是南京人,家里没有吃的传统,我甚至不知南京有烤鸭一说。我吃烤鸭的经历是反着来的,因为大学一年级暑假去了趟北京,当个项目,在前门烤鸭店把北京烤鸭吃了,南京本地的烤鸭倒是后来才补的课。
南京烤鸭,说起来“古已有之”,问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似乎已近于消失(所以不少有点岁数的老南京都认定,南京人过去都是吃盐水鸭,八十年代以后吃烤鸭才开始变得普遍),至少是难得一见,鸭都全凭盐水鸭勉强支撑大局。所以个体户蜂起的那个时代,才是我这个年纪的人的烤鸭元年。
我会与人做“烧”“烤”之辩,是在《雅马哈鱼档》里看到烧鹅以后:分明是“烤”,怎么说“烧”?据说烧鹅之外又有烧鸭,到底怎么“烧”?被我询问的那位,坚称烧与烤是两回事,却说不出区别在哪儿。后来当然知道了,现在“烧”大多指“先用油炸,再加汤汁来炒或炖,或先煮熟再用油炸”,但作为烹饪方法还有一义:就是烤,故烧鸭即烤鸭,我们现在干脆把“烧”“烤”叠起来用,所谓“烧烤”其实并不“烧”,就是“烤”。
推敲这个“烧”字恰好暴露了我的不够“老南京”:原先南京人是把烤鸭叫作“烧鸭子”的,现在有些上了年纪的老南京还那么叫。再往前推,文献上所说,都是“烧鸭”。《随园食单》“羽族单”里有“烧鸭”条:“用雏鸭上叉烧之”,系烤鸭无疑,写得明明白白。陈作霖《金陵琐志》记南京鸭子:“鸭非金陵所产也,率于邵伯、高邮间取之。么凫、稚鹜千百成群,渡江而南,阑池塘以畜之,约以十旬肥美可食。杀而去其毛,生鬻诸市,谓之水晶鸭;举叉火炙,皮红不焦,谓之烧鸭;涂酱于肤,煮使味透,谓之酱鸭;而皆不及盐水鸭之为无上品也。淡而旨,肥而不浓,至冬则盐渍日久,呼为板鸭。”可见民国年间的南京,烤鸭还是称为“烧鸭”。
再后来还知道,广东、南京、北京之外,云南宜良的鸭子也很有名,而且是一直称“烤鸭”的。宜良是昆明市的一个县,很不起眼,烤鸭却是远近皆知。一九九二年往云南走亲戚,到了已近中越边境的砚山,有一顿饭,主打就是宜良烤鸭,不知是宜良人把生意做到了砚山,还是大老远从宜良买过来的。我虽是从号称“鸭都”的南京来的,也得承认,宜良烤鸭,一点不差。
可以让南京人自豪一把的是,天下烤鸭是一家,追本溯源,甭管北京的、广式的,还是宜良的,老祖都是“金陵烤鸭”。北京烤鸭是随大明迁都带过去的,最早做北京烤鸭出名的“便宜坊”,要表示有来历,打出的名头居然是“金陵片皮鸭”;广式烧鸭源自南京;宜良烤鸭是朱元璋下令移民云南的南京人传过去的。
与诸多来历久远的美食一样,金陵烤鸭闻名遐迩,也少不了种种传说的帮衬,“讲好烤鸭故事”中最流行的版本,是和朱元璋绑定的。帝王崇拜深入人心,美食硬往上扯,意料中事。喜欢拿来说事的,乾隆是一位,下一趟江南,就能留下诸多美食的想象空间;朱元璋也要算一位,“珍珠翡翠白玉汤”因同名单口相声广为人知,常熟“叫花鸡”也着落他头上,再有便是金陵烤鸭,是当皇帝之后的事了,说是“日食烤鸭一只”。不像“十全老人”的乾隆,朱元璋苦孩子出身(打天下的皇帝,特别是起于微末的皇帝,我们会直呼其名,乾隆那样的,名字都搞不清),与之相关的美食亦接地气,“珍珠翡翠白玉汤”“叫花鸡”都是落魄时的充饥物;吃金陵烤鸭时天下已定,自可放开肚皮吃。
有意思的是,民间想象也是“有迹可寻”的,乾隆生来锦衣玉食,“日食烤鸭一只”不会往他头上安,安到朱元璋头上,即使意在突出烤鸭味道之美,也还是带出了他贫寒出身的草莽食量。出于好奇,想查“日食烤鸭一只”的出处(众口一词,都称“据说”),却查不到。当然,即使有文献佐证,也只能证明朱皇帝早年“饥来驱我”的记忆让他成为暴食暴饮的典型,妥妥的“报复性消费”。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金陵烤鸭南传北传,虽无改烤鸭之为烤鸭的根本(焖炉、明炉、叉烤,都是“烤”),因地制宜,改良变通,则是势所必然。选用的鸭种不必说了(都用本地鸭,或是填鸭),做法、吃法也有差异,太“技术流”的那些不说,只说外行也一望而知的,蘸料,就不一样。北京烤鸭,是甜面酱;南京烤鸭,是特制的卤子;广式烧鸭,多蘸酸梅酱;宜良烤鸭似乎没有一定之规,可蘸甜面酱,也可以是椒盐,我“亲测”的那次,是辣椒粉和盐巴的混合。
做法上最像南京烤鸭的,也许是宜良烤鸭,虽然和广式烧鸭一样表皮刷蜂蜜,不像南京的涂麦芽糖稀,但烤前不加腌制,却是一般无二。腌制可使入味,广式烧鸭即是腌后再烤,吃起来因此更觉入味。腌制的另一效果是令鸭肉更紧致弹牙,反过来说,盐的加入会让肉变得结实(此处的腌属于“暴腌”范畴,时间短,少则几小时,长不过三四天),反过来说,未腌制则鸭肉更鲜嫩也未可知。反正我吃南京烤鸭,觉得就鸭肉的酥嫩而言,更在盐水鸭之上,因为烤,又比盐水鸭多了一份焦香。
广式烧鸭是用一小盒装酸梅酱,南京烤鸭给的卤汁要多得多,用小塑料袋兜着,回家倒出来,吃饭的碗能有大半碗。这个量,绝对有必要,因烤鸭虽经腌制,大旨在去腥提鲜增香,不在入味,故空口吃则味淡。烧鸭则是更入味的,酸梅酱带来的是风味之味,烤鸭卤汁则还要负责咸淡的。一般的做法,似乎是将卤汁浇到鸭块上去,谓之“浇卤子”,我以为还不够味,因不够利益均沾。一碗鸭子,下面的部分固然淹在卤中,堆上面的只是水过地皮湿,最好是另以一碗盛装卤汁,鸭块依次浸泡其中,稍待片刻再夹起。
鸭卤是从鸭子的腔子里来的,这也是南京烤鸭的特别处:烤制时是要往鸭肚子里灌水的,外面烤得滋滋滴油,腹内则是沸腾的状态,故有“外烤内煮”之说。总觉南京烤鸭特别嫩,与此也不无关系。但关键不在这里,对许多老南京而言,烤好之后从腹腔中放出的鲜汁构成了卤汁的基本面,才是要紧的。倒也不是特别浓,毕竟烤制的时间也就二三十分钟,但内蓄的一包汁水,仍自透着鲜。当然还需加入各种调味料调制,加什么、比例如何,没有一定之规,各家都有独得之秘。调出的卤汁皆作深浓的酱油色,据说讲究的是自炒焦糖色,要不加一滴酱油,才算本事。于各家卤汁的种种细微处,老南京吃家自有以辨之,不免神乎其技。这也是要有阅遍千山的经验的,我道行不够,这家那家的鸭子,吃得出皮肉的差异,反是几乎要被说成独门暗器的卤汁,我觉得各家大差不差。称为南京烤鸭的“灵魂”,好像高下尽在一卤,夸张了吧?
但这是回到内部而言,论“大局观”,同别种蘸料(甜面酱、酸梅酱)相比,我绝对是卤汁的拥趸。不管哪种烤鸭,以意度之,都偏鲜甜口,表皮要刷糖稀或蜂蜜且不论,北京烤鸭蘸甜面酱,其“甜”可知,广式烧鸭配酸梅酱,南京烤鸭的卤汁也是偏甜口。然有黏滞浓稠与清爽之别,从重浊到清爽,依次是甜面酱、酸梅酱、卤汁。比起来,卤汁竟有一清如水的轻盈。蘸酱不免拖泥带水,卤汁则浸入片刻,浴卤而出,得其味却一无挂碍,最能保持鸭肉的清鲜之气。
当然蘸料是“托儿”的角色,也是一物配一物,错不得,拿南京烤鸭蘸甜面酱固然货不对板,北京烤鸭浇了卤汁荷叶饼包起来吃也难以想象。
北京烤鸭其实与其他诸烤鸭是不好并论的,因从金陵到新的皇城,改造之后,烤鸭在北京已然又是一番气象。从烤制到吃法,与所从来处可谓渐行渐远,可以说上一大通,但我独对各自的“应用场景”最感兴趣,这也最是一望而知的:北京烤鸭须堂食,别种烤鸭,堂食外带两便;北京烤鸭须热食,其他的,热食冷食两便——刚出炉的更佳,但似乎还是冷食为多。广式烧鸭常进入快餐系列,是为“烧鸭饭”,南京人的“斩鸭子”,不拘下酒、佐餐,皆不与饭做一处,快餐饭、盖浇饭得用别的菜“下饭”。又有“冒烤鸭”者,是川渝一带传来的新晋吃法,属“冒菜”的推陈出新,另当别论。
堂食、热食,将北京烤鸭推向庙堂之高。即使上了席,南京的烤鸭也是作为冷荤、前菜出现,不像北京烤鸭,就算不是绝对的主打,也属一道大菜、硬菜,足以独当一面。不管老派的全聚德、便宜坊,还是新派的“大董”,登场皆隆而重之,厨师当场片皮,仪式感拉满。南京烤鸭一如“斩鸭子”的说法传达,满满的里巷风。在过去,天热之时,家门口小桌上摆买回的鸭子,解开塑料袋,装鸭子的快餐盒都懒得换成盘碗,坐小凳上小酒就可以喝将起来。
北京烤鸭须堂食、热食,还有它的仪式感,大部分要着落在鸭皮上。其酥脆,也的确堪称一绝。我头一次在前门新店吃,记得是连肉带皮一起片的,曾几何时,尝鼎一脔,独属鸭皮了。又有一法,不是和葱白丝、黄瓜丝一起蘸酱,春饼裹了吃,是以片下的鸭皮径直蘸了白糖送进嘴里,一口下去,满口油脂香,让我联想到小时大人将熬油余下的油渣让小儿蘸了糖或盐吃。有次对请客的北京哥们儿开玩笑说了句大不敬的话,称北京烤鸭精华在鸭皮,鸭皮的本质是油渣。
与北京烤鸭皮与肉的分离主义倾向不同,南京烤鸭的皮与肉是二位一体的,连皮带肉一起吃,才得其妙。事实上,南京人论烤鸭高下,鸭皮也是一端,以“皮还是脆的”为尚,斩回的鸭子若皮仍有脆意,则如中彩,只不过这是加分项,不像北京烤鸭,皮若不脆则几乎一无是处。明清烤鸭北传,便宜坊的烤鸭既然打过“金陵片皮鸭”的旗号,可知南京的烤鸭也是片皮的,现在本地的烤鸭再无此说。广式烧鸭斩剁时常见皮不附肉,南京的斩鸭子通常却相当之“完形”。我倒不在意看相,一口下去,皮香脆与肉鲜嫩,口感上有层次,才是关键,皮是皮肉是肉就打了折扣。好比吃红烧肉,每一口须得有皮有肉才好。
这些年,北京烤鸭似乎很有几分“下沉”的意思了,不少小城市里也能见着踪影。在南京,北京烤鸭火过一阵,碑亭巷一带,曾是北京烤鸭店扎堆的地方,一溜开了好多家。洗牌几轮之后,就有“褚记”冒出来,连锁性质,好多家,有个Slogan(英语:口号)的,大意:“吃烤鸭,到褚记”,价格相当之平易近人。前几年褚记开出一家奔高端去的“玄锦·鸭府”,以“传世国宴”相号召,记得把全聚德的传统菜火燎鸭心等等也搬上菜单了,但似乎没多少人追捧,不知何时就销声匿迹了。北京烤鸭则仍一径在往平民化的路上走,先是菜场左近一类的地方出现了“北京果木烤鸭”,后来则有升级版,装饰着大红门头的“北京烤鸭”,都是做外卖,堂食“三吃”里的汤免了,后者鸭架取现在最流行的方式,油炸。片皮,片肉,早已分装好的春饼、葱白丝、黄瓜丝、甜面酱,打个包,店家手法麻利得很。虽然没有堂食的地道,油炸的鸭架上撒着辣椒粉孜然粉的我尤其不接受,然回家吃起来,至少鸭皮还保持了几分酥脆。
这是让北京烤鸭走上街头巷尾了,可见平民化是大势所趋。不过要说平民化,哪里比得了南京烤鸭呢?我觉得它是自带烟火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