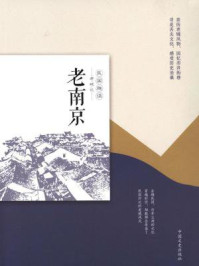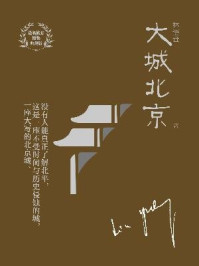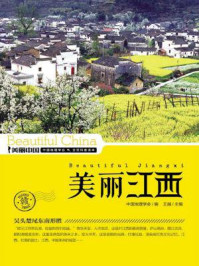有“新”必有“旧”或“老”。老版《南京味道》十多年前在三联书店出版,收入“闲趣坊”丛书,有一“小引”,对内容有所交代之外,对书名何所取义也有一番“狡辩”,其中有些意思没变,还可用;有些意思要变通,须接着说。不管不变或改变,接着说都要有“底本”,原打算把“小引”附在后面,现在想想,也许照抄一下更能接得上也未知,就照抄如下:
关于吃,大概每个人都有很多记忆。我那辈人的记忆中比较特别的一项,是都吃过“忆苦饭”。不会多,也就一两回,却是印象深刻。应该也是各式各样,有地域色彩的。干的稀的我都吃过,干的是窝窝头,稀的是糊糊,要皆符合“吃糠咽菜”的描述,对我们而言,那是关于“旧社会”最直接的体验。印象中稀的稍好些,糠做的窝窝头特别难以下咽,不仅是“味同嚼蜡”,还粗粝到刮喉咙。那是小学时的事,在当时一个“活学活用”积极分子顾阿桃的家乡。大家都是一脸的痛苦,饶是有老师督阵,好多人还是只吃得一两口,就偷偷扔了。其时我颇显示了一点“大无畏”的精神,将窝头整个吃下,且尽量做到神态自若,似乎权当励志,也可说是“咬得菜根,百事可为”的“革命”版吧?另一同学做得要更夸张些,一边吃一边还说:“其实一点也不难吃。”当时不觉,事后就觉这样的表态颇成问题:“不难吃”引申起来,岂不是说“旧社会”并非“暗无天日”到不可忍受?
“忆苦”意在“思甜”,有糠窝窝头垫底,我们平日所食,竟算得上“天上人间”了,虽然事实上那是个缺吃少穿的年代,理论上却应该是不以为苦的。无如在吃上面人本能地“取法乎上”,越是没东西可吃,吃的冲动越是强烈,于是一些于今看来绝对当不得“美食”二字的吃食,也在匮乏的背景上尽显其诱惑性。吃的非“革命”、非“精神”性质固然要求我们抵制诱惑,乃至于特定的时候还会有罪恶感,因小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劣根性而大加忏悔,批判会上一概归为“剥削阶级思想”的作祟,然而兀自在肚里蠕动不已,凡有吃喝的场合则汹涌暗潮必决堤而出,整个原形毕露。大体上,“吃”与“革命”各走各的道,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虽然吃起来不能那么明目张胆,理直气壮。所以待火红年代过去,脑子固然因受洗而终不能完全复原,吃的本能却因未受实质性伤害,颇能一任天真。
然而毕竟是生于吃事荒芜的年代,又加家里没有吃的传统,这上面的童子功是没有的,条件所限,后天的修炼也差得远,难望美食家的门槛。虽然于美食的境界,不胜向往,吃来吃去,却终是在“下里巴人”里打转,不足以言“美食”,只能在一些美食书里聊寄相思。据我想来,写吃的书是得有资格的,或遍尝山珍海味;或于一地食尚了如指掌;或精通厨艺,下得厨房;或对一饮一馔的来历如数家珍……凡此种种,我无一具备。之所以写了一些关于吃的文字,多半还是因为马齿渐长,时或回想起旧事,正因当年“吃”之珍稀,记忆中些许味美之物竟自“熠熠生辉”起来,诸多吃事的细节居然也不招自来,分外鲜明。所以它们与其说是关乎吃,不如说是关乎记忆。至于写到现在时的吃,则是过去之余——大着胆子写来,也是因为现而今“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已然是受到鼓励的了。
因此之故,将这一类的文字收到一起,本想就以“吃的记忆”为题,只因似乎不够浑成叫不响,终于放弃。现在的书名则基于“务实”的考虑:据说关及吃的书与一地相连属,在市场上更易行销。既然是南京人,这地方当然就该是“南京”。名实相副,我所欲也,然而书能多卖,更属实惠,务虚终归敌不过务实,“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便是好猫”,其理在此,倘当真多卖出些个,将来多下几回馆子,亦不失以吃养吃之道。有此俗念,也便从权——虽然是否如愿,也就难说,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也是有的。
起初打算叫作“南京胃”:书中所写,远出于南京之外,然南味北味,固是从我肠胃而过,我的肠胃则有明显的南京印记——夸张点说,饮食习惯的养成,于五味的亲疏远近,乃至对某样具体食物的好恶,皆由南京这方水土、文化塑造。诚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如此这般,称作“南京胃”,似乎还说得通。此外自觉也还别致。
问题是不大明确,伤于“空灵”,没准读者会误以为是比喻性的说法,与吃的联系在有无之间。若称“南京味道”,或可免易生浮想之弊吧?“务实”当真是条不归路,以“吃的记忆”始,以“南京味道”终,也就这样了。强作解人,我把“南京味道”解作“南京胃”的另一说法,如我之辈,其胃口也确乎有某种“南京大萝卜”的味道。
市面上以某地“味道”冠名的美食书恐不在少数,想来皆可充一地的美食地图。本书显然不是,倘有读者希望按图索骥,必会大失所望,失望之余,或者要以“挂羊头卖狗肉”相讥。怎么说呢?——也是该的。(2012年4月15日)
想以强作解人的“狡辩”堵住众人之口是不可能的,书出来以后即有不少读者指责“南京味道”名不副实,也有熟人开玩笑,说我这是如同抢注商标一般,占据了资源。这些我辩无可辩,不说其他,书里有些归类的标题,“关乎烟酒”“觅食槟城”之类,或是去“味道”甚远,或是一看便知与“南京”八竿子打不着——简直是“授人以柄”。所幸还有许多读者宽宏大量,“得鱼忘筌”,不去计较书名的“托大”,于书中的饮食记忆多有会心,甚至浑不介意将书中模糊不清的“南京”也给认领了。
虽然如此,我对书名的被讥讽,还是不无耿耿,“忍辱负重”之余,再写关于吃的文章,有意无意间就会强调“南京”的存在,有时甚至刻意找些和南京有关的题目来写,想着有朝一日,出一本于南京的吃真正“切题”的书,也算是“以赎前愆”。
曾经有过一个机会,我做过一点南京化的小型努力:南京2019年成功获选“世界文学之都”,该项目的主事者选定《南京味道》作为对外推广书目中的一种,译成英文,在海外出版发行。篇目可做调整,我便抽去了显而易见文不对题的部分,代之以较“南京”的篇什。但也是便宜行事,只是拣到那时为止写就的相对“切题”的文章用上,并未专门添写新的。潜意识里恐怕是觉得,老外对中国饮食尚且是一囫囵的概念,地方性的吃吃喝喝,他们哪里拎得清?大概其的就行了,不必顶真。
读者眼前的这本书与那本英文版又不同,是“以赎前愆”念头的某种“变现”。沿用了“南京味道”作为书名,内容却做了大大的调整,不是修订,是旧作的“痛改前非”版,原先的篇目,仅有少量留用。三联版是先有文章,书名属事后追认,胡乱安上;新版是意在笔先的“循名责实”。这里的“实”,包括对南京独有的吃食的寻思,比如盐水鸭,比如菊花脑,比如旺鸡蛋、活珠子,比如油球,比如炖生敲……但并不限于“本地风光”,或者,“本地风光”原本就是一个重叠的概念,“南京味道”与淮扬菜系有相当重合,江南饮食习惯大差不差,画地为牢大可不必,袁枚的《随园食单》几乎要被看作金陵菜谱了,事实上却是覆盖了古人的“江南”,说南京,其实也是在说江南,反过来说,也一样。
另一方面,饮食传统是一直在变动当中的,不少外地美食,经了一番“本土化”的适应、改造后,已然进入了我们的食谱,成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比如煎饼馃子、胡辣汤,缺了它们,现今南京的早点市场虽不至于没法维持,却显然是不完整的。再如源自四川的酸菜鱼,上至大酒家,下至路边店,甚至学校的食堂,踪迹处处可见,你甚至很难想出有哪道南京菜比它更“无孔不入”。从异地到本土,扎根和变异,其演化的过程,恰是我感兴趣的看点。你不能说,那和“南京味道”就不相干。
此外书中还有些处看似“景深”更大,说吃不限于一地,扯到了别地的饮食,属于食分南北的比较学,远近衬映的差异论。然而说东说西,说南说北,横看侧看,有意无意间,都是以南京为本位,即使异地风味,也是南京眼光,是以南京为基点去比较的。
但这并不是说由旧版到新版,要变身美食攻略或美食地图了——不管怎么说,新版是由老版脱胎而来,有些痕迹是抹不去的,也没打算尽行抹去。尽行抹去,于我自己,就大有忘了初心的意味。“初心”为何,已抄在上面,现在这样,固然“南京”多了,“味道”多了,但更多的,还是关乎记忆。这些年对于吃,兴味有增无减,但要成为真正的吃货,路漫漫其修远,笔下“干货”因此也就有限。我在网上追看高文麒的“探店”视频,常自惭形秽,更觉大有藏拙的必要——人家那才叫言之凿凿,“干货”满满。
“干货”一词,本义就是由吃而来,具体地说,是指用风干、晾晒等法去除了水分的食品、调味品(木耳、牛肉干、葡萄干、胡椒……可以举出一大堆),药材也算;现在本义不彰,似乎已被网络义覆盖,狭义是指网上的实战指南之类,泛指涵盖面就广了,不限于实用,似乎比较“硬核”者都在内,与“水货”正可对举。
当然“干货”“水货”是比较的概念,我的理解,是对硬知识的强调。何者为干货,何者为水货,还是要依知识的硬核程度而定。比如古人论文,考据、义理、辞章,说起来三位一体,比较起来,考据就更容易被视为干货。吃上面属干货者,不拘饮食上的“知识考古”,还是实地考察式的“探店”,都算。这些我的文章里也不是没有,但都做不到“铁案如山”。更多牵扯出来的,可能倒是吃的周边,比如个人经历、时代氛围之类。所以才会有“也算‘探店’?”一辑,说的是我年轻时南京的几家饮食店,着墨多是一鳞半爪的印象,店家的名点名菜甚至也有拎不清的,记忆所及,吃食与场景打成一片,倒是所谓“年代感”的一部分了。
饮食的味道,与一时一地的气息,与陆游所谓“世味年来薄似纱”的“世味”,原本就是连作一气的。如果读者于食物的滋味之外还辨出些其他味道,倒也不算全是误打误撞。且容我不够专注,“拖泥带水”地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