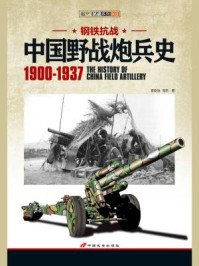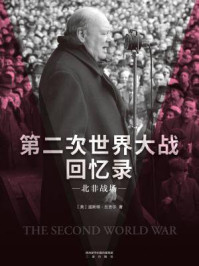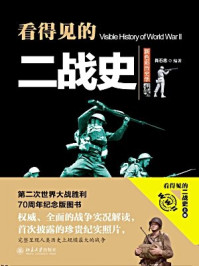侍从室的组织,始于1933年南昌行营的侍从高级参谋室,原编制为第一组警卫,第二组秘书,第三组调查及记录,第四组总务,另附设侍从参谋若干人。1935年南昌行营结束,蒋介石乃将侍从室改组,分设第一、二两处,第一处设第一(总务)、第二(参谋)、第三(警卫)三组,第二处设第四(秘书)、第五(研究)两组,1939年2月增加第六组,办理情报事宜。1939年7月侍从室又增加第三处,主管人事业务。

侍从室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由侍五组负责。侍五组的前身为南昌行营的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蒋介石设立此一机构的目的,乃是希望网罗一批年轻的学者、专家及留学生,从事“进剿地区”的调查、设计、审议等工作。设立之初,采常务委员制,由杨永泰任秘书长主持日常会务。1937年4月,改为主任制,由陈布雷任主任。
1935年南昌行营结束,改设“剿匪”总部于武昌,陈布雷所担任的设计委员会职务,以该会撤销而解除。在牯岭时,蒋介石决定修改侍从室的组织,第一处设立第一(总务)、第二(参谋)、第三(警卫)三组,第二处设第四(秘书)、第五(研究)两组,命原侍从室主任晏道刚为第一处主任,陈布雷为第二处主任。研究组设秘书8—12人,以设计委员会原任设计委员徐庆誉、张彝鼎、李毓九、高传珠、徐道邻、罗贡华、傅锐、何方理8人出任。2月,陈布雷赴汉口,就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职,兼第五组组长。
侍五组的研究工作分为内政、法制、文化教育、国际时事、中日关系及经济等各类,各秘书每人任一类为主,并认一类为副。
 陈布雷并要求每个人于3个月内提出研究报告2件为限。又分配翻译工作如下:(1)英文:张彝鼎、徐庆誉;(2)法文:何方理、徐道邻;(3)德文:徐道邻、李毓九;(4)俄文:高传珠、李毓九;(5)日文:傅锐、罗贡华。各以一人为主,一人为辅。并规定凡翻译报纸、杂志材料,每周汇送一次,紧急者随时呈送。陈又撰《剪报要目》30项与《剪报须知》20条,油印后发交剪报员开始剪贴。
陈布雷并要求每个人于3个月内提出研究报告2件为限。又分配翻译工作如下:(1)英文:张彝鼎、徐庆誉;(2)法文:何方理、徐道邻;(3)德文:徐道邻、李毓九;(4)俄文:高传珠、李毓九;(5)日文:傅锐、罗贡华。各以一人为主,一人为辅。并规定凡翻译报纸、杂志材料,每周汇送一次,紧急者随时呈送。陈又撰《剪报要目》30项与《剪报须知》20条,油印后发交剪报员开始剪贴。

1937年6月,蒋介石也曾指示陈布雷,将侍五组研究秘书依研究领域及研究区域分为党务、政治、外交、经济及各省、市、区各股,接洽公文及研究,并嘱陈物色人才以充实侍五组阵容。陈布雷则认为此事委员长期望已久,不过由于侍从室的性质与组织特殊,甚难实行,原因有三项:(1)文书与研究工作不易打通;(2)人才难得,甄用进退更易牵涉到不易解决的困难;(3)现有秘书中,急功自见,好出主张者多,而平情虚心肯研究者少。因此本案只能徐徐策划。
 不久,抗战全面爆发,此事遂不了了之。
不久,抗战全面爆发,此事遂不了了之。
参事室成立后,侍从室的规模缩小,主要业务变成为蒋介石整理文告和文稿,不过政策方面的研究仍持续进行。此一时期,侍从室最重要的秘书为李惟果。李毕业于清华大学,公费留美,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博士,1937年9月入侍从室任五组秘书,
 周佛海追随汪兆铭出走后,李接任周侍五组组长的职务。初期陈布雷曾要其研究志愿兵问题。
周佛海追随汪兆铭出走后,李接任周侍五组组长的职务。初期陈布雷曾要其研究志愿兵问题。
 1938年4月曾撰写《日本对苏俄开战之可能及我国对策》研究报告。
1938年4月曾撰写《日本对苏俄开战之可能及我国对策》研究报告。
 1939年1月,李撰写《中日抗战与国际形势》报告,文长约1万字,文字流畅而不沉闷,陈布雷读后觉得“此才可造,为之心喜”。
1939年1月,李撰写《中日抗战与国际形势》报告,文长约1万字,文字流畅而不沉闷,陈布雷读后觉得“此才可造,为之心喜”。
 1940年,蒋介石决定办一个《三民主义月刊》,以弘扬三民主义,领导青年思想为宗旨。此事本属中宣部业务,不过或许是由于中宣部部长王世杰是个自由派学者,蒋不愿碰钉子,于是想让陈布雷负责此事,不料陈不愿接,
1940年,蒋介石决定办一个《三民主义月刊》,以弘扬三民主义,领导青年思想为宗旨。此事本属中宣部业务,不过或许是由于中宣部部长王世杰是个自由派学者,蒋不愿碰钉子,于是想让陈布雷负责此事,不料陈不愿接,
 于是找了何浩若、潘公展、李惟果、林桂圃等人来讨论编辑方针、取材标准及负责人选等问题。最后决定以李惟果为社长,李泰华、傅筑夫分任主编及常务编辑,林桂圃任经理。
于是找了何浩若、潘公展、李惟果、林桂圃等人来讨论编辑方针、取材标准及负责人选等问题。最后决定以李惟果为社长,李泰华、傅筑夫分任主编及常务编辑,林桂圃任经理。
 不久,陈布雷又要李惟果兼经理职。
不久,陈布雷又要李惟果兼经理职。
 显示陈对他的器重。12月,李惟果获派外交部总务司司长离职,
显示陈对他的器重。12月,李惟果获派外交部总务司司长离职,
 陈布雷对此十分不舍。此时陶希圣由香港至重庆,陈布雷多次找陶长谈,认为他“具识精卓,诚益友也”。
陈布雷对此十分不舍。此时陶希圣由香港至重庆,陈布雷多次找陶长谈,认为他“具识精卓,诚益友也”。
 1942年3月28日,蒋介石下令侍从室应设理论研究宣传设计组。陈布雷则约见陶希圣,希望他能留在重庆担任宣传指导设计的工作。
1942年3月28日,蒋介石下令侍从室应设理论研究宣传设计组。陈布雷则约见陶希圣,希望他能留在重庆担任宣传指导设计的工作。
 6天之后,陶持理论研究宣传设计的计划来见,陈读后甚感快慰,认为陶能留渝相助,将为一得力的益友。
6天之后,陶持理论研究宣传设计的计划来见,陈读后甚感快慰,认为陶能留渝相助,将为一得力的益友。
 4月4日,陈布雷获蒋同意侍五组业务增加理论研究及宣传设计两项,不另成立新组。并核准第五组组长以陶希圣担任。陈当日曾于日记记载:“余之工作固不因此减少,然第二处阵容加强矣。”
4月4日,陈布雷获蒋同意侍五组业务增加理论研究及宣传设计两项,不另成立新组。并核准第五组组长以陶希圣担任。陈当日曾于日记记载:“余之工作固不因此减少,然第二处阵容加强矣。”
 陈对陶寄望之深,由此可见。
陈对陶寄望之深,由此可见。
陶希圣上任后,首先即感到研究所需资料的不足。
 侍五组平日经常收到国民政府驻外使节报告的副本,以及军事委员会驻延安联络参谋的报告,和各国驻华使馆也有来往,因此对于国际动态和延安动向尚能掌握,
侍五组平日经常收到国民政府驻外使节报告的副本,以及军事委员会驻延安联络参谋的报告,和各国驻华使馆也有来往,因此对于国际动态和延安动向尚能掌握,
 不过一般研究所需数据仍然不足。于是他经常以该组所拥有的一些外汇委托在英国的叶公超和在美的陈之迈购买外文书刊,以空运寄回,所以虽然战时日本实施海上封锁,但是侍五组还是自海外进口了一些书刊,仍能从事国际政治及军事方面的研究。例如陶希圣本人,即曾于侍五组任职期间将过去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修订出版,并翻译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1)的《战争原理》(Principles of War)及《拿破仑兵法语录》(Military Maxims of Napoleon)等。
不过一般研究所需数据仍然不足。于是他经常以该组所拥有的一些外汇委托在英国的叶公超和在美的陈之迈购买外文书刊,以空运寄回,所以虽然战时日本实施海上封锁,但是侍五组还是自海外进口了一些书刊,仍能从事国际政治及军事方面的研究。例如陶希圣本人,即曾于侍五组任职期间将过去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修订出版,并翻译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1)的《战争原理》(Principles of War)及《拿破仑兵法语录》(Military Maxims of Napoleon)等。
 在政治方面,则以《中国之命运》和《中国经济学说》二书的拟撰,影响较大。
在政治方面,则以《中国之命运》和《中国经济学说》二书的拟撰,影响较大。
侍五组虽然是侍从室主要的研究部门,不过其他各处也经常会进行一些政策性的研究。例如侍三处即曾于1939年奉蒋介石之命,找专家研究三民主义经济制度及经济政策。侍三处主任陈果夫当时找了中央政治学校财经教授刘振东、赵兰坪、王世颖、寿勉成、胡善恒、萧铮、黄通等人负责研究,每星期开会一次,写成报告,由陈果夫自任主席,侍三处专员吴铸人为承办人,担任记录者。开会若干次后,始推赵兰坪起草报告,继推刘振东重拟,不料陈果夫均不满意,乃命吴铸人一试。吴为北京大学毕业,牛津大学农业经济学硕士,曾任教于中央政治学校蒙藏学校。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篇约2万字的《三民主义的经济制度及经济政策》,经陈果夫修改,再经开会讨论后,送呈蒋介石,奉批交财、经二部制定政策时作为主要参考资料,随后并由侍三处印成小册子形式发行,分送相关机构及首长参考。
 侍三处的此项政策性研究,在当时的学界尚无类似的作品,
侍三处的此项政策性研究,在当时的学界尚无类似的作品,
 因此应具相当价值,不过完成后对于财经政策的制定到底产生多大的影响,由于受到史料的现制,不得而知。
因此应具相当价值,不过完成后对于财经政策的制定到底产生多大的影响,由于受到史料的现制,不得而知。
侍三处又曾于1941年9月呈准蒋介石,针对战后收复沦陷区所可能立即面临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该处曾请内政部、社会部、司法行政部各指派代表1人,另聘请政治大学政治系主任萨孟武等对于此项工作素有研究的人员共10名,各自从治安、救济、经济、文化等方面,找出在沦陷区收复后可能立即发生而急需解决的问题,拟定“沦陷区收复后之重要问题”20则,分发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各期毕业学员,进行研讨。一年后,陆续收到各学员及各地学员通讯小组的研究报告共300余件,经侍三处汇整后,完成《沦陷区收复后之重要问题暨其解决办法》一册。蒋介石对此份研究报告十分重视,曾仔细阅读并加批注。侍三处于奉蒋核阅后付印,
 供政府相关部门参考。侍三处人员认为国民政府战后处理汉奸和伪军问题,如能依此小册子去做,或许中共不至于成功得如此迅速。
供政府相关部门参考。侍三处人员认为国民政府战后处理汉奸和伪军问题,如能依此小册子去做,或许中共不至于成功得如此迅速。
 侍五组的重要工作,有下列几项:
侍五组的重要工作,有下列几项:
(一)《中国经济学说》拟撰:该书原为陶希圣在侍五组所完成的一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报告,说明中国如何在不平等条约下,沦为半殖民地的问题。指出中国历代经济建设均有计划,如汉、唐时期,国家建设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由首都向四方发展交通干道,同时有计划的发展水利、运河等。至近代以后,由于不平等条约,全国交通则由通商口岸、租借地向内地发展,如东三省是由旅顺、大连向内部发展,华北是由天津、北京向内部发展,华中是由上海、南京向内部发展,而华南则是由香港、广州向内部发展,无法做全国性整体的规划。
蒋介石读完此一报告后,甚为满意,遂要陶撰写《中国经济学说》一书,一方面批判共产主义的统治,一方面批判自由主义的经济。书稿完成后,分别寄请西南联大、西北联大的经济系教授提供意见,经过多次修改后,最后由蒋介石修订定稿,
 于1943年出版。
于1943年出版。

《中国经济学说》一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并未引起多大的讨论,在政界的影响较大。孙科认为此二书批评了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却未批评法西斯主义;中共则直指此二书为法西斯思想。同盟国中印缅战区总参谋长史迪威的助手谢志伟(John Service)在致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称:“国民党目前的意识形态,一如蒋介石的两本著作——《中国之命运》和《中国经济学说》所显示的,不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均为排外与反民主的。”

由于《中国经济学说》的内容十分含混,战后各种不同立场的学者对此书的解读也就颇不相同。例如政治学者格雷戈尔(A. James Gregor)认为此书继承了孙文《实业计划》,主张要解决土地问题,从而可以终止商人的炒作与兼并,最后可以有助于工业化;本土产业可经由进口关税予以保护,本土产业发展后可为经济与工业的发展奠定下基础。

(二)国际问题研究:1935年,侍从室首次进行改组。分设第一、第二两处,其中第二处设第四(秘书)、第五(研究)两组。
 研究组设秘书8—12人,以南昌行营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原任设计委员徐庆誉、张彝鼎、李毓九、高传珠、徐道邻、罗贡华、傅锐、何方理8人出任。2月,陈布雷赴汉口,就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职,兼第五组组长。
研究组设秘书8—12人,以南昌行营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原任设计委员徐庆誉、张彝鼎、李毓九、高传珠、徐道邻、罗贡华、傅锐、何方理8人出任。2月,陈布雷赴汉口,就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职,兼第五组组长。
侍五组的研究工作分为内政、法制、文化教育、国际时事、中日关系及经济等各类,各秘书每人任一类为主,并认一类为副。
 业务分工,并会视需要而做调整。数据显示,1936年2月,分工即曾做过以下的调整,并决定每周四开组会一次。
业务分工,并会视需要而做调整。数据显示,1936年2月,分工即曾做过以下的调整,并决定每周四开组会一次。
(1)资料收集与研究:
政治:罗贡华
法制:徐道邻
对日问题:李毓九
苏俄问题:高传珠
英美问题:张彝鼎
文化:徐庆誉
(2)翻译:
德文:徐道邻
法文:何方理
日文:李毓九、傅锐,罗贡华协助
英文:张彝鼎、徐庆誉

陈布雷除了指挥幕僚做研究,有时自己也收集资料,做一些研究。例如1936年底他即曾利用空闲的时间,收集有关国际形势变迁的资料进行研究。
 在研究的过程中,他甚至发现:“近时之研究国际问题者,十有其九皆怀成见,以附和社会主义为取悦读者计,其真能就事论事者,不多觏也。”
在研究的过程中,他甚至发现:“近时之研究国际问题者,十有其九皆怀成见,以附和社会主义为取悦读者计,其真能就事论事者,不多觏也。”
 他广泛阅读各杂志中讨论欧洲两大阵线的论文,以及有关巴尔干半岛各国形势的分析。
他广泛阅读各杂志中讨论欧洲两大阵线的论文,以及有关巴尔干半岛各国形势的分析。
 最后他起草了论文大纲,
最后他起草了论文大纲,
 不过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他的论文也就没有写成。
不过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他的论文也就没有写成。
侍五组成立初期所进行的研究课题,有些系蒋介石所指定,如罗贡华所作关于庚款研究;
 有些系陈布雷所指定,如1936年6月,陈布雷要徐庆誉、张彝鼎研究苏俄宪法,张彝鼎、高传珠研究对意撤销制裁问题,并嘱李毓九留意英国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爵士(Sir Frederick Leith-Ross, 1887—1968)赴日后日本舆论的反应。
有些系陈布雷所指定,如1936年6月,陈布雷要徐庆誉、张彝鼎研究苏俄宪法,张彝鼎、高传珠研究对意撤销制裁问题,并嘱李毓九留意英国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爵士(Sir Frederick Leith-Ross, 1887—1968)赴日后日本舆论的反应。
 不到两星期的时间,各秘书即缴交报告8件,由陈布雷核转蒋介石,其中高传珠的《苏俄新宪草研究》、张彝鼎的《蒙特娄会议与土耳其》、李毓九的《罗斯谈话与英日关系》、陈认为“均尚精确可诵”,徐庆誉的报告则内容较为空泛。
不到两星期的时间,各秘书即缴交报告8件,由陈布雷核转蒋介石,其中高传珠的《苏俄新宪草研究》、张彝鼎的《蒙特娄会议与土耳其》、李毓九的《罗斯谈话与英日关系》、陈认为“均尚精确可诵”,徐庆誉的报告则内容较为空泛。

侍五组的秘书均为留学各国的青年才俊,各具特长,他们所提供的专业建议,应对蒋介石外交决策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一位侍从室幕僚人员对于侍五组的成员以及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互动,曾有以下生动的描述:
第五组有研究秘书8人,都是留学各国的专家和学者,有留日的罗贡华,他仪表堂堂,回国后当过民政厅长;留英的徐庆誉,研究法律有一定造诣,戴一幅金边眼镜,和颜悦色,一派学者风度;留苏的高传珠,山东人,研究苏联历史颇有见解;留法的何方理,浙江人,家庭生活简单朴素,夫人是法国人,常吃西菜;留日的傅锐,浙江人,口才尤佳,议论日本问题侃侃而谈,头头是道,后因泄露军事机密,成为令人唾弃的汉奸,终归逮捕法办;留德的徐道邻,江苏萧县人,民国初年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幕僚长徐树铮的次子,法学博士,是号称“八大秘书”的佼佼者,夫人德国人,大陆解放后,夫妇俩才离开中国定居德国;留美的张彝鼎,湖南人,有真才实学,智慧超群;留日的李毓九,个子虽然又高又胖,却也风度翩翩,喜欢谈天说地,知识广博。他们各具特长,没有奴颜婢膝的气味;他们专供蒋介石关于国际问题的咨询,类似外交智囊团。蒋介石召见他们,提出问题后,只是洗耳恭听,不插话,不表态,听他们讲述后,从中分析利弊。

固然侍五组的秘书多为学历高、外语能力强的青年才俊,不过陈布雷逐渐发现这批人多不明了其职务的性质,常思越位言事,或请求调查各机关状况,或喜捕风捉影攻讦主管人员,或条陈意见而未能详参法令或事实,这令陈十分困扰,
 有一次陈召集五组秘书开谈话会,讨论五组工作事项,会中公开告诫各秘书,说明第五组的主要目的,在收集资料,备委员长索阅或呈送参考,决不可自视为有若干经纶;要知秘书属于辅佐地位,故工作不在上陈意见,而在留心收集各种问题的相关材料,选择归纳,附具结论,以贡献于委员长。不料当天五组秘书又集体向陈对待遇有所请求,为陈所拒。
有一次陈召集五组秘书开谈话会,讨论五组工作事项,会中公开告诫各秘书,说明第五组的主要目的,在收集资料,备委员长索阅或呈送参考,决不可自视为有若干经纶;要知秘书属于辅佐地位,故工作不在上陈意见,而在留心收集各种问题的相关材料,选择归纳,附具结论,以贡献于委员长。不料当天五组秘书又集体向陈对待遇有所请求,为陈所拒。
 陈布雷认为这批秘书行事超越本分,屡劝不听,
陈布雷认为这批秘书行事超越本分,屡劝不听,
 乃于1937年9月对侍五组进行改组,将原任秘书8人及书记、司书2人均予解职,改编至军委会秘书处内。
乃于1937年9月对侍五组进行改组,将原任秘书8人及书记、司书2人均予解职,改编至军委会秘书处内。
 并引用李惟果、陈方、罗君强3人任侍五组秘书(陈方旋调侍四组组长),侍二处副主任周佛海兼任侍五组组长。
并引用李惟果、陈方、罗君强3人任侍五组秘书(陈方旋调侍四组组长),侍二处副主任周佛海兼任侍五组组长。

随着抗战战事范围的日渐扩大,各种专门问题均有待收集材料,分类研究,以供统帅参考;各方面的条陈或请示裁决的案件,有时也非经签拟则统帅无从加以审择决定;加上各界有志之士愿自效者甚多,蒋介石既已不兼行政院院长,也宜有一直属的机关以资延揽,凡此种种,均已非侍从室原有的架构所能应付。陈布雷乃建议蒋于军事委员会内增设一智囊团性质的参事室,获蒋同意,命陈草拟组织以呈。1938年3月,参事室正式成立于武汉,由朱家骅任主任。

自从参事室成立后,侍从室的规模缩小,主要业务变成为蒋介石整理文告和文稿,不过政策方面的研究仍持续进行。此一时期,侍从室最重要的秘书为李惟果。李毕业于清华大学,公费留美,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博士,1937年9月入侍从室任五组秘书。
[1]
1938年4月,曾撰写《日本对苏俄开战之可能性及我国对策》研究报告。

1938年3月,侍五组由汪日章兼任,开始主管一些党政高级官员(省府委员、厅局长、行政督察专员等简任官)之调查、考核和任用的业务。5月9日,汪日章调任行政院简任秘书,由李惟果继任组长。李任组长期间,对于政策方面的研究仍未间断。1939年1月,李所撰写的《中日抗战与国际形势》报告,文长约1万字,文字流畅而不沉闷,陈布雷读者觉得“此才可造,为之心喜。”
 1941年12月,李获派外交部总务司司长离职。李惟果本不愿就此职,在蒋介石的坚持下,他才赴任。
1941年12月,李获派外交部总务司司长离职。李惟果本不愿就此职,在蒋介石的坚持下,他才赴任。
 陈布雷对此十分不舍。
陈布雷对此十分不舍。
1942年3月28日,蒋介石下令侍从室应设理论研究宣传设计组,4月4日,陈布雷获蒋同意侍五组增加理论研究与宣传设计两项,不另成立新组,并核准第五组组长以陶希圣担任。
 陶希圣为学者出身,抗战爆发后,在侍从室资助下,与周佛海创办艺文研究会于武汉,自此开始撰文分析国际问题,以评论表明抗战建国的立场与政策。其文字受到陈布雷的赞赏。1940年11月11日,陈布雷将陶的一份研究报告抄呈给蒋介石,并称此份报告:“综论世界大势,以经济观点推断国际变化与中国前途,目光四射,洵佳著也。”
陶希圣为学者出身,抗战爆发后,在侍从室资助下,与周佛海创办艺文研究会于武汉,自此开始撰文分析国际问题,以评论表明抗战建国的立场与政策。其文字受到陈布雷的赞赏。1940年11月11日,陈布雷将陶的一份研究报告抄呈给蒋介石,并称此份报告:“综论世界大势,以经济观点推断国际变化与中国前途,目光四射,洵佳著也。”
 1942年3月,陶希圣由香港至重庆,陈多次找陶长谈,认为他“具识精卓,诚益友也”。
1942年3月,陶希圣由香港至重庆,陈多次找陶长谈,认为他“具识精卓,诚益友也”。
 由他出任第五组组长,将使侍二处的阵容大为加强。
由他出任第五组组长,将使侍二处的阵容大为加强。

陶希圣上任后,首先即感到研究所需数据的不足,于是经常以该组所拥有的一些外汇,委托在英国的叶公超和在美的陈之迈购买外文书刊,以空运寄回,所以虽然战时日本实施海上封锁,但是侍五组还是自海外进口了一些书刊,仍能从事国际政治及军事方面的研究。

侍从室人员,除了从事本单位的政策研究,有时并且参与其他政府部门的研究计划,例如邵毓麟即曾于抗战后期参与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所领导之战后国际和平组织及战后外交对策的研究。同时参与研究的专家、学者尚包括王化成、浦薛凤、吴景超、张忠绂、杨云竹,以及若干外交界人员。

(三)联系知识分子:侍从室于抗战时期借用民间力量进行宣传工作,除蒋介石个人文稿的撰拟外,尚包括设立文宣社团,艺文研究会即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社团。
中共于1937年7月15日提出“共赴国难宣言”,国民政府于9月22日宣布准许中共加入抗战阵营后,中共即运用其擅长的文宣工作,在文化界建立统一战线,进行全面总动员,书局与书刊有如雨后春笋般设立。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自然是袖手旁观,其副部长周佛海,
 徒呼无奈,因此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与焦虑,亟欲成立一个团结学术及文化界人士的团体,与中共文宣工作对抗,名称拟定为“励学社”,与既有团结军人的团体“励志社”并称。经与侍二处主任陈布雷商议后,陈以为“励学社”和“励志社”并称,恐有两种疑虑:一是使社会人士误以为又要成立一个半官方的机构,而不是一个学术团体;二是学术文化界人士会误以为此团体是“御用工具”,因而不愿意参加。蒋认为所言有理,于是在书架上翻阅书籍作取名参考。忽然发现《汉书·艺文志》,便欲取名为“艺文社”,陈乃建议取名为“艺文研究会”,获蒋肯首。名称既定,陈布雷乃与周佛海及北大教授陶希圣晤谈,传达蒋意,由二人出面组织。蒋因忙于前方战事,且不宜曝光,以免中共反弹,故请汪兆铭就近指导,以加强国民党对中共的文宣反攻。
徒呼无奈,因此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与焦虑,亟欲成立一个团结学术及文化界人士的团体,与中共文宣工作对抗,名称拟定为“励学社”,与既有团结军人的团体“励志社”并称。经与侍二处主任陈布雷商议后,陈以为“励学社”和“励志社”并称,恐有两种疑虑:一是使社会人士误以为又要成立一个半官方的机构,而不是一个学术团体;二是学术文化界人士会误以为此团体是“御用工具”,因而不愿意参加。蒋认为所言有理,于是在书架上翻阅书籍作取名参考。忽然发现《汉书·艺文志》,便欲取名为“艺文社”,陈乃建议取名为“艺文研究会”,获蒋肯首。名称既定,陈布雷乃与周佛海及北大教授陶希圣晤谈,传达蒋意,由二人出面组织。蒋因忙于前方战事,且不宜曝光,以免中共反弹,故请汪兆铭就近指导,以加强国民党对中共的文宣反攻。

艺文研究会会址设于汉口,以周佛海为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为研究总干事,并由陶负责日常会务。下分总务、研究、出版等组,由侍四组秘书罗君强兼办总务工作。另设有编辑委员会,网罗学术文化界人士及各党派领导人,如前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民社党主席张君劢,青年党领导人李璜、陈启天、余家菊等,均为编辑委员。对于各党各派领袖,艺文研究会均以其刊物(如民社党的《再生》、青年党的《醒狮》、陈独秀的《抗战向导》)名义致送一些生活费,其他的民间报刊,也做选择性的资助
 。
。
艺文研究会活动,主要包括:(1)国际问题的研究:于香港和上海收集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的资料,以及各国的主要报纸、杂志,集中之后加以整理与分析,做成有系统的报告,供社会参考;(2)于西北、西南进行社会、经济考察;(3)出版《艺文丛书》;(4)出版学术性的刊物。
 其中影响最大的学术活动,应为陶希圣、陈之迈和吴景超策划的《艺文丛书》。根据笔者调查所得,《艺文丛书》共出版有以下16种书籍:
其中影响最大的学术活动,应为陶希圣、陈之迈和吴景超策划的《艺文丛书》。根据笔者调查所得,《艺文丛书》共出版有以下16种书籍:


数据源: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上海:编者印行,1979年),页156—157;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Inc., WorldCat. http://www.worldcat.org.
上表显示,参与写作者,均为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学者;《艺文丛书》中所收录的书籍,有一些至今甚至已成为经典著作,例如蒋廷黻所著《中国近代史》一书,即系其1938年春卸任驻苏大使职务返国后,应陈之迈之邀而撰写,不到二个月即写完交稿,
 蒋时年43岁。又如方显廷所著《中国工业资本问题》,则系其34岁所著Industrial Capital in China一书
蒋时年43岁。又如方显廷所著《中国工业资本问题》,则系其34岁所著Industrial Capital in China一书
 的中文本,至今仍经常为中外学者所引用。
的中文本,至今仍经常为中外学者所引用。

此外,艺文研究会并资助几十种报纸和刊物,包括《政论》(何兹全主编)、《民意周刊》(叶溯中主编)、《半月文摘》(陶涤亚主编,后易名为《星期文摘》《文摘月报》),以及未办出版登记的地下刊物《游击战》(陶希圣主编,后易名为《观察》《前卫》)等,并成立一青年出版社(后易名为独立出版社),此一出版社曾出版数十种《抗战建国小丛书》,
 除了宣传抗战,并且阐扬三民主义及政府政策,与中共宣传相抗。此外,并成立中国文化服务社,作为发行机构。艺文研究会一切活动、出版及发行的经费,均来自军需署。
除了宣传抗战,并且阐扬三民主义及政府政策,与中共宣传相抗。此外,并成立中国文化服务社,作为发行机构。艺文研究会一切活动、出版及发行的经费,均来自军需署。
1939年周佛海、陶希圣自渝出走,蒋介石立即下令停止该会经费,由总务组长罗君强向陈布雷办清交待手续。
 但独立出版社仍继续营运,并加以扩充。扩充计划系由陈布雷负责审查修改,蒋介石批准后实施。
但独立出版社仍继续营运,并加以扩充。扩充计划系由陈布雷负责审查修改,蒋介石批准后实施。

(四)赞助复性书院与中国哲学会:蒋介石曾经由侍从室赞助过一些学术机构和社团,其中以复性书院和中国哲学会最为重要,以下拟分别予以讨论。
复性书院的创办人马浮为民国时期重要思想家。与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合称为中国当代四大儒。1936年,蒋介石曾约见马浮,请示行己为政、修身治国之道。马提出一个“诚”字,强调“诚即为内圣外王之始基”,并推崇张载的《西铭》,赞其气象磅礴、包罗宏广。于是蒋指示,全国党政人员研读《西铭》,不久高中国文课本也选《西铭》作为教材。

抗战军兴,马浮随浙江大学西迁,暂住于泰和宜山。他不愿在大学任教,乃接受弟子寿景伟(毅成)、刘百闵等人的建议,在一山水胜地创办一所书院,继续讲学。寿、刘等人又通过陈布雷,将复性书院的建院计划呈报蒋介石。
 马本人也于1939年3月1日在陈布雷的陪同下晋见蒋介石,
马本人也于1939年3月1日在陈布雷的陪同下晋见蒋介石,
 当面拜托。获蒋特准创办,并捐专款3万元作为建院基金,命中央赈济委员会副委员长、浙籍大佬屈映光主持事,
当面拜托。获蒋特准创办,并捐专款3万元作为建院基金,命中央赈济委员会副委员长、浙籍大佬屈映光主持事,
 并指示教育部主动与马浮商洽创设。于是教育部随即成立书院筹备委员会,聘屈映光等15人为筹备委员,展开筹备工作。6月1日,教育部公布《私人讲学机关设立办法》,使书院的设立有了法令的依据。复性书院随即以“讲明经术,注重文理,欲使学者知类通达,深造自得,养成刚大贞固之才”为宗旨开始招生。
并指示教育部主动与马浮商洽创设。于是教育部随即成立书院筹备委员会,聘屈映光等15人为筹备委员,展开筹备工作。6月1日,教育部公布《私人讲学机关设立办法》,使书院的设立有了法令的依据。复性书院随即以“讲明经术,注重文理,欲使学者知类通达,深造自得,养成刚大贞固之才”为宗旨开始招生。

出次征选共有700余人报名,由于国学基础普遍不佳,仅录取20余人。入院研习以3年为期,其间享有公费。为了扩大入学范围,又设“参学人”,凡好学之士愿来参问,或有职业而未能长期住院者,由主讲、知友介绍,得为参学人,在院问学不超过半年,且为自费。
9月,书院正式于四川乐山开讲。书院课程分为“通治”与“别治”二门。前者为共同修习,以孝经、论语为一类,孟、荀、董、郑、周、程、张、朱、陆、王诸子附之。后者相当于选修,以尚书、三礼为一类,名、法、墨三家附之;易、春秋又一类,道家附之。
 师资除了主讲马浮及马所聘的开设特设讲座的熊十力,另设不定期来院短期讲学的“学友”(相当于大学的客座教授),曾邀请赵熙、谢无量等人担任。马浮每月的“主讲修金”为500元,熊十力等特设讲座者每月的“讲座修金”为300元。
师资除了主讲马浮及马所聘的开设特设讲座的熊十力,另设不定期来院短期讲学的“学友”(相当于大学的客座教授),曾邀请赵熙、谢无量等人担任。马浮每月的“主讲修金”为500元,熊十力等特设讲座者每月的“讲座修金”为300元。
 同一年,顾颉刚和吴文藻这两位云南大学“中英庚款讲座教授”每月实领的薪资,也仅有330元,
同一年,顾颉刚和吴文藻这两位云南大学“中英庚款讲座教授”每月实领的薪资,也仅有330元,
 而当时在乐山,虽有通货膨胀,一个家庭每月如有60元即可丰衣足食,
而当时在乐山,虽有通货膨胀,一个家庭每月如有60元即可丰衣足食,
 蒋介石对马浮、熊十力等大儒的礼遇,由此可见一斑。1940年筹备委员会即组为董事会,邵力子、陈布雷、屈映光、刘百闵、寿景伟、陈其采、周惺甫、谢无量、沈尹默、沈敬仲等先后担任董事,屈映光为董事长,陈其采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副董事长,董事会聘马浮为主讲,主持教事,刘百闵为董事兼总干事。
蒋介石对马浮、熊十力等大儒的礼遇,由此可见一斑。1940年筹备委员会即组为董事会,邵力子、陈布雷、屈映光、刘百闵、寿景伟、陈其采、周惺甫、谢无量、沈尹默、沈敬仲等先后担任董事,屈映光为董事长,陈其采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副董事长,董事会聘马浮为主讲,主持教事,刘百闵为董事兼总干事。
 刘百闵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兼国民党中宣部中国文化服务社社长,因此凡董事会一切业务及书院应办事项,均由中国文化服务社义务兼办。
刘百闵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兼国民党中宣部中国文化服务社社长,因此凡董事会一切业务及书院应办事项,均由中国文化服务社义务兼办。
书院员生膏火及一切开支,均依赖基金利息及政府补助。筹备阶段时,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曾拨款10万元作为基金;教育部每月拨给经常费,开始时为4000元,
 1940年9月以后增为每月6000元,但是往往不能及时汇到。书院经费不济时,常有赖董事寿景伟从其主管的中国茶业公司借支垫款。经武汉大学教授张颐(真如)1941年1月于四川省参议会上提议,获省政府同意每年补助书院经费1万元,由财政厅分4期支付。
1940年9月以后增为每月6000元,但是往往不能及时汇到。书院经费不济时,常有赖董事寿景伟从其主管的中国茶业公司借支垫款。经武汉大学教授张颐(真如)1941年1月于四川省参议会上提议,获省政府同意每年补助书院经费1万元,由财政厅分4期支付。

书院自1939年秋天开讲,肄业学生及参学人员尚不满50人。有些人震于马浮及熊十力大名,前来瞻仰,并非有决心研习,日久难安枯淡,乃逐渐离去。熊十力由于在一次日机袭乐山时被炸受伤,且认为书院当众说并陈,由学生择善而从,多方吸收,并习用世之术,以谋出路,主张仿效一般大学改革书院制度,与马发生冲突,不多久即离院。
 历史学者贺昌群,也因理念与马不同而离开。
历史学者贺昌群,也因理念与马不同而离开。
 至于1941年以后,物价上涨,书院经费难以维持,马浮打算辍讲,为董事会所慰留,1941年终,马又提出维持书院办法,以刻书为主,讲学为副。董事会经过讨论后,决定呈请蒋介石报告院务,为刻书事请求特别捐助。此件呈文经董事陈布雷代呈后,获蒋同意一次补助刻书费10万元。
至于1941年以后,物价上涨,书院经费难以维持,马浮打算辍讲,为董事会所慰留,1941年终,马又提出维持书院办法,以刻书为主,讲学为副。董事会经过讨论后,决定呈请蒋介石报告院务,为刻书事请求特别捐助。此件呈文经董事陈布雷代呈后,获蒋同意一次补助刻书费10万元。
 战后由于经费缺乏,曾一度成立基金劝募委员会,推举陈果夫为主任委员,对外募款,
战后由于经费缺乏,曾一度成立基金劝募委员会,推举陈果夫为主任委员,对外募款,
 不过最后仍于1950年停办。
不过最后仍于1950年停办。
近代中国第一个以研究哲学为宗旨的学术团体,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哲学研究会。此团体于1917年所创刊的《哲学会刊》(半年刊),为近代中国第一份哲学研究刊物,主要刊登哲学研究论文、译著,以及会务报道。
 不过此一团体性质属于校内社团,故影响有限。至于第一个哲学研究的社会团体,应为傅铜、吴康等人于1921年在北京所创办的哲学社。此一社团的职员并不多,其机关刊物《哲学》杂志存在的时间不长,因此影响也不大。真正影响大的,为1927年于北平所创办的《哲学评论》,以及由《哲学评论》聚餐会酝酿而生的中国哲学会。
不过此一团体性质属于校内社团,故影响有限。至于第一个哲学研究的社会团体,应为傅铜、吴康等人于1921年在北京所创办的哲学社。此一社团的职员并不多,其机关刊物《哲学》杂志存在的时间不长,因此影响也不大。真正影响大的,为1927年于北平所创办的《哲学评论》,以及由《哲学评论》聚餐会酝酿而生的中国哲学会。
1927年4月,由瞿世英、张东荪、黄子通、林宰平等人主办的《哲学评论》(月刊)创刊。在创刊之初,该社曾约请了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许地山等30多位哲学学者撰稿,在当时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至20世纪30年代初,在《哲学评论》周围,逐渐以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哲学系教师为主干,积聚了一批以介绍西方哲学和研究中西哲学为共同志趣的学者,每1月至2月,采用“沙龙”性质举行聚餐会,间亦宣读论文。1934年10月,始有人提议举行哲学年会,推举贺麟、冯友兰、金岳霖、黄子通负责筹划。1935年4月,中国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于北京大学召开,会中决议扩大组织全国性质的中国哲学会,并推举贺麟等11人组织筹委会,由首届年会原有筹备委员贺麟、金岳霖、黄子通3人负责召集。
 1936年4月,中国哲学会第二届年会于北京大学召开,会中正式通过中国哲学会会章并选举理事15人组成理事会,其中冯友兰、金岳霖、祝百英、宗白华、汤用彤为常务理事,同时编辑出版会刊《哲学评论》。1937年元月,第三届年会于南京中央大学召开,此时已有北京、南京和广州3个分会。会中决议:(1)请教育部增加哲学课程,令教育部一律增设哲学系;(2)编纂《哲学大辞典》;(3)请中央研究院增设哲学研究所。
1936年4月,中国哲学会第二届年会于北京大学召开,会中正式通过中国哲学会会章并选举理事15人组成理事会,其中冯友兰、金岳霖、祝百英、宗白华、汤用彤为常务理事,同时编辑出版会刊《哲学评论》。1937年元月,第三届年会于南京中央大学召开,此时已有北京、南京和广州3个分会。会中决议:(1)请教育部增加哲学课程,令教育部一律增设哲学系;(2)编纂《哲学大辞典》;(3)请中央研究院增设哲学研究所。
 会议并决定第四届年会于广州召开。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学者四散,年会与《哲学评论》均无法维持而告中断。
会议并决定第四届年会于广州召开。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学者四散,年会与《哲学评论》均无法维持而告中断。
蒋介石年轻时即对宗教、哲学问题感兴趣,1938年起更对哲学着上了迷,甚至曾因研究黑格尔哲学而致失眠。
 他对《哲学评论》十分怀念,于是接受陶希圣的建议,恢复中国哲学会与《哲学评论》,经陶与西南联大哲学系商议后,决定合作。
他对《哲学评论》十分怀念,于是接受陶希圣的建议,恢复中国哲学会与《哲学评论》,经陶与西南联大哲学系商议后,决定合作。
 由于中国哲学会依会章并未设会长,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被视为是国民党官方哲学的代表人物,如果中国哲学会设会长,势必选陈担任,此为大家所不乐见之事。
由于中国哲学会依会章并未设会长,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被视为是国民党官方哲学的代表人物,如果中国哲学会设会长,势必选陈担任,此为大家所不乐见之事。
 而冯友兰当时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中国哲学会常务理事兼《哲学评论》的主编,遂被指定负责此事。
而冯友兰当时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中国哲学会常务理事兼《哲学评论》的主编,遂被指定负责此事。
1941年8月29日,中国哲学会第四届年会在侍从室的资助下,于昆明云南大学顺利召开,会期3天。
 本届年会虽因抗战未能按第三届年会决定的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但与会会员除在滇会员外,以广州占多数,而在滇者大多来自北平。在首日的会议中,通过了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致敬电,以及向前方将士致敬电,随即展开3天的论文宣读及讨论。大会结束前,曾召开中国哲学会的会务会议,由冯友兰报告编辑委员会会务,要点为《哲学评论》复刊,在上海排印,仍由开明书局发行。又听取各分会报告会务。会议中通过设立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由贺麟任主任委员,冯友兰、汤用彤、宗白华、张颐为委员;设立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由冯友兰任主任委员,汤用彤、贺麟、宗白华、黄建中为委员。
本届年会虽因抗战未能按第三届年会决定的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但与会会员除在滇会员外,以广州占多数,而在滇者大多来自北平。在首日的会议中,通过了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致敬电,以及向前方将士致敬电,随即展开3天的论文宣读及讨论。大会结束前,曾召开中国哲学会的会务会议,由冯友兰报告编辑委员会会务,要点为《哲学评论》复刊,在上海排印,仍由开明书局发行。又听取各分会报告会务。会议中通过设立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由贺麟任主任委员,冯友兰、汤用彤、宗白华、张颐为委员;设立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由冯友兰任主任委员,汤用彤、贺麟、宗白华、黄建中为委员。
事实上,此二委员会均由侍从室提供经费援助,蒋介石还指定陶希圣为侍从室与两委员会之间的联络员,
 不过二委员会的缘起并不相同。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的缘起,乃是1941年1月15日,蒋介石约见贺麟(是为二人首次见面),双方讨论黑格尔哲学。
不过二委员会的缘起并不相同。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的缘起,乃是1941年1月15日,蒋介石约见贺麟(是为二人首次见面),双方讨论黑格尔哲学。
 在蒋、贺见面前,贺曾先于1月7日拜访陈布雷,谈其研究知难行易学说的心得及哲学研究的方法。
在蒋、贺见面前,贺曾先于1月7日拜访陈布雷,谈其研究知难行易学说的心得及哲学研究的方法。
 当蒋问贺有无需要协助之处,贺则表示需要一些钱办一个编译委员会,学严复介绍西方古典哲学,以贯通中西思想、发扬三民主义的精神,
当蒋问贺有无需要协助之处,贺则表示需要一些钱办一个编译委员会,学严复介绍西方古典哲学,以贯通中西思想、发扬三民主义的精神,
 获蒋同意。
获蒋同意。
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成立初期所出版的书,计有贺麟译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的《致知编》(Treatise on the Correction of the Understanding)、陈康译柏拉图(Plato)的《巴曼尼得斯篇》(Parmenides)、谢幼伟译鲁一士(Josiah Royce)的《忠之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oyalty),以及樊星南译鲁一士的《近代哲学的精神》(The Spirit of Modern Philosophy)等。以上各书原著均为著名思想家的经典作品,译者也均为著名学者,每种译本前还由译者撰写长序介绍该书内容,因此甚获学界好评。其中《忠之哲学》一书,对社会影响尤大,被视为是呼应蒋介石的效忠主义,与其抗战建国的想法直接相关。

至于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则是蒋介石希望恢复中国哲学会与《哲学评论》,要陶希圣去办此事,陶经由西南联大哲学系找上了冯友兰,要冯成立一个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并由冯担任主任委员。
 不过所提供的经费甚少,每月只有1.8万元。当时通货膨胀已十分严重,这个数目实际上也办不了什么事。
不过所提供的经费甚少,每月只有1.8万元。当时通货膨胀已十分严重,这个数目实际上也办不了什么事。
 冯友兰才想到将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作为中国哲学会的一个附属组织,接收哲学方面的稿件,由委员会致赠稿费。短篇论文,刊登于《哲学评论》,长篇著作,则以专书形式出版。
冯友兰才想到将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作为中国哲学会的一个附属组织,接收哲学方面的稿件,由委员会致赠稿费。短篇论文,刊登于《哲学评论》,长篇著作,则以专书形式出版。

据现有的数据显示,由中国哲学研究会主编的《中国哲学丛书》共出版了以下各书。
甲集:
(1)熊十力著,《新唯识论》,1944年3月重庆初版,1947年3月上海初版。
(2)黄建中著,《比较伦理学》,1945年4月重庆初版。
(3)熊十力著,《读经示要》,1945年12月初版。
(4)冯友兰著,《新知言》,1946年12月初版。
乙集:
(1)稽文甫著,《晚明思想史论》,1944年重庆初版。
(2)冯友兰著,《新原道》,1945年4月重庆初版,12月上海初版,1946年5月上海再版,10月上海3版。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通货膨胀的日益严重,蒋介石曾试图将补助中国哲学会的办法予以扩大,以便能够接济更多的大学教授。1942年6月,他致电侍二处主任陈布雷,指示拟定两种办法:(1)参考当前补助哲学会办法,组织政治、经济、社会以及自然科学等研究会,或资助杂志、刊物译书、举办征文等活动;(2)针对各大学教授生活最困难者,予以信用贷款,不收利息或收最低利息。并要求他与教育部长陈立夫妥筹办法,限当年暑假前发表施行。

侍从室为蒋介石最重要的智囊机构。在党政政策研究方面,侍从室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成果,即为1945年国民党六全大会政纲的研拟。侍从室汇整党内各派立场各异的政策意见,整合为大多数人均能接受的政纲,将国民党的经济政策,由倾向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转型为计划自由经济,并且尝试建立社会安全体系,对于日后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外交方面,侍从室第五组和国防设计委员会在战前为蒋介石最重要的咨询机构。
1938年蒋介石在陈布雷的建议下设立参事室,1941年蒋又命陈布雷和王宠惠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内设置国际问题讨论会,专门研究战后国际问题。此二机构出现后,侍从室在外交决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即大为缩减,无法与其在党政决策上的重要性相比,不过仍积极介入中日秘密外交、韩国独立运动等活动,并出席重要国际会议,协助蒋介石进行“元首外交”。国民政府的决策机构众多,包括行政院、国民党中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等,各自均参与部分的决策制定,而侍从室在其中往往扮演最后“把关者”的角色。例如在战前“五五宪草”审查的过程中,贯彻蒋介石的意志,将内阁制的宪草法案转换为大权集中于总统的宪法草案;又如在年度政府预算案的审查过程中,协助蒋执行最后把关的工作。
侍从室和学界的联系,主要包括邀请学者为蒋介石草拟书告,参与法案、政策的研拟,或执行政策性的研究。侍从室并曾成立艺文研究会,赞助数十种报纸及刊物,并出版《艺文丛书》;协助著名学者马浮创办复性书院,萧一山从事清史研究,建立“民族革命史观”;又协助哲学界恢复中国哲学会,不仅扩大知识分子的参与,也强化了国民政府政权的合法性。也有少数学者接受蒋介石个人的委托,协助办理元首外交,杭立武即为一例。杭立武,伦敦大学博士,曾任考试院编纂,中央大学政治系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英文化协会秘书长。
 1940年7月,英国与日本在东京签定协议,封闭滇缅公路运输3个月,使得中国对外国际路线完全断绝,影响抗战甚大。
1940年7月,英国与日本在东京签定协议,封闭滇缅公路运输3个月,使得中国对外国际路线完全断绝,影响抗战甚大。
 蒋介石除致电丘吉尔,表示为中央双方利益计,从速恢复滇缅运输路线外,
蒋介石除致电丘吉尔,表示为中央双方利益计,从速恢复滇缅运输路线外,
 另派杭立武以其私人特使的身份赴英,面见丘吉尔,谈判重开滇缅路。丘吉尔表示封闭滇缅路仅为拖延之计,3个月之后一定重开滇缅路。杭立武得此承诺后返回重庆,10月英国果然重开滇缅路。
另派杭立武以其私人特使的身份赴英,面见丘吉尔,谈判重开滇缅路。丘吉尔表示封闭滇缅路仅为拖延之计,3个月之后一定重开滇缅路。杭立武得此承诺后返回重庆,10月英国果然重开滇缅路。
 蒋、邱来往函电均由侍从室负责办理,避免了一般行政体系公文层转耗时的弊病。
蒋、邱来往函电均由侍从室负责办理,避免了一般行政体系公文层转耗时的弊病。
侍从室和新闻界的联系,除指导官方媒体外,主要为扶植《大公报》。
战前至抗战中期,侍从室和民间学界及新闻界的联系尚称顺利,五五宪草在审议过程中,侍从室运用学者和媒体的力量,成功的将原倾向于内阁制的宪草调整为倾向于集权制,充分贯彻蒋介石的意志,即为一例。至抗战后期,由于孔家弊案未能迅速处理,在媒体大肆宣传下,国民政府贪腐形象深植人心,侍从室及宣传官员要想扭转此一负面形象,已非易事,遑论掌握舆论,学界也无人愿意为国民政府辩护。战后此种情势依然持续,直至政权易帜。
侍从室身为蒋介石最重要的智囊机构之一,到了后来还扮演了为党国考察、选拔及考核人才的角色。这工作主要是由1939年成立的侍三处负责,关于这部分,我们会在后面章节做详细介绍,在此先不做赘述。
[1]
陈布雷:《回忆录》,页122。
陈布雷:《日记》,1937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