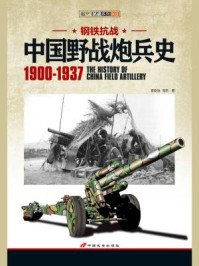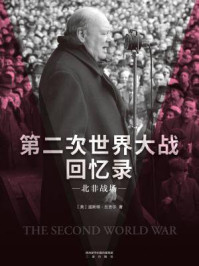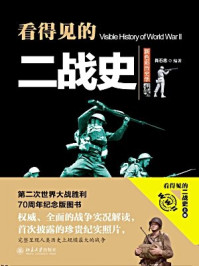国防设计委员会,系蒋介石在钱昌照(1899—1988)的建议下所成立的智囊机构。钱昌照,字乙藜,江苏常熟人,1919年赴英国留学,1922年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学位后,入牛津大学从事经济学研究。1924年返国,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秘书、国民政府文官处秘书,1931年6月任教育部次长(部长为蒋介石自兼,政务次长为陈布雷)。九一八事变后,钱昌照以外侮日亟,应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筹建一个国防设计机构。广义的国防应包括军事、国际关系、教育文化、财政经济、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土地及粮食、人才的调查等方面。钱昌照向蒋介石提议创办此一机构的目的除了富国强兵和抵御外侮,更是巩固统治——利用此一机构延揽各界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和专家学者加入政府,即可扩大统治基础,巩固统治秩序。蒋介石十分赞同钱昌照的建议,促其草拟人选。两周之后,钱氏草拟了一份40余人的名单,大致如下:
军事方面:黄慕松、杨杰、陈仪、周亚卫、俞大维、钱昌祚等。
国际关系方面:王世杰、周鲠生、谢冠生、徐淑希、钱端升等。
教育文化方面:胡适、蒋梦麟、杨振声、傅斯年、周炳琳等。
财政经济方面:吴鼎昌、张嘉璈、徐新六、陶孟和、杨端六、王崇植等。
原料及制造方面:丁文江、翁文灏、顾振、范旭东、吴蕴初、刘鸿生、颜任光等。
交通运输方面:黄伯樵、沈怡、陈伯庄等。
土地及粮食方面:万国鼎、沈宗瀚、赵连芳等。
名单的特色有二:一是均为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或是知名的企业家,二是没有孔祥熙、宋子文系统或是CC(陈果夫、陈立夫)系统的人。蒋介石对名单完全接受,仅在军事方面增加林蔚一人。
 并指派钱昌照先和名单上的人选联系交换意见,再约其中部分见面或讲学。
并指派钱昌照先和名单上的人选联系交换意见,再约其中部分见面或讲学。
晚近学界对于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研究虽多,
 不过由于均出版于十余年前,所利用的档案史料有限,且均未从蒋、汪人才争夺战的角度观察。
不过由于均出版于十余年前,所利用的档案史料有限,且均未从蒋、汪人才争夺战的角度观察。
其实汪兆铭(即汪精卫)在1929年12月自巴黎返抵香港,策划讨蒋全局。当时各反蒋军事行动均告失败,一时无从着手。汪的首席智囊顾孟余即加强结纳有声望的学人,争取舆论同情。他首先调查各派系(包括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蒋系、桂系、阎系、冯系、东北系等)在各省工作的西洋留学生
 ,凡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乃至中央大学的名教授,能保持接触者即降心相处,重要者包括蔡元培、胡适、周鲠生、王世杰、杨端六、张慰慈、高一涵等,令唐有壬、彭学沛司联络之责。胡适和顾若即若离,顾也不介意。对于南京方面,顾孟余仍和丁惟汾、朱家骅、段锡朋等,及昔日的北大学生一一联络,造成南京的CC系中隐然有一北大系存在,以分散蒋介石的势力,且与宋子文、黄郛信使往还。此时宋正图掌握金融力量自成一系,与蒋、汪鼎足而三,于蒋、汪纷争中,对汪仍表诚敬;黄郛则于顾任北大教务长时,获聘为军事教官,与顾两人关系良好。
,凡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乃至中央大学的名教授,能保持接触者即降心相处,重要者包括蔡元培、胡适、周鲠生、王世杰、杨端六、张慰慈、高一涵等,令唐有壬、彭学沛司联络之责。胡适和顾若即若离,顾也不介意。对于南京方面,顾孟余仍和丁惟汾、朱家骅、段锡朋等,及昔日的北大学生一一联络,造成南京的CC系中隐然有一北大系存在,以分散蒋介石的势力,且与宋子文、黄郛信使往还。此时宋正图掌握金融力量自成一系,与蒋、汪鼎足而三,于蒋、汪纷争中,对汪仍表诚敬;黄郛则于顾任北大教务长时,获聘为军事教官,与顾两人关系良好。

1932年元月汪兆铭就任行政院院长后,联系知识分子更是名正言顺。
 他接连邀集学者召开了两次会议。第一次是1932年4月的国难会议,第二次是同年7月的专家会议。国难会议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首次由政府召集党政要员与民间人士共商国是的会议,因此社会大众期望甚高,各主要报刊纷纷提出各种救国主张,盼能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但是汪兆铭将议事范围仅限于御侮、“剿共”和救灾三项,并声明不谈政治,导致许多主张取消党治的人士拒绝出席。原定出席520余人,实际到会者仅144人,闭幕式时也仅有167人。学者出席者包括皮宗石、陶孟和、周炳琳、陶希圣、何思源、蒋廷黻、钱端升、高一涵、蒋梦麟、马寅初、朱经农、童冠贤等,请假者则有胡适、张伯苓、丁文江、陶行知、梁漱溟、周诒春等。议程原规划不谈政治,不料与会人士不仅提出大量有关政治改革的议案,而且讨论十分激烈。最后仅通过政府应切实办理地方自治,如期结束训政,成立民意机关,保障人民各种政治自由等决议,较出席代表最初的提案尚有一定差距。
他接连邀集学者召开了两次会议。第一次是1932年4月的国难会议,第二次是同年7月的专家会议。国难会议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首次由政府召集党政要员与民间人士共商国是的会议,因此社会大众期望甚高,各主要报刊纷纷提出各种救国主张,盼能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但是汪兆铭将议事范围仅限于御侮、“剿共”和救灾三项,并声明不谈政治,导致许多主张取消党治的人士拒绝出席。原定出席520余人,实际到会者仅144人,闭幕式时也仅有167人。学者出席者包括皮宗石、陶孟和、周炳琳、陶希圣、何思源、蒋廷黻、钱端升、高一涵、蒋梦麟、马寅初、朱经农、童冠贤等,请假者则有胡适、张伯苓、丁文江、陶行知、梁漱溟、周诒春等。议程原规划不谈政治,不料与会人士不仅提出大量有关政治改革的议案,而且讨论十分激烈。最后仅通过政府应切实办理地方自治,如期结束训政,成立民意机关,保障人民各种政治自由等决议,较出席代表最初的提案尚有一定差距。
 蒋廷黻在会议结束后对此次会议曾有以下的评论:
蒋廷黻在会议结束后对此次会议曾有以下的评论:
政府对国难会议的态度,全不一致,连行政院本身就不一致,外交部、军政部、财政部,倘以他们对会议的报告为标准,显然是无诚意的。汪精卫先生则又当别论。

蒋廷黻的文章显示,此次会议虽然未必可算是成功,但是对汪兆铭加强与学者之间的联系来说,毫无疑问是很有帮助的。
1932年7月,汪兆铭与蔡元培(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再度邀请蒋梦麟、王世杰、丁文江、周鲠生、张奚若、杨端六、徐淑希、蒋廷黻、王星拱、李书华、高一涵、陶孟和、胡适等30余位学者专家至京研讨国难期间各项问题,讨论范围包括外交、内政、建设、教育4项。

另外,虽然汪系大将陈公博和顾孟余关系不佳,
 但是他所掌握的实业部,也是一个和学者联系较多的机构。陈公博和顾孟余相同,均为经济学者出身,重视统计资料,上位后任用研究统制经济的学者罗敦伟为简任秘书
但是他所掌握的实业部,也是一个和学者联系较多的机构。陈公博和顾孟余相同,均为经济学者出身,重视统计资料,上位后任用研究统制经济的学者罗敦伟为简任秘书
 ,一方面协助陈公博起草《四年实业计划》(同时参加起草者尚包括许仕廉、章元善等);一方面主持编纂《中国经济年鉴》。罗敦伟广聘学者专家担任编纂委员和编纂,包括翁文灏、柯象峯、马寅初、乔启明、杨端六、陈长蘅、卫挺生、杨汝梅、许仕廉、章元善、陈翰笙等百余人均在罗致之列。当时国内尚无类似书籍,因此1934年5月出版后颇受各界好评,一个月即再版。
,一方面协助陈公博起草《四年实业计划》(同时参加起草者尚包括许仕廉、章元善等);一方面主持编纂《中国经济年鉴》。罗敦伟广聘学者专家担任编纂委员和编纂,包括翁文灏、柯象峯、马寅初、乔启明、杨端六、陈长蘅、卫挺生、杨汝梅、许仕廉、章元善、陈翰笙等百余人均在罗致之列。当时国内尚无类似书籍,因此1934年5月出版后颇受各界好评,一个月即再版。
 承印此著作(共600余万字)的商务印书馆本来以为会亏本,不料反而大赚了一笔。
承印此著作(共600余万字)的商务印书馆本来以为会亏本,不料反而大赚了一笔。
 参加编纂的学者专家,原本以为是纯属义务劳动,不料竟分得许多版税,于是第一回年鉴出版后,第二、三回连续出版,第四回虽编妥,但由于全面抗战突发,未及出版。
参加编纂的学者专家,原本以为是纯属义务劳动,不料竟分得许多版税,于是第一回年鉴出版后,第二、三回连续出版,第四回虽编妥,但由于全面抗战突发,未及出版。

汪兆铭为著名的宣传家,胡汉民曾称赞汪兆铭在演讲时,“听者任其擒纵,于二十年未见有人演说过于精卫者。”
 其文字的鼓动能力也极强。
其文字的鼓动能力也极强。
 左舜生品评国民党当代人物,认为主持党务工作最适当的人选,“前为汪精卫,后则陈立夫”,因为两人均深具江湖气质,群众乐于接近。
左舜生品评国民党当代人物,认为主持党务工作最适当的人选,“前为汪精卫,后则陈立夫”,因为两人均深具江湖气质,群众乐于接近。

汪兆铭一连串联系学者的动作,自然引起蒋介石左右的疑惧,被视为在“收买知识阶级的人心”。
 蒋介石也发现汪兆铭的声望日增,一部分CC分子被其吸收,且顾孟余、陈公博等,及《现代评论》社主干周鲠生、王世杰及若干北大教授均拥汪,蔡元培清望尤高,也支持汪、顾。蒋考虑到党内嫡系如陈果夫、陈立夫、邵力子、叶楚怆等,绝非汪、顾的对手,亟需吸引人才。故于就任行政院院长后,有计划地争取人才,以与汪兆铭相抗。
蒋介石也发现汪兆铭的声望日增,一部分CC分子被其吸收,且顾孟余、陈公博等,及《现代评论》社主干周鲠生、王世杰及若干北大教授均拥汪,蔡元培清望尤高,也支持汪、顾。蒋考虑到党内嫡系如陈果夫、陈立夫、邵力子、叶楚怆等,绝非汪、顾的对手,亟需吸引人才。故于就任行政院院长后,有计划地争取人才,以与汪兆铭相抗。
 蒋介石此时目光投向了留学生、大学教授、职业团体、北洋旧官僚和外交界。他曾在日记中记载其求才的心路历程:
蒋介石此时目光投向了留学生、大学教授、职业团体、北洋旧官僚和外交界。他曾在日记中记载其求才的心路历程:
时以不得襄助之人为念!世道日非,人欲横流,欲得一贤能之士为助,如何求之?旧党员多皆腐败无能,新党员多恶劣浮嚣,而非党员则接近不易,考察更难。古之山林之贤,今不可复见,而租界反动之流,多流氓之亚者。其在留学生中、大学教授中、职业团体中、旧日官僚而未在本党任仕有风格者中、外交界中,其在此中求之乎?

在北洋旧官僚方面,既有的杨永泰无清望,缺乏号召力,于是想到久被排斥的“甲寅派”领袖章士钊。
 1931年10月,蒋邀章赴京,初欲用为司法行政部部长,章不就,继乃向章提议改行政院秘书长为特任,以章充任,蒋外出指挥军事时,由章全权处理院务,章仍不就,并发表声明不就政府任何职务,仍仅执行律师业务。
1931年10月,蒋邀章赴京,初欲用为司法行政部部长,章不就,继乃向章提议改行政院秘书长为特任,以章充任,蒋外出指挥军事时,由章全权处理院务,章仍不就,并发表声明不就政府任何职务,仍仅执行律师业务。
 至于留学出身的大学教授,蒋介石则觉得素无渊源,考察更为不易。
至于留学出身的大学教授,蒋介石则觉得素无渊源,考察更为不易。
蒋笼络知识分子不成,此时钱昌照提议筹设国防设计委员会,蒋介石自然是十分赞同,积极约见学者专家,展开筹备工作。1932年春、夏、秋三季,在南京、牯岭、武汉,由钱昌照陪同和蒋介石见面或为其讲学者,计有王世杰、周鲠生、徐淑希、胡适、张其昀、吴鼎昌、徐新六、杨端六、丁文江、翁文灏、顾振、范旭东、吴蕴初、陈伯庄、万国鼎等二三十人。
 33岁的钱昌照虽然是教育部常务次长,但是认识的文教界人士毕竟有限。他有两个连襟,一个是带他进入政坛的黄郛,另一个则是陶孟和(1887—1960)。陶孟和为天津人,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返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教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所所长,南开大学董事等职,认识的学者极多,被视为地位仅次于张伯苓的华北文教界人士。
33岁的钱昌照虽然是教育部常务次长,但是认识的文教界人士毕竟有限。他有两个连襟,一个是带他进入政坛的黄郛,另一个则是陶孟和(1887—1960)。陶孟和为天津人,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返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教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所所长,南开大学董事等职,认识的学者极多,被视为地位仅次于张伯苓的华北文教界人士。
 上述钱昌照介绍给蒋介石认识或讲学的学者专家,有许多即通过陶孟和的关系。蒋介石礼贤下士,邀请学者为其讲学,目的在了解内政、外交上的各项问题及解决之道,作为其决策的参考。当时曾有媒体以《蒋介石经筵讲官》为题撰文报道,
上述钱昌照介绍给蒋介石认识或讲学的学者专家,有许多即通过陶孟和的关系。蒋介石礼贤下士,邀请学者为其讲学,目的在了解内政、外交上的各项问题及解决之道,作为其决策的参考。当时曾有媒体以《蒋介石经筵讲官》为题撰文报道,
 蒋本人对此一机构的筹备也极为重视,曾多次致电钱昌照有所指示,如1932年6月24日电钱指示演讲题目:
蒋本人对此一机构的筹备也极为重视,曾多次致电钱昌照有所指示,如1932年6月24日电钱指示演讲题目:
设计会开会时间不必过速,当先物色人才,宜多备约谈时间,然后再定期召集会议,则更能见效,请与咏霓(翁文灏)兄先确定人选,再约定次序,请其各个来谈。兄与咏霓兄能于暑假时来汉、浔常住一处,以便接洽。前约王雪艇(世杰)、周鲠生诸兄所讲题目为何,请电告。兹再列举项目如下:一、教育则讲制度与方针,二、经济则分土地、币制、财政、金融、交通、工业、农产七项,三、外交则分对租界抵制之方略、外债整理之方针、对治外法权与外军驻防之抵制法等四项,四、内政则分人口、粮食、土地等之调查与整理,以及各省警察、民团之制度等项,五、法治则分审计制度、铨叙制度、合作制度、劳动保险制、养老抚恤制、民法、刑法、工厂法,营业、所得、遗产、累进等税项之改正与确定等,而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二原则之实现步骤与方略当为以后研究中心理论之焦点,如有友人愿任此作者,当不厌其详悉也。请将以上各项,择各人之所长分配讲题,陆续请来讲解。

同日又电钱指示设计会人事安排原则,并推荐人选:
调查处长与各组主任,不妨假定多名以备慎选,凡假定之人选,均需先约其来行营详谈数次,方得决定,故不必预告其任何职也。杭州徐青甫先生与前国府参事刘冕先生为研究币制与经济之人,亦请代我与之讨论,观其实在有能力否,并请徐君来汉一叙。

经过一年左右的筹备,国防设计委员会于1932年11月1日正式成立于南京。依《国防设计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国防设计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参谋本部,职权包括:
(1)拟制全国国防之具体方案;
(2)计划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事业;
(3)筹拟关于国防之临时处置。

由蒋介石兼任委员长,翁文灏任秘书长,钱昌照任副秘书长。国防设计委员会设委员36—48人,蒋介石所聘委员大多为钱昌照所建议者,蒋仅增列林蔚(时任侍从室主任)1人。在委员之外,又先后聘请了200名左右的专门委员,均为各方面的技术专家,并按专业予以区分,其中国际贸易专门委员会委员有孙拯、孙景萃、吴申伯等;电气专门委员会委员有王崇植、朱其清、恽震等;国防军备专门委员会委员有王守竟、洪中、吴光杰等;国防化学专门委员会委员有吴承洛、范旭东、林继庸等;矿冶专门委员会委员有李四光、金开英、孙越崎、刘厚生等;边疆研究专门委员会委员有向达、竺可桢、张其昀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的名单中,包括有一些著名的企业家,如范旭东、吴蕴初、刘鸿生等。设计会经由这些企业家,得以了解企业界的需求,吸取其经验与建议;这些企业家也得以增加接近国民政府高层人事的机会,有利于日后反映企业的意见并争取政策性的优惠措施。

国防设计委员会所聘委员,大多为钱昌照所推荐,蒋介石仅增加一位贴身军事参谋林蔚(目的应为俾使就近随时掌握该会状况),自然是表示对钱昌照的尊重。其实蒋介石在此时求贤若渴,心中也有若干人选,如1932年6月20日他即曾在日记中盘点各领域的人才:
经济:马寅初、刘振东、翁文灏、俞大维。
内政:张群、杨永泰、谷正伦、蒋伯诚、朱世明、何浩若。
外交:余日章、斐复恒、程沧波、周鲠生、徐谟。
法律:王世杰。
教育:戴季陶、朱家骅、蒋梦麟、钱昌照、罗家伦。

本章在一开始所引蒋介石6月22、24两日的日记更直接列举了一些拟与派职的名单。历史的“后见之明”显示,钱昌照所推荐的委员名单虽然均为一时之选,但是如果将其与蒋心目中的人才名单加以比对,即使扣除钱昌照所有意避免的孔宋系统和CC系统,仍有一些遗珠之憾,马寅初即一个例子。
马寅初(1882—1982),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1915年返国后即先后任教北大、中大,在经济学界的辈分极高。1930年代初期马寅初倡导统制经济,蒋介石曾多次邀请其讲国际经济大势,听完甚至还有“乐甚”的记载,
 1932年并不止一次将他列入拟用的人才名单,钱昌照推荐的名单中也有他,但是蒋认为他态度傲慢,将他从名单上去除,于是财经方面的委员最后出线的是钱昌照心目中的“中国三大银行家”——张嘉璈、吴鼎昌、徐新六
1932年并不止一次将他列入拟用的人才名单,钱昌照推荐的名单中也有他,但是蒋认为他态度傲慢,将他从名单上去除,于是财经方面的委员最后出线的是钱昌照心目中的“中国三大银行家”——张嘉璈、吴鼎昌、徐新六
 和他的连襟陶孟和等人。
和他的连襟陶孟和等人。
国防设计委员会会址设于南京三元巷二号,对外保密,不悬招牌,信封只印“三元巷二号”。经费方面,每月的经常费10万元(当时拥有10个研究所的中央研究院,每月的经常费也不过10万元)
 ,蒋介石由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特别费内开支,无需向审计机关报销。该会发给委员每月200元、专门委员100元作为研究费用,十分礼遇(根据1933年一位学者陈东原所做比较,当时一个部长,每天能有30—40元收入,政府机关的书记,每月只有30—40元,乡村小学教师,则每年仅有30—40元)。
,蒋介石由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特别费内开支,无需向审计机关报销。该会发给委员每月200元、专门委员100元作为研究费用,十分礼遇(根据1933年一位学者陈东原所做比较,当时一个部长,每天能有30—40元收入,政府机关的书记,每月只有30—40元,乡村小学教师,则每年仅有30—40元)。
 另资助14所著名大专院校和北平地质调查所、北平社会调查所,按期给予补助。
另资助14所著名大专院校和北平地质调查所、北平社会调查所,按期给予补助。
 蒋介石对于设计委员会和学术界的合作和联系,特别重视,常亲予指示。如1933年8月在接见蒋廷黻及何廉后,即致电钱昌照,请其介绍蒋、何二人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要求他们对于县政及社会地方组织的调查,切实合作共同研究,各种调查助手的训练也可互相调剂。并要求设计会日后应与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以及上海的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切实合作联络。同济大学拟开办兽医班,经费不足,也准由设计会酌量补助,以促其成。
蒋介石对于设计委员会和学术界的合作和联系,特别重视,常亲予指示。如1933年8月在接见蒋廷黻及何廉后,即致电钱昌照,请其介绍蒋、何二人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要求他们对于县政及社会地方组织的调查,切实合作共同研究,各种调查助手的训练也可互相调剂。并要求设计会日后应与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以及上海的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切实合作联络。同济大学拟开办兽医班,经费不足,也准由设计会酌量补助,以促其成。
 在人员进用方面,设计会在专门委员之下设助理研究员和练习员,均由接受该会补助的14所院校毕业生择优录用,月薪80元,较一般行政机构高20元,颇有助于人才的引进。
在人员进用方面,设计会在专门委员之下设助理研究员和练习员,均由接受该会补助的14所院校毕业生择优录用,月薪80元,较一般行政机构高20元,颇有助于人才的引进。

国防设计委员会和学术机构的密切合作,也是和汪兆铭进行人才争夺战的一部分。改组派对国民党员的任用与协调,由汪兆铭自己主持,对知识界的联络,则由顾孟余主持。汪任行政院院长时,顾任铁道部部长,手中拥有资源可资利用。例如1932年朱家骅于教育部部长任内拟设国立编译馆,但经费不足,经顾孟余同意,每月补助5000元,始获准成立。
 又如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费有限,除从事社会调查外,甚至无法负担订阅大量报刊及剪报所需人事费用,副所长陈翰笙(所长为院长蔡元培自兼)乃向在北大任教时的旧识顾孟余求助。顾乃聘陈为铁道部顾问,每月致酬400元。陈乃将此笔钱雇了4人剪报,每人月薪30元,剩余的钱均用于订购报刊。
又如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费有限,除从事社会调查外,甚至无法负担订阅大量报刊及剪报所需人事费用,副所长陈翰笙(所长为院长蔡元培自兼)乃向在北大任教时的旧识顾孟余求助。顾乃聘陈为铁道部顾问,每月致酬400元。陈乃将此笔钱雇了4人剪报,每人月薪30元,剩余的钱均用于订购报刊。
 陈翰笙又欲介绍数个研究生至铁道部工作,顾则表示铁道部正值裁员,无法安插,但可委托陈调查京沪铁路沿线及江苏全省经济情况,作为铁道部改良旧路及筹建新路的参考,每月补助5000元,如社科所的人力充足,调查范围能扩及浙赣路,补助尚可增加。陈翰笙大喜而去。此举并非仅为汪兆铭联络学界的手段,顾孟余也确有发展铁路的抱负。新上任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闻讯,也来请助。
陈翰笙又欲介绍数个研究生至铁道部工作,顾则表示铁道部正值裁员,无法安插,但可委托陈调查京沪铁路沿线及江苏全省经济情况,作为铁道部改良旧路及筹建新路的参考,每月补助5000元,如社科所的人力充足,调查范围能扩及浙赣路,补助尚可增加。陈翰笙大喜而去。此举并非仅为汪兆铭联络学界的手段,顾孟余也确有发展铁路的抱负。新上任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闻讯,也来请助。
 罗家伦由于党政关系良好,经费并不虞匮乏,在各国立大学中,仅次于中山大学。
罗家伦由于党政关系良好,经费并不虞匮乏,在各国立大学中,仅次于中山大学。
 不过顾孟余以罗家伦原为北大学生,仍按月助以10000元。对于新成立不久的武汉大学,知名教授为王星拱、周鲠生、石瑛、皮宗石、杨端六、刘秉麟等,早已亲汪、顾,顾则主动请武大调查平汉铁路沿线及北方各省的物产及生产潜力,并请其工学院(院长石瑛)特别研究铁路建筑工程,按月补助经费5万元。
不过顾孟余以罗家伦原为北大学生,仍按月助以10000元。对于新成立不久的武汉大学,知名教授为王星拱、周鲠生、石瑛、皮宗石、杨端六、刘秉麟等,早已亲汪、顾,顾则主动请武大调查平汉铁路沿线及北方各省的物产及生产潜力,并请其工学院(院长石瑛)特别研究铁路建筑工程,按月补助经费5万元。

1932年11月1日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后,依照条例规定和工作计划展开工作。但是制定国防计划既非仓率可期,也非既有财力、人力所能胜任,仅能先从调查研究开始入手。翁文灏系著名的地质学者,自清末起即在各地进行地质调查工作,自然极力强调调查研究在制定计划时的重要性。1932年6月,翁曾在《建设与计划》一文中对当时各种距离事实甚远的计划大加抨击:
计划的必要中国现在大约已普遍承认的了,所以近几年来虽然没有多大建设,却天天可听见许多计划。但是计划的内容往往离事实甚远,所以一经实行便即失败……至今常常听见许多离开事实的大计划,例如山西尺许厚的褐铁矿,四川几寸厚的菱铁矿,以及蒙古沙漠边上,都可以树立中国钢铁业的大中心。而听者似乎并不觉得奇怪。

因此,国防设计委员会自筹备阶段起,即特别重视调查研究。该会为了了解既有及现在进行中的研究,以避免重复,并发掘人才,特别设计了“国防设计问卷”
 发给各专门委员,国防设计委员会再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将亟待研究的计划,分为军事、国际关系、经济与财政、原料与制造运输与交通、文化、土地与粮食等组,分组进行调查和规划,后由设计会汇整制订总的国防计划。各组调查及研究情形分述如下:
发给各专门委员,国防设计委员会再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将亟待研究的计划,分为军事、国际关系、经济与财政、原料与制造运输与交通、文化、土地与粮食等组,分组进行调查和规划,后由设计会汇整制订总的国防计划。各组调查及研究情形分述如下:
(一)军事组:为应付日本的侵略,在军事上、兵工生产上应做何种准备,甚至各地要塞兵营的建筑,江防、海防、空防的设备,军、民用航空建设,均在调查范围之内。但是实际上,军事委员会和参谋本部另有专门机构从事军事方面的计划工作,设计会难以插手。因此军事组的工作远未如计划所要求的广泛。该组研究了有关国防统计的分类和资料收集方法,设计了64种调查表格,分别函请主管机关填送,以求了解当时国内军事情况,但并无结果。此外,军事组曾和其他机关合作,拟定《国防军事建设计划》《国防军备十年计划》《国防航空五年计划》《兵工整理计划》等。原由陈仪主持,但他未参加实际工作,而由洪中、庄权、杨继曾等负责。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洪中(1882—1961)。洪中为著名的兵工专家,曾任河南巩县兵工厂厂长、汉阳钢铁厂厂长、沈阳兵工厂之化学兵器厂及火药厂厂长,九一八事变后离开东北,任军政部兵工署副署长。翌年其升任署长,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洪中(1882—1961)。洪中为著名的兵工专家,曾任河南巩县兵工厂厂长、汉阳钢铁厂厂长、沈阳兵工厂之化学兵器厂及火药厂厂长,九一八事变后离开东北,任军政部兵工署副署长。翌年其升任署长,
 并兼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1932年,蒋介石接受陈仪建议,欲任俞大维为兵工署署长
并兼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1932年,蒋介石接受陈仪建议,欲任俞大维为兵工署署长
 ,钱昌照乃将洪中改聘为国防设计委员会驻会专任委员(也是唯一的驻会委员),主持军事组,负责钢铁工
,钱昌照乃将洪中改聘为国防设计委员会驻会专任委员(也是唯一的驻会委员),主持军事组,负责钢铁工
 业的规划,并主持“低温蒸馏”的试验,从含挥发成分较高的煤炭提取轻油,以解决一旦海岸遭受封锁后的燃料问题。
业的规划,并主持“低温蒸馏”的试验,从含挥发成分较高的煤炭提取轻油,以解决一旦海岸遭受封锁后的燃料问题。

(二)国际关系组:重点集中于日本、苏联和美国,特别是有关日本的资源状况、国内政治局势及其对华政策。研究了日本、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在华利益,尤其是在经济与文化领域的利益,同时聘请一些旅欧华裔学者撰写《欧洲国际关系报告》。该组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为派员至关外秘密调查伪满洲国成立后的动态,收集整理有关新疆、西藏、蒙古及西南边疆地区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人文经济状况等资料,并进行研究,由王世杰主持,周鲠生、徐淑希、钱端升等人负责。
 值得注意的是,周、徐、钱3位固然均为知名学者,该组其余成员日后有些成为国民政府外交方面的骨干(如徐道邻、李惟果、徐公肃、袁道丰),有些则当了汪伪政府的汉奸(如吴颂皋、高宗武和周隆庠)。
值得注意的是,周、徐、钱3位固然均为知名学者,该组其余成员日后有些成为国民政府外交方面的骨干(如徐道邻、李惟果、徐公肃、袁道丰),有些则当了汪伪政府的汉奸(如吴颂皋、高宗武和周隆庠)。

(三)经济与财政组:该组的任务包括两项:一是研究平时财政收入如何能尽量满足国防需要,以及战时关税、盐税、统税等主要税收如丧失后,如何弥补而不致造成通货膨胀的办法;二是估计全国人口总数,确定粮食供需平衡的办法,研究各种必需物资的替代、补充、购买,以及限制国防必需物资的输出、奖励输入的办法,并配合其他各组制定粮食管理计划、工业动员计划及战时金融统制办法等。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几项:
1.参与币制改革
1932年,中国受到世界经济危机恐慌的影响,经济开始陷入萧条。1934年6月,美国政府颁布《购银法案》(Sliver Purchase Act of 1934),高价收购白银,致使国际市场银价高涨,在华外商银行纷纷将白银装运出国,投机牟利。中国当时以白银为货币本位,白银大量外流,造成国内银根紧缩,出现白银挤兑现象,部分银行、钱庄倒闭,因此币制改革的工作成为当务之急。1935—1936年的法币改革为民国史上的一件大事,因此相关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
 ,晚近有学者开始留意蒋介石货币改革的决策过程
,晚近有学者开始留意蒋介石货币改革的决策过程
 ,不过每多忽略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此处拟稍做补充。
,不过每多忽略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此处拟稍做补充。
国防设计委员会在成立之初,即着手研究币制改革,由孙拯主持,多方收集资料。
 1934年3月3日,蒋介石决定以设计会对币制统一制定实施计划。
1934年3月3日,蒋介石决定以设计会对币制统一制定实施计划。
 钱昌照与宋子文商议,请徐新六和顾翊群两位金融专家协助,获宋同意。
钱昌照与宋子文商议,请徐新六和顾翊群两位金融专家协助,获宋同意。
 自此,徐、顾二人成为设计会经济与财政组主要成员,参与策划币制改革。徐新六为著名的银行家,1908年曾与翁文灏同船赴欧留学,长期担任浙江兴业银行(民初与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并称“南三行”)总经理。
自此,徐、顾二人成为设计会经济与财政组主要成员,参与策划币制改革。徐新六为著名的银行家,1908年曾与翁文灏同船赴欧留学,长期担任浙江兴业银行(民初与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并称“南三行”)总经理。

顾翊群,江苏淮安人,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文学硕士及纽约大学商业行政管理硕士,返国后历任中华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财务秘书、财政部币制委员会委员、上海中孚银行副经理。
 1933年8月,顾翊群向蒋介石上陈《中国货币金融政策草案》,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签注意见为:“顾君为国内研究经济之有名学者,所拟货币金融政策确有商榷之价值,非普同条陈可此。请阅全文,如认为诚有可采之处,可抄交庸之[孔祥熙]、总裁、子文部长,并另行指定数人切实讨论,再行具签呈核。”获蒋介石批交宋、孔采阅。
1933年8月,顾翊群向蒋介石上陈《中国货币金融政策草案》,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签注意见为:“顾君为国内研究经济之有名学者,所拟货币金融政策确有商榷之价值,非普同条陈可此。请阅全文,如认为诚有可采之处,可抄交庸之[孔祥熙]、总裁、子文部长,并另行指定数人切实讨论,再行具签呈核。”获蒋介石批交宋、孔采阅。
 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后,顾氏获钱昌照之邀,聘为专门委员。1934年春,顾翊群由全国经济委员会派赴欧洲研究关税币制,行前钱昌照安排其赴南昌进谒蒋介石。
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后,顾氏获钱昌照之邀,聘为专门委员。1934年春,顾翊群由全国经济委员会派赴欧洲研究关税币制,行前钱昌照安排其赴南昌进谒蒋介石。

顾翊群出国期间曾历访国际联盟财经处,英、法、德、美各国中央银行,考察其制度与业务,为期一年,其间与钱昌照来往函电不断。
 顾返国后,奉派任行政院参事,并参加与英派遣李滋罗斯代表团(Leith-Ross Mission)来华的联系工作。
顾返国后,奉派任行政院参事,并参加与英派遣李滋罗斯代表团(Leith-Ross Mission)来华的联系工作。

另一方面,蒋介石也责成法币改革的权责机关财政部着手研拟改革的具体办法。1935年1月17日,蒋介石上午接见财政部钱币司司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随即又接见上海银行业代表,听取业者对改革看法,下午商议统制金融与币制办法。

1935年9月,由英国政府所派遣的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Frederick Leith-Ross)来华,协助中国解决币制与财政问题。同行者还包括英国财政部的霍尔帕奇(Edmund Hall-Patch)和英格兰银行(the Bank of England)的罗杰斯(Cyril Rogers)。3人9月21日抵华后,顾翊群(时任行政院参事)已将财政部所拟,且经蒋介石审阅的法币改革实施办法6条备妥。
 每周一至周六,由徐新六、顾逸群、罗杰斯和霍尔帕奇4人整理资料,周日则由宋子文、钱昌照、李滋罗斯和徐新六4位助手一起商量,如此一共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方将币制改革方案确定。双方商定新货币与英镑折算方式。由于国民政府的力量尚无法及于全国,东北、云南、西藏、新疆仅能暂不实施。
每周一至周六,由徐新六、顾逸群、罗杰斯和霍尔帕奇4人整理资料,周日则由宋子文、钱昌照、李滋罗斯和徐新六4位助手一起商量,如此一共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方将币制改革方案确定。双方商定新货币与英镑折算方式。由于国民政府的力量尚无法及于全国,东北、云南、西藏、新疆仅能暂不实施。

11月3日,财政部公布《紧急安定货币金融办法》,即通称的“法币政策”,主要内容如下:
(1)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司款项之收复,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罪处治。
(2)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仍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即以截至11月3日止流通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酌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钞票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印未发之新钞及已收回之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其核准印制中之新钞,并俟印就时一并照交保管。
(3)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而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
(4)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司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类者,应自11月4日起,亦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除银本位币按照面额兑换法币外,其余银类各依实含纯银数量兑换。
(5)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6)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同时,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发表由顾翊群草拟的宣言,指出国际银价提高后对中国经济所造成的损害,并声明政府于实施新货币政策后,谋求维护币信、整理财政与恢复经济繁荣的决心。

财政部所公布的法币政策六条办法,为钱币司司长徐堪所拟,根据徐事后的回忆,李滋罗斯抵华后,孔祥熙“即以所拟法币办法六条征询意见,完全赞同,并无一字修改,旋即于11月4日公布实施”。
 但是事实上,国内财经学者在1934年至1935年间对于法币政策的理论及执行,均有极多的讨论,可说朝野上下均已具共识,绝非徐堪一人所能独揽其功。
但是事实上,国内财经学者在1934年至1935年间对于法币政策的理论及执行,均有极多的讨论,可说朝野上下均已具共识,绝非徐堪一人所能独揽其功。

此外,国防设计委员会自成立之初即已着手研究币制改革,由于英国对孔祥熙不信任,蒋介石乃将此事交由宋子文主持,并以钱昌照为副手。钱又邀顾翊群、徐新六两人协助。因此设计会在币制改革过程中,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自此,宋子文和钱昌照的关系日益密切,对资委会的事业也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
。
2.编制国内外贸易统计
设计会有鉴于中国国际贸易逆差不断增大,国际收支状况日趋恶劣,为研究挽救之道,首先需查明历年来国内外贸易情形。该组根据海关铁路运输的详细统计,逐国逐货编制了各铁路及各口岸间重要物资流通状况统计,作为有关部门改定税则、修改商约的参考。
 巫宝三所著《中国粮食对外贸易——其地位趋势及变迁之原因(1912—1931)》
巫宝三所著《中国粮食对外贸易——其地位趋势及变迁之原因(1912—1931)》
 一书,即为社会调查所接受设计会委托调查案下的部分成果。
一书,即为社会调查所接受设计会委托调查案下的部分成果。
3.调查各省财政制度与现状
设计会为明了全国财政收支状况,曾派员赴长江流域的湘鄂赣皖江浙6省、华北的豫晋秦绥察冀鲁7省,实地调查各地财政制度与现状。当时国民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大部分集中于沿海地区,设计会考虑到战争爆发后沿海地区可能被占,需以地方税收加以补充。因此除调查外,还研究了改进田赋和营业税(地方税收大宗)的方法,以备不时之需。

(四)原料及制造组:该组与地质调查所、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合作,对中国的矿业和工业进行了广泛的调查。
1.矿业调查
矿业资源调查的范围,包括煤矿、金属矿和石油矿。煤矿调查分为两路,一路调查沿铁路和长江现有煤矿生产运销状况,作为战时实施燃料统制的准备;另一路调查在内地发展工矿事业需加开采或扩充的煤矿,如江西的萍乡、天河、高坑等矿,湖南的谭家山煤矿。
金属矿调查包括青海、四川的金矿;长江流域及山东、福建等省的银矿;湖北、河南、山西、四川、云南的铜矿;广西的铅、锌矿;湖南、江西的锡、钨、锰矿;云南的锡、钨、锑矿;浙江的矾土矿等。其中大部分拟定了开采计划。
石油矿调查包括四川、陕西的油田调查。设计会于成立之初,鉴于石油资源在国防上的重要,曾委托中央地质调查所派王竹泉、潘钟祥至陕北一带做地质调查,并于1933年组织陕西油矿探勘处,由孙越崎率领,赴陕西延长地区实地钻探。探勘处利用原美孚石油公司于民国初年在此探勘时留下的部分机械,觅地钻井。所钻各井均曾出油,但产量甚少,难以大量开采。后来该地区为红军占领,石油矿成为陕甘宁地区的一项重要经济事业。

2.工业调查
由设计会委托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进行全国性的工业调查。中国经济学社1931年获得太平洋国际学会捐款,成立研究委员会,由刘大钧主持,曾对上海1600余家工厂进行调查。1932年又接受国防设计委员会委托调查全国工业,乃与中国统计学社合作,成立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对全国2400余家工厂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由刘大钧编为《中国工业调查报告》
调查结果由刘大钧编为《中国工业调查报告》
 一书出版。由于受到现实环境的限制,调查人员未能对外资企业进行调查,边境各省及日本占领下的东北工厂也未列为调查对象,兵工厂由设计会另派员调查,造币厂被列为非工业性质,均不在此次调查之列。除此之外,刘大钧几乎对所有符合工厂法的华资工厂均进行了调查,调查范围之广,结果之准确,为当时其他工业普查所无法企及,日后关于民国时期工业总产值的两项研究——巫宝三等人的《中国国民所得》(1947)和刘大中、叶孔嘉的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National Inco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33-1959 (1965)也均系依据《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的数字为基础进行估算。
一书出版。由于受到现实环境的限制,调查人员未能对外资企业进行调查,边境各省及日本占领下的东北工厂也未列为调查对象,兵工厂由设计会另派员调查,造币厂被列为非工业性质,均不在此次调查之列。除此之外,刘大钧几乎对所有符合工厂法的华资工厂均进行了调查,调查范围之广,结果之准确,为当时其他工业普查所无法企及,日后关于民国时期工业总产值的两项研究——巫宝三等人的《中国国民所得》(1947)和刘大中、叶孔嘉的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National Inco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33-1959 (1965)也均系依据《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的数字为基础进行估算。

(五)交通及运输组:该组工作分为铁路、公路、航运、电讯4部分。铁路方面,由顾振负责,重点在掌握各路设备、军运能力及应予改进之处,并编制《全国铁路军事运输能力审查报告》。公路方面,由陈伯庄负责,注重调查华中七省并推及华南、华北各省公路通车情形、汽车辆数、汽车修理厂及其能力。航运方面,由王洸负责,调查水道、船舶、港口设备、引水人员等状况。电讯方面,由朱其清、陈绍霖负责,调查全国无线电台、有线电报、电话、电讯材料、人才等状况,并草拟有器材储备制造,以及紧急时期国内重要电工器材厂迁移计划。

该组成员和其他各组不同,较少学者,而以交通界人士为主。例如负责航运的王洸,即出身交通世家,其父王倬为留日学生,长期任职于北洋政府交通部航政司,曾主编《交通部月刊》和《交通史航政篇》。王洸,1906年生,就读北平交大管理科时即曾与同学创办《苏光》(季刊),后改名《交通经济汇刊》,毕业后入交通部,曾自费创办《交通杂志》(月刊),发行数陆续增至5000份,渐有文名。1933年获钱昌照之邀,入设计会主持航政工作,专门规划航政、航业和造船工作。钱表示该会各组主持人均以委员名义兼领组务,但王无国外大学学位,故仅能以助理研究员名义任用,不过得支领此职等最高薪180元。王洸日后两度奉派出国,成为著名的航运专家,曾历任交通部航政司司长、路政司司长等职。

(六)文化组:研究的内容包括学生体检制度、学校教授法、平民军训、体育教育、民歌及流行歌曲、查禁鸦片及其他用品、医药供给等。该组并负责研究如何为国防建设奠定智能、体能和精神的基础,包括对民族精神和国家观念的培育及对科技知识的推广,也重视研究世界各国训练青年的方式。
 影响较大的工作,则为邀请学者专家撰写中小学教科书,如杨振声、朱自清编国语教科书,张其昀编地理教科书,张荫麟编历史教科书。
影响较大的工作,则为邀请学者专家撰写中小学教科书,如杨振声、朱自清编国语教科书,张其昀编地理教科书,张荫麟编历史教科书。
 蒋介石对此事十分重视,尤其是对修身课本,甚至曾亲电翁文灏和钱昌照指示编写原则,
蒋介石对此事十分重视,尤其是对修身课本,甚至曾亲电翁文灏和钱昌照指示编写原则,
 不过最后是否编成,不得而知。此处拟就各科教科书编纂经过,略做介绍。
不过最后是否编成,不得而知。此处拟就各科教科书编纂经过,略做介绍。
1.国语科
国文科负责人原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杨于1933年夏邀沈从文合作,1934年12月沈又拉朱自清加入。1936年,由杨振声主编,沈从文、朱自清协助的《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以国立编译馆的名义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书店联合出版。随后他们继续合作撰写《中学国文教科书》,于1940年交稿,不过国立编译馆以此书稿质量虽佳,但不合学校使用,尤其不合抗战期间使用之故,弃置未用。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朱自清在编教科书的过程中,于文章注释外,又旁参博考,做了若干国学要籍的提要和说明,最后成为名著《经典常谈》的底本。

2.历史科
历史科负责人,钱昌照原想请傅斯年担任,傅分不开身,乃推荐张荫麟自代。张在美留学期间,即已有撰写通史之志,遂答应此事。为了专心写作,张甚至向清华请了长假,花了两年时间于1937年完成高小教科书。
 此书虽然预备作为课本使用,但是张荫麟希望它能成为一般儿童的读物,故原名《儿童中国史》。根据张荫麟所写的《自序》,《儿童中国史》一书的书名系仿英国文豪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1853—1854年所出版《儿童英国史》(A Child's History of England),文体也有意模仿,但是取材的标准则大为不同,张荫麟选择中国自古至今具有代表性的30个历史人物为中心进行书写,只有最后一章以叙述淞沪之战收尾。此章由负责近现代史部分的助手杨联陞撰写长编,杨查考一切可得的史料,反复考虑后,决以蒋介石为中心书写,未获张同意,仍仅叙事而不叙人,为全书中唯一的变例。张的理由为:“若夫表扬当路者之德言功业,以起信于童蒙,则就课程之编配言,宜入党义之科;就著作之分工言,宜别选和声鸣盛之能手。”
此书虽然预备作为课本使用,但是张荫麟希望它能成为一般儿童的读物,故原名《儿童中国史》。根据张荫麟所写的《自序》,《儿童中国史》一书的书名系仿英国文豪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1853—1854年所出版《儿童英国史》(A Child's History of England),文体也有意模仿,但是取材的标准则大为不同,张荫麟选择中国自古至今具有代表性的30个历史人物为中心进行书写,只有最后一章以叙述淞沪之战收尾。此章由负责近现代史部分的助手杨联陞撰写长编,杨查考一切可得的史料,反复考虑后,决以蒋介石为中心书写,未获张同意,仍仅叙事而不叙人,为全书中唯一的变例。张的理由为:“若夫表扬当路者之德言功业,以起信于童蒙,则就课程之编配言,宜入党义之科;就著作之分工言,宜别选和声鸣盛之能手。”
 抗战期间,张荫麟出版《中国史纲》一书,在自序中他将起草此书的时间上溯至接受国防设计委员会之聘的1935年,在感谢的名单中他首先感谢的,即邀请他写此书的傅斯年和钱昌照。
抗战期间,张荫麟出版《中国史纲》一书,在自序中他将起草此书的时间上溯至接受国防设计委员会之聘的1935年,在感谢的名单中他首先感谢的,即邀请他写此书的傅斯年和钱昌照。

文化组所策划编写的教科书,虽然最后未获采用,但是毕竟催生出一些经典的作品,因此长期来看,并不能算是失效,其原因在于设计会能够聘请到一批新锐学者,在待遇上和时间上能够给予优渥的支持。

(七)土地及粮食组:主要任务为调查全国粮食的生产、运输、市场供应状况,拟制粮食储备计划和战时粮食统制的办法。至于人口和土地,由于范围极广,且另有专门机构负责,设计会仅就最重要而其他机构未曾兴办的项目试行创办,其中最重要者包括江苏句容县人口状况、土地调查,江苏武进、南通及浙江22县田赋调查,以及华中六省粮食运销状况等,并在各大城市建立定期报告制度,由设计会提供经费,委托金陵大学进行农村调查工作,金大教授谢家声、钱天鹤等人参与。
 部分调查报告并曾正式出版,至今仍经常为学者所引用。
部分调查报告并曾正式出版,至今仍经常为学者所引用。

粮食方面自为该组重心所在,系由曲直生负责。曲原为中央政治学校教授,1942年应陶孟和之邀,任设计会专员,研究全国粮食,在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为了了解各地民众的主要食料,曾以通讯方式向全国各县政府征求答案。由于华北各县回复情况较佳,即先整理成《华北民众食料的一个初步研究》一书出版。
 此书打破过去一般人所认为“南人食米,北人食麦”的粗浅概念,指出“南人食米”一句大致正确,因为除了华南山地间有吃杂粮的地方,90%的南方人均吃米。但是“北人食麦”一句话则跟事实相去甚远。据曲直生的调查,华北各省的食料,因地域及出产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如东北各省、热河与河北省天津以东的县,大致均以高粱为主要食粮;绥远、察哈尔两省,以糜子及燕麦为主;河北全省及山东、山西、河南一部分,以粟为主;山东则间有高粱;河南以吃麦为主;山西南部、陕西及甘肃,以小麦为主食;宁夏吃米者也占相当的比例;青海则吃青稞。由于此书系根据调查数据写成,学术价值甚高,至今仍经常为学界所引用。
此书打破过去一般人所认为“南人食米,北人食麦”的粗浅概念,指出“南人食米”一句大致正确,因为除了华南山地间有吃杂粮的地方,90%的南方人均吃米。但是“北人食麦”一句话则跟事实相去甚远。据曲直生的调查,华北各省的食料,因地域及出产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如东北各省、热河与河北省天津以东的县,大致均以高粱为主要食粮;绥远、察哈尔两省,以糜子及燕麦为主;河北全省及山东、山西、河南一部分,以粟为主;山东则间有高粱;河南以吃麦为主;山西南部、陕西及甘肃,以小麦为主食;宁夏吃米者也占相当的比例;青海则吃青稞。由于此书系根据调查数据写成,学术价值甚高,至今仍经常为学界所引用。

(八)专门人才调查:设计会成立未久,即将专门人才调查列为国防资源调查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设立了专门人才委员会,杨公兆负责,其任务为调查并组织全国专门人才,以取得有效联络。1934年起,专门人才委员会制定了各种调查表格,向全国文教、经济等机关团体和公私厂矿广为分发,调查范围除技术人才外,旁及一般专门人才,先后动员10余人,花费3年多时间,共征得调查表约8万份,其中约有2.5万份为工程技术人员所填,当时先将矿冶及机械两门予以整理并参附统计,编印《全国专门人才调查报告》二巨册,不幸印刷甫竣,即匆促迁移,仅有一份随同卷宗迁渝。
 所幸其调查原卷关于工程部分,尚获保全,后由资委会技术室整编为《中国工程人名录(第一回)》(1941)一种,共收录2万余人,以供各方网罗人才参考。
所幸其调查原卷关于工程部分,尚获保全,后由资委会技术室整编为《中国工程人名录(第一回)》(1941)一种,共收录2万余人,以供各方网罗人才参考。
 虽然此书迟至1941年才出版,但是设计会早期征集约8万份的调查表,在规划全国专门人才总动员时,即曾发挥极大功能。
虽然此书迟至1941年才出版,但是设计会早期征集约8万份的调查表,在规划全国专门人才总动员时,即曾发挥极大功能。
 该会早期从事工矿建设所需要的技术、管理人员,许多即系据此招募而来。
该会早期从事工矿建设所需要的技术、管理人员,许多即系据此招募而来。

除以上各类调查外,设计会尚有对特殊区域的全面调查。西北、西南两区,战前朝野即已公认为抗战最后根据地,设计会成立未久,即组织西北调查团,分为5组,分任水利测量、地质矿产、垦牧及民族、农作物及移垦、人文地理5项。西北调查团主其事者,均为当时的新锐学者,如主持农业考察者为金陵大学教授沈宗瀚,他邀请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教授汤惠荪、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雷力田,分任土地、农业调查之责。参与的学者尚包括北平地质调查所的土壤专家梭朴(James Thorp)和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卜凯(John Lossing Buck)。考察结束后沈宗瀚向设计会提交名为《西北农村急宜救济的几件大事》的调查报告,建议:“全国经济委员会对西北之交通、水利、兽医、卫生等正在建设之中,自属要举,惟尚有四事为救济西北当前急务:(1)连年兵灾匪祸,苛税繁重,甘肃农民相率弃田西逃,以致耕地荒芜。中央应加派良好军队驻凉州、甘州、肃州及宁夏,以安定社会,厉行招徕,奖民复业。(2)禁止种吸鸦片,在甘肃可增产美国烟叶与小麦(蓝麦最好),陕西可增植棉花。(3)栽草种树掩护童山。(4)团结汉、回、蒙、藏四民族,防免俄、日、英、土的离间。”

另一个例子是主持人文地理调查的张其昀(1901—1985)。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张其昀1932年应翁文灏之邀,入国防设计委员会任专门委员,当时虽然只有31岁,但是他于1928年所编高中《本国地理》教科书,至1932年底已发行共17版,
 此书和林语堂所编《开明英文第一读本》、戴运轨所编《开明物理学教本》当时被誉为中国三大中学教科书。
此书和林语堂所编《开明英文第一读本》、戴运轨所编《开明物理学教本》当时被誉为中国三大中学教科书。
 1934年9月,张其昀率领中央大学毕业生林文英、李玉林、任美锷3人,赴西北调查人文地理,北登阴山,南越秦岭,西至敦煌、阳关,先后几达一年之久。其间曾以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名义在陕西南郑发表《在南郑讲复兴汉中》公开演讲并见诸报端,经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检举向蒋介石举报。蒋介石见到报告后,立即致电翁文灏和钱昌照,除了重申设计会的机密性质,并指示类似错误不得再犯:“近如《华北日报》南郑通讯记载国防设计专门委员张其昀于1月24日以本会委员资格,公开演讲,迹近招摇,殊失检点,应予申戒,希即知照各委员嗣后不得以会内情形或委员资格,擅自对外宣传夸张为要。”
1934年9月,张其昀率领中央大学毕业生林文英、李玉林、任美锷3人,赴西北调查人文地理,北登阴山,南越秦岭,西至敦煌、阳关,先后几达一年之久。其间曾以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名义在陕西南郑发表《在南郑讲复兴汉中》公开演讲并见诸报端,经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检举向蒋介石举报。蒋介石见到报告后,立即致电翁文灏和钱昌照,除了重申设计会的机密性质,并指示类似错误不得再犯:“近如《华北日报》南郑通讯记载国防设计专门委员张其昀于1月24日以本会委员资格,公开演讲,迹近招摇,殊失检点,应予申戒,希即知照各委员嗣后不得以会内情形或委员资格,擅自对外宣传夸张为要。”

事实上,国防设计委员会虽然号称为机密机关,但是保密工作做得甚差,消息经常见诸媒体,
 其中不少新闻报道还是由国民党党营的中央通讯社发布。1933年8月甚至有读者投稿《国防设计委员会存废》一文至《西京日报》(国民党中宣部所办报纸)专门讨论西北开发问题的“建设”版,
其中不少新闻报道还是由国民党党营的中央通讯社发布。1933年8月甚至有读者投稿《国防设计委员会存废》一文至《西京日报》(国民党中宣部所办报纸)专门讨论西北开发问题的“建设”版,
 显示保密工作已形同具文。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媒体上有关设计会的报道,大多为有关该会派员赴各地调查的消息,以该会人员身份做公开演讲者,确不多见,尤其张其昀当时身份仅为“专门委员”,但经媒体报道为“委员”,
显示保密工作已形同具文。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媒体上有关设计会的报道,大多为有关该会派员赴各地调查的消息,以该会人员身份做公开演讲者,确不多见,尤其张其昀当时身份仅为“专门委员”,但经媒体报道为“委员”,
 自然难免“招摇”之嫌。张其昀受此打击,暂时脱离政坛,将事业重心置于学界,是为西北考察团的一段插曲。
自然难免“招摇”之嫌。张其昀受此打击,暂时脱离政坛,将事业重心置于学界,是为西北考察团的一段插曲。

虽然如此,西北考察团由于考察地点路途遥远,交通迟滞,调查时间几达两年之久,整理数据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完成了13项调查报告,其中对于羊毛改进、森林利用与农垦设施,均有具体的计划。不过由于经费不足等原因,这些计划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前,都还停留在纸上作业。
 不过考察团在培育人才上所产生的效果,仍值得注意。当代中国著名的地理学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任美锷(1913—2008)1934年自中央大学的地理系毕业后,在翁文灏介绍下,入国防设计委员会任练习员,协助张其昀工作,曾随张至西北考察人文地理,晚年在回忆此段60多年前的历史时,仍有以下生动的描述:
不过考察团在培育人才上所产生的效果,仍值得注意。当代中国著名的地理学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任美锷(1913—2008)1934年自中央大学的地理系毕业后,在翁文灏介绍下,入国防设计委员会任练习员,协助张其昀工作,曾随张至西北考察人文地理,晚年在回忆此段60多年前的历史时,仍有以下生动的描述:
我在前资源委员会工作两年,其中有一年随晓师[张其昀]到西北进行人文地理考察,这是我一生野外工作永远难忘的一年。我们西至敦煌和阳关,欣赏敦煌的艺术瑰宝,凭吊“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遗迹,西南至甘肃拉卜楞等,领略藏族生活和青藏高原的草原风光,穿越陕甘黄土高原,南望陇山,并乘羊皮筏子在黄河上漂流而下,从兰州经宁夏,直至包头。在兰州与宁夏(今银川市)间亲历黄河峡谷的惊涛骇浪。这一切大大丰富了我的地理知识和人生经历,成为我终生受用不尽的知识来源。例如我最近写的《黄河——我们的母亲河》一书中,还引用一九三五年夏我乘皮筏过兰州与宁夏间黄河峡谷的情景,来说明黄河上游的河势。

设计会所做的各项调查,大多系根据自身的需求而执行,不过也有少数系采纳外界的建议而做,1932年对三峡水利的勘测即为一例。
电气专家恽震与钱昌照为熟识的朋友,1932年时任建设委员会全国电气事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一次谈话中向钱昌照表示有志实地调查勘测长江三峡水利开发的可能性,并研究可建立水电站、水坝的地点,但是建设委员会无意于此项工作,也没有勘测水利的预算。钱昌照则表示国防设计委员会已有人在进行浙、闽一带河流的水利勘测,因此可以协助恽震进行此一最大河流的勘测,所需经费可由设计会支应,所需专家可由设计会以公函借调。恽震于是邀集曹瑞芝、宋希尚、史笃培(C. G. Stoebe)、陈晋模4人组成勘测队,于该年11月5日至23日对长江三峡进行勘测和调查,返京后完成《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报告》和初步开发计划,正本呈送国防设计委员会,副本送请建设委员会和交通部分别备案,宋希尚也以另一副本送呈其服务单位交通部长江水道整治委员会备案,后经钱昌照批准,该报告并刊布于该年中国工程师学会主办的《工程》杂志。
恽震等人在报告中指出,最适合建水电站的地点为葛洲坝和黄陵庙至三斗坪一带。任一处计划如能完成,每年可发电30万千瓦时,利用长江三峡丰富的水电资源,可以固定空气中的氮气,制造化学肥料,发展电气、化学工业,供应川汉铁路用电。如果尚有剩余,则可送电沙市和汉口供工、农业用电。扬子江上游发展至最后时期,自宜昌至宜宾,必有若干水坝、水闸及发电厂相互联属,水面降落各成阶级,届时不但航行的滩险问题可以完全解决,即两岸的农田也可因水位抬高而享灌溉之力,对于建坝后回水淹没地区的经济损失,报告中也做了估计。
 1933年5月3日,交通部对恽震等人所提《长江上游水力发电计划》批复:“所呈计划尚属详明,应予存案备查。”并附了一些修正意见供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参考。全案形同搁置。报告所建议的两个水坝,虽然坝址对日后三峡坝址的确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33年5月3日,交通部对恽震等人所提《长江上游水力发电计划》批复:“所呈计划尚属详明,应予存案备查。”并附了一些修正意见供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参考。全案形同搁置。报告所建议的两个水坝,虽然坝址对日后三峡坝址的确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不过规模较小,均为低坝,与日后所建的高坝不同。
不过规模较小,均为低坝,与日后所建的高坝不同。
根据资源委员会出身之水利专家徐怀云事后的推测,当时未考虑高坝的原因或有以下几种:(1)虽当时美国的著名大坝如胡佛大坝(Hoover Dam)已于1931年开工,但沙斯塔坝(Shasta Dam)和大苦力水坝(Grand Coulee Dam)均尚未兴建,国际间对大坝尚未熟悉,文献也不多。(2)当时国内电力市场有限,长途高压电线系统尚不存在。(3)当时建高坝所需要的精密地形、地质、水文、气象、农作物分布、土壤等资料,尚未健全。(4)当时国内建筑与设计高坝的人才和经费,均尚未具备。

为了减少大型工程对于生态环境和社会的冲击,当代欧美主要国家大多反对兴建高坝,而主张以低坝替代,对于20世纪中国以及第三世界常见的大型水坝,也多持负面看法。

从历史的“后见之明”看来,当时国民政府对于美国高坝大师萨凡奇(John L. Savage)深信不疑,媒体对于此项建国大计及萨氏伟大人格也都大幅报道,
 恽震等本土派专家的规划,自然被国民政府视为“落伍”而不予以考虑。事隔半世纪,恽震晚年在回忆国民政府此段决策过程时,仍感愤愤不平,不过对于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探勘工作则依然予以肯定:
恽震等本土派专家的规划,自然被国民政府视为“落伍”而不予以考虑。事隔半世纪,恽震晚年在回忆国民政府此段决策过程时,仍感愤愤不平,不过对于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探勘工作则依然予以肯定:
鉴于当时国力和工业的薄弱,电力需要不多,明知三峡水利工程开发,其蕴藏的可能性容量,必在1000万千瓦以上,如计划建设高坝和巨型水电站,在当时徒然惊世骇俗,殊无实现之可能,故不如按其常年最低流量,设计造一低坝,长期出力30万千瓦,建设费用每千瓦300元左右。这一设想,实际上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根本不会予以考虑。……该报告[按:系指1933年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探勘报告]的价值,乃在于根据地质、地文资料,在1933年就选定了黄陵庙及三斗坪的建坝地点。美国萨凡奇专家在1944—1945年费了很多时间和力量,却忽视客观上早已存在的数据,故其所选的几个坝址地点,在地质、地形上都不及我们中国人自选的地点。

设计会虽然会接受外界的建议而进行一些调查和研究,不过也会先进行评估,并非是来者不拒。如1934年李煜瀛(石曾)曾透过蒋介石介绍勤工俭学出身的比利时华侨沈宜甲,盼设计会能对其所发明的秘密无线电补助1万元,
 钱昌照则以设计会前后已补助沈宜甲五六千元,现已嘱其早日返国,请蒋介石转告李煜瀛设计会似不需津贴无线电机发明费。
钱昌照则以设计会前后已补助沈宜甲五六千元,现已嘱其早日返国,请蒋介石转告李煜瀛设计会似不需津贴无线电机发明费。
 沈宜甲早期赴法勤工俭学,1928年毕业于法国国立矿冶大学,后定居比利时,从事科学研究,抗战爆发后返回服务,其间曾发明用无烟煤气代替汽油,并于桂林创办无烟煤气机制造厂。
沈宜甲早期赴法勤工俭学,1928年毕业于法国国立矿冶大学,后定居比利时,从事科学研究,抗战爆发后返回服务,其间曾发明用无烟煤气代替汽油,并于桂林创办无烟煤气机制造厂。
设计会各部门的调查与研究,范围虽然广泛,但是由于受到人力和财力的限制,重心仍在国防经济。其中致力较多者,为矿产、水利、工业、交通、运输、财政经济及区域调查等项,除矿产、水利两项技术成分较多外,余均为经济调查研究。

国防设计委员会委托学术机构所做的各项调查,有些在当时虽未对国防产生立即的效益,但是日后却对学术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基会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即为一例。北平社会调查所原名社会调查部,系中基会1926年2月接受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Institute of Social and Religious Research)捐款所成立的调查研究机构,附设于中基会之下,每年另由该会酌量补助,曾出版有《社会调查方法》《中国妇女在法律上之地位》《北京生活状况》《塘沽工人调查》《直隶棉花之贩运》《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中国劳动年鉴》《社会研究月刊》《北平生活费指数》
 等书刊。由于成绩甚佳,中基会在3年期满后,觉得仍有赓续的必要,乃于1929年6月改组为北平社会调查所,其经费全由中基会负担,由陶孟和(原社会调查部秘书)任所长。
等书刊。由于成绩甚佳,中基会在3年期满后,觉得仍有赓续的必要,乃于1929年6月改组为北平社会调查所,其经费全由中基会负担,由陶孟和(原社会调查部秘书)任所长。
 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后,陶孟和由于钱昌照的关系获得该会的资助,得以强化经济问题的研究,全所的研究方向也因此而转变。第一,开始清代经济史的研究。利用故宫档案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刊登于1932年11月创刊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并出版《中国厘金史》等书。第二,重视税制、货币、国民所得等经济议题的研究。相对的,早期工人、劳动问题的社会调查工作,则不再重视。
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后,陶孟和由于钱昌照的关系获得该会的资助,得以强化经济问题的研究,全所的研究方向也因此而转变。第一,开始清代经济史的研究。利用故宫档案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刊登于1932年11月创刊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并出版《中国厘金史》等书。第二,重视税制、货币、国民所得等经济议题的研究。相对的,早期工人、劳动问题的社会调查工作,则不再重视。

而经过近一年半的努力,国防设计委员会各处、组及专门委员会至1934年4月共完成调查报告156项。
 该会并利用此批数据立即加以研究设计,分别拟订方案,逐步实施,重要者包括:
该会并利用此批数据立即加以研究设计,分别拟订方案,逐步实施,重要者包括:
(1)拟定《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以为开始建设的准绳;
(2)《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如战时成立的燃料管理处及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均系本此计划而付诸实施;
(3)全国铁路军事运输能力报告及运输报告,与运输动员及统制初步计划,曾提供主管机关作为重要参考;
(4)粮食存储及统制计划。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后来成为资源委员会“重工业三年计划”重要范本,影响至为深远。
1935年4月1日,设计会与军政部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名为“资源委员会”,并由参谋本部改隶军事委员会。工作范围不局限于调查、研究与设计等工作,更直接从事各项国防工矿事业。资委会成立之初,仍继续从事设计会未完成的调查工作。1935年12月7日,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继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12日,蒋主持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行政院所属各部长官人选:内政部部长蒋作宾、外交部部长张群、交通部部长顾孟余、铁道部部长张嘉璈、实业部部长吴鼎昌、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海军部部长陈绍宽。
 蒋介石另任命翁文灏为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为行政院政务处处长。在此次新任首长名单中,张嘉璈、吴鼎昌、王世杰、翁文灏均为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蒋廷黻虽和设计会无关,但也是钱昌照推荐的,至于CC系成员,则完全无人获选。故当时有人称此次的内阁为“三元巷内阁”,
蒋介石另任命翁文灏为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为行政院政务处处长。在此次新任首长名单中,张嘉璈、吴鼎昌、王世杰、翁文灏均为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蒋廷黻虽和设计会无关,但也是钱昌照推荐的,至于CC系成员,则完全无人获选。故当时有人称此次的内阁为“三元巷内阁”,
 由此显示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养士功能,至此已充分发挥。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调查研究告一段落,遂决定了3个方针:(1) 1936年7月起创办重工业;(2)尽量利用外资;(3)尽量利用外国技术。又在兼顾国防和经济的要求下,根据先前拟订的《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衡量自有的能力,制定一项“三年计划”,内容如下:
由此显示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养士功能,至此已充分发挥。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调查研究告一段落,遂决定了3个方针:(1) 1936年7月起创办重工业;(2)尽量利用外资;(3)尽量利用外国技术。又在兼顾国防和经济的要求下,根据先前拟订的《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衡量自有的能力,制定一项“三年计划”,内容如下:
(甲)统制钨锑,同时建设钨铁厂,年产钨铁二千吨;
(乙)建设湘潭及马鞍山炼钢厂,年产三十万吨,可供国内需要之半;
(丙)开发灵乡及茶陵铁矿,年产三十万吨;
(丁)开发大冶阳新及彭县铜矿,同时建设炼钢厂,年产三千六百吨,可供国内需要之半;
(戊)开发水口山及贵县铅锌矿,年产五千吨,可供国内需要;
(己)开发高坑、天河、谭家山及禹县煤矿,年产一百五十万吨,补充华中华南产煤之不足;
(庚)建设煤炼油厂,同时开发延长及巴县、达县油矿,年产二千五百万加仑,可供国内需要之半;
(辛)建设氮气厂,年产硫酸铔五万吨,同时制造硫酸、硝酸以为兵工之用;
(壬)建设机器厂,包括飞机发动机厂,原动力机厂,及工具机厂;
(癸)建设电工器材厂,包括电线厂,电管厂,电话厂,及电机厂,每年产品可供国内需要。

1930年代,计划经济的潮流风行全球,中国也不例外,于是“学者们又由宪法与约法的请求,转到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的献议”。
 1932年8月,中国工程师学会于天津召开第二届年会,《大公报》特刊出社评祝贺,期勉:“工程界诚能与经济学界及军事科学家,自行合作,产出整个的伟大计划,并拟定其实施步骤,则此一有权威之计划,便将成为政治上最高的纲领。微论现政府决不至漠视,假若此政府不负责,国民当然建一能行此计划之政府。”
1932年8月,中国工程师学会于天津召开第二届年会,《大公报》特刊出社评祝贺,期勉:“工程界诚能与经济学界及军事科学家,自行合作,产出整个的伟大计划,并拟定其实施步骤,则此一有权威之计划,便将成为政治上最高的纲领。微论现政府决不至漠视,假若此政府不负责,国民当然建一能行此计划之政府。”
 国民政府在此时代思潮冲击下,各财经部会均纷纷制定各种计划,如建设委员会的《十年实业计划》、实业部的《实业四年计划》、全国经济委员会的《三年发展规划》,但是这些计划最后均为纸上谈兵,无一能够付诸实施,唯一的例外即为资委会制定的三年计划,其原因在于该计划系经过长期的调查和研究后才制定,具有较大的可行性,且获得蒋介石的全力支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德国工业界的参与,计划的实施获得了启动的资金和技术的保证。
国民政府在此时代思潮冲击下,各财经部会均纷纷制定各种计划,如建设委员会的《十年实业计划》、实业部的《实业四年计划》、全国经济委员会的《三年发展规划》,但是这些计划最后均为纸上谈兵,无一能够付诸实施,唯一的例外即为资委会制定的三年计划,其原因在于该计划系经过长期的调查和研究后才制定,具有较大的可行性,且获得蒋介石的全力支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德国工业界的参与,计划的实施获得了启动的资金和技术的保证。

1936年,资委会获得国民政府拨给事业费1000万元,同时得到不少外国贷款,因此三年计划中的事业得以推动了一大部分。除湘潭炼钢厂稍微落后,飞机发动厂因有特殊情形陷于停顿,煤炼油厂、氮气厂未及动工,贵县铅锌厂未及开发外,余者悉照程序表进行。虽然期间遭遇到一些困难(如人才和数据不足),但是该会始终相信三年计划可以完成,因为所有计划范围内的建设,技术上较为困难者,均已与外国订有技术合作办法,限期完成。直至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全部计划受到莫大影响,厂矿或内迁或停顿。不过损失虽大,整个基础尚未破坏。

由于八年全面抗战和随之而来的国共内战,国民政府自此再无机会支持如此庞大的工业发展计划。但是,资委会的三年计划确实留下了一些珍贵的遗产——无论在战时及战后经济,甚至1950年代海峡两岸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均可见到资委会的影子。对德国来说,中国无法完成三年计划虽非一场灾难,不过损失也不小。德国以军火武器和中国交换战略性的矿砂,虽然小规模地持续进行至1940年,但是参与中国工业的可能性,却由于战争的爆发而受挫。根据当时一位德国驻华官员的说法,若非战争的因素,资委会三年计划所提供的合同,将可使德国工业兴旺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