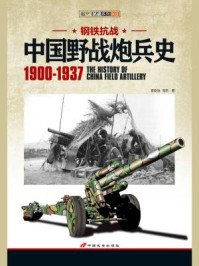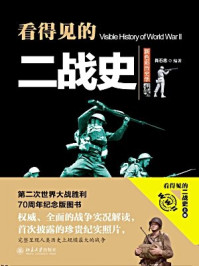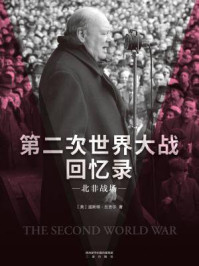蒋介石属于“刚毅型”的领袖,具有“英雄造时势”的气概。意志坚强,遇有强敌,可以退让,但绝不投降。
 其缺点即为盛气凌人,宽厚不足,以至于虽想选贤任能,但每多无法如意。早在1919年,蒋介石对他自己性格上的缺点,即曾有过以下的反省:
其缺点即为盛气凌人,宽厚不足,以至于虽想选贤任能,但每多无法如意。早在1919年,蒋介石对他自己性格上的缺点,即曾有过以下的反省:
人才难得,盖由于自身精明不足,易为人欺,而不易为我用者半。又由于自身学业不足,易为人所轻视,而不愿为我乐助者亦半也。总之,蛮横轻浮者,易为人所弃。恕和宽厚者,必为人所亲,吾自常有骄矜暴戾之色,盛气凌人之势,而又不能藏垢纳污,虚心包容,此其人所以不乐为我所用也,以后应事接物之间,以浑厚宽恕四字,三注意也。

蒋介石早期权位不稳时,多方尊崇革命元老及前辈。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在1920年到1930年均与蒋过往甚密,而对自己同辈的革命党人和政治人物,如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叶楚伧、戴季陶、阎锡山、冯玉祥,蒋都以谦卑态度处之。廖早死,叶、戴渐形“老朽”,与汪、胡、阎、冯、李、白诸人,有分有合,有些人虽可共事一时,后来多半分道扬镳。蒋早期掌握者,多为军事机关,所用的人主要凭借保定系、士官系,又培养出庞大的黄埔系。文人的亲信中,邵元冲、陈果夫、陈立夫后来在政治、党务方面有重大影响力。全面抗战前他重用黄郛和杨永泰,战时张群、宋子文、孔祥熙承担多方面任务。
 蒋常自叹人才不足,例如1932年6月22日的日记:
蒋常自叹人才不足,例如1932年6月22日的日记:
为政在人,余一人未得,何能为政?尝欲将左右之人试量之,多非政治上人。戴季陶[传贤]、陈景翰[韩]、余日章三友可为敬友,而不能为我畏友;其他如朱骝先[家骅]、蒋雨岩[作宾]、张岳军[群]、俞樵峰[飞鹏]皆较有经验,而不能自动者也;其次朱益之[培德]、朱逸民[绍良]皆消极守成而已,无勇气,不能革命矣。其他如贺贵严[耀祖]、陈立夫、葛湛侯[敬恩]皆器小量狭,不足当事也。兹再将新进者分析之,党务:陈立夫、张厉生、张道藩、刘健群、罗志希[家伦]、段锡朋、方觉慧、齐世英、方治、鲁涤平、罗贡华选之。其他如内政、外交、经济、法律、教育诸部,从长考选,不易多得也。

两天之后,他又思考同一问题:
近思旧识干部人才,几无一得,而本党原有之干部,更难多得。季陶、益之较有干才,而其消极、懒慢,不能为用,是为最大之不幸。其次则张岳军、蒋雨岩、朱骝先,亦只能尽一部之责而已。

党内干部既然不能为用,蒋于是开始尝试向学界求才。
中国自古受到科举制度的影响,一直即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近代科举制度废除后,年轻人的心态开始产生了变化。知识分子有鉴于政局的动荡,加上受到“实业救国”宣传的影响,总以为救国的根本不在政治而在科学与教育、实业与学问。“政治乃是一件极无聊赖的事,他们是不屑去做的。”

不过到了1920年代,知识分子又发现政治的不上轨道使得实业不能发达,教育日益腐败,学者也因为生活的不安定而无法安心地研究学问,逐渐觉得过去观念是错误的,以为政治的改进,原来也是建设事业的一个基本条件。于是过去立誓不入政界的人,也开始谈起政治了。
此时正值蒋介石开始向党外求才,自然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如北大教授陈衡哲即观察到:“这个当局对于一班人才的意向,以前的不去说他。自从国难以来,却不能不说是渐渐的改为友谊的,虚心的,甚至于诚意的了。虽然他们对于党外人才的征求与引用,仍不过是一个微之又微的开始。”
 这位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和她的丈夫任鸿隽,均为胡适多年的好友,因此她的观察,颇能代表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看法。
这位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和她的丈夫任鸿隽,均为胡适多年的好友,因此她的观察,颇能代表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看法。
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所直接掌控的智囊机构,主要包括国防设计委员会、南昌行营调查设计委员会、侍从室与参事室。本章拟依序讨论以上各机构,并对其得失与影响进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