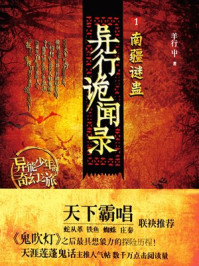一行人回到内书房,狄公用疲倦的声音道:“楚大远心性机巧。他表面上是个乐天、喜欢动的家伙,马荣乔泰你们均喜欢他,但事实远非如此,此人身体上某方面的缺陷败坏了他。”
他给陶干做了个手势,陶干赶紧为他斟满茶。狄公极快地喝完,然后继续对马荣和乔泰道:“我得有时间搜查他的房子,并且必须让他毫不知情,因为此人聪明得可怕。故而我只好派你们俩同他去五羊村跑那趟空头差事。要是洪亮未被杀害,昨晚我会把对楚大远犯罪的推论全都告诉你们。可出事后,我无法要你们试着对洪亮之死做出无动于衷的样子。我知道自己也做不到!”
“要是我早知道,”马荣激愤地说,“我肯定用这双手把那只狗给掐死了!”
狄公点头,静默良久。
接着陶干问:“大人何时发现那具无头尸并非潘氏呢?”
“我本该当场就怀疑的!”狄公痛苦地说,“因为尸体有个明显的不协调处。”
“是什么?”陶干急切地问。
“戒指!”狄公答道,“叶平在验尸时说到红宝石被取走了。既然凶手要宝石,他何不干脆将戒指从尸体上拿下来呢?”
陶干用手拍了拍额头。狄公继续道:“那是凶手的第一个错误。可我不仅未发现不妥之处,还忽略了另一个说明那尸体不是潘氏的线索,那便是,她的鞋子不见了!”
马荣点了点头。
他说道:“那些女人身上穿的宽松袍子和轻而薄的内衣是否合身很难看清,不过鞋子则是另一回事!”
“完全正确。”狄公道,“凶手知道,要是他留下潘氏的衣服而拿走鞋子,我们可能会想鞋子到哪儿去了;而要是把鞋留下,我们或许会发现鞋子不合尸体的脚。于是他聪明地把什么都带走,猜想这样便可迷惑我们,从而让我们忽略鞋子不见的重要性。”
狄公吁了口气继续道:“不幸的是,他的猜测非常正确!然而他犯了第二个错误,那使我回到正确的路上,让我意识到我先前所忽略的事情。他由于对红宝石有癖好,无法忍受将它们留在潘家,于是便趁潘峰在狱中时闯进房间,从衣箱里拿走了宝石,还愚蠢地答应潘氏的请求,拿走了几件她最喜欢的袍子。而这一事实令我意识到潘氏一定还活着,因为倘若凶手犯案时已知道藏宝之处,他当时就已经将它们拿走了。一定有人事后告诉过他,而那人只可能是潘氏。”
“接着,没有宝石的戒指的重要性令我明朗起来,也让我明白了为何凶手把所有的衣服都拿走,那是为了不让我们发现那尸体不是潘氏。凶手知道唯一会发现的人是她丈夫,但他又一次猜对了,到潘峰为自己澄清时,那尸体早就被装了棺。”
“大人是何时将楚大远与谋杀案联系起来的?”乔泰问。
“是在最后一次跟潘峰谈话之后。”狄公答道,“一开始我先怀疑叶泰。我问自己那个被害的妇人是谁。由于廖姑娘是唯一被报告失踪的,我想那必然是她。仵作称那尸体并非是处女,而我从于康的供认中了解到廖姑娘也不是处女。再则,我们那时认为叶泰绑架了廖姑娘,而且他又很健壮,能割下她的头。有一会儿,我有个很吸引人的推理,即叶泰在狂怒之下杀了廖姑娘,其妹为帮他掩盖凶杀一事,便自愿失踪。但我很快便放弃了这个推测。”
“为什么?”陶干迅速问,“我听起来很合理。我们知道叶泰与其妹很亲近,而这给了潘氏离开她丈夫的机会。”
狄公摇头。
他说:“别忘了漆毒这个线索。从潘峰的陈述中,我了解到只有凶手可能曾因大意而碰到那张油漆未干的桌子。潘氏对此很清楚,她一定会小心以避免碰上桌子,而叶泰也并未受到漆毒,于是漆毒引向了楚大远。我记得曾发生过两件本身极细小的事,现在它们突然有了特别的意义。首先,由于漆毒,楚大远突然决定在室外举行猎宴而非在厅内办普通的酒席,因为他得一直戴着手套来掩盖他中毒的手。其次,那也可解释凶杀后那天早上,马荣和乔泰与他出去打猎,楚大远为何错失良机未能打中狼。楚大远经历了一个可怕的夜晚,而且他的手痛得厉害。”
“再则,凶手一定住在潘家附近,并且可能有座大宅。我知道他一定是带着一个没人看到的妇人及一个大包袱离开了潘家。他不敢冒险碰见守夜人或巡逻队,因为那些人有个值得称道的习惯,也就是会拦住并盘问夜间带着大包袱行走之人。现在我们知道潘峰住在一条冷僻的街上,从那儿沿城墙内侧走可到楚宅后面,而城墙那边只有旧货栈。”
陶干道:“可是在到他家之前,他必须穿过靠近东城门的主道。”
“那不过是个小小的风险而已,因为守门士卒只仔细盘查出入城门的人。”狄公道,“在我认定楚大远是最大的嫌疑犯后,我当然马上问自己他的动机是什么。接着我突然想起楚大远一定有某种不对劲之处。一个健康强壮的男子,有八名妻室却无儿无女,这说明他应该有身体上的缺陷,并且这种缺陷有时会对人的性格产生危险影响。从戒指上取走宝石证明他对红宝石有癖好,以及夜盗潘家,拿走手镯,皆为我对楚大远的画像增添了重要的笔触:那是一个心智扭曲的男人。促使他杀害廖姑娘则是因为对她的狂躁的憎恨。”
“大人,那时你是如何清楚这些的?”陶干又问。
“我先想到忌妒,”狄公答道,“一名年长男子对年轻夫妇的忌妒。但我立刻摒弃了这个想法,因为于康与廖姑娘订婚已有三年,而楚大远强烈的憎恨是最近才有的。接着我想起了一个奇怪的巧合。于康向我们报告说,叶泰在楚大远书房前的走廊跟老女佣说话时得知了他的秘密,也告诉我们他曾向老女佣试探过这件事,又是在楚大远书房前的走廊。我想到楚大远可能两次对话都偷听到了。第一次那女用人告诉叶泰于康在卧房中幽会之事,提供了楚大远憎恨廖姑娘的理由:她在楚大远自己家里给了一个男人欢乐,而这种快乐,楚大远被造化剥夺了。我可以想象到廖姑娘对楚大远来说是他压抑的象征,而他觉得占有她是唯一可以让他恢复男子能力的办法。再则,他偷听到于康和老女佣之间的谈话,而知道叶泰是个敲诈者。楚大远知道叶泰与其妹很亲近,他担心潘氏可能已把他们的会面甚至可能把集市上那个姑娘的事都告诉了叶泰。楚大远认定无法冒被叶泰发现并敲诈一辈子的风险,于是决心将叶泰除掉。这与实际情况十分相符,因为叶泰就在于康跟老女佣说话的那天下午失踪了。”
“当我确定了楚大远有动机和机会进行犯罪之后,我又有了另一个想法。你们都知道我并非是个迷信之人,但那并非说我否认有超自然现象的可能性。到楚家赴宴的那晚,我瞧见一个雪人坐在一侧花园内,而当时我清楚地感觉到了惨死的罪恶气氛。我现在记起,在席间,楚大远曾暗示我那是他用人的孩子们所堆的雪人。然而马荣和乔泰曾告诉过我,楚大远以前自己也堆雪人,用作练习射箭的靶子。我突然想到,要是某人得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很快藏好一个被割下的人头,将它盖上雪当作雪人的头倒是个不坏的办法。这个办法楚大远尤其喜欢,因为那可进一步帮助他消减对廖姑娘的异常憎恨。那靶子一定令他想练习射箭,一箭又一箭地射向雪人的头。”
狄公沉默了,颤抖着。他赶紧将皮袍紧了紧。他的三名随从看着他,脸色苍白憔悴。那种疯狂罪行的恶毒气氛,似乎在房里游游荡荡。
停顿了许久,狄公继续道:“那时我相信楚大远便是凶手,只是缺乏具体证据。昨晚退堂后,我曾打算向你们解释我的推论,并与你们商议如何对他家进行突击搜查。要是我们确能在那儿找到潘氏,楚大远便输了。可是楚大远却杀害了洪亮。假如我与潘峰的谈话能早半天,便可在楚大远杀害洪亮前去抓他了。可命运却做了另一种安排。”
房中陷入一阵哀伤的沉默。
狄公最后道:“陶干知道以后的事。你们和楚大远出城后,我和陶干、班头去了楚宅,在那里找到了潘氏。她被密封的轿子送至衙门,无人知晓。陶干在所有的房间里都发现了窥孔。我查问了老女佣,证实她对于康的情事一无所知。现在我们从潘氏的供词中知道,是楚大远自己偷看到了于康及其未婚妻之事。我猜测楚大远不小心跟叶泰说了几句,而那个狡猾的无赖猜出了其余的事,但当于康问叶泰是如何知道自己的秘密时,叶泰编造了老女佣的事,因为叶泰不敢把楚大远放在自己敲诈的计划中。后来叶泰是否大胆去敲诈楚大远,抑或楚大远偷听到于康和女用人的谈话,担心叶泰会去敲诈自己,我这样猜想,这些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晓了。楚大远已经疯了,而我相信叶泰的死尸正躺在雪野中的某处。”
“我也盘问过了楚大远的八位妻妾。我希望能忘掉她们告诉我的她们与楚大远生活的情况。我已签发必要的命令,将她们送回各自家中,结案后她们可得到一大笔楚大远的财产。如今楚大远发疯,这有可能使他置于法律惩处之外。”
狄公拿起眼前桌上洪亮的旧荷包。他用手指轻轻地摩挲着褪色的缎子,然后小心地将它放在袍子里。
他在案上摊开一张纸,拿起了毛笔。他的三名随从赶紧起身告退。
狄公先给刺史写了份关于廖莲芳一案的详细报告,然后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在太原狄公弟弟家当管家的洪亮的长子。洪亮是个鳏夫,他儿子现在乃一家之主,得决定埋葬之处。第二封信写的是太原狄公老岳母家的地址,是给他大房的。他先询问老太太的病情,然后也向她通报了洪亮之死。在这些正式词句之后,他加了一句带个人感情的话。他写道:“所爱之人亡去,我们不仅失去了他,亦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
狄公将信交给役卒立刻送出后,独自在书房内用了午膳,沉浸在悲伤的思绪中。
狄公不愿去想蓝涛奎被杀或是陆氏的那个案子,他觉得无比劳累。他命役卒拿来他写的官府赈贷计划文件,那些官贷是要在庄稼歉收时无息放给农民的。这是他最喜爱的计划,是他耗费了许多晚上和洪亮一起研究,努力做成的一份报告,希望这份计划能得到户部的批准。洪亮甚至曾想以减少地区行政开支来实现这项计划。狄公的随从们进来时,看到他正在专心计算。
他推开文件,说道:“我们得商量一下蓝师傅被杀之事。我仍然认为是个妇人毒死了他。但迄今为止,我们所能掌握的他熟识一名妇人的唯一线索,是那名年轻拳师的陈述。他告诉你们一名妇人晚上曾去见蓝师傅,但从他偶然听到的对话中,我们无法找出那妇人是谁。”
马荣和乔泰苦笑着点点头。
乔泰道:“它仅使我想到两人都未讲客套话,由此可知他们彼此十分相熟。但正如大人以前所讲,我们早就了解这点,因为妇人进浴房时蓝师傅并未想要盖上他的裸体。”
“那年轻人听到的只言片语到底是什么?”狄公问。
“哦,”马荣答道,“没什么特别的。她似乎很生气,因为蓝师傅避开她。而蓝师傅回答说不是那回事,并加了个词——听起来像是‘猫咪’。”
狄公猛然站了起来。
“猫咪?”他不敢相信地问。
他突然想起了陆氏小女儿的问题。她曾问她妈妈和客人说话的猫咪在哪里。这改变了一切!他迅速吩咐马荣:“立刻骑马去潘峰家。陆氏还是小孩儿时潘峰就认识她了。问他陆氏是否有绰号。”
马荣看上去很惊讶,但他没有问问题的习惯,立刻便出去了。
狄公没有再说话。他叫陶干煮新茶,然后与乔泰商量本地区巡逻队对平民管辖所出现的困难的解决之道。
马荣很快就回来了。
“嗯,”他报告说,“我见老潘非常难受。关于他妻子行为不端的消息比最初她被谋杀的消息对他打击更大。我问他陆氏的事,他说以前邻里都叫她绰号‘猫咪’。”
狄公把拳重重砸在案桌上。
“这就是我要的线索!”他大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