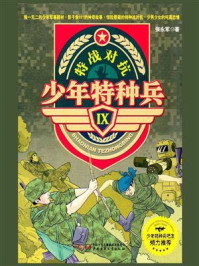狄公不慌不忙道:“我曾详细察看过这一带的地图。此城位置绝佳,周围有天然屏障可做依托。城北一带尽为悬崖,居高临下,悬崖之下有一条大河蜿蜒向东流向大海。城东又有一条宽阔深邃的溪涧与此大河相接,大河尽头通海口处设有一关防要塞,驻扎重兵把守。城南则是一片沼泽,极难行走,不宜驻防。唯有此西门之外地势稍显平坦,然亦设有哨卡,派有兵卒把守。数年之前,我朝征战高丽之时,为防高丽战船沿城北河道侵入,凡经河口关防的船只皆须接受严查之后方得通行。故此城易守难攻,实无须高墙厚垣。在这一带,蓬莱乃唯一天然良港,故此地亦是我朝与高丽、日本商贸往来之枢纽。”
“在京城时,我听人说,”此时洪亮道,“许多高丽人南下迁居此地,且来者多为水手、船匠及佛教信徒。他们集中居住于城东溪涧另一边,居住区内还建了一座不小的寺庙。”
乔泰闻言,笑着对马荣道:“兄弟,想来你艳福不浅,此番又可勾搭高丽女子,且可去那附近寺庙求菩萨成全你的风流愿。”
此时两名守门军士走来将城门打开,放狄公四人入城。四人沿城中大街徐徐而行,只见大街两旁满是店铺、商贩,人来人往,十分热闹。未几,四人便到了县衙院墙之外,沿墙边向南行不到百步便到了衙门口,但见几个守门衙役正懒懒散散地坐在门口大鼓下一条长凳上闲聊。见有官员到来,这几个衙役慌忙立起,恭敬地向狄公四人行礼。然狄公刚走过去,这几名衙役便又嬉皮笑脸,相互挤眉弄眼,递送眼色。洪亮在后皆看在眼前。
书吏跑来拜迎狄公,将狄公等引入前厅。前厅内有四名书吏正挥毫疾书,边上一位瘦骨嶙峋的短须老者正来回巡视。
见新县令到来,短须老者慌忙趋前迎接,前言不搭后语地自称姓唐,乃本县县丞,临时代理本地衙署事务。
只见这唐县丞神色慌张言道:“在下事先未获通报,不知大人今日驾到,以致未及预备接风筵席,实在——”
“我本以为边防官驿会差人先行通报你等,”狄公不待县丞言毕即道,“必是何处出了差错,以致如此。然我既到,你便引我等巡视衙署。”
唐县丞先将狄公等引至大堂。大堂里砖砌地面清扫得干干净净,里边高台上设一高大案桌,案桌上铺一块簇新红锦桌布。案桌之后则为影壁,其上挂一块褪了色的紫绸幕布,几乎将整面影壁遮蔽得严严实实。那幕布中央用金线绣着一只象征威武、敏锐的狻猊。
绕过影壁便是大堂后门,出后门是一条狭长走道,沿着这条走道便进入了县令老爷处理日常公务的后堂书房。书房内陈设完善,书案擦拭得一尘不染,光可鉴人;墙面洁白,显然新近才粉刷过;书案后放置一张长睡榻,其上铺了一条深绿色锦褥。书房之侧连接一室,室内放置文书案卷。狄公探头向内随意扫视了一眼,便步出书房,走入内院。内院正前方即为客厅。
唐县丞神情紧张地向狄公解释道:“自那朝廷御史离去之后,此客厅便未再启用过,只是其中桌椅或许曾被移动。”
狄公见唐县丞神态慌张,甚觉奇怪。为使其消除疑虑,狄公和颜悦色道:“近日难为县丞在此操持,将衙内事务料理得如此井井有条。”
唐县丞朝狄公深深作了个揖,期期艾艾道:“回禀大人,在下年轻时即被招募,入衙之初只是一名小小公差,至今已有四十年。在下做事一向喜好按部就班、有条有理。从前此处一直平安无事,不想如今却——”
说话间,众人已来到客厅门口。唐县丞上前将客厅大门打开。
众人步入客厅,围聚于客厅中央一张华美雕花桌旁。唐县丞恭敬地将桌上一方衙署大印捧起呈递与狄公。狄公仔细将印与原注册簿上的印纹比照一番之后,方才签收。收下大印,狄公便可正式掌管蓬莱地方事务了。
狄公手抚长须道:“自今日起,本县将全力以赴处理前任县令遭人谋害一案,其余一应公事暂且一概置后。今日本县先行召见县衙大小官员,此后尚需择适宜之机接待本地名人士绅并会晤四乡里正。”
“禀大人,本县另多一位里正,”唐县丞道,“此人为高丽里正。”
“高丽区域的里正是我汉人否?”狄公问道。
“不,大人。”唐县丞答道,“不过此人通晓我国言语。”说至此,唐县丞踌躇片刻,又以袖掩口咳嗽数声,然后胆怯地继续言道:“大人,在下窃以为此事似有不妥之处,但州府刺史大人已决定在城东溪涧高丽人集居地另设一里,并允其自治。此里之内安全事务皆由其里正自行负责,倘未获其许可,衙门官吏皆不得擅入其里干涉其事务。”
“此事确实不甚寻常,”狄公低头思量道,“我会于近日调查此事。现在你先去前厅将衙门内一应官吏、差役等召集于大堂上。本县先去后院私宅歇息片刻,待精力有所恢复便召见各位。”
唐县丞闻言,面上显出为难神色。迟疑片刻道:“大人住处甚好,去年夏天,前任汪县令才命人将宅邸粉刷一新。然不幸的是,汪县令家私行李仍在其中,尚未搬出。在下亦在等候汪县令在世的唯一亲人,即他的胞弟的回音,故在下实不知将那些私人物件送往何处为好。汪县令早年鳏居,一向只使唤几个本地仆役,自他被害亡故后,这几个仆役便相继离去了。”
“然朝廷调查案件之御史来此又居于何处?”狄公问道。此时他心中颇感诧异。
“回禀大人,御史大人夜晚只于书房长榻上就寝,”唐县丞眉头紧锁道,“御史大人亦在那间房内用餐。在下十分惭愧,府内事务纷乱无序,在下曾与汪县令之弟去过数封书信,可至今未获回音,在下实在不知如何——”
“你也不必如此为难,”狄公言道,“此案不破,本县不会将家眷、仆役等接来同住。近日我便于书房中安歇罢了。现时你可将我随从带去其住处稍歇。”
“大人,”唐县丞急道,“衙门对面有一极佳客栈,平日在下与老妻即居住其间,而且我敢保证大人您及您的随从——”
“此话差矣!”狄公闻言,面色陡变,不待县丞说完便道,“为何县丞不居住于衙门之内,却要居住于客栈之中?你一向在衙门内做事,亦该知晓衙门内规矩!”
“回禀大人,在下在客厅后楼楼上确有几间住房,”唐县丞急忙解释道,“然因此房须翻修屋顶,故在下只好临时寄居客栈,还望大人见谅!”
“也罢,你便暂居于客栈之中。”狄公不耐烦道,“然本县随从仍须居住于衙署内,你只需将他们安顿于守卫衙役的房内便是。”
唐县丞无奈,只得朝狄公深施一礼,然后领着马荣与乔泰离开客厅。洪亮则跟随狄公回到书房。
回至书房,洪亮先帮狄公换上一件新官服,又为狄公沏了杯热茶,再将一块热手巾递与狄公。狄公边以手巾拭面边问洪亮道:“洪亮,你看唐县丞此人如何?”
“据我看来,他像是十分讲究繁文缛节的那种人。”洪亮答道,“我想,我们的突然到来一定使他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应付。”
“我想,”狄公沉思道,“此人必定担忧衙署内何事发生,不然不会移居客栈。不知其中有何缘故。”
此时,唐县丞来到书房,告知狄公衙署官役一应人等皆已齐集大堂内,专候狄公召见。狄公闻报便戴上乌纱帽,径自走向大堂。洪亮与唐县丞紧随其后。来到大堂,狄公在那案桌后就座,并示意马荣、乔泰立于其后。
堂上大小官员、衙役共四十人皆跪于阶下。狄公好言勉励一番之后,唐县丞便向狄公一一介绍。狄公注意到县衙文职官吏皆身着蓝布袍,守卫兵丁与衙役则身束皮甲,头戴铁盔。众人皆不敢言笑,任由狄公审视。狄公见阶下衙役班头生得一脸横肉,一看便知是个心狠手辣之人,令人望而生畏。但狄公知道此类人大多生相如此,需要时常调教方可信任。再看仵作,此人姓沈,甫逾中年,面相温文尔雅且聪颖机敏。唐县丞俯身轻声告知狄公,仵作沈郎中是本地最负声望的名医,此人品行高尚正直。
待唐县丞将文武县吏逐一介绍完毕,狄公遂宣布洪亮为本县主簿,令其掌管衙署前厅所有日常公务。马荣与乔泰为县衙武吏的统领,统领衙门上下衙役和兵卒,一并监管衙内法纪及门卫、牢房等处事务。狄公回至书房,叮嘱马荣、乔泰即刻去察看门口防卫与牢房监管之情况。
“然后,”狄公又道,“你二人须集合操练衙役、士卒,以便熟悉各人品行,看其是否称职。此后你二人再往城中行走,打探城中情况。我本欲与你二人一同前往城中行走,只是今晚我须查询前任汪县令被人谋害一案之细节,故无法与你等一同前往。今夜,你二人回府须来此将城中见闻回报于我,我会在此等候二位。”
当下两人遵令离去。未几,唐县丞步入书房,其后跟随一名小吏,手拿两支烛台。狄公命唐县丞坐于洪亮身旁。跟来的小吏将烛台放在桌上,随即转身离去。
“方才,”狄公对唐县丞道,“我留意到衙署官员花名册上有个录事樊仲,然今日未见其人,不知是何缘故?难道此人病了不成?”
唐县丞以手击头,结结巴巴道:“在下正要将此事禀报大人。樊录事月初去青州府度假,按说昨日早晨便该回府,可不知何故并未回来。今晨在下曾差一名公人去城西樊录事田庄上探问。庄客称樊录事与随从昨日便已回庄,约莫中午时分离开田庄,不知去了何处。在下得此消息亦感困惑不解,心中正自忧虑,不知如何是好。樊录事做事精细,是个能干的官员,一向准时无误,实在不知其究竟出了何事。樊录事——”
“不会让老虎吃了吧?”狄公不耐烦地讥讽道。
“不,大人!”唐县丞闻言忙叫道,“不,不会如此!”此时但见唐县丞面色陡然变得煞白,双目充满惊恐神态。
“不必如此紧张!”狄公面色阴沉,言道,“本县理解你此时的心情,或许你因前任县令被害而一直心有余悸,然此事已过去半月有余,如今尚有何事令你如此忧惧?”
唐县丞以袖擦拭额头上渗出的汗水。
“还望大人海涵,”唐县丞结结巴巴道,“几日前,城外丛林内曾发现一名被咬断咽喉、吃剩的庄客尸首。此地必有一只食人恶虎。近来在下为此一直心神不安,无法安睡。方才大人提及老虎之事,令在下闻之胆寒。”
“县丞不必忧虑。”狄公道,“马、乔二位县尉均善狩猎,近日本县即差他二人去猎杀那恶虎便是。此刻你去为我倒杯茶来,待会儿我要与你谈谈公事。”
唐县丞去倒了杯热茶,回来递与狄公。狄公呷了两口,将杯放于桌上。
“本县想知道汪县令被害是如何被发现的,你可详细为本县道来。”
唐县丞摸着颔下短须,小心翼翼地开始叙述事情的来龙去脉。
“前任县令是一位极有风度与涵养之人。平日里汪大人虽随遇而安、不拘小节,每逢重大事务却从不含糊,格外精细。汪大人年约五十,见多识广,是个颇为能干的县令。”
“此地可曾有他的仇人?”狄公问道。
“在下从未听说他有何仇人。”唐县丞道,“汪大人断案迅速、公正,名闻四乡,在这一带口碑甚佳,深得百姓厚爱与拥戴。”
狄公频频点头,示意唐县丞继续讲述。
唐县丞又道:“十几日前,一日早晨该击鼓升堂之时,汪县令管家跑来前厅寻我,告知我汪大人一夜未曾入睡,卧房中灯烛亮了一夜,房内书斋门则从里边被反锁。在下知道汪大人有夜读习惯,经常秉烛读书至深夜方才安寝,有时即伏案而睡,故在下当时以为汪大人定又是伏案而睡,忘了时辰。于是在下忙跑至其书斋喊门,却不见里面有丝毫动静。在下担心汪大人有何意外,遂唤来力大的衙役破门而入。”
说到此处,唐县丞稍顿了顿,嘴角不自觉地抽搐了数下,略定了定神,方继续说道:“门打开之后,我见汪大人仰面朝天倒卧在茶炉旁地面上,两眼直瞪着屋顶,又见一只茶杯滚落于汪县令右手边的篾席之上。在下上前摸了摸汪大人身体,发觉已冰冷僵硬,随即传来仵作沈郎中。沈郎中验尸后称汪大人约莫死于夜半之时,并从茶壶内取出一点茶水以作验证。他将——”
“那茶壶当时放于何处?”狄公插话道。
“禀大人,放在书斋左侧茶具柜上,”唐县丞道,“茶具柜旁是烧水的铜茶炉。那茶壶内尚有半壶茶水,沈郎中将其中一点茶水喂与一条狗吃,那狗只挣扎几下便倒地而亡。沈郎中将茶壶内茶水又再热过,嗅之似有异味,乃断定其中有毒药。当时那茶炉上尚且煨着一把烧水铜壶,因壶内水已烧干,所以沈郎中无法检验铜壶内是否有毒。”
“平日里都是何人递送茶水入室?”狄公追问道。
“并无专司送茶水之人,都是汪大人亲自所为。”唐县丞急忙回复道。他见狄公抬头审视自己,不觉语速加快了许多:“禀大人,汪大人嗜饮茶,且十分讲究。汪大人总坚持亲自从其宅院内的井中取水,并亲自于卧房书斋中茶炉上烧水沏茶,不让旁人插手。其所用茶壶、茶杯与茶叶罐皆是贵重的古董。他将这些茶具小心收藏在茶炉旁茶具柜内,还加了锁以防失窃。当时在下还命沈郎中验了茶叶罐内的茶叶,未发现其中有毒。”
“此后你又采取了何种措施?”狄公继续追问。
“大人,当时在下即刻差遣一名老练信使前去州府将此噩耗禀报刺史大人,并将汪大人遗体暂时盛殓,放置于汪大人私人宅堂内,然后将汪大人书斋上了封条。到了第三日,朝廷派来调查此案的御史从京城至此。他命此处军塞防御使拣选六名干事助其彻查此案,并将汪大人身边仆役一并拘禁,严加问讯。他又——”
“此事我已知晓,”狄公有些不耐烦地说道,“我看过此人呈给朝廷的奏章。奏章中说得明白,无人接触过那杯茶水,亦无人于汪县令身亡那日退堂之后去过其卧房书斋。然我想知道御史大人究竟是何时离开蓬莱的?”
“第四日早晨。”唐县丞小心回复道,“御史大人传唤在下,命在下将汪大人灵柩移至东城门外白云寺内停放,待死者孪生胞弟有了回音,再定葬于何处。随后他便将防御使的六名干事遣返军塞,又告知在下他将带走汪大人所有私人书函,然后便离开了蓬莱。”说至此,唐县丞面露忧容,忐忑不安地望了狄公一眼,问道,“大人,不知御史大人可曾向大人提及他突然离去之原因?”
“他说,”狄公信口应道,“此案已有眉目,其余细节交由新任县令继续查办更为妥帖。”
唐县丞闻言心下宽慰许多,少时又问道:“不知御史大人身体安康否?”
“他已离京赴南方任职去了。”狄公起身道,“如今本县要去那卧房书斋走一遭。你与洪亮在此商议一下明日早堂需要办理之事务。”说罢,便自桌上拿起一支烛台,走出房去。
前任汪县令故宅位于衙署客厅后面花园内。因雨后初霁,且已是傍晚时分,园内花坛、树间好似有一层薄雾缭绕,显得格外幽静神秘。狄公步入园内,只见宅门半开,便推门入内。
早在京城时,狄公便从案卷所附汪县令宅邸平面图上得知,汪县令卧房书斋位于宅内走廊尽头,所以未费多大工夫,狄公便找到了那条走廊。穿过走廊,狄公发现旁边有两条狭窄通道,但因烛光微弱,无法看清两条通道通往何处。狄公秉烛正待深入仔细探视,却忽然收住脚步,因烛光映照处,只见一个瘦小男子正从其中一条通道内径自走出,因走得急,几乎与狄公迎面相撞。
此人一时不知所措,木然呆立,两眼茫然直视狄公。狄公见此人左颊上有一块铜钱般大小的胎记,又见他未戴帽子,头发灰白,在头顶束了个松散的发髻,模模糊糊中又见他身穿一件灰色便袍,腰系一条黑色汗巾。忽遇此人,狄公觉十分突兀,着实吃惊不小。
两人呆立片刻,狄公开口问是何人,那人也不答话,却忽地无声无息转身快步向黑暗通道内退去。狄公迅即举烛照射,意欲看那人去往何处,不想动作过猛,晃灭了烛火。周围顿时一片漆黑。
“嘿,你是何人?快与我出来!”狄公叫道。黑暗中只听得狄公自己的声音。狄公等候片刻,不见动静,整座屋宇内空荡无人,寂静得出奇。
“此人实在可恶,焉敢如此无礼!”狄公气愤至极,自言自语道。黑暗中,狄公以手抚墙,沿走廊缓缓退至花园,然后迅速走回书房。
此时,唐县丞正拿一大册案卷与洪亮在书房内翻阅,忽见狄公怒气冲冲走进来,不知何故。
“本县必要彻查一番,将此事弄个水落石出!”狄公对唐县丞怒道,“衙门官员、差役无人可不着衙门服而于衙内肆意行走,即便在夜间或退堂之后亦不可!方才本县撞见一名穿便服之人,此人居然连帽子也未戴便在后园内闲荡!本县质问此人,不想此人竟十分无礼,不予理睬,径直离去。现你速去将此人招来,我非好好教训此人不可!”
见狄公如此震怒,唐县丞早已浑身战栗不止。只见他此时惊恐万状,双目呆滞,不知所措。狄公见他这般神态,心中反倒觉得自己的言语有些唐突,此事不该责备于他,毕竟唐县丞亦是尽了责的。于是狄公语气和缓道:“当然,此类差错时有发生。然此人究竟是何人?或许是更夫?”
唐县丞惊恐地向狄公身后敞开的房门扫视了一眼,结结巴巴道:“那人是否……是否身穿灰色长袍?”
“是又怎样?”狄公道。
“那人左颊上有无一块胎记?”
“有又如何?”狄公不耐烦道,“速速说来,那人究竟是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