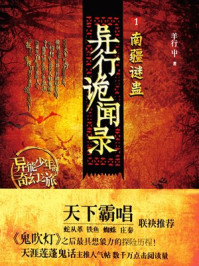且说狄公一行四人避开了薄凯,回到府中已将近三更时分,大家赶紧各自回房歇息不说。次日凌晨,狄公早早便起身了。自白云寺归来,他便感觉浑身乏力,精疲力竭,却一直睡不安稳。这一觉只睡了一个时辰左右,倒有两次梦见汪县令站立于睡榻前,面无血色地盯着自己。当他大汗淋漓地惊醒过来,屋中又分明不见一人。如此两次三番后,狄公索性起身,点燃蜡烛,秉烛而坐,也不再睡觉,直至晨光映红窗纸,衙役为之送来早饭。
狄公方才用完早餐,洪亮便手捧一壶热茶走进书房。洪亮禀告狄公,马荣、乔泰已领人去修缮那破损的水门,并顺路去前一夜雾中目击谋杀案的河边察看,或许早堂之前不能及时赶回。洪亮又告知狄公,据报樊仲仍未归来,亦不知现在何处;另据唐县丞仆役来衙禀报,唐县丞前一夜身体不适,待稍愈后便回衙待命。
狄公低声道:“我亦感有些不适。”说罢,连饮了两杯热茶,然后又道,“可惜京城家中的书未带来此处。有卷书中讲述鬼魂与食人虎之事颇为详细,只可惜当初我未曾在此方面花气力研读。作为县令,本应具有全面的学问,而不可忽视任何看似无用的知识!洪亮,那唐县丞昨日说过早堂须办理何事?”
“回禀大人,今日早堂只有一桩案子要办。”洪亮答道,“有两个农人因田界不明而发生争执,二人告上衙门,望县令大人公断,只此一事而已。”说罢,从袖中取出一份案卷递与狄公。
狄公接过案卷,略略翻阅一过,便将案卷置于案上,道:“此案易断。唐县丞于本县土地注册上曾下过不少气力,各田庄地界在地图上均标注得十分明白。今日将此案断毕,即早早退堂,我等尚有许多要紧公务需要办理!”
狄公说罢,起身。洪亮为狄公取来一件深绿色锦缎官袍。狄公方将官袍、纱帽穿戴齐整,便听得三声鼓响,已到了早堂时分。
当下狄公步出书房,穿过走廊,来到大堂后门。从后门进入大堂,绕过那绣着狻猊的幕壁,去那铺着红锦台布的高大案桌后的椅上坐定,然后向堂下望去,只见堂下人头攒动,好不热闹。蓬莱百姓来者甚众,大家皆欲争睹新任县令威仪,要看是何等人物。
狄公迅速向堂上扫视一眼,察看公人们站位是否有误。他见两边各置一矮桌,其后坐着两名书吏,已将笔墨纸砚准备停当,专候记录。案桌前,台下,六名衙役分两边站定,边上立着衙役班头,手中来回甩动一根皮鞭。堂上气氛凝重,肃静威严。
狄公见一切就绪,遂将惊堂木一拍,高声宣布审案开始。传唤过了原告与被告,狄公即俯身将洪亮为其展开于案上的卷宗、地图又看了一遍。阅毕即命班头将那两个农人带上,跪在案前听宣。狄公宣布断案结果,二人连连叩头于地,口服心服。
狄公拿起惊堂木,正欲宣布退堂,此时堂下人群中一瘸一拐地走出一人。只见此人峨冠博带,手拄一根竹杖,面容端庄俊秀,胡须修剪齐整,看去四十上下年纪。
此人走至案前,费力地跪下,然后以和缓文雅的口气说道:“在下船东顾孟彬叩见县令大人。县令大人适才上任升堂,顾某即冒昧叨扰,心中不胜惶恐之至。今有一事相求大人。顾某拙荆曹旎失踪多日,至今下落不明,顾某心中忧虑如焚,还望大人为顾某做主,派人查寻。”
顾孟彬说罢,匍匐于地,连叩三个响头。
狄公闻言,朗声道:“顾员外但请详述案情,以便本县据实决断。”
顾孟彬随即禀道:“十日前,顾某与曹氏新婚,当时因前任县令突然辞世,顾某未敢大宴宾客。婚后第三日,新娘子即依本地风俗回母家探亲。其父乃本地名流学士曹鹤仙,家住西城门外乡间。按说娘子本应于第十四日即前日午后回转家中,可当天她并未归家。顾某猜想或许娘子还要多住一日。可昨日午后,娘子仍未回到家中,顾某心中着急,便差手下管事金桑去岳父大人家探问。岳父曹公告知金桑,娘子确实已于前日返回,乃是吃了午饭,与其弟曹明一同离去的。途中,曹明步行,紧随其阿姊马后,一直陪伴前行。曹明于那日黄昏时分返回岳丈家中,告知其父,那日伴送阿姊行到大道附近,见路边一棵大树顶上有个鹳巢,便叫阿姊在前先行,待其上树取几个鸟蛋后再来赶上她。可当曹明攀上树,不想踏着一根朽枝,跌落下来,将足踝给扭伤了,只得忍痛挪至附近农家,包扎了一番,也不去追赶阿姊,便借那农家毛驴骑回家中。曹明称他与阿姊分手之后,见阿姊向大道方向骑去,故猜想阿姊会沿大道直接进城。”
说至此,顾孟彬稍歇,用袖擦去额上汗珠,然后继续道:“顾某手下管事金桑在回城途中曾去乡间小路与大道交接处之哨卡询问,并沿进城大道一路询问附近农家与店家,可均无人看见那日有妇人独自骑马经过。为此,顾某心中甚是不安,深恐娘子遭遇不测。如今恳请大人尽早派人寻查顾某拙荆之去处。”说罢,从袖中取出一个折子,恭恭敬敬地用双手将折子举过头顶,又道:“在下顾某写有一个呈状,内中详述拙荆曹旎形容、衣着及坐骑模样,呈请大人过目。”
边上班头走上前,接过折子,递与狄公。狄公展开阅毕,问道:“员外之妻归家途中可曾随身携带珠宝钱财?”
“回禀大人,拙荆回家途中并未携带任何珠宝钱财。”顾孟彬答道,“此事金桑亦曾问过顾某岳丈,岳丈大人告知金桑,其女离家之时只随身携带了一只藤篮,内装几块糕饼,皆是其父要她带回送与小婿的。”
狄公点点头,又问道:“员外仔细想来,是否有忌恨你而欲加害于员外之妻之人?”
顾孟彬摇头道:“回大人话,或许有人忌恨顾某,商场向来如战场。然顾某自思,即便有人忌恨顾某,亦不敢无视王法,做出此等卑劣之事!”
狄公以手抚须,心想顾某之妻极有可能与他人私奔而去,但此事乃是隐私,不便当堂理论,故决定先了解顾妻品行与乡里名声之后再做决断。想到此,遂开口对顾孟彬道:“本县将迅速就此事展开必要的调查。退堂之后,员外即去通告手下管事金桑即刻前来本县书房,将其寻访实情详细禀告本县,以免衙门再遣人去乡间寻访,徒费时日。一旦本县有何音讯,亦会立刻告知员外。”
狄公说罢,即拿起惊堂木向案上重重一拍,宣布退堂。
狄公回至书房,见一名书吏正在书房等候。问之何事,其禀道:“船东易员外到此,有要事想见大人。小人已将他领入衙内,现正在客厅等候。”
“易员外是何人?”狄公问道。
“回禀大人,易员外名为易鹏,乃本地巨富,”书吏答道,“他与顾孟彬同是本地船东,两家船只经常往来高丽、日本经商。两家在城北河港处专有一处大船坞,那里是他们造船、修船之处。”
“也罢,”狄公道,“我正待要见另一位客人,然既是易员外有要事相见,我便先去见他也罢。”转身又对立在一旁的洪亮道:“洪亮,烦你先去接待一下金桑,请他讲述一下如何寻访顾员外之妻的详情细节。待我见了易鹏,听他说些什么,即来会见金桑。”
吩咐已毕,狄公便径自往客厅走去。
客厅内,易鹏正站立一旁,恭候狄公到来。他见狄公走上门口石阶,慌忙跪伏于地迎候狄公。
狄公入内,搀扶易鹏道:“易员外免礼,此处不是大堂,无须如此客气,快快请起,请坐。”
易鹏称谢起身。狄公在茶几旁一张太师椅上就座,易鹏则在狄公对面一张椅子边沿小心就座。狄公见此人生得肥胖,长着一张肉鼓鼓的圆脸,厚嘴唇上方留有两撇薄薄胡须,下颌上亦稀稀落落长着些短须。狄公不甚喜欢他那对滴溜溜乱转的小眼。
易鹏端起仆役递与的热茶呷了一口,张口欲言又止,似乎不知从何说起。
狄公见状乃先开口道:“易员外,本县打算几日后邀请本地士绅名流来此聚会,届时我想与员外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今日本县公务繁忙,故而还请员外免去客套,有话但说无妨。”
易鹏闻言,遂深施一礼,开口道:“大人,在下是本地一船主,自然常去码头等处巡视,知晓那里一些事情,故今觉有义务禀告大人一件要事。近日一直有传言称大批兵器正从此城偷运出境。”
狄公闻言,即刻坐起,将信将疑问道:“兵器?运往何处?”
“回大人话,必是运往高丽。”易鹏答道,“易某听说高丽人因战败而十分怨恨,正谋划袭击我朝驻防军队。”
“员外是否知晓何人从事此项卖国交易?”狄公问道。
易鹏摇头道:“大人,十分遗憾,易某尚不知此是何人所为。但易某敢言,易某所辖船只绝对不会为此凶险阴谋所利用!当然,此事只是传言,但本地军塞防御使也已获知有关讯息,据说近日所有离港出海船只皆须接受严格检查方可出海。”
“员外若是获知什么音讯,休要忘了即刻通知本县。”狄公道,“在此,还要顺便向员外请教一事,不知员外对同行顾孟彬娘子失踪一事有何见教?”
“大人,此事易某不知,实在无可奉告。”易鹏答道,“不过,如今曹公必定十分后悔未将女儿嫁与易某之子!”
狄公听易鹏如此说,不觉为之一振,抬眼注视易鹏。
易鹏又道:“大人,易某乃曹公老友,我二人皆笃信儒学,不喜佛学。虽说我二人之间未尝提过儿女亲事,但据我两家关系,易某向来以为曹公会将女儿许配给易某长子。但不想三月前曹公之妻亡故,曹公忽然宣称要将女儿嫁与顾某。大人,你想,那姑娘年方二八,如花似玉,而那顾孟彬是个狂热的佛教徒,听人说他还要捐献——”
“本官知员外之意了。”狄公对家庭琐事毫无兴趣,故未待易鹏将话说完便道,“昨晚本县两名手下曾与员外手下管事薄凯会面,听说此人似乎非同寻常。”
易鹏见狄公问起薄凯,脸上显出赏识的神态,回道:“薄凯喜好饮酒,昨夜又饮了许多,半夜方归,但并未大醉。此人总是半醉半醒,也颇好吟诗,但其诗作甚是平淡无奇。”
“既如此,员外何以仍要留用此人?”狄公不解道。
“易某以为,”易鹏道,“这醉诗人有理财的天赋!大人,此人精通理财之道,算账速度之快令人不可思议。不久前,一日晚间,易某约薄凯一同查账,当时他坐在一旁,易某向他解释。但他未听几句,便从易某手中取过账册,迅速翻阅一过,并记下若干数字,然后便将账册交还与易某,又拿来笔墨纸砚,清清楚楚地将易某买卖收支情况书写于纸上,竟然无丝毫差错!次日,易某又命薄凯用六七日时间估算一下为海防要塞建造一艘战船所需的费用,不想薄凯竟在那日午后便将一卷写有估算费用的纸稿交付于我!易某因此得以赶在同行老友顾孟彬之前将方案提交与海防统领,轻易便获得了一笔造船的大生意!”易鹏说时得意之态溢于言表,末了又道,“只要薄凯不误事,心里想着易某,他愿饮愿唱,自由他去。薄凯聪明,做事敏捷,在下因此付给他极高的报酬。但易某不喜他是个佛教信徒,也不喜他与顾孟彬手下管事金桑往来。不过,薄凯信奉佛教,与金桑交往,此事对易某倒也无害,且有时尚可从金桑处获知不少顾孟彬生意的内情,回来报与易某,还颇有益于易某的生意呢!”
“员外,请勿忘告知薄凯,”狄公道,“叫他这几日择个时辰来见本县。本县在衙内找到个记事簿子,内有一些账目,本县想要听听他的高见。”
易鹏闻言,迅速望了狄公一眼,方欲开口询问,见狄公已起身告辞,只得也起身告退。
却说狄公辞了易鹏,即向书房而行,途中遇见马荣与乔泰。
二人上前施礼。马荣道:“禀报大人,那水门栅栏已修好。”接着又道,“回衙途中,我二人去那第二座桥近处大户人家询问,那些人家的仆役皆称未曾看见昨日晚间之事,只说附近住家有时会用大筐装载大包垃圾至河边,将之倾入河中。我二人心有不甘,又挨户询问,仍无人知晓我与乔泰所见之事。”
“看来此事已显而易见!”狄公说道,心中释然许多,“你二人现随我回房,金桑已在书房等候我等。”
狄公边走边将顾孟彬之妻失踪一事简要说与马荣、乔泰二人知道。
不一会儿,三人回到书房,只见洪亮在屋内正与一位眉清目秀、二十五岁上下年纪的青年说话。洪亮见狄公来到,便将身边年轻人介绍与狄公。狄公问道:“足下姓金,莫非具有高丽血统?”
“是的,大人。”金桑恭敬地说道,“金某生于本地高丽乡,从小生长在此。只因顾孟彬雇用许多高丽水手,金某通晓两国言语,所以顾孟彬便雇请金某为其管事,监管其手下高丽水手,并为其充当翻译。”
狄公点头称是,并随手取过洪亮递与的方才与金桑谈话的记录,细阅一遍,又将之传与乔泰、马荣,然后问洪亮道:“洪亮,那樊仲最后被人见到亦是在十四日吗?亦是在那日午后吗?”
“回大人话,正是如此。”洪亮答道,“樊仲田庄的佃户称樊仲于那日午饭之后即离开庄园,同行者尚有其贴身随从吴免,二人是向西面走的。”
狄公点点头,又道:“那曹鹤仙家亦位于同一地区。拿地图来,我且看此地究竟是何模样。”
洪亮取来地图,展开在书案上。狄公视之,以笔在图西部画出一个圆圈,指着图中曹鹤仙家宅处道:“且看此处,十四日,顾员外的新娘用了午餐即离开此地向西而去。新娘于第一个路口向右转弯。那么,金相公,其兄弟是于何处与之分离的呢?”
“是在经过一小片林地时,彼处是两条乡间小道会合之处,大人。”金桑答道。
狄公又道:“如今那佃户称樊仲亦是于那日午后离去,亦是向西而行。此处便有个疑问,为何樊仲不向东行,东行可直接通往城里,为何偏要舍近求远,向西绕行呢?”
“大人,从地图上看,向东行确实近得许多,”金桑道,“但此路崎岖不平,况且又路径不明,甚是难行,若逢雨天,更是无法行走。故而此路虽近,却比走大道绕行更费时间。”
“这便是了。”狄公道。说罢,拿起笔又于乡间小道与大道之间画出一个记号。
“我不信会有如此巧合之事,”狄公道,“我以为我等可假定顾夫人与樊仲在此处相会。金相公,你可知他二人从前可曾相识?”
金桑犹豫片刻道:“大人,金桑不知他二人是否相识。不过从图中看,樊仲庄园离曹公家不远,或许顾夫人未出嫁时曾与樊仲见过面。”
狄公点头称许道:“金相公所言十分重要。今后如何行事,本县尚须认真思考一番,因此今日便不奉陪金相公了。”
金桑起身告辞。
目送金桑离去后,狄公转身,意味深长地注视着三位手下,神情庄重地说道:“诸位若还记得那九华园酒店主人议论樊仲人品之言,我想问题便昭然若揭了。”
“看来那姓顾的找错了目标。”马荣做个鬼脸,言道。
洪亮却疑虑重重,慢慢说道:“大人,若是二人私奔,为何大道哨卡处卫卒不曾看见他二人呢?那哨卡前总有些士卒坐着,除了饮茶,便是注视过往行人。何况那些士卒一定认得樊仲,若是他与一名妇人同行,必定逃不过他们眼去。且樊仲随从吴免又怎样了呢?”
此时乔泰起身,看那地图道:“我看,不管发生何事,总是发生在这荒僻古庙之前。听那独臂店主说,这一带曾发生过许多骇人怪事!况且这一段乡间道路因有树丛遮挡,正好是哨卡士卒看不见的地方,不管是从樊仲庄园出来,抑或从曹鹤仙家走出,皆是如此。即便从顾娘子兄弟包扎腿伤的小农庄也望不见这段被遮挡的道路。看来顾娘子、樊仲与那随从均在这段路上化为轻烟消失了!”
狄公听众人说毕,忽地站起身来,说道:“我等不可仅在此书房中按图索骥,必要实地考察一番,并与曹鹤仙、樊仲佃户细谈之后方可心中有数。此时天色晴朗,正可外出前往彼处一看!有昨夜之经验,我想,今日白天出巡,且又骑马,去乡间必定十分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