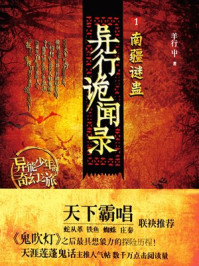次日,狄公起身时,见天色已晚,很是懊恼。匆匆用过早膳,便来到县令私宅办理公务。
狄公见到室内已被打扫得干干净净,靠椅已被修复,书案也被擦得锃亮,而且书案之上已整齐地摆放着狄公心爱之文房四宝,收拾得甚是细致。狄公心中明白,此乃洪亮所为。
狄公在卷宗室内见到洪亮。洪亮已同陶干一起,扫了地面,开了窗户,将阴湿的房间透好了气。二人还给红皮卷宗箱抹了蜡,故此房内蜡香四溢。
狄公心内满意,点头赞许,走到书案后坐下,命陶干将马荣、乔泰唤到房内。
狄公见到四名干事都到了案前,便先问洪亮和马荣二人情形如何。二人答道,前一夜打斗中所受之伤已不碍事。洪亮已将头上绑带换下,贴上了一张油纸膏药,马荣左臂也能活动,只是还不太灵便。
马荣禀报说,一大清早他便携同乔泰查看了县衙的兵器库房。库房中有许许多多兵器,剑戟盔甲一应俱全,然全都年久生锈,积满尘土,须好好擦拭方可使用。
狄公听罢,缓缓言道:“方达所言之事,听来似乎可信,倒是道出了此处怪异情形之缘由。若其所言全属实情,我们务须在钱牧探明我欲和他作对之前,就迅速有所作为,来个出其不意。古语云:‘恶犬不露齿,张嘴就咬人。’”
“我们该如何处置那个牢头?”洪亮问道。
“暂且留在那里,不要管他。”狄公答道,“我当时灵机一动,将那厮锁了起来,倒也合该我等走运。那厮分明是钱牧爪牙,若非将他投入牢中,他早就跑到主子面前禀报我等全部情形了。”
马荣张嘴意欲问话,狄公举起手臂,令其勿言。而后,继续说道:“陶干,你即刻就出县衙,尽你所能,多多打探钱牧及其手下底细,还要一并查问一位富人的情形。该人名唤余基,是朝廷著名旧臣余寿乾之子。余寿乾约九年前已于兰坊过世。
“我则和马荣去到城中打探城内大体情形。洪亮与乔泰留在县衙之内,总理一应事务。县衙各门要把实锁严,我离衙期间,除管家可去街市采买食用之物外,任何人都不得进出县衙。我们午时时分在此处相会。”
狄公站起身来,戴上一顶黑色小帽,穿上一领素净蓝袍,看似一位悠闲自得、学识渊博之士绅。
狄公步出县衙,马荣则于一旁跟随。
起初,两人向南慢慢踱去,看了看名闻遐迩的兰坊九层宝塔。该塔位于荷花池中小岛之上,荷花池沿岸棵棵垂柳在晨风中微微飘忽,煞是动人。狄公、马荣心中有事,无意驻足,便转身向北,混杂于人群之中。
如往常清早一般,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大街两旁的店家也生意繁忙,只是很少听见笑语欢声,百姓们都压低声音说话,且说话前还要迅捷地左右张望,显出小心翼翼的模样。
狄公和马荣行至县衙以北的双座牌楼,又向西拐去,慢慢走到鼓楼前的市廛。该市廛别有一番有趣景象,可看见来自边界那边的商贩,他们身着色彩艳丽异装,声音粗哑地夸耀着自己的货物;还不时见到天竺游僧化缘。
一群闲汉围着一个鱼贩,看着他和一位衣着整齐的年轻男子大声争吵。一看便知,那鱼贩向那后生多索了银钱。最后,那后生将一把铜钱扔进鱼贩的篓里,愤然叫道:“倘若此地管辖有方,你岂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欺诈良善?”
话音未落,一个肩宽腰厚的汉子迈向前来,猛地将后生拧转身,当脸就是一巴掌。
“这巴掌让你领教中伤钱大人的后果!”他大声吼道。
马荣欲上前干预,可狄公伸手搭在他臂膀之上,将其制止。
围观之人见此情形,连忙四散而走。那后生则一言不发,抹去嘴上血迹,径自离去。
狄公向马荣使了个眼色,二人便尾随那后生而行。
后生走进一条僻静小巷之时,狄公紧走几步,赶到他身边,说道:“恕在下冒昧。适才我碰巧见到那泼皮如此凶狠地对待你,你为何不将他告到县衙?”
那后生听此言语,即驻足不前。他满腹狐疑地将狄公和那魁梧健壮的扈从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
“倘若你们是钱牧的奸细,”他冷冷地说道,“你们倒要等些时日,我才会再自寻倒霉。”
狄公将小巷从头至尾扫视了一遍,只见小巷之内别无他人。
“后生可是大错特错了,”狄公平心静气地说道,“我乃本地新任县令狄仁杰是也。”
后生听罢,脸色灰白,好似见了鬼怪一般。随后他用手摸了一摸额头,定下神来,长舒了口气,眉眼舒展,乃至笑容满面。他深作一揖,恭敬地说道:“晚生姓丁名浩,现为贡生,祖籍长安,乃丁虎锢将军之子。大人大名,晚生久仰,如此一来,兰坊可得了位名副其实的县令了。”
狄公将头微微一侧,以示赞同。
狄公依稀记得,丁将军数年前遭了厄运。当时北部边境胡寇来犯,丁将军率军战而胜之。未料班师回朝之后,不仅未得封赏,反遭罢黜。狄公心中寻思,丁将军之子何以来到此僻远之地?遂对后生言道:“此处形势极不正常,我想请你多将此处情形实言相告。”
丁浩并未立即作答。他沉思片刻,而后言道:“公众场所,人多眼杂,非说话之地。能否有幸邀二位同饮香茗?”
狄公应允。三人来到小巷街角茶肆之内,找一无人茶桌坐下。
伙计上茶毕,丁浩压低声音说道:“兰坊有个恶霸,名唤钱牧,集全县大权于一身,全县无一人敢与他作对。钱牧在府中豢养了百来名打手,他们整日无所事事,只是东游西逛,恫吓良民百姓。”
马荣问道:“这帮东西都使用何种兵器?”
“这帮无赖到得街中,常拿些棍棒刀剑。但若说钱府之中各式兵器样样俱全,我丝毫不以为怪。”
狄公问道:“城中是否常见边界那边过来之胡人?”
丁浩使劲摇头,答道:“晚生从未见过一个胡人。”
狄公对马荣说道:“看来钱牧向朝廷奏报胡人来犯之说,纯系信口胡诌,意在使朝廷相信,兰坊缺他钱牧不可。”
马荣问道:“丁公子可曾进过钱府?”
书生闻听此言,失色惊呼:“此事苍天不容!晚生平素对那去处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会去?钱牧将其府第用里外两层墙围得严严实实,那府第四个角上还盖了哨楼,实像一座兵营,晚生怎会去自投罗网?”
狄公问道:“钱牧如何篡得兰坊大权?”
丁浩答道:“钱牧从其亡父手中继承了万贯家财,却没继承他一丁点儿的节操德行。钱父乃兰坊本地人氏,为人诚实勤勉,靠经营茶叶发了大财。直到数年之前,通往西域于阗等诸国之官道还穿兰坊而过,故此城乃交通要塞、边陲重镇。后来沙漠通道沿线之三片绿洲干涸成荒漠,官道向北移了三百余里。钱牧乘机网罗了一帮无赖,俟时机成熟,便自封为兰坊之首。
“此人聪明而有决断,倘若从军,自会战功卓著。可他自恃才高,目中无人,要当兰坊不容争议之首领,而不愿受朝廷丝毫管束。”
“如此情形真乃兰坊之厄运也。”狄公说道。言毕,尽饮盅内之茶,起身要走。
丁浩忙俯身向前,乞求狄公再稍坐片刻。狄公迟疑一会儿,但见后生十分悲苦,才又坐回椅上。丁浩忙不迭地将茶斟满,显得不知从何说起。
“若心头有事,”狄公说道,“丁公子只管道来。”
“实不相瞒,大人,”丁浩终于说道,“有一事始终重重压在晚生心头。此事与恶霸钱牧无丝毫干系,只是晚生家事。”
说到此处,丁浩顿了一顿。马荣此时坐在椅上已烦躁不宁了。
“大人,有人意欲谋害家父!”
闻听此言,狄公扬起双眉,言道:“尔既预知此事,就不难制止罪行发生!”
后生摇头,说道:“请大人恩准,听晚生细说其详。大人也许听说,当年我那年迈老父曾遭其刁滑部将吴棣陷害。吴棣忌妒家父出师平北,战绩卓著,竟上奏章诬告我父。尽管吴棣拿不出真凭实据,兵部还是将我父革职为民。”
“令尊遭罢黜一事,我倒是记得。”狄公言道,“但不知令尊是否也居住在此城内?”
“家父是在兰坊,”丁浩答道,“一则因为家母系兰坊本地人氏,二则是要避免在大都邑内遇见往日同寅而不堪窘迫,以为在此边远地区可以安稳度日。
“岂料一月之前,晚生见到几个形迹可疑者常到敝舍附近转悠。数日之前,我暗中尾随其中一人,到得本城东北一隅之一家酒肆,此酒肆名为‘永春’。晚生向此街上别家店铺询问得知,吴棣将军长子吴峰投宿于那家酒肆楼上。晚生惊诧之情实在难以言表!”
狄公显出不解模样,问道:“吴将军已毁了你父前程,为何还要遣子前来滋扰令尊?如继续作祟,只能为其招致祸患。”
“晚生知其所为何来!”丁浩难抑心中焦虑之情,愤而言道,“吴棣那厮获知家父在京都的旧友故交已查获证据,当年吴棣上本参奏之事纯属捏造。如今他遣子至此,意图谋刺家父,以便自己苟延残喘!大人对吴峰此人还不甚了解。此人嗜酒如命,行为放荡,更喜施暴动武。他雇用市井无赖打探我家情形,一俟有机可乘,便会下手。”
“即便如此,”狄公说道,“我也无由插手,只能劝你密切注意吴峰行止,并在府中做些举措,小心提防。只是你可曾觉察吴峰与那钱牧有何瓜葛?”
“这个晚生倒未曾查得,”丁浩答道,“表面看来,吴峰尚未有依仗钱牧行凶之举。说到防范之道,家父因解甲返乡以来,收到多封恐吓书信,故一直深居简出,府门上锁,日夜落闩。除此之外,还将书斋门窗全都用砖砌死,只留扇便门进出。此门只有一把钥匙,由家父随身携带。家父进得书斋,就落下横闩,将门关严,在书斋内撰写《边关征战史》以消磨大部分时光。”
狄公吩咐马荣记下丁府府址。丁府离此茶馆不远,一过鼓楼即是。
狄公起身,行前对丁浩说道:“如再有风吹草动,务去县衙禀报。我亦须起身离去。你须明白,目下我本人在城内的处境亦不安妥。待我料理完钱牧之事,自当立即处置你家事务。”
丁浩谢过狄公,引狄公来到茶肆门口,而后深作一揖,辞别而去。
狄公和马荣行回大街。马荣说道:“这年轻后生倒令我想起杞人忧天之掌故。”狄公摇了摇头,忧心忡忡地言道:“此事好生奇怪,也着实令人心中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