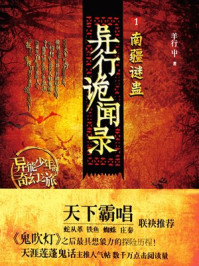乔泰诧异地看着城门,那城门大得惊人,城门上面是高高的城楼。此时,他记起兰坊是座边陲城镇,得防备西部草原上的胡人突然来袭。
乔泰用刀柄猛敲包有铁钉的城门。
过了好大一阵工夫,城楼之上一扇小窗的窗扉才打开来,传出嘶哑的喊声:“入晚不开城门。明日请早!”
乔泰敲得城门雷鸣般响,喊道:“开门!县令大人驾到,快快开门!”
“哪位县令大人?”那声音问道。
“兰坊新任县令!”
城楼之上,窗扉啪地关上了。
马荣拍马骑到乔泰身边,问道:“为何耽搁许久?”
“懒狗们睡着了。”乔泰鄙夷地说道。他边说边用刀连续敲打城门不止。
乔、马二人听到铁链的叮当声,随后,沉沉的城门开了几尺。
乔泰纵马闯入城内,差点儿踢倒两个衣着邋遢、头盔满是灰尘的兵卒。
“将城门大开,懒狗!”乔泰厉声喝道。
兵卒们狠狠地看着两个骑马者,其中一个张嘴要说些什么,可是看到乔泰脸上那恶狠狠的模样,就改变了主意。无奈,他和同伴一起将城门推开。
车队穿过城门,沿着漆黑的大街向南而行。
只见城内凄凉一片,景色萧条,大多数店家都用厚实的门板关了店铺。
零零落落一小堆、一小堆的人围着街头小贩的油灯,车队过去之时,他们转过身子,漠然地对着马车看了片刻,之后又转过身去继续吃那碗中面条。
无人出来迎接新任县令,也不见丝毫迎候的迹象。
车队穿过一座牌楼。此时,大街沿着一堵高墙分成左右两半。马荣和乔泰思忖,这便是县衙的后墙了。
他们沿墙向东,到得一扇大门跟前,门上挂着一块风侵雨蚀的木板,上面刻着四个大字:兰坊县衙。
乔泰甩镫下马,使劲叩门。
过了一阵,一位身穿补丁长袍的矮墩墩的男子出来将门打开。
他胡须乱蓬蓬的,脏而油腻,双眼极斜,模样甚是吓人。他提着一盏纸灯笼,照着乔泰,打量了一番后继而吼道:“你这兵痞,岂不知衙门关着?”
乔泰哪里受得住这些,他伸手拽住这男子的胡须,狠劲搡其脑袋,通通通地往门柱上撞,直到听得哭喊求饶方才松手。
乔泰厉声叫道:“新任县令狄大人驾到,快快开门,速速传齐衙门一应人众!”
那厮急急忙忙地打开两扇衙门。车队穿门而过,到宽敞的接客大厅前面大院之中停下。
狄公下得车来,环顾四周,只见接客大厅的六扇门都落闩上锁,对面衙厅窗扇也都一一紧闭,院内一片漆黑,空无一人。
狄公双手插袖,命乔泰将门丁引来问话。
乔泰揪着门丁衣领,将其拽到狄公跟前,那矮墩墩的家伙慌忙跪倒在地。
狄公简要地问道:“你系何人?卸任的邝大人现在何处?”
该男子期期艾艾地答道:“小人乃牢头。邝大人今日一早出南门而去。”
“县衙印信现在何处?”
“印信定放在衙厅内的某个地方。”那牢头答道,吓得声音直颤。
狄公再也按捺不住,顿足喊道:“县衙守卒何在?班头何在?刑房书办何在?书吏何在?这县衙之人都到何处去了?”
“班头上月就已离去,书吏已告病假二十余日。”
“如此就只剩下你一人了?”狄公打断他的话头,随即转过身来向乔泰说道:“将此牢头下到他自己监管的牢中。我要亲自弄个明白,堂堂县衙何以弄成这等光景?”
牢头意欲开口申辩,可乔泰猛地打他耳光,并将他双手反绑。随后,乔泰将牢头拨转身子,又踢上一脚,厉声喊道:“前面引路,去你的牢房!”
县衙左厢,在空荡荡的衙卒下房后面,他们来到一宽大的牢房。一眼便知,牢房已许久不用,然牢门看起来仍很牢固,且牢窗之上安有铁栅。
乔泰将牢头推入一间小牢房,随手将牢门锁上。
狄公说道:“我们且去看看公堂和衙厅。”
乔泰提起灯笼引路。他们一路行来毫不费力地寻到公堂的两扇大门。乔泰用手将门一推,门晃了开去,锈迹斑斑的铰链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乔泰将灯笼高高举起。
面前的宽大厅堂空空如也,地面的青石板上覆盖着厚厚的尘土,只见盖公案的红布已破旧褪色。一只硕大的老鼠急急地逃了开去。
狄公向乔泰招手示意。随后,狄公走上案台,绕公案走了一圈,又将遮门帷帘拉到一旁,可灰土纷纷扬扬地落了狄公一身。此门通往大堂之后县令内室。
内室之中除一张快要散架的桌子、一张坏椅子和三张木制小凳外,空无一物。乔泰将对面墙上之门推开,一股阴湿的气味向他们袭来。只见沿墙立满书架,架上堆放着成排的公文案卷皮箱,皮箱因发霉而成了绿色。
狄公摇了摇头低声叹道:“这些案牍竟弄到这等田地!”
狄公一脚踹开通向走廊之门,一言不发地走回大院。乔泰则手提灯笼在旁引路。
马荣和陶干已将抓获的强人锁进牢中,三具强人的尸体则搁在衙卒住地。狄公的仆人忙忙碌碌地在管家的率领下从车上搬卸行囊包袱。管家向狄公禀报道,县衙后部的县令居所完好无损,整洁干净。卸任而去的县令离任之时,房内物品井井有条,房间已经打扫好,家具用品也相当洁净,狄公的厨子正在生火做饭。
狄公闻听此言,不由得舒了口气,至少他的妻室儿女有个栖身之所。
狄公命洪亮和马荣退下,他们可以到内宅的厢房打开铺盖,暂且歇息。之后,他向乔泰和陶干招手,示意他们随自己而行。三人一同来到空无一人的县令私宅。
陶干点燃两支蜡烛,放于案上。狄公小心翼翼地坐进那把摇摇晃晃的扶手椅中,两名干事则吹掉脚凳上的灰土,也蹲身坐下。
狄公交叉双臂,支于案上,一时间竟无人言语。
三人这般模样在此室中,场面颇为奇特。三人还都穿着赶路的灰色袍服,经和强人打斗后,袍服都已撕破,并沾满泥土。烛光摇曳之中,三人都显现疲惫憔悴之态。
倒是狄公先开口说话:“二位老友,时辰已晚,而我等既乏且饿,本该早些歇息,然我看到此处情势甚为怪异,故还想和二位商议。”
乔泰、陶干频频颔首。
狄公继续说道:“该城甚是令我费解。我之前任居住于此整整三载,居所干净整齐,完好无损,却从未使用县衙大堂,这点显而易见。彼又将县衙之内一应人等全都遣散回家,想必报信之人早已投书于他,报称我等将于今日下午抵达兰坊。尽管如此,彼却不留一纸文书给我就离任而去,而把县衙印信交与一个流氓般的牢头,且辖区内的其余官员对我等到任亦不予理会。依二位之见,这究竟如何解释?”
“大人,”乔泰问道,“是否此地的刁民图谋反抗朝廷?”
狄公摇头。
“确实,”他答道,“天色尚早,兰坊城内就已空旷无人,店铺也闭门停业,此情实属异常。不过,我等未见骚动迹象,也无蒺藜路障或要动刀动枪的气氛,街内百姓态度也无敌意,只是冷漠些罢了。”
陶干忧心忡忡地捻着左脸黑痣上长着的三根稀毛,说道:“我一时以为,或是时疫,或是某个流行险症正在本地肆虐。可百姓们丝毫不惊不慌,还在街市上安闲地吃面喝汤,此情此景和我的忧虑甚是不符。”
狄公用手指梳理了一下头发,除去长长的鬓须上沾着的几片干树叶,之后稍待片刻,又说道:“我不愿向那牢头询问,那厮长得一副泼皮模样,令人生厌。”
管家进到室内,身后紧跟着狄公两名家人。其中一人端着数碗米饭和汤菜,另一个则提着一大壶茶水。
狄公命管家叫人给狱中犯人送饭。之后,三人低头用膳,并不言语。
三人草草饭毕,又喝了盅热茶。乔泰捻转短须,沉思着坐了片刻,然后开口说道:“大人,我和马荣之见全然相同。我们在城外山内之时,马荣言道,打劫我们的这路强人不像专行劫道的响马。我们何不问问那伙强人此处的情形?”
“此主意甚好!”狄公喜道,“快去查清谁是头领,速速将他带来。”
少顷,乔泰手持铁链回来,链上拴的不是别人,正是那名挺枪欲刺狄公的强人。狄公犀利的目光扫视了一下来人,只见他身体壮实,五官端正,相貌开朗,看来更像小店铺的掌柜或匠人,不像劫道的响马。
他在狄公案前跪下,狄公简言命道:“你姓甚名谁,做何营生?”
那人恭敬答道:“小人姓方名达,我家祖辈数代均在这兰坊城中居住。小人也一向以打铁为业,不久前才更换营生。”
狄公问道:“你原本从事年代久远且又体面的营生,为何去当那拦路行劫见不得人的强盗?”
方达低头,闷声答道:“我拦路行劫,意欲行刺,确属有罪,小人供认不讳,无须再要证词。小人十分明白,不日就要身首分离,大人又何必费心再加盘问?”
方达言辞之间透出绝望之意,狄公却不紧不慢地说道:“本县在犯人彻底招供之前,从不将其定罪。你且高声些,回我问话。”
方达回道:“小人自幼随父学艺,当铁匠已三十余载。我同拙荆生有一子二女,全家个个身健体壮。我们一日三顿,饭餐不愁,且时时还有猪肉佐餐,小人自觉日子过得尚且美满。谁知,一日祸事降临,钱牧手下见犬子年轻体壮,强行将他掳去为钱牧当差。”
“这钱牧又是何许人?”狄公打断他的话头,问道。
方达恨恨地答道:“钱牧何人不是,何恶不作?自他篡夺兰坊大权以来已八载有余。如今一半的田地和四分之一的店铺房屋都归他所有。他既是县令,又是兰坊官兵首脑,集军政司法大权于一身。他按时给州衙官员送去行贿财物。州衙离此地甚远,骑马要五天行程。他说道,若非他钱牧在兰坊,边界那边的胡人早就来犯了,而那帮污吏也都信了他的鬼话。”
“对此种犯法乱纪之事,我之前任都默许了不成?”
方达哼了一声,答道:“到此地任职的几任县令很快就明白,将全部权力拱手交给钱牧,安心当钱牧的影子要舒适安全得多。只要他们安心充当傀儡,钱牧就每月都以厚礼相酬。这些老爷都过得安泰舒适,却苦了我们平头百姓。”
狄公冷冷说道:“你之所言听来甚是荒唐!确实,地方上的恶霸偶尔也能篡了边远城镇的大权,此实属不幸之事。更不幸者,有些县令软弱无能,竟然也接受了这种目无王法的安排。可是依你所言,八年之中几任县令都屈服于钱牧的淫威,本县岂能相信?!”
方达冷嘲道:“如此说来,我等兰坊百姓天生命苦!四年之前,有一位县令要和钱牧斗上一斗,岂知,只过了半月,他就身首分离,暴尸于河岸之上了。”
狄公突然俯首向前,问道:“这位县令可是姓潘?”
方达点头。
狄公继续说道:“当时有人向朝廷奏本,报称回纥游牧部落兴兵犯境,潘县令率兵与之奋战,为国捐躯。本县记得当年潘县令的尸身按军旅礼仪移至京师下葬,并被追封为刺史。”
“钱牧就以此法掩盖其杀人罪行,”方达冷冷地说道,“我知事情之原委,潘县令尸身我也曾亲眼见到。”
“往下讲来!”狄公说道。
“就是这样,”方达继续说道,“我之独子被迫加入那伙恶徒,钱牧将其用作家丁,故而我再也未能见他一眼。
“不久,一个干瘪老太婆找上门来,这人是钱牧派来的牙婆,言称钱牧愿出十锭白银换娶我长女白兰,我自然一口回绝。三日后,小女去到集市就再也没有回转。小人几次三番去到钱府,央求得见小女一面,可每次都遭到毒打,被赶离钱府。
“失去独子和长女之后,拙荆一病不起,于半月前去世。小人抄起先父留下的宝剑,径往钱府。钱府家丁将我截住,一顿棍棒将我打昏,之后便把我当死人扔在街心。七天之前,一帮恶徒放了把火,烧了小人店铺,我因无处容身,只好带着二女儿离开兰坊,到得城外山内,和一帮走投无路之人结伙。今晚我们首次出动打劫过往行人,没想就一败涂地。大人所擒之女子,即是小人次女。”
室内寂然。狄公正欲将身子往后仰靠在椅背之上,忽然想起椅背已坏,故忙将双肘重新撑到案上。狄公又言道:“你所言之事,我已耳熟能详——常常在遇到这类哀戚之事后才去当强人,才会打劫被捉,然后在公堂之上和盘托出。倘若你以谎言欺骗本县,你定会被绑赴刑场,砍去脑袋。若所言皆是实情,本县自会延期判案,酌情处置。”
“我已无活命之望。即使大人不砍小人之头,钱牧也必会杀死小人,左右都是死。小人的同伙都遭受过钱牧残害,想必下场也都一样。”
狄公向乔泰使了个眼色,乔泰站起身来,将方达押回牢中。
狄公起身离座,在室内来回踱步。乔泰回来之后,狄公停住脚步,忧心忡忡地说道:“方达所言之事分明都是实情。兰坊城内地方恶霸猖獗,县令毫无权能可言,不过是傀儡罢了。城内百姓态度怪异,缘由就在于此。”
乔泰气得用拳捶腿,愤然说道:“我们非向钱牧那恶棍低头不成?”
狄公淡然笑道:“时辰已晚,你等二人还是退下去,好好睡上一晚,明日我还有许多事要烦二位去做。我则还要待上半个时辰,翻阅旧时卷宗。”
陶干、乔泰欲留下相帮,狄公执意不允。
二人刚刚离去,狄公就手持蜡烛,进到隔壁室内。因为白天赶路,袍服沾满尘土,狄公遂用袍袖拭去卷宗箱标牌上的灰土霉迹,仔细察看,发现最新的档案也属八年之前写就。
狄公将此箱搬入自己的室内,取出内中物品铺于书案之上。
狄公熟悉此类案牍,目光老到,只需片刻,就认出其中大多属县内日常行政事务。然在箱底却见一小卷卷宗,上写“余氏兄弟诉讼案”,狄公坐下,打开卷宗,快速地过起目来。
看毕才知,那是一桩牵涉遗产继承的讼案。九年之前,告老归隐的按察使大人余寿乾身故兰坊,身后二子为争遗产而对簿公堂。
狄公合上双眼,忆起十五年前在京都任书吏时的往事。其时余寿乾名闻华夏,他才能超群,清正廉明,为国为民,不辞辛劳,因而赢得了“仁爱之官,为政英明”的好名声。后来圣上委其以按察使之职,余寿乾却突然声称体弱多病而辞去所有官职,到一边陲城镇潜迹隐踪安度晚年。皇上亦曾要其重做考虑,然余寿乾固辞不从。狄公记得清楚,当时余寿乾突然辞朝,确在京城引起不小震撼。
如此说来,余寿乾人生中最后几年便是在兰坊度过的。
狄公再次缓缓展开此案卷,从头至尾细细看来。
据案卷说,余寿乾到兰坊过退隐生活之时,年逾花甲,已鳏居数年,膝下有一独子,名唤余基,其时恰逢三十。到兰坊之后不久,余寿乾便续了弦。他选中一位年方十八的农家女儿为妻,其妻娘家姓梅。婚后,老夫少妻生下余门次子,此子名唤余杉。
后来这位朝廷旧臣一病不起,明白自己行将入土,遂把长子余基及少妻幼子唤至病榻之前,吩咐道,他亲手所绘一轴画卷将留给孀妻和次子余杉,所剩其余财产则通通归长子余基所有。他又嘱咐说,余基务必要使其后母及异母兄弟得到其分内之物。交代完毕,老人便咽了气。
狄公看了看案卷上的日期,断定余基现年四十多岁,那寡妇三十有余,其子为十二岁。
案卷记载道,余基将父亲遗骸下葬之后,马上就将后母和余杉赶出府门,言道,其父临终遗言分明暗示这孩童非他所生,故自己并无责任要为这幼童和不贞的后母承担丝毫责任。
故此,梅氏一纸诉状告到县衙,否认其先夫有此遗言,并要求按照常律,分给其亲子一半财产。
这时,钱牧刚刚在兰坊确立权势,因此县衙并未做任何举措来了断此案。
狄公将案卷卷起,心内忖度,乍一看来,那寡妇的讼词并不有力可信。那位朝廷旧臣的临终遗言,加上他和续弦之间的年龄差距,似乎都在暗示梅氏夫人确曾对其丈夫不忠。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像余寿乾这样一位年高德劭的能人,选此荒诞之法来宣称余杉非其亲生骨肉,实是不亦怪哉!倘使他果真发觉少妻对他不贞,他也该会悄悄地将她休掉了事,然后将她和幼子送至偏远之地。这样,既保住了自己的名誉,亦使余家显赫的声望免遭耻辱。他又何必要用此怪异之法遗赠画卷给她母子?
余寿乾没留遗书,也实属蹊跷。余寿乾为官多年,自然知晓口述遗言常引得兄弟阋墙,家庭不睦。
这案子有多处症结,需要仔细勘查。兴许,了断此案也能使余寿乾突然辞官之谜真相大白。
狄公再次翻查卷宗,却再也找不出与“余氏兄弟诉讼案”相关的卷目,也没找到可用来对付钱牧的证据。
狄公复将案卷放回箱内,坐于案前,沉思良久,心中揣度有何办法可以剪除钱牧。可是,狄公的思绪时时回到那朝廷旧臣和他那荒诞的遗言上。
一支蜡烛“毕剥”一声,蜡尽灯灭。狄公叹了口气,举起另一支蜡烛,走回内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