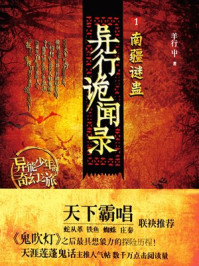次日上午,陶干正穿越县衙大院往狄公私宅走去,见马荣双手抱头,曲身坐在一石凳之上,便站停看那一言不发的马荣,问道:“仁兄身体有何不适?”
马荣举起右臂随便挥了挥,头也不抬,嘶哑着嗓音答道:“仁兄只管忙去,我要在此歇息歇息。昨日夜间,我与那吴峰饮了几盅,后因夜色已深,故留在那酒店之中住了一宿,希冀多打探到吴峰之所作所为。我刚回县衙不久,故而有些疲乏。”
陶干将信将疑地看了马荣一眼,不耐烦地说道:“随我同去,我正要向大人禀报,你须前去听听,还须看看我拿了何物回来。”
陶干边说边拿出一油纸小包。马荣无奈,好不情愿地站起身来。二人穿过大院,进到狄公私宅之内。
狄公坐在书案之后埋头审阅公文,洪亮则坐在私宅一角呷着香茗。狄公抬起头来问道:“二位,那画师昨夜可曾出得酒店?”
马荣见问,抬起大手直搓前额。
“大人,”马荣愁眉不展地回道,“我目下头痛得紧,好似装满一头石子。禀报之事还得劳烦陶干!”
狄公注视马荣,见其面容憔悴,遂不多问,转过身来听陶干禀报。
陶干将其尾随吴峰到“三宝寺”一事,以及吴峰之奇特行止原原本本地讲述一遍。
陶干禀报毕,狄公无语,紧锁双眉沉思片刻,然后言道:“如此说来,那年轻女子未曾露面!”
洪亮与陶干闻言,皆面露惊诧之色。马荣尽管身体不适,亦想听个究竟。
狄公拿起吴峰所赠之画,起身将画展于书案上。用镇纸压住画之两端,又取过数张宣纸将大半画面盖住,只露出观音菩萨面容。
狄公命道:“诸位过来细瞧此脸!”
陶干与洪亮站起身来,低头观画。马荣亦起身离凳,然又旋即坐下,面露疼痛之色。
陶干看了一阵,缓缓言道:“大人!此脸绝非常见观音面容。佛门女菩萨之脸向来画得恬静而不露声色,然此画上乃一生气勃勃的年轻女子。”
狄公闻言,面露喜色。
“正是如此,”狄公高声说道,“昨日我遍观吴峰之画,只觉所有观音菩萨不但相貌相同,且颇富凡人气息。我以为,吴峰定是深爱一名女子,其面容不断出现在他脑中,故吴峰所画之菩萨都是此女相貌,而自己却未曾察觉。既然吴峰画艺甚佳,此画定是那神秘女子的精妙画像无疑。我断定,吴峰正是为此女子而滞留兰坊。从此女子身上兴许能找到线索,可以弄清吴峰与丁将军遇害一事有何干系!”
洪亮道:“要寻找这女子并非难事,我们不妨去那寺庙四周转转。”
狄公道:“此法甚好。尔等三人须将此面容熟记,以便辨认。”
马荣呻吟着站起身来,看了一眼画像,又用双手压住太阳穴,合紧双眼。
陶干嘲讽道:“我们的酒仙有何不适?”
马荣并不恼怒,睁开双眼慢慢言道:“我定是见过这位女子。不知何故,我看此相貌甚是面善。然我苦思冥想,也记不起在何时何地见过此女子!”
狄公复将画轴卷起,言道:“待你头脑清醒时兴许能回想起来。陶干,你手中所持何物?”
陶干小心翼翼地打开小包,包内有一木片,木片之上贴着一方小纸。陶干将木片置于狄公面前,说道:“大人须仔细,这薄纸仍潮湿未干,极易撕破。今日清晨,卑职揭下余大人画轴衬里之时,见得此纸糊于画轴缎边衬里之后,纸上所写正是余大人遗言!”
狄公俯身看那蝇头小楷,脸色骤变,然后将身子靠在椅背上,气得直拽胡须。陶干摊了摊手,显出一副无奈的模样。
“大人,相貌常给人错觉。那余夫人一直在戏弄我等。”
狄公将木片推至陶干面前,冷冷地命道:“高声念来!”
陶干听命,念道:“本人余寿乾,自知不久于人世,特立遗嘱如下:本人填房梅氏向来为妇不贞,其所生之子非我骨血,故本人全部遗产均归余之长子余基所有。余基须好生照顾家产,扬我余家之遗风。立嘱人余寿乾(签字并盖章)。”陶干停顿片刻,继而言道,“我自然已将此遗嘱上之印鉴与余大人画轴之印鉴做了比较,两个印鉴全然相同!”
室内一片寂静。
不过片刻,狄公俯身向前,以拳猛击书案,言道:“全然错了!”陶干不解地看了洪亮一眼,洪亮微微摇头,马荣则瞪大眼睛望着狄公。
狄公叹了口气,说道:“我来说明我何以确信其中定然有假。余寿乾远见卓识,聪明过人,我依此推断,他必定明白其长子余基心术不正,而对其异母幼弟忌恨万分。余杉出世之前,余基素来自以为是余家唯一后嗣。因此余大人行将就木,想的必然是如何保护年轻的夫人及幼小的次子,使其免受余基诡计之害。
“前按察使大人明白,即便他将家财在二子之间平分,更不用说不给余基家财,余基必定会伤害其年幼异母兄弟,甚至可能杀了余杉来夺取那份遗产。故而余大人表面上并不分给余杉财产。”
洪亮听了点头,又意味深长地瞥了陶干一眼。
狄公又道:“余大人在其画中隐藏着把大部分家财留给余杉的真实用意。从老按察使大人在留遗言时所采用的古怪方式,就能看出端倪。余大人说得明白,画轴须归余杉所有,而余下之物归余基所有;他不说明这‘其余’二字究竟所指为何,可谓用心良苦。前按察使大人想借此暗藏之遗言保护幼子,直至其长大成人,继承遗产。余大人希望,约莫十年之后有位聪明县令能解开画轴之谜,使余杉应得的那份遗产物归原主。他嘱其遗孀将画轴交给每位到任的新县令验看,正是为此。”
“大人,”陶干插话道,“兴许余大人从未有过这等吩咐,我们不过是听了余夫人的一面之词。依卑职之见,此遗书说得明白,余杉乃私生子。余大人心地善良,宽宏大度,意在免使余基为其复仇。同时,余大人又欲在适当时机使真相得以大白,故而把遗书藏在画轴之内,等哪位新任县令发现了遗书,就可以以遗书为凭,驳回余夫人诉余基之状纸。”
狄公仔细听罢此番言语,问道:“余夫人企盼解开画轴之谜,你又作何解释?”
陶干答道:“凡女子都以为,男子若是深爱自身,便会体贴入微,处处为之着想。女子往往高估此事。卑职深信,余夫人指望余大人出于仁爱会在画轴之内藏一银票或一纸文字,指点其寻得藏匿好的家财,补偿其所失之一半家产。”
狄公摇头道:“你之所言听来倒也有理,然与余大人之为人甚是不符。我确信,此遗言为余基仿造而成。我想余大人在画轴之中曾藏了一封不甚要紧之遗书来蒙骗余基。我先前已说过,余大人若使用此画轴来藏匿至关紧要之文书,不免过于笨拙,以余大人之智,绝不会有此愚笨之举。依我之见,在此虚假证据外,余大人必定在画轴中藏下真实遗言。余大人担心,余基若疑心此画轴中藏有珍贵之物,必会将其毁掉,故而在画轴内衬中安下一纸文字,故意让余基找到,以此法来确保余基在找到文书后,不会再去找寻那真实遗言。
“余夫人对我言道,余基拿走此画,留了七日有余方才归还余夫人。余基自有充裕时间寻找画中所藏之文书。且不论此文书上写了何种言语,余基定是以此假遗书将其取代。那样,不论余夫人如何处置此幅画轴,他都可以高枕无忧了。”
陶干点了点头,说道:“大人之说,卑职听来也确实有理,然卑职还是以为,卑职之说更为简单明了,合乎案情。”
洪亮道:“卑职以为,要弄到余大人手迹来对比一番,原本并非难事。然而不巧的是,余大人在画上所题之字乃篆体。”
狄公忧心忡忡地言道:“我早已打算拜访余基,今日午后便去设法弄得余大人日常手迹和印鉴样品。洪亮,你即刻拿我的名帖去到余府,就说我想登门造访。”
洪亮和陶干、马荣起身离去。穿过衙院之时,洪亮说道:“马荣,你现在需要一壶热乎乎的浓茶,喝上几盅,酒自然会醒。在你酒醒之前,我不愿你离开县衙而去。”
马荣称是。
到得衙役值房,三人见方班头正坐在方桌旁与其子说话。方班头之子见三人进来,忙起身让座。
众人坐定后,洪亮命当值衙役取来一壶浓茶。闲聊数语之后,方班头说道:“三位爷进来之时,我正与犬子计议应往何处找寻我长女下落。诸位有何高见,望不吝赐教。”
洪亮呷了口茶,缓缓言道:“方班头,在下本不想提起刺痛你内心的话题。既然你提起此事,我倒要说,令爱可能已与意中人一起远走高飞,也未可知。你须估计有此可能。”
方达听了,使劲摇头,言道:“在下长女与小女儿大不相同。黑兰任性有主见,仅长到膝头高矮时,便知该做何事,并知如何去做。黑兰原该生成男儿身;相反,我之长女为人宁静,素来听话,性格温和柔顺,从未想过要找个心上人,更不用说与之私奔了。”
陶干说道:“既然如此,恐怕我等须做最坏打算,是否有人将她掳去卖给了青楼?”
方班头凄然点头,叹道:“陶兄所言甚是有理,在下亦以为须查查那些风月场所。这类去处,兰坊城内有两个,一个称作‘北寮’,位于城墙的西北角。北寮的女子大多来自疆界那边,当年通西域之路经过兰坊时,这去处甚是繁华,现时却盛时已过,反成了城内泼皮偷儿等常去之处。另外一处称作‘南寮’,其间都为上等妓院。那里的女子全为汉人,其中有的颇识得几个字,与都市大埠中的歌伎舞姬并无不同之处。”
陶干拽了拽左颊上的三根稀毛,说道:“依我之见,应从北寮查起。在下据你所言推断,南寮的烟花场所应不敢掳掠女子,逼良为娼。似那类高等妓院大多小心谨慎,他们往往出钱买人,不致违法行事。”
马荣将大手按在方班头肩上,说道:“方班头休要烦恼,一俟狄大人审毕丁将军命案,我即向大人请命,请大人委派我和陶兄寻访你长女下落。如有人能找到令爱,那必定是陶干这老鬼精灵,更加上有我为他出力动手,我想必定能够成功。”
方达含泪谢了马荣。
此时,黑兰一身侍婢打扮进得门来。
马荣见了,即刻喊道:“干这活计,姑娘是否喜欢?”
黑兰并不搭腔。她向其父深施一礼,说道:“父亲,女儿有事禀报县令大人,请带女儿前往。”
方达起身,道声“少陪”,洪亮也出了县衙去余府知会余基。方班头携女儿穿过衙院到得狄公私宅。二人见狄公双手托腮,独自坐于案后沉思。
狄公见到方达、黑兰二人,脸露喜色。二人鞠躬请安,狄公点头,忙不迭地说道:“姑娘,把你在丁府探得的全部情形禀报本县。慢慢细说,不必着急!”
黑兰说道:“大人,丁将军生前十分怕人谋害,这事千真万确。丁府侍女告诉奴婢,丁将军所食之物都要先喂过狗,以确证其中无毒。丁府大门和边门日夜关门落锁,众仆人深感不便,因每每有客来访,或有生意人来做买卖,皆须开锁,落锁,十分费事。丁将军怀疑每个仆人,丁少爷也严密盘问每人行止,因此仆人们都十分烦恼,不愿在丁府伺候,往往做不数月就辞工而去。”
狄公命道:“给本县说说丁府诸人。”
黑兰又说道:“丁将军之大夫人已于数年前去世,现由二夫人管家主事。二夫人整日怕别人瞧她不起,很难侍奉。三夫人目不识丁,又胖且懒,不过要令其满意倒也不难。四夫人十分年轻,丁将军到了兰坊后才娶其为妾。奴婢以为四夫人乃男人心中的美貌女子。不过今晨梳妆时,我见她左胸有颗黑痣,甚是丑陋。她整天不是设法从二夫人手中弄钱,就是面对镜子顾影自怜。
“丁少爷和少夫人另居在一小院之中,膝下尚无子女。少夫人不甚美貌,且长其夫婿几岁,但奴婢听众人说道,她颇有才学,读书颇多。少爷几次提起要纳二房,她断然不依。少爷现今想在年轻女仆中拈花惹草,却不太得手,因此没有仆人愿在府中伺候,婢女们也不怕冒犯少爷。今晨我收拾少爷房间时,将他私人信札文摘偷着略略翻阅一遍。”
狄公听了,冷冷说道:“本县未曾命你做这种事。”
方班头则怒目圆睁,瞪了女儿一眼。
黑兰满脸通红,忙往下说道:“奴婢在一抽屉内见到丁少爷所写的一扎诗稿与书信。那文笔太深奥,我只是不懂。可我从看得明白的几句诗文中看出,所写之文甚是奇特,故带了出来,给大人过目。”
黑兰边说边用纤手从袖中取出一包诗文信函,恭恭敬敬地深施一礼,呈给狄公。
狄公以异样的目光溜了火冒三丈的方达一眼,便自顾自快速阅览起那些诗文。狄公放下诗文信札,说道:“这些诗文说的都属违法风月艳情,言辞甚是不堪,你看不懂倒是好事。信札所说之事也不过如此,落款都为‘奴丁浩拜上’。丁浩写此诗文信札只为宣泄心头之情,并未送至应去之处。”
黑兰说道:“丁少夫人是个才学女子,丁少爷不会写此诗文给她。”
方达此时已按捺不住,听得女儿说话放肆,便狠掴了她一个耳光,喊道:“你这贱人,大人不曾问话,你安敢多言?!”说罢,又转身面向狄公,歉疚道:“大人,此乃拙荆教女无方所致!”
狄公微微一笑,说道:“待我等具结完此件凶案,本县要为令爱择个佳婿。教导任性女孩之法,莫过于让其安心操持日常家务,彼时,令爱自然会循礼办事了。”方班头恭敬道谢。黑兰挨打,虽脸露愠色,却不敢吭声。
狄公用食指轻敲书文小包,说道:“本县自会命人立即誊抄出来,今日午后你将这些诗文、信札放回原处。姑娘,你差事干得不错。你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过仍须小心,不要翻看关严的抽屉箱柜。明日再来禀报本县。”
方达携女离去之后,狄公命人将陶干唤入,说道:“此乃一扎诗文信函。你须小心誊抄清楚,从这些艳词丽句中找出线索,推断收信者究竟是何许人。”
陶干溜了一眼诗文,不禁双眉倒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