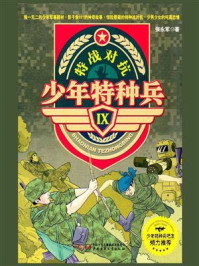丁浩刚出书斋,狄公便命洪亮道:“仔细搜看死者衣衫。”
洪亮伸手将死者两个袍袖摸了个遍,从其右袖内取出一方手帕与一个锦缎小袋,袋内装有牙签和耳挖子一套;又从左袖取出一把造型精巧的大钥匙和一个纸盒;再摸腰带,又找到一方手帕,此外别无他物。
狄公打开纸盒,盒内装九颗蜜饯梅子,三颗一行,整整齐齐排成三行。梅子乃兰坊名产。盒盖之上有红纸一张,上写“恭贺寿诞”四字。
狄公看罢,叹息一声,将纸盒放在书案之上。仵作将毛笔从死者僵直的手指之间拔出,也将其放于书案之上。此时两名衙卒走了进来,将老将军尸首置于一竹制板床上,抬了出去。
狄公于死者所坐之椅中坐下,说道:“尔等均去大厅伺候,本县要在此稍坐片刻。”
众人离去之后,狄公身靠椅背,看着摆满书卷的书架,颇费思量。书斋之内,唯窄门两侧没有书架,然墙上却挂有画轴。窄门上方,悬有横匾一块,上刻“自省书屋”四个大字。不问便知,此乃丁将军为其书斋所起之名。
狄公又将整整齐齐摆于书案上的文房四宝细细端详一番。那石砚极为雅致,堪称上品,砚旁竹制笔架手工也相当精巧。石砚一侧,有一红瓷水缸,其上面亦有蓝色“自省书屋”字样。显而易见,此缸乃专为丁将军而做。书案之上,还有一玉雕墨架,上有黑墨一块。
书案左首,狄公见到两块黄铜镇纸,上面各镌有一行文字,合于一处,乃一副对联:
春风和煦拂嫩柳,秋月清朗映流波。
联后署名“竹林修士”。狄公估量,此乃丁将军一友人之雅号,镇纸定是他请人制作,送与丁将军的。
狄公又拿起死者用过之笔。此笔亦精美异常,笔端以长长的狼毫所制;笔杆儿为红色雕琢漆器,上刻“桑榆之赠”四字,边上刻有一行俊美蝇头小字——“贺丁兄六十寿诞——宁谧轩”。看来,此笔乃一友人所赠之寿礼。
狄公放下毛笔,细细读那死者所书之文字。只见纸上字迹豪放,仅两行而已:
序
史籍浩繁,上溯远古,史书所记,多为历代豪杰,其英雄业绩,足可彰示子孙后代。
狄公心想,此句意思完整,可见丁将军书写之时,并未受人打扰。兴许,正当其思索下句该如何措辞之时,凶犯下了毒手。
狄公再次拿起那红色雕漆笔,聊无兴味地观看那笔管上所雕之云龙图案。这书斋与别处房舍分隔而建,此时又极其静谧,书斋之外,一丝声响也透不进来。狄公顿生莫名恐惧之感,觉察自己正坐在死者坐过的椅中,且姿态和丁将军死时完全一样。狄公迅即抬头观看,猛见门旁一轴歪斜不正,心里不禁发慌。难道凶犯是从此画背后的暗道进得室内,然后将匕首刺入丁将军咽喉?狄公想道,若情形果真如此,他本人只能听凭凶犯处置。狄公双眼紧盯画轴,等那画轴移至一边,露出凶犯狰狞面目。
过了片刻,狄公竭力定下神来,心中想道,倘若果真有暗门,陶干绝不会疏忽不见。想必是陶干察看墙壁之时将画给弄歪了。
狄公擦去额头冷汗,心中不再慌张,然他始终无法摆脱那不祥之感:凶犯正在离他不远之处。
狄公将笔在水缸中蘸湿,俯身于书案之上,竟欲试试笔锋。此时,狄公只觉右首的烛台碍手。狄公正欲将烛台推向一边,却又突然停住不动。
狄公仰身向后,身靠椅背而坐,颇费思量地看着烛台。显然,在写完开头两行文字之后,丁将军停下片刻,将烛台移近。丁将军此举并非是要看清字迹,若如此,他会将烛台推向左首。丁将军定是见到烛光下有某样东西,想要看个明白。就在此刻,凶犯下了毒手。
狄公蹙起双眉,放下毛笔,拿起烛台细细观瞧,却看不出丝毫独特之处,便又将其放回原处。
狄公心怀疑虑,频频摇头,于是猛然站起身来,步出书斋。狄公沿走廊走去,只见两名狱卒在廊内值哨,便命其好生看守书斋,在门板被修复、贴上封条之前,不得让任何人靠近。
大厅之内,诸事皆已备妥。狄公于临时公案之后坐定。公案之前有芦席铺地,丁将军尸身就停放在芦席之上。丁浩验明尸身确系其亡父后,狄公便命仵作动手验尸。
仵作小心翼翼地脱下死者衣袍,那消瘦干瘪之尸身便暴露无遗。
丁浩心中不忍,忙用袖掩面。书办与其他衙员则在一旁默默观看。
仵作蹲于尸首一旁,细细验看,对致命之处尤其留心,并且用手摸了死者头颅,看有无击打痕迹。仵作又用一银质薄板撬开牙齿,查验舌喉。
验毕,仵作站起身来向狄公禀道:“死者生前身体康健,并无疾病。手臂、腿上有铜钱大小的色斑,舌头之上覆有厚厚的灰色黏膜。咽喉处伤口不足致命,丁将军之所以丧命,乃插入咽喉之薄刃上剧毒所致。”
观看验尸之人尽皆愕然。丁浩垂下双臂,目视其父尸身,脸现惊惧之色。
仵作打开包裹匕首之油纸,将匕首置于临时公案之上。
“大人请看,”仵作言道,“紧靠血迹那一点斑渍之上留有异物,此乃毒素是也。”
狄公捏住刀柄,提起匕首,仔细察看那匕首上之褐色斑渍。看毕,问仵作道:“此系何毒,你可知晓?”
仵作摇头笑道:“大人,鉴别此类外用毒药,我等尚无良法。若是内服毒药,我等尽皆知晓,对其所致症状也了如指掌。然涂于匕首之毒却十分罕见。据尸身四肢色斑判断,小的仅知此系蛇毒。”
狄公听了,未置可否,只将仵作所言做了正式笔录,然后命其过目,并捺下指印。
随后狄公说道:“将尸首穿戴整齐入棺。将那管家唤来见我!”
衙卒替丁将军尸身穿好寿衣,置于竹制板床之上。此时,丁府管家到得大厅,跪于案前。
狄公对其言道:“你主管丁府日常事务,理应知晓府内之事。你须把昨夜之事一字不差地说来。就从昨日晚宴说起。”
管家听罢,言道:“丁将军寿宴就摆在此间大厅之内。丁将军居中朝南而坐,同桌坐于丁将军四周之人乃将军之二夫人、三夫人、四夫人,与少爷夫妇及丁将军大夫人两名表亲。丁将军大夫人已于十年前亡故。雇来的一队乐手在厅外平台之上吹奏寿乐,但在丁将军离席之前一个时辰已离府而去。
“将近午夜时分,少爷举杯向丁将军敬酒之后,丁将军便起身说是要回书斋。少爷随即一同前往,小人则手持蜡烛在后跟随。
“丁将军打开门锁,我进得书房,用手中烛火将书案上两支蜡烛点燃。小人可以做证,此时房内绝无他人。小人出书斋之时,少爷正跪伏于地,给丁将军叩请晚安。少爷请安之后站起身来,将军则把钥匙放入左袖之内,进得书斋关上窄门。将军大人插上门闩,少爷和小人都听得真切。小人所禀俱是实情。”
狄公向书吏示意,于是书吏将所录管家证词当厅念了,管家确认所录证词准确无误,遂签字画押。
狄公命管家退下,转过头来问丁浩道:“你离开书斋之后,又做了何事?”丁浩闻言,面露不安之色,欲言又止。
狄公厉声道:“回本县问话!”
丁浩好不情愿,勉强答道:“说来惭愧,晚生和拙荆大吵了一架。晚生离开书斋,径直回到自己住处。拙荆责怪晚生在寿宴之上对其不够尊重,使其在众位女眷面前丢了脸面。因时辰已晚,晚生于寿宴之后甚感疲乏,故未认真与其争个长短。趁两个侍婢为其宽衣之时,晚生则坐在床头喝了盅茶水。而后,拙荆又称头痛不适,命侍婢为其捶背捏肩。又过了半个时辰,我等才各自上床安息。”
狄公将自己记录案情之纸卷了起来,漫不经心地说道:“本县实难看出,此案同吴峰有何干系。”
丁浩听言叫道:“小人恳请大人将凶犯抓来严刑拷问,凶犯必定如实招供!”狄公不动声色,起身言道:“初审已毕。”说罢,便一言不发地来到前院,上轿回衙。丁浩站于轿旁躬身长揖,送狄公离去。
到得县衙,狄公立即赶至大牢。牢头回禀,钱牧依然昏迷不醒。
狄公闻言,命其遣人去请郎中,务使钱牧苏醒过来。离了大牢,狄公携陶干与洪亮来到县令私宅。
狄公在书案之后坐定,从袖中取出凶犯所用之匕首,又命书办取来一壶热茶,三人各饮一盅。狄公身靠椅背,手抚须髯,说道:“此命案非比寻常。且不说须查明作案动机及凶犯为何人,我们面前就有两道难题:其一,那书斋关得严严实实,凶犯何以出入?其二,凶犯又何以将此怪异凶器刺入死者咽喉?”
洪亮不解,只是摇头。陶干则一边细心察看那小巧利刃,一边用手指捻着左颊上的三根黑毛,少顷,也慢慢说道:“大人,卑职曾以为已解开此谜。昔日,卑职浪迹南方各州府时,曾听人说起山中的生番,他们以长条吹管捕杀猎物。卑职刚才以为,此形状怪异之匕首兴许是从此类吹管中所射出。凶犯可能从书斋之外,透过墙上格栅将凶器射向丁将军。然而,后来卑职又发觉,此凶器刺入死者咽喉之角度与我先前之推断不符。除非凶犯坐于书案之旁,不然就无法以此角度射出凶器。此外,卑职见到书斋后墙对面有一堵严实高墙,无人能在那里架设梯子。”
狄公慢呷浓茶,过了片刻,开口言道:“吹管之论难圆其说。然而,你之所言有一处我甚觉有理,即那匕首并非直接刺入死者咽喉。此匕首的把手小得异乎寻常,即使孩童也捏拿不住。再看这刀刃形状,也是非同一般。刀刃中间凹陷,形状不像匕首,却更像扁凿。我等刚着手勘查案情,我不想猜测凶器如何刺入死者咽喉。陶干,你须依样做出一把木匕首,以便我用来揣摩时不致伤及性命。不过,你仿制之时需特别小心,那刀尖之上涂有何种毒药,唯有天知晓!”
此时洪亮于一旁言道:“依卑职愚见,我等还须继续勘查此案背景。我们何不将吴峰传来问话?”
狄公点头称是,说道:“我正欲前去拜访吴峰。我素来主张去嫌犯所在之处实地勘查。我将微服前往,洪亮可与我同行。”
言毕,狄公起身。不料此时,牢头闯进狄公私宅,高声说道:“大人,钱牧已苏醒过来!小人以为,他恐怕是活不长久了。”
狄公听罢,急随牢头而去,洪亮与陶干紧跟在后。
到得大牢,只见钱牧躺在木床之上,四肢挺直,双眼紧闭,直喘粗气。牢头先前已将一条冷毛巾敷在钱牧额上。
狄公俯下身来。此时钱牧睁开双眼,看着狄公。
狄公急问:“钱牧,谋害潘县令者究竟何人?”
钱牧双眼通红,怒视狄公。他动了动嘴唇,竟没说出一个字来。最后,他用尽全身力气才含含糊糊地迸出一声,随即,便不再言语。
突然,钱牧高大的身躯抽搐不止。只见他紧闭双眼,伸直身躯,接着,双腿一蹬,便躺着不动了。
洪亮见钱牧气绝,便说道:“他刚才说了个‘你’字,却无力将话说完。”
狄公直起身子,慢慢点头道:“钱牧没供出我等急需之案情便一命呜呼,真是可惜!”然后,狄公又低头看那尸身,哀叹道,“潘县令为谁所害,我们再无办法查清了!”
狄公将双手伸入袖中,朝私宅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