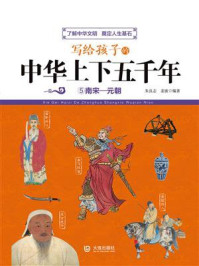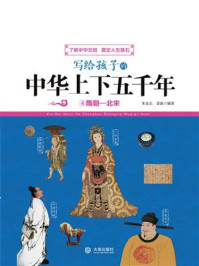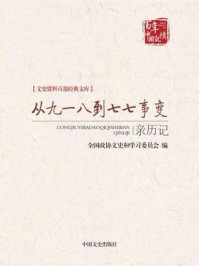故事的舞台再次转移到了东魏。
为建立新的国家而鞠躬尽瘁的高欢,在武定五年(若以梁的年号为记则是太清元年,547)正月丙午(初八日)殁于晋阳丞相府,享年五十二岁。在此之前,依靠着高欢强大的领导力,东魏国内诸势力达到了平衡。高欢的死让这一平衡的形势濒临打破的危险。高欢的世子高澄此时还是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而作为高欢拥戴者的旧部,也就是“勋贵”之中,存在着不少对世子继承父业有异议的人。其中的急先锋不是别人,正是侯景。在高欢生前,侯景就曾毫无忌惮地大放厥词:“王在,吾不敢有异;王无,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
 高澄一听到父亲病倒,就从邺城赶往晋阳,同时假冒父亲的名义命令侯景前往晋阳。但是侯景并没有前来。以前每次高欢在寄送给侯景的书信上,都会在其背面点上一点作为两人约定的防伪标记,而这一次侯景对高澄发来的这封后面没有标记的书信产生了怀疑。世子侍奉在高欢枕边,他脸上不安的表情没能逃过父亲的眼睛。
高澄一听到父亲病倒,就从邺城赶往晋阳,同时假冒父亲的名义命令侯景前往晋阳。但是侯景并没有前来。以前每次高欢在寄送给侯景的书信上,都会在其背面点上一点作为两人约定的防伪标记,而这一次侯景对高澄发来的这封后面没有标记的书信产生了怀疑。世子侍奉在高欢枕边,他脸上不安的表情没能逃过父亲的眼睛。
“我虽疾,尔面更有余忧色,何也?”

高澄无言以对,只是凝视着父亲的脸。
高欢接着说道:“岂非忧侯景叛邪?”

高澄点头称是。
“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跋扈志,顾我能养,岂为汝驾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发哀。……少堪敌侯景者唯有慕容绍宗,我故不贵之,留以与汝,宜深加殊礼,委以经略。”

高澄听从父亲遗命,秘不发丧。在高欢死后仅仅五天的正月辛亥(十三日),侯景就在河南起兵反叛。其实高欢病倒的消息很早就传入了侯景的耳中。假冒的书信到达更是证明了高欢身边的混乱。侯景的狡黠让他并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侯景突然的谋反令天下皆知,传言御史中尉崔暹是导致侯景反叛的主要原因。当初,正是高澄推荐了身为博陵
 望族的崔暹成为御史中尉,后者与同为高澄举荐而就任尚书左丞的宋游道一起,对勋贵们的违法行为采取了严厉惩治的措施。司马子如、元羡、慕容献、高坦、可朱浑道元、孙腾、高隆之、元弼,还有侯景,他们都受到了弹劾。与现实主义的父亲不同,高澄因为年纪轻,而似乎是理想主义的信奉者。事已至此,高澄为了敦促侯景回心转意,同时阻止事件进一步影响到其他勋贵,决定斩杀崔暹。但因为有一位臣子力谏,避免了崔暹被斩。这则谏言是这样的:“今四海未清,纲纪已定。若以数将在外,苟悦其心,枉杀无辜,亏废刑典,岂直上负天神,何以下安黎庶?”
望族的崔暹成为御史中尉,后者与同为高澄举荐而就任尚书左丞的宋游道一起,对勋贵们的违法行为采取了严厉惩治的措施。司马子如、元羡、慕容献、高坦、可朱浑道元、孙腾、高隆之、元弼,还有侯景,他们都受到了弹劾。与现实主义的父亲不同,高澄因为年纪轻,而似乎是理想主义的信奉者。事已至此,高澄为了敦促侯景回心转意,同时阻止事件进一步影响到其他勋贵,决定斩杀崔暹。但因为有一位臣子力谏,避免了崔暹被斩。这则谏言是这样的:“今四海未清,纲纪已定。若以数将在外,苟悦其心,枉杀无辜,亏废刑典,岂直上负天神,何以下安黎庶?”

颍州刺史司马世云为响应侯景而举兵。之后,侯景攻打豫州、襄州、广州,并逐一使其臣服,他的势力得到了扩张。然而侯景军在攻打西兖州
 时,却遭遇到了顽强的抵抗,二百名士兵全部成了俘虏,而且东魏出类拔萃且拥有美名的文士、西兖州刺史邢子才所作的檄文在东魏东部各州流传,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侯景向东方进军已经没有希望。究竟要如何在困境中破局呢?侯景在不安和焦虑中反复思考。经过深思熟虑,他终于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向昨日还曾作为敌人并与之战斗过的西魏以及梁归顺。做出这个决定意味着侯景对目前自身的实力很有自知之明,因此要借助西魏和梁这两股势力。令人意外的是,西魏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另一边,他派去江南的使者、行台郎中丁和也到达了建康,到达的时间是二月庚辰(十三日),比西魏下决定接纳侯景的日期晚了几天。梁武帝立即召开了宫廷会议。以尚书仆射谢举为首的重臣们异口同声地陈述着接受友好邻国东魏叛将的不利之处,但梁武帝却显然不太想听从这些意见。
时,却遭遇到了顽强的抵抗,二百名士兵全部成了俘虏,而且东魏出类拔萃且拥有美名的文士、西兖州刺史邢子才所作的檄文在东魏东部各州流传,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侯景向东方进军已经没有希望。究竟要如何在困境中破局呢?侯景在不安和焦虑中反复思考。经过深思熟虑,他终于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向昨日还曾作为敌人并与之战斗过的西魏以及梁归顺。做出这个决定意味着侯景对目前自身的实力很有自知之明,因此要借助西魏和梁这两股势力。令人意外的是,西魏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另一边,他派去江南的使者、行台郎中丁和也到达了建康,到达的时间是二月庚辰(十三日),比西魏下决定接纳侯景的日期晚了几天。梁武帝立即召开了宫廷会议。以尚书仆射谢举为首的重臣们异口同声地陈述着接受友好邻国东魏叛将的不利之处,但梁武帝却显然不太想听从这些意见。
“虽然,得景则塞北可清;机会难得,岂宜胶柱。”

这天,结论还没得出,梁武帝便下令散会了。之后数日,移驾武德阁的梁武帝没有和任何人说话,而是喃喃自语,仿佛在劝说自己似的:“我国家如金瓯,无一伤缺,今忽受景地,讵是事宜?脱致纷纭,悔之何及?”
 此时,在梁武帝身旁静候的正是中书舍人朱异。他出身于贫穷的寒门,本来只能一辈子做刀笔吏,却因为机灵能干、才华横溢而见幸于梁武帝。数十年间,梁武帝将国内的万端事务都委任给了这个男人。梁武帝的喃喃自语应该难以逃过朱异的耳朵。梁武帝在侯景的问题上很是头疼。虽然他想要接受侯景的归顺,但最后的决心还未下定。在这一年的正月乙卯(十七日),还发生了下面这样一件颇为离奇的事情。这天,梁武帝对朱异说起自己在梦中见到中原牧守纷纷携其地来降:“吾为人少梦,若有梦必实。”
此时,在梁武帝身旁静候的正是中书舍人朱异。他出身于贫穷的寒门,本来只能一辈子做刀笔吏,却因为机灵能干、才华横溢而见幸于梁武帝。数十年间,梁武帝将国内的万端事务都委任给了这个男人。梁武帝的喃喃自语应该难以逃过朱异的耳朵。梁武帝在侯景的问题上很是头疼。虽然他想要接受侯景的归顺,但最后的决心还未下定。在这一年的正月乙卯(十七日),还发生了下面这样一件颇为离奇的事情。这天,梁武帝对朱异说起自己在梦中见到中原牧守纷纷携其地来降:“吾为人少梦,若有梦必实。”
 朱异心领神会道:“此乃宇内混一之兆也。”
朱异心领神会道:“此乃宇内混一之兆也。”
 据使者丁和所述,侯景决心叛乱的时间正是在正月乙卯。必须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巧合。
据使者丁和所述,侯景决心叛乱的时间正是在正月乙卯。必须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巧合。
朱异对梁武帝说道:“圣明御宇,南北归仰,正以事无机会,未达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来,自非天诱其衷,人赞其谋,何以至此!若拒而不内,恐绝后来之望。”
 此言一出,彻底消除了梁武帝心中的芥蒂。时值二月壬午(十五日),侯景从梁朝得到大将军、总督河南北诸军事、大行台、河南王之位。因此,梁武帝下令司州刺史羊鸦仁带着三万士兵和所需粮草前往悬瓠
此言一出,彻底消除了梁武帝心中的芥蒂。时值二月壬午(十五日),侯景从梁朝得到大将军、总督河南北诸军事、大行台、河南王之位。因此,梁武帝下令司州刺史羊鸦仁带着三万士兵和所需粮草前往悬瓠
 援助侯景。但是在羊鸦仁的军队到达之前,东魏对侯景的攻击就已经开始了。侯景只得放弃悬瓠而出奔颍川,不料却在此处陷入了包围之中。他提出可以割让土地,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来请求西魏派军支援,希望借此摆脱当前的危机。为了向梁武帝解释这个举动,侯景派使者来到了建康。虽然梁武帝加以斥责,但也说了下面这样安慰的话语:“如《公羊传》所言,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卿诚心有本,何假词费!”
援助侯景。但是在羊鸦仁的军队到达之前,东魏对侯景的攻击就已经开始了。侯景只得放弃悬瓠而出奔颍川,不料却在此处陷入了包围之中。他提出可以割让土地,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来请求西魏派军支援,希望借此摆脱当前的危机。为了向梁武帝解释这个举动,侯景派使者来到了建康。虽然梁武帝加以斥责,但也说了下面这样安慰的话语:“如《公羊传》所言,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卿诚心有本,何假词费!”

但是,西魏的宇文泰与梁武帝不同,对首鼠两端的侯景非常厌弃。因此侯景和西魏的关系破裂了,分道扬镳。以梁为后盾的侯景,对东魏而言成为了难缠的主儿。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侯景收到从高澄处寄来的一封劝降的书信。高澄保证侯景终身保有豫州刺史的地位,且追随他叛乱的文武官员全都不予追究,困于狱中的侯景妻儿也将立刻送还。书信是高澄用怀柔策略写就的,但侯景并未被对方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他的第一心腹、行台郎王伟代为执笔回信,鲜明且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诉求:
为君计者,莫若割地两和,三分鼎峙,燕、卫、晋、赵足相奉禄,齐、曹、宋、鲁悉归大梁,使仆得输力南朝,北敦姻好,束帛交行,戎车不动。仆立当世之功,君卒祖祢之业,各保疆界,躬享岁时,百姓乂宁,四民安堵。

回信中说,东魏、西魏、梁三国鼎立的形势维持原样,并且用春秋战国时代的列国名燕赵晋魏等来称呼各地,即河北之地尽归东魏,齐曹宋鲁等河南之地尽归于梁。侯景的意思是,我侯景为梁而尽力,你高澄继承父祖以来的事业,南北的友好关系继续维持,以此为结局岂不是对各方都有益?
复寻来书云,仆妻子悉拘司寇。以之见要,庶其可及。当是见疑偏心,未识大趣。何者?昔王陵附汉,母在不归;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脱谓诛之有益,欲止不能,杀之无损,徒复坑戮,家累在君,何关仆也。

回信中的这一段是讲在楚汉之争最白热化的阶段,项羽抓捕了刘邦部将王陵的母亲。王陵派出使者来到项羽军营,项羽热情地请王陵的母亲坐在上座,并希望她劝说王陵投降自己。王陵之母送别使者时,在使者的身后说道:“为老妾语陵,谨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
 说罢立即自戕而死。另一方面,刘邦在广武与项羽对峙,粮道被对方断了。项羽制作了一块高高的木板,并把俘虏的刘邦的父亲刘太公放在上面,大声呼喊:“今不急下,吾烹太公。”
说罢立即自戕而死。另一方面,刘邦在广武与项羽对峙,粮道被对方断了。项羽制作了一块高高的木板,并把俘虏的刘邦的父亲刘太公放在上面,大声呼喊:“今不急下,吾烹太公。”
 刘邦反驳道:“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刘邦反驳道:“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由此可见,王陵也好,刘邦也好,为了“大业”一点都不介意舍弃父母的性命。那么,不及父母尊贵的我侯景的妻子儿女的生命,那就任君自由处置吧。
由此可见,王陵也好,刘邦也好,为了“大业”一点都不介意舍弃父母的性命。那么,不及父母尊贵的我侯景的妻子儿女的生命,那就任君自由处置吧。
在高澄寄给侯景书信的同一时间,在梁国国内,流传着一封署名为“高澄”的书信,有几句的内容如下:
本使景阳叛,欲与图西,西人知之,故景更与图南为事。

信中这几句的意思是说侯景的谋叛是伪装的,是高澄与侯景的合谋,最初是想要图谋西魏,但是被宇文泰看穿了阴谋,侯景受挫后,才重新图谋于梁。这封信里的谣言传到梁武帝的耳中时,他笑了出来,认为这不过是高澄的把戏,为的是离间梁和侯景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