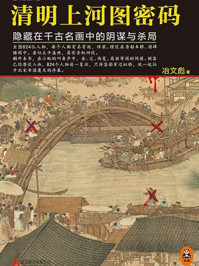“西市的烧鸡味道没有东市的味道好了!引凤堂在东市开的几家女装店也更招京中妇女喜欢……再这样下去,东市那边的人气会越来越比西市旺了!”罗乞泰一边大口大口地啃着手中的鸡腿,一边和身边的几个青年乞丐絮絮叨叨地说着,“让弟兄们多分流一批到东市去要饭,人气一旺,财气就足嘛!讨要的东西也就更多了!”
他一头像鸟窝似的蓬乱头发,脸上是红一道黑一道的泥痕,破破烂烂的衣衫,但除了淡淡的汗臭之外,却无其他异味。毕竟他是顺天府十六家养济院的总丐头,管着当地的几千家丐户和所有的外来游丐,又经常出入府衙各署,故而还是要注重一些仪表体面的。
“好的,好的。罗老大说得对。”那几个青年乞丐纷纷答应着。
正在这时,一个乞丐敲着竹杖过来禀道:“老大,外面有一个蒙面公子要见你,他还递了一张字条进来,说你一看到后就知道他是谁了。”
罗乞泰漫不经心地一手接过,只见上面写着一个不大不小的“白”字。他顿时停住了啃咬鸡腿,脸色变得十分庄肃。思忖了片刻后,他对那来报的乞丐说道:“你快去带他进来。”同时又吩咐另外几个在场的青年乞丐道:“你们都去外边把风,谁也不许靠近这里。”
进来的这位公子确是青布蒙面,只留眉眼在外,双眸亮光闪闪,语调却是江南人氏那样的平和绵柔:“我是白清卓公子的朋友,代他过来请教一些问题。”
罗乞泰把鸡腿丢在一边,大咧咧地将那张写着“白”字的纸条抖了一抖:“我罗某人不太会识别这笔迹,不晓得是不是仿冒的。”
“那好,我再说一件事情证明自己的身份。罗乞泰,你在万历八年七月十六日之前名叫罗四狗,对吧?万历八年七月十六日后,你就改名叫‘罗乞泰’了吧?”
罗乞泰把手一摆:“少来。这个事情当时有不少人知道。”
“他们不知道的是你这个名字正是白公子帮你改的,而‘乞泰’二字则是‘乞求国泰民安’之寓意,对吧?”蒙面青年徐徐道来,“你当时还想改成‘乞太’,寓意为‘乞求太平盛世’。白公子说,你身为丐头,多一份灵动的‘水性’最好,还是坚持让你改名为‘乞泰’。这个细节,恐怕更是只有你们二人知晓了。”
罗乞泰立刻谦恭至极地站了起来:“公子原来真的是白恩公的朋友,这个秘密确实只有我和白恩公才知道,没有第三者知道。”
蒙面青年却面色平静,直直地盯着他:“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十年,罗君也从当年东城巷的小丐头做到了今天顺天府的总丐头。真是沧海桑田、白云苍狗啊!不知罗君变了没有?又或变了多少呢?”
原来,万历八年之时,内阁次辅张四维为了巴结首辅张居正,鼓吹“张公德高,天下无丐”,上书建议把顺天府的养济院补助款从每月三千两削减成了一千两,把京中的丐户强行外迁三分之二。而当时罗乞泰便在这外迁名单之中。他悲愤之中便欲跳河自尽,却被白清卓救下。白清卓问清情况后,上书给申时行,申时行又转呈张居正。张居正从善如流,废止了张四维的迁丐之举。事后,罗乞泰视白清卓恩同再造,一直感佩于心。
此时听到蒙面青年如此问话,他依然是极为恭敬地回答道:“无论世事如何变化,罗某对白恩公的一片感恩效劳之心永远不会改变。”
“那七年前白公子离京前送你的那件信物还在?”
罗乞泰“嗯”了一声,急忙从胸口贴肉处取出一块小小银牌递在蒙面青年手里:它正面镌刻着“金白水清”四字,背面镌刻着“卓尔不群”四字,笔法刚劲有力。
蒙面青年看过之后把它又还给了罗乞泰,深深点头说道:“难为你还始终佩戴着它,说明你确实是一直把你白恩公挂在心头的。那你可知道你白恩公现在回京城来办什么事情了吧?”
“恩公作为辽东镇的特使,特来京城协查黄启祥被三眼神铳劫杀案。我已经在下面做了一些功夫,就等着恩公上门来取。”
“那好。”蒙面青年依着白清卓交给他的问题清单,一项一项地问道,“最近……也就是黄启祥出事的前两三个月至今,京城中有什么异常的人物和异常的事情?”
罗乞泰扳着手指头一件一件地说道:“德润斋近来施舍给丐户们的米粥越来越浓稠了,越来越喜欢做不赚钱的生意了,这异不异常?琉球国的商人东方胜在东市坊增开了一片店铺,取名引凤堂,近年来风生水起,居然就在德润堂眼皮底下做大了,这异不异常?……”
蒙面青年也认真地听着,老老实实地拿笔全部记录了下来。
然后,他拿出洪尔林的人头画像递给罗乞泰:“把这幅人脸画像拿去给你们所有的弟兄辨认回忆: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在办什么事情,一一火速报告上来。”
罗乞泰看了看那画像,卷好了放在兜里。他手下所有的京丐和游丐都是他的“耳目”细作,追踪调查有关人氏也确是熟门熟路。
蒙面青年又点道:“兵部武库司包天符这个人,你们要重点盯梢他。对他的任何异动,都要及时来报。”
罗乞泰“咦”了一声:“辽东留京署东霖院那边也有人在盯他。”
蒙面青年的声音一下硬了起来:“他们盯他们的,你们只管盯你们的。”
罗乞泰也明白了:白清卓在防备东霖院里有内奸。他想了一下,问道:“罗某收集到了这些消息后,到哪里来交给白恩公呢?还是送到东霖院去?”
“不能送到那里。”蒙面青年双目灼然生光,“你就拿着这块信物银牌到北城的喜来客栈找我,我住甲字号单间房。如果我不在,你就以银牌为凭证,找那里的崔掌柜,他会替我收好消息的。”
“好。”罗乞泰朗朗而应。
“既然你已知道白公子为黄启祥案件而来,那你应该也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了。”蒙面青年又款款问道,“我问你,那个黄启祥,生前在京城中比较熟识的是哪些人氏?”
“一类是从他们朝鲜国过来京城定居的商绅,一类是朝廷礼部的官员,还有一类……可以说还有一个人,可能你们连想也不会想到。”
“谁?”
“黄启祥一向喜好诗文,和左都御史方应龙大人的公子方宝棠素来交好。”
“方应龙的公子?”蒙面青年微微一怔。
“是的。黄启祥多次赞叹方宝棠为‘京城第一才子’,那位方公子也回赠他是‘三韩第一秀士’。”
蒙面青年马上单刀直入:“那你们可调查过了,黄启祥被杀的那天晚上,方宝棠可有不在场的证明?”
“我的弟兄们回报:那天晚上,很多人看到方宝棠在‘春香楼’和高正思、邬涤尘等公子贵人们饮酒作乐。”
“哦。看来,没有他直接介入此事的证据啊。”蒙面青年淡淡一叹,“没有第一手的证据,便不好说啊。”
“可是他如果也像今天您代表白恩公来见我一样派人去见黄启祥呢?由方宝棠亲笔书写一张凭证字条,那个人再带在身上,然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见到黄启祥了;黄启祥也不疑有他,而被那个人当面一铳毙命。”罗乞泰侃侃而道。
“这样的推理调查,顺天府唐鉴也已经做过了吧?”蒙面青年冷不丁地问了一句。”
“唐鉴?唐鉴怎么敢去这样调查、询问方应龙的公子?”罗乞泰摇了摇头,“唐鉴这个人最擅长见风使舵……”
蒙面青年淡淡说道:“白公子也没准备寄期望于他们顺天府衙。你刚才说的,其实只是一种假设。”
“没有大胆的假设,哪来对真相的挖掘?”罗乞泰搓了搓手,“目前,遵循获利最高者可疑的常识判断,李成梁和辽东军一旦被定罪成功,最大的获利者就是方应龙和萧虎臣那一帮人。你看,现在都察院对李成梁的攻击那是何等密集、何等激烈?所以说,方宝棠为他老子如此活动和设局,也在情理之中。”
蒙面青年笑了一下,直接给他挑明:“你白恩公向我分析过:黄启祥案件震惊中外、影响巨大,方应龙和他的手下没这个胆子去做。他们不会主动栽赃李成梁和辽东军,只会落井下石趁机诬陷。当然,一切要靠证据来说话。你也可以按照你刚才的假设去追查,只是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据,你便不能妄言妄动。方宝棠和他背后的势力毕竟非同小可。”
“好的。罗某自会谨慎小心。”罗乞泰肃然而答,“另外,有些事情,我要向你先说明一下:其实也有人在找我们来盯梢白恩公。所以,白恩公让你代表他来见我,实是十分英明。”
“谁让你们盯梢白公子的?”蒙面青年不动声色地问。
“唐鉴,就是那个唐鉴。他是顺天府总捕头,我是总丐头。他管着我。他让我派人盯梢白恩公的。”
“原来是唐鉴?”蒙面青年若有所思,“他让你派人盯,你就派人盯吧。说不定,他还有另外的耳目在盯白公子呢。你放心,白公子让你们看到的踪迹,就是他想让你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影响不了什么事情。”
“好的。白恩公事先明白就行。”罗乞泰连连点头。
蒙面青年掏出一张八百两的银票向他递来:“我知道你们‘养济院’的弟兄们也很辛苦。这些茶水钱,你拿去分给他们吧。”
罗乞泰很生气地将银票推了回来:“‘养济院’的弟兄们为白恩公奔走效劳,乃是万死不辞!决不会要他一分一文的!”
“很好,很好。你的诚意,我一定带给白公子。”蒙面青年起身临别之际,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情,“另外,你再帮白公子调查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罗乞泰还是那么积极地问道。
“七年之前,白公子在午门血书上谏之后,礼部侍郎上官平芝一家至今所有活动情况,包括上官雪衣为何会背叛白公子,她这七年里又在做什么。”
“这……这也是白公子自己指定要调查的?”罗乞泰十分诧异。
“不错。这桩任务,你也要尽快完成。”蒙面青年的眼中异光一闪,口吻却显得极为坚定,“尤其是上官雪衣的一切动态。”
“好的,好的。”罗乞泰摸了摸后脑勺:白清卓离京前倒是说过让他们丐帮平日关照一下上官小姐的情况,但像今天这样明确要求对上官家深查、细查的做法却有些令人意外。莫非白恩公也怀疑上官平芝彻底倒向了方应龙一派?
清亮亮的井水一股股注入那方贝叶纹奇石砚池之中,一粒粒晶莹剔透的细贝、圆螺顿时浮凸而现,栩栩然流光溢彩,闪烁如星,煞是好看。
方宝棠站在案前,轻袍华冠、一身贵气。他手拈墨块,瞧着砚中这一幕奇景,几乎不忍下墨细研:“宝芹帮我选的这方宝砚可真漂亮!弄得我都不好拿来研墨而污了它的珠光宝气!”
高正思、邬涤尘、吴承信等人围成一圈在旁边观赏着,也是连声赞道:“宝芹小姐的眼光真好!这宝砚可真是稀世奇珍!”
方宝棠似笑非笑地斜眼看着他们:“你们知道这方石砚是谁推荐给我妹子买下的吗?”
“我看砚角有德润斋的印记,自然是德润斋那些鉴宝师吧……”高正思开口说道。
“非也。据宝芹所讲,竟是一个自称‘白清卓’的人从旁推荐的。”
“白清卓?”高正思、邬涤尘、吴承信等人不禁面面相觑,“居然是他?宝芹小姐还见过他?”
“难道不应该是他?从这方宝砚来看,他识物辨宝的眼光还不错嘛!圣手狂生,果然有些意思。”方宝棠欣赏了贝叶纹奇石砚半晌,终于还是忍不住了,拿着那块父亲所赠的“御墨”,在砚池里慢慢研磨了起来。一缕黑线在清水中徐徐扩散开来,淡淡的墨色轻轻掩盖了砚底的细贝光彩。
“咳咳咳……我去巡边外察时看到的白清卓,身上很少有书卷气。”邬涤尘随时随地都要贬损一下白清卓,“他简直是一个‘老兵痞子’……”
“丹池诗会就要举办了。”方宝棠仿佛十分随意地讲了一句,“今年的办会款项已经有着落了。”
“应该还是像去年那样由德润斋出钱主办吧?”高正思问。
“去年是一万两的预算,全由德润斋负责。今年却是一万四千两的预算,德润斋这一次只承担三分之二,另外的三分之一是由东市近年兴旺发达的引凤堂承担。”方宝棠提起了一支玉管狼毫笔,徐徐伸入砚池墨汁之中,“引凤堂派人来求家父的亲笔墨宝题名,就是引凤堂三个字。这大概也是他们愿意为丹池诗会出钱的条件之一吧。家父让我来代笔。”
高正思敛色叹道:“方大人、方公子为筹办丹池诗会真是苦心孤诣、不辞劳苦。”
邬涤尘见方宝棠已经准备挥毫泼墨,就把高正思、吴承信拉至一边,说道:“我们就不要打扰方公子书写墨宝了,到这边来谈一谈怎样对付白清卓吧。”
“要对付他,还不容易?”高正思冷笑了一下,“自古武将最贪财。你查到白清卓在南兵营参将职位上有什么贪墨行为了吗?”
邬涤尘连连摆手:“没有,没有。我翻来覆去到处追查——他却是把所有的薪俸都捐给了南兵营,而自己还为解决南兵营欠薪问题在德润斋牟万琛那里借了不少银两。”
高正思叹了一口长气:“照你这么说,他可是比咱们都察院里最清廉的监察御史还清廉!都快赶上海刚峰了!”
吴承信却从旁直问:“我听闻他身边一直有个小师妹在跟着他,这其间会不会有什么苟且之事?”
“似乎也没有。”邬涤尘暗暗抽了一口冷气,“这个……这个,这个凌姑娘不好招惹呀!况且白清卓目前还是单身未婚,身边有一个女子陪侍,似乎也不好定他一个什么罪名。”
“那他就真的没有一丝漏洞?”高正思咬了咬牙,看向吴承信,“吴兄,你也说一下?”
吴承信却直直地迎视着他:“对了,我们也不要单单打倒白清卓一个人呀!高大人,你近来去辽东镇清查三眼神铳配备、使用等情况,又查出了什么?”
“这件事情我已经向方大人禀报过了。辽东镇对三眼神铳这种‘国之利器’还是十分重视的。每一次战役结束后,该镇军械署都把三眼神铳在战场上遗失、损毁的情况登记在册。我对每一份记录都核查过了,不似有作伪的情况,而且和兵部提供的底单也相吻合。所以,从这一点入手,做不出什么‘大文章’。”高正思也细细地答道,“辽东镇麾下人才济济,在这方面应该是有高人指点和协助的。”
“难道他们不会把一部分三眼神铳借着对外遗失、损毁为名而私藏在手?”吴承信直问过来。
“你怀疑得对。但他们到底私藏在哪里、私藏了多少件,又或者流失到市面有多少件,这些疑问是要拿证据来说话的呀!”高正思长叹一声,“我们可以风闻奏事众口交攻,但是要给他们定罪到位,却不能光凭空口白话啊!你要相信,我绝不会放过辽东镇一丝漏洞的。”
听高正思讲得如此直白,吴承信一时也无话可说。
高正思静了下来,也想到了前天自己从辽东镇调查回来后和方应龙的一番交谈。当时,他也对方应龙直言道:“高某也赞成对辽东李氏施以打压,但万一黄启祥劫杀案的背后另有真凶呢?我们岂不是被人利用而替真凶火中取栗了?”
方应龙沉沉答道:“为了让萧总兵真正在朔方掌权上位,哪怕黄启祥一案确是另有真凶,我们也要把它栽在李成梁父子的头上!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战,你此刻千万不能有半分动摇。”对此,高正思当时也只有沉默不语。
这时,邬涤尘按捺不住,重重地一拳砸在桌面上,焦躁至极地叫道:“难道我们真的就拿白清卓、李成梁他们一筹莫展了?”
“慢着,慢着。”吴承信阴险地说道,“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一做文章,用来一挫白清卓的锐气。只不过它拿到台面上来,似乎让人感到稍稍阴损了一些……”
“哪件事情?”高正思和邬涤尘几乎是同声问道。
“白清卓不是一直对外声称南兵营缺薪、缺饷吗?他不是一直在以南兵营补薪代言人而自居吗?甚至还托了卢光碧等人到处试图打通‘关节’。我们可以来一招釜底抽薪,要堵得他无话可说。”吴承信的目光愈发阴寒而尖利。
“哪一招釜底抽薪?”高正思不禁探身追问。
“吴某翻查户部的旧档,知道了这样一件事情:十多年前,戚继光自称为了防寇,组织戚家军和大量工匠修建了长达两千里的蓟辽长城,每一里城墙耗银四千五百两,合计总费九百万两白银;又修了二千零七十一座空心炮台,每座耗银七十两,合计总费十四万四千余两白银。当时的国库为之损费三分之一。那么,如此巨额的工程款项,有多少笔不是落进了戚家军的腰包?他们以役获薪,每个人还不是分得油水多多?哪里还有缺薪、缺饷之说?咱们把这一大笔烂账重新翻出来,白清卓只怕也唯有结舌认输!”吴承信像是挖到了什么绝招秘诀一样,越讲越是兴奋,两眼都放出炙热的光芒来。
听了他这长长的一席话,高正思和邬涤尘却坐在那里面面相觑,也不似他这般激动,神色更是平淡得很。
吴承信也察觉了他俩的异样,愕然而问:“你……你们怎么回事?”
邬涤尘有些尴尬地咳了几声:“吴郎中,戚家军修长城的款项账目,我们都察院在万历十年张居正死后就开始启动清查啦……你认为,这么大的一个‘把柄’,方应龙大人会白白错失?不过,当年似乎就没查出什么问题来……”
“那……那为什么户部竟然没有他们修长城的存底账本?”吴承信讶然说道,“既是没有账本,那便还有文章可做……”
“咳咳咳……你是在万历十四年后进的户部,可能有所不知:当年内阁和司礼监最后不都是认可了戚继光的说法吗?那些账本是被潜入军营的外贼细作放火烧了吗?”高正思也有些吞吞吐吐地说道。其实,这件事暗底下真实的原因是:张四维、张鲸见从账面上找不到戚继光的漏洞,干脆派出刺客去偷偷焚烧戚家军的账本,然后栽赃给戚继光。不料,那些刺客却被戚继光手下精兵生擒活捉,并押送到了内阁、司礼监。张四维、张鲸遭到如此打脸,才迫不得已对外宣称戚家军账本系外贼奸细所烧,对内则不敢再拿此事诬陷戚家军。而这一内幕,当时朝廷上下都是心知肚明的。
吴承信问清了事情的本末底细,略一思忖,厚着脸皮又道:“当时与此事有关的三个当事人:戚继光、张四维、张鲸等而今都已死去,这就叫‘死无对证’!咱们便又可以翻出这笔旧账来攻击南兵营!这样一来,白清卓也不得不低头示弱了。”
高正思听罢,转脸望向邬涤尘:“老邬,你怎么看?”
邬涤尘有些结结巴巴地说道:“这个……这个,我觉得可以照吴郎中所言去试一试。咱们可以拿出这笔旧账来敲打白清卓,让他无法为南兵营争取补薪。毕竟那时的当事人都不在了,而且账本也确实没有留底,咱们闹将起来,他白清卓也不好还嘴。”
高正思在心底暗暗一叹,虽然也觉得这种做法未免太过无耻,但在嘴上却只得说道:“如今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那边,方宝棠恰巧丢下了手中毛笔,仰天大呼一声:“写好了!”
高正思、邬涤尘、吴承信三人亦觉大事已定,心情终于放松下来,各个起身走到桌案前:只见那雪白的宣纸条幅之上,“引凤堂”三个斗大的楷书方字恍若峰耸岳峙,气势雄浑,夺人心魄!他们不禁纷纷喝彩:“方公子的书法真是冠绝四海、妙不可言!”
方宝棠斜斜抬眼看着他们:“刚才你们一直在那边议论怎样对付白清卓——怎么?他很厉害吗?让你们很头痛吗?”
“他……他就是一个自恃几分才气的‘狂生’……”高正思嘻嘻一笑,“吴郎中已经想出手段收拾他了……”
“既然他也是个书生,我们便邀请他参加此番丹池诗会吧!咱们就在文才诗艺上打掉他的气焰,让他从此在京城里直不起腰来!”方宝棠面色一正,森然言道。
“好!好!好!”高正思等三人互相对视了一眼,都不禁鼓起掌来,“宝棠公子出马,必能砸掉他那个圣手狂生的纸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