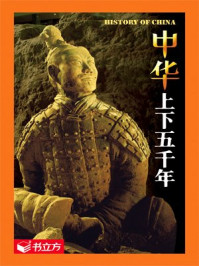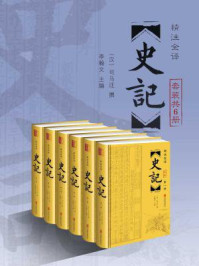走在一起,是因为相互倚重;走在一起,也可能相互憎恨。并非所有的同行都是同道。
大臣们抖动双腿进宫的时候,乌鸦们也正抖动双翅飞入宫中。下午的紫禁城,澄泥砖上看不出人影,满眼都是云淡风轻。
明代的紫禁城,分为外朝与内廷,以乾清门为界。乾清门南是“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这些是皇帝举行朝会和国家举行大典礼的地方;文华殿、武英殿等在三大殿两侧,这些是内阁等重要部门办公的地方。乾清门后是“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这是皇帝与皇后的正宫。后三宫两侧是东、西六宫,这些是嫔妃们的生活场所。
紫禁城里的建筑大多高大、宏伟。什么叫“宫”,什么叫“殿”?从外观、形制上是看不出来的,关键是看建筑的使用功能:“宫”的主要功能是生活,“殿”的主要功能是办公。
大臣们平时所说的“进宫”,指的是越过乾清门,到内廷与皇帝议事。皇帝不出门,臣子们跑跑腿。如果没有皇帝的召唤和太监的引领,臣子是不能进入内廷的。擅自越过朱红的乾清门,被守卫打残那是幸事,丢掉脑袋也是完全可能的。
奉召进内廷乾清宫是荣耀的,因为那是帝王的生活区。有人在京城当了一辈子官,也不知道乾清门内是什么景象,告老还乡后,也只能道听途说、添油加醋,与亲朋好友们胡侃神吹。
进宫之路其实也是一条危途,皇帝在乾清宫与大臣们讨论的,自然是大事、要事、敏感的事。这些不便在大范围或公开场合讨论的事,皇帝自然是想听听臣子的意见。臣子不能没有意见,也不能太有意见,否则,一条敏感的意见可能就将一生的仕途,甚至性命都“敏感”掉了。
没有哪个大臣进宫时不提心吊胆,甚至有人进宫前都立好遗嘱。出家门是人,进家门是鬼,意料之中的事在意料之外,意料之外的事在意料之中,这也就是官场中人为何要时常如履薄冰。
不将乾清门放在眼里的,估计只有紫禁城的乌鸦们。它们可以在天空中翱翔,也可以在宫殿上驻足。紫禁城是威严的,乌鸦们是猥琐的——民间视乌鸦为“不祥之鸟”,皇家其实也是这么认为的。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但也有两样无可奈何:一个是上天,一个是乌鸦。打从明成祖迁都北京时起,乌鸦就成了紫禁城里的常客。
不请自来,驱之不去,皇家只能选择忽略。何必徒劳无益,跟乌鸦过不去,跟自己过不去呢?
但是,为帝王着想的臣子总是层出不穷:明睿宗当年前往封地,舟停龙江关,数万只乌鸦聚集在江边柳树上,朝着船队鸣叫,李梦阳说这是日后“嘉靖中兴”的前兆;明孝宗登基之初,朝堂钟鼓一响,常有数万乌鸦飞往龙楼,这属于“弘治中兴”的征兆;万历朝探花顾起元,第一次上朝时即见乌鸦盘旋皇城,久久不散,顾探花顿时想到这是乌鸦在朝拜,谓之“鸦朝”,然后一本正经地写进了《客座赘语》。明朝君臣关系复杂,紫禁城与乌鸦们的关系也复杂。
其实,乌鸦们哪懂许多啊!它们只是觉得这地方宽敞,房子结实,住下来安全,冬天也暖和——今天的科学家,把这叫作城市热岛效应。
聚集紫禁城的乌鸦,种类也是复杂的:有寒鸦,有大嘴乌鸦,还有小嘴乌鸦。但宫内宫外的人,从不管这些,反正都叫乌鸦,乌鸦就乌鸦呗。
远远望去,乾清宫九个垂脊兽上,各站了一只乌鸦。龙头上的一只乌鸦,长喙在龙头上蹭来蹭去,猛然“哇”的一声长鸣,粗劣而嘶哑。方从哲吓了一跳,差点跌倒。
方从哲(1562—1628),字中涵,其先浙江德清人。家在北直隶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大兴),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
这帮进宫的大臣中,方从哲是老迈又老到的一个,也是官职最高的一个——“宰相”(内阁首辅),并且是从前万历朝干到今泰昌朝。方从哲是一位太极高手,深受前内阁首辅、东林党领袖叶向高的器重,但他又遏制东林势力,在前朝形成齐、楚、浙三党鼎立的局面。他从不以朋党领袖自居,事实上又是浙党领袖,齐党领袖亓诗教还是他的门生。朝中朋党林立,方从哲则游刃有余。
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方从哲没有见过?万历四十六年(1618),后金(大清)军队攻克抚顺,皇帝都急得睡不着觉;各地方水旱灾荒引发大范围动乱,弄得中央与地方焦头烂额;家里大小事一样不少,儿子杀人犯下命案,弹劾、讥笑方从哲的官员不计其数。换上一个心理素质差的,想死的心思都会有的,但方从哲泰然自若,安然无恙。
——不管怎么评价方从哲,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方从哲不是一个庸官,不是“纸糊阁老”,而是有真才实干和丰富阅历的官场老手。“官场老手”不是一个贬义词,朝政不堪的事也不能全算到方阁老头上。万历朝后期的危难局势,没有方从哲这样的阁老,恐怕更加不成样子。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方从哲,竟差一点被一只乌鸦吓趴下,杨涟有点想不通,本能地在后面扶了一把,其实也没用得上什么力。方从哲没想到是杨涟,回头拱了一下手,眼神的余光全是警惕。
杨涟(1572—1625),字文孺,号大洪,德安府应山(今湖北广水)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
杨涟是这班官员中官职最小的一个,却是知名度颇高的“当红官员”。杨涟考中进士后初授常熟知县,举全国廉吏第一,调入京城任户科给事中。泰昌皇帝登基后,命杨涟署礼科印信,又任兵科给事中。“六科”归皇帝直接领导,六科给事中主要是辅助皇帝处理政务,职责很重要,但品级还是正七品。
这次被皇帝召进乾清宫的大臣,一共有十三人:大学士方从哲、刘一燝、韩爌,英国公张惟贤,尚书周嘉谟、李汝华、孙如游、黄嘉善、黄克缵,左都御史张问达,给事中范济世、杨涟,御史顾慥。这班官员中,至少是找不到比杨涟级别更低的。
韩爌特意放慢脚步,等杨涟靠近,摆了一下手,低语了一句,意思是今天情况特殊,让杨涟不要话太多。跟人聊天,多听少说;一群人聊天,只听不说;自己不顶天立地,最好别指点江山。韩爌行事老成持重,欣赏杨涟,也担心杨涟。韩爌的声音很小,方从哲还是听见了,回了一下头。
韩爌(1566—1644),字虞臣,号象云,平阳府蒲州(今山西永济)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刚刚与何宗颜、刘一燝以礼部尚书衔兼东阁大学士。
韩爌的提醒,并不是多余的。杨涟的话不是一般多,尤其是遇上事情时,他沉不住气,简直不像谙熟官场的人,特别容易出乱子。最近闹出的一个乱子,到现在还不能算完。
一周之前,泰昌皇帝也召见过一次这帮大臣,并且钦点了杨涟参加,韩爌知道后,心里当即咯噔了一下,感觉杨涟是凶多吉少。
朱常洛(1582—1620),明神宗朱翊钧与才人王氏之子,明朝第十四位皇帝,年号泰昌,庙号光宗。
年纪轻轻的泰昌皇帝,登基仅仅四天便一病不起,宫中顿时传言纷纷:有说是郑贵妃进献八位美女,把泰昌皇帝给累的;有说郑贵妃唆使中官崔文升进泻药,把泰昌皇帝给害的。宫中实情,外臣实际上是搞不清的,但杨涟倒好,听风是雨,一道奏疏递上去,弹劾崔文升“用药无状”,指斥郑贵妃欲封皇太后,措辞严厉地要郑贵妃移宫。
朝中想说这些的人不少,但都忍着,坐等杨涟这样的“大炮”发声。人性最大的恶,是见不得别人好,巴不得别人出问题、栽跟头,自己在一旁偷着乐,或直接、间接得点好处。官场上的这种人多的是,但方从哲还真不是。能坐在内阁首辅的位子,方阁老最了不起的地方是磨出了自己的格局。刘一燝,江西党元老;韩爌,东林党元老。方阁老与这二位同处内阁,即便背后有什么矛盾,表面上别人也看不出。方从哲是内阁首辅,整个内阁乱糟糟的,他这个首辅脸上能有光彩?
三位阁老放心不下的就是杨涟这种人,都到了知天命的时候,还不知道天高地厚;青春的尾巴都秃了,还依旧是一枚意气少年。方阁老尤其清楚,杨涟实际上既不知实情,又不知道皇帝的心思,想当然地替皇帝做主,把自己的观点和盘托出,最终将得罪哪路神仙,自己压根都不知道。官场水深,玄机也多,要多看多听多想,就是不要多说话。
方阁老还听说一个令人担心的消息:皇帝在宣召杨涟的同时,还宣锦衣卫官校一起入宫。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影视中常有这样的情形——皇帝动怒了,把桌子一拍:“来人哪,推出去斩了!”
谁出来斩那个倒霉蛋?落实皇上旨意,出来执行斩首任务的,就是这类锦衣卫官校。
不过,方阁老也作了一个预判:杨涟被皇帝当场斩首,这个倒是可能性不大;但当场挨上几十大板(廷杖),怕是在劫难逃了。
还真不出方阁老的预料:皇上看见杨涟,果然一动不动地死死盯着。刘一燝、韩爌见状,跟着倒吸了一口凉气。
还好,皇帝这次召集重臣议事,核心是讨论皇太后的册立。这事应该是郑贵妃催的,否则没必要这么急,毕竟先皇驾崩后连安葬的事都还没有办完。
郑贵妃(1568—1630),顺天府大兴(今北京大兴)人,明神宗朱翊钧宠妃,福王朱常洵生母,万历十四年(1586)被册立为皇贵妃。
郑贵妃催得急,也是可以理解的:“皇贵妃”上面便是“皇后”,郑贵妃离皇后只有一步之遥。改朝换代了,册封郑贵妃为神宗的皇后,也就是本朝的皇太后,虽说万历皇帝遗嘱上有交代,但煮熟的鸭子都可能飞,东西揣进口袋才能落袋为安。
杨涟一听,急切起身道:大行皇帝(刚去世的万历皇帝)有元后,皇上生母还立不立皇太后?再立这么一个皇太后,没见过这规矩。
杨涟大嗓门说话,泰昌皇帝不住地皱眉——这对重病在身的人来说,表情已经算是够丰富的了。
方从哲见状,赶紧将话头接了过来:“杨涟之言虽有些道理,但言辞急切,违拂圣意,宜由科、道纠劾。”
方阁老的意思,是先将现场降温,不管事后杨涟被如何处理,总比皇上当场动怒要强些。好汉不吃眼前亏,庙堂江湖皆适用。
皇上听后,猛然抬起手,指着杨涟的方向。三位阁老的心,一下子又提到了嗓子眼。
皇上一字一顿道:“此真忠君。”
泰昌皇帝的声音不大,在场的人还是听得真真切切,大家悬着的心一下子全落了地。
一级官员,一级水平,皇帝不乏顶级智慧。泰昌皇帝不仅没有降罪杨涟,还按照杨涟的意见,将封郑贵妃为太后的旨意收回,也是深有原因的。
泰昌皇帝朱常洛是个苦命的人,虽说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长子,但其母王氏只是一个普通宫女,后来才获得一个“才人”的封号。宗法制度下,朱常洛只是皇长子。朱翊钧的元配王皇后无子,因而也就没有嫡长子。“皇长子”与“嫡长子”有什么区别?看看古代的婚姻制度就清楚了。
很多人认为,中国古代是“一夫多妻制”,这个说法其实并不严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夫多妻制”,只有“一夫一妻多妾制”,除非是少数民族政权。妻与妾是什么关系呢?是主仆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是对等与平等关系。贵族与平民,都是这样。皇帝的正妻叫皇后,皇帝的媵妾就是各种封号的嫔妃,这些嫔妃见了皇后都要磕头。妻的儿子叫嫡子,妾的儿子叫庶子,民间称作“小娘养的”。嫡子有继承权,庶子没有。
明朝皇后以下,皇帝侍妾封号分为十二等,依次为:(一)皇贵妃;(二)贵妃;(三)妃(贤妃、淑妃、庄妃、敬妃、惠妃、顺妃、康妃、宁妃);(四)嫔(德嫔、贤嫔、庄嫔、丽嫔、惠嫔、安嫔、和嫔、僖嫔、康嫔);(五)贵人;(六)才人;(七)昭容;(八)昭仪;(九)婕妤;(十)美人;(十一)选侍;(十二)淑女。
皇后与嫔妃之子,相互间的差距太大:继承皇位的,是皇帝的“嫡长子”,嫡长子即使年龄比皇长子再小,皇位也轮不到皇长子身上,除非皇帝一个嫡子都没有。
王皇后到死都没有生下儿子,这下皇位该归朱常洛继承了吧?不一定。万历皇帝宠信的是郑贵妃,王皇后去世后,郑贵妃的封号比王才人高太多,如果在嫔妃中册封皇后,郑贵妃的可能性远远大于王才人。郑贵妃一旦成为皇后,郑贵妃的儿子就变成了皇帝的嫡长子,朱常洛就彻底与皇位无缘了。
泰昌皇帝对杨涟的戏剧性态度,方阁老同样没有感到惊讶。方阁老脑子转得快,能打败方阁老的,可能只有下一秒的方阁老:泰昌皇帝生母王氏不被万历皇帝待见,自己的太子地位差点不保,饱受郑氏欺凌数十年,战战兢兢的人生啊——“有仇不报非君子”,“得饶人处且饶人”,古人的很多话,都极富哲理。
当然,阻止郑贵妃的企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杨涟只是一个先锋,还是眼下的急先锋。
太子乃“国本”,万历朝的“国本之争”长达十五年,官场玄机的深不可测尽显其中:“国本之争”本来发生在皇帝与内阁大学士、部院大臣这些高层官员之间,迟迟没有结果,导致御史、给事中这些下层的言官介入。这些言官,监督权很大,世俗权力很小。权力与权利失衡,必然导致眼红。言官们斗争的矛头,开始指向内阁与部院,也指向了皇帝,多少带有权力寻租的色彩,不仅仅是空洞地斗。
外廷文官与皇权博弈,通常是没有胜算可能的。但是,皇帝家里也有家长里短,万历帝的母亲李太后,站到了文官们的一边,迫使万历帝不得不让步。这场博弈的结果,是文官集团获胜,言官群体实现了权力的最大化。同时,也养成了官场习气:年纪轻、资历浅的言官们,开始理直气壮地抨击内阁与部院,其中的多数人成为后来的东林党。
这场争斗,外廷文官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十几年里,有四位内阁首辅被逼辞官,六部及地方官员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但斗争目标实现了:泰昌皇帝成了太子,又成为皇上。
泰昌皇帝是一个仁慈、厚道的人,对拥戴自己成为太子并顺利登基的臣子,是心存感激的,即便他们说些过激的话,也不会轻易下狠手,包括杨涟,包括自己的老师方从哲。
事不过三,官场上要懂得见好就收,别拿往事当经验,兔子不在原窝里。
此番再次进宫赴召,韩爌与方从哲对杨涟再次提醒,仍旧不是多余的。两位阁老以多年的官场经验判断,皇帝这次必定有更重要的事拿出来商议,杨涟若是再管不住嘴,神仙也保不住皇帝永远有好脾气。
乾清宫门外,太监李进忠正垂手等待。看见打头的方从哲,李进忠急步上前,连连抖手催促:“快点哟——”
一个“哟”字,让方从哲等人心头一沉,很想从李进忠口里先打听点什么。李进忠绷着脸,扯了一下方从哲的衣边,恨不得一下子把他从宫门里塞进去。
杨涟这回倒格外冷静,从身后细细打量了一下李进忠,心里感觉怪怪的,忍不住想:太监都是一副婆娘相,这家伙倒是人高马大,甚至还有几分威严,就是有点山猫野狗的性格。竟有相貌堂堂的太监,杨涟想笑,但忍住了。
李进忠将大臣们引到了东暖阁,皇帝正头倚在睡榻上。杨涟记得,上次召见大家,皇帝还是坐着的。今天半卧在御榻上,看来皇帝的病情加重了。
方从哲与众臣向皇帝行礼,皇上摆摆手,嘴巴也动了动,但没听出说的是啥,大概就是免礼平身的意思。接着,皇帝又指了指御榻旁边。
杨涟这才注意到,御榻旁边站着一个少年,斯斯文文,一副小秀才的模样,还病恹恹的。
杨涟正琢磨呢,几个大臣也在犹豫。这个少年,有几个大臣是认识的:皇长子朱由校。
朱由校(1605—1627),泰昌皇帝与才人王氏之子。
见到朱由校,大臣们应该即刻行礼。大臣们在犹豫,他们是遇到难题了,不是没有见识:朱由校的生母王氏,去世前只是个“才人”,朱由校明显是“庶出”;万历皇帝刚刚去世,朱由校由“皇孙”变“皇子”不过二十来天,尚未及封王,更未被册立为太子——这叫作“白身”。朱常洛登基后,东林党人吁请册立朱由校为太子,都准备举行册立仪式了,但因朱由校身体太弱,仪式又被往后推迟了。
这下尴尬了。宫廷礼仪是严格的,大臣见朱由校,是按白身皇子、亲王还是按太子的礼仪行礼呢?乱行礼仪,是违制甚至属于犯罪。官场上不要轻易出头,跟风是一条不错的为官之道,大臣们努力让自己愚钝一回。
站在最前边的方从哲,也是一副很迟钝的样子,又像是在思考。韩爌没有耍滑头,或许早已成竹在胸,立马跪倒在地向朱由校行礼。众臣也不再想许多了,紧随韩爌一齐跪下。韩爌叩拜一下,皇帝勾起一个指头;再叩拜一次,皇帝勾起两个指头——一共勾起了四个指头。
越是大事,越要靠小动作。四拜而止,这是大臣见皇太子的礼仪。
大臣行礼之际,泰昌皇帝始终努力地睁着眼睛,然后轻声道:“国家事,卿等为朕尽心分忧,辅皇长子为尧舜之君,卿等共勉之。”
请大臣辅佐朱由校为“尧舜之君”,这四个字是重点。皇帝的声音很小,信息量很大,方从哲听得真真切切。再世故的官僚也有真情,方从哲一下子没忍住,酸楚的眼泪涌了出来。失态了,方从哲借故抬起袖子,以免旁人看出心思。
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一定有更大的悲情即将发生。方阁老思忖。方阁老从未失算。
朱常洛登基之后,方从哲、刘一燝、韩爌等阁臣和礼部的官员,就开始考虑册立皇太子之事,虽然大家意见有所差异,但基本上主张早立太子,这也是接受万历朝的教训。
当今天下大势,不比万历朝好到哪里去,说今不如昔那就欠智慧并且大煞风景了。但内外形势明显就摆在那儿,本朝如果再闹出“国本之争”之类的事,日渐加重的内忧外患,后果肯定会更加严重。册立太子,仪式又不举办,会不会是泰昌皇帝态度在摇摆?方从哲只能心里急,一时也想不出好办法。韩爌这一领头行出太子大礼后,皇帝用这几句话明确表态,确实出乎方从哲的意料。
皇帝今天为何这般痛快表态?方从哲越想越是担忧:皇帝病重,无力回天?难道,这是在临终托孤?一想到这里,方从哲又不禁悲从中来。
册立太子的事,终于议定了。册立时间,初定为九月初九日,具体要由礼部商定。朝廷礼制,是有明确规定的。
皇帝大概是没有气力了,眼睛闭了好长时间。忽然,皇帝微睁双眼,又对朱由校说:“你刚才恳请之事,直接说吧,对内阁诸先生说说。”
朱由校利索地行礼:“皇爹爹,要封皇后!”
朱由校的声音不是太大,但很清亮,仿佛学堂里的琅琅背书声。杨涟吃了一惊:托孤的主题,怎么突然变了?
这又是天大的事情:皇帝是天下之主,皇后是内宫之主。今天皇上要将两件大事都明确下来?
泰昌皇帝说完,这下子像是又有了气力,头从榻上抬了一下,意思是大家赶紧表态。
方从哲不知道是真不明白,还是有意装糊涂打哈哈:“那……那啥?”
皇帝没有接话茬,将脸歪向朱由校,意思是由他明确作答。朱由校的脸腾的一下红了。这后面的话怎么说呢?没有人事先教咋说啊。站在远处的李进忠,想开口又不敢开口,想上前更不敢上前,对着朱由校半竖手指,朝着屏帷后戳了一下。
李进忠的这个动作,没有逃过杨涟的眼睛,刚才他都集中关注皇上了。这下杨涟看清楚了,几根纤细的手指,正扶在屏帷外,里面站着的,分明是个女子。
不等杨涟再往下猜,屏帷内的女子走了出来,是个一袭红衣的妇人。妇人动作极利索,伸手从泰昌皇帝面前将朱由校拉入屏帷内,叽叽喳喳了一阵子。
再从屏帷内走出时,朱由校有些失色,面对皇上道:“皇爹爹,要封李——选侍阿娘为皇后。”回答的语气,显然比不上刚才那般流利。
朱由校这一说,杨涟彻底明白过来了:那妇人就是李选侍。
选侍李氏,泰昌皇帝最宠信的妃子。
对朱常洛来说,选侍李氏的帮助是很大的,从生活,到精神,每一个层面。朱由校、朱由检生母去世后,也全由其抚养。朱常洛登基以后,准备直接晋封李选侍为皇贵妃。但是,李选侍的心大了,居然不同意。
李选侍有李选侍的想法。朱常洛的太子妃郭氏已经去世,朱常洛登基后便没有皇后,选侍李氏想一步到位,直接晋为皇后。这个时候,礼部侍郎孙如游上奏说:太后、元妃等人的谥号还没有尊上。按照“先母后妻”的规矩,李选侍封皇后的事就拖下来了,皇贵妃的事情也没解决。
杨涟虽没见过李选侍,但对李选侍早就没有好感。不过,这事还真不是杨涟意气用事,或是对女性的一种偏见。杨涟对李选侍的了解,是听太监王安亲口说的。
王安,万历六年(1578)被选入内书堂读书,是个有文化的宦官。因担任皇太子朱常洛伴读,王安深得朱常洛信任。朱常洛登基后,王安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
泰昌皇帝病后,李选侍入乾清宫侍奉。女流当中,李选侍确是一位佼佼者:有志向,精力好,身体也好。此刻东暖阁中的十几号人,后来好死、赖死的都有,只有李选侍活到了最后:康熙十三年(1674)五月十八日,李选侍方寿终正寝,享年八十有余。那时,大明王朝已经死去几十年了。
李选侍还有些文化,特喜欢问事。泰昌皇帝病重,难以处理公务,李选侍要求通政使司将每日奏章先交她审阅。“这哪合祖制呢!”王安当面说于杨涟与左光斗,这二位当时就气不打一处来。
此时的王安正随侍在泰昌皇帝身旁,是离皇帝最近的内臣。皇帝轻声说了句什么,王安立即示意方从哲上前。皇帝声音低沉地对方从哲道:“由校和朕都是这意见,册封选侍之事,卿等速办。”
方从哲知道皇帝的意思,顺着皇帝的话回奏道:“臣让礼部速拟册封皇贵妃仪注。”
“是册立皇后仪注。”皇帝纠正道。
方从哲没有料到,皇帝居然又这么清醒。望了望皇帝的面容,方从哲只说了三个字:“臣遵旨。”
方从哲的这三个字,其实是几十个字:皇帝的旨意,不能不遵从;皇帝的旨意,不等于马上办。册立皇后,那是有典章制度规定的。“先母后妻”的理由孙如游已经说过,皇帝今天仍又提出,再重复就是与皇帝过不去了。皇帝的旨意不合祖制,那就花时间慢慢磨吧,关键是不能把慢慢磨的路子一下子堵死。
让时间解决问题,是一条官场秘籍。
太医院院使过来,催促皇帝按时服药,皇帝没有说话,王安示意众臣悄悄退出。这一下,皇帝慌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呢!
更重要的事情,居然是让大臣们为皇帝准备后事。
杨涟想:皇帝病情像是很重,但还不至于病入膏肓吧?其他大臣心里也是这么想的,托孤的事是可以的,安排皇帝后事的事,刘一燝、韩爌与方从哲交换了一下眼神。方阁老上前与皇帝说了一些,主要是关于先帝万历皇帝葬礼与陵寝。
又是一片宁静,好长时间后,皇上手指朱由校,对诸臣道:“辅他为要。”诸臣跪倒,山呼万岁。只能这样了。
离开东暖阁,众人心事重重,没有一个主动说话。杨涟对方从哲刚才的表态很有意见,眼见就要出宫门了,肚子里的话实在憋不到第二天,于是紧走两步,准备拉住方从哲。
韩爌一个斜步插了过来,杨涟差点撞了上去。韩爌竟然又没说话,像是刚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不知是乾清宫上哪个垂脊兽上的哪只乌鸦,猛然又“哇”的一声巨叫,杨涟快出嗓子的话也被吓回去了。
这一天,是农历八月的最后一天,泰昌元年(1620)八月二十九日;这一天,也是泰昌皇帝的最后一天。丝绢般的白气漫过天空,一灯盏大的表白色流星掠过东方。
京城比天空更紊乱:辽东战事再起,浙江士兵哗变,道路传闻纷纷。紫禁城的澄泥砖是暗淡的,谁都没想到这些。更没有谁料想到,一个剑拔弩张、分崩离析的朝代会接踵而来。
韩爌又挡在了杨涟的前面,木然地望着空中,头也不回,对杨涟道:大洪,回去,好好休息。
为啥呢?杨涟准备问,还没开口,韩爌走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