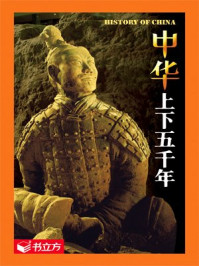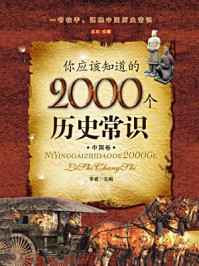自社会最底层走近权力的顶峰,以不学无术之身与知识精英为邻,宦官的色彩不能不魔幻,太监王安也是这样。
宦官群体也是一座金字塔,王安差不多就是塔顶上的那块石头。自万历年间入宫,就如一锹沙子抛下江河,他这一粒是惊涛裂岸还是泥流入海不可知,作为沙子,他连随波逐流的命运都不能自主。
必然是一种概率,偶然是一种概率,反之就是奇迹。一粒寂寞的沙子,切不可轻言未来,无论是哪个方向,它都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选项中也不存在乐观、悲观。
宫廷规矩格外森严,宦官群体却充满着一股江湖气,至少也是民间徒子徒孙那般的人身依附。王安入宫后的奇迹出现,是他被分到太监冯保的名下。但冯保名下的宦官是一堆,不是一个,冯保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转机的出现总是瞬息万变,隆庆六年(1572)五月,明穆宗朱载垕驾崩,十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登基,冯保、张居正与李太后之间形成了权力的“铁三角”,“万历中兴”的局面迅速形成。“皇室领袖”李太后、内相冯保、外相张居正,三人以正面形象留在了历史舞台。
直接照管王安的是太监杜茂,性格耿介,勤奋好学。这是一位好师傅,王安从师傅这里获益匪浅。万历六年(1578),王安进入内书堂读书,由于年龄太小,玩性很重,从未读过书的王安上课时老是走神。哪有不用管,自己成才的孩子啊?杜茂瞧见了,将王安的两条腿绑在两只桌腿上,非得把规矩养起来。王安的字要是没写好,杜茂的一根棍子就过来了。王安后来能与科班出身的文官们诗词唱和,时常写写扇面与骚情赋骨的文人们雅集互赠,那真的不是附庸风雅。王安与东林人士之间的朋友圈,可以说是太监杜茂用棍棒打出来的。
冯保并没有给予王安直接的帮助,但王安看到了榜样与理想。哪一天能够等到梦想成真,这需要机遇。机遇是一种漫长的等待,等待必然与偶然的意外相逢。王安等到了这种意外,也是内书堂与时代带给他的福音。
宦官的本质属于皇权,皇权又绝对置于政权之上。朱元璋时代的明朝,禁止宦官干政,铸了一块铁牌挂在宫门:“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这时的宦官都在做孙子,当奴才。但你看准了,这孙子是皇帝的孙子,奴才也是皇帝的奴才。你千万别拿皇帝的孙子当自己的孙子,也千万别拿皇帝的奴才当自己的奴才,要不哪天掉坑里了都不知道挖坑的是谁。
到朱棣时,宦官的皇权面目就大变了:宦官又是带兵打仗,又是率团出国,又是下基层检查,又是扩权增编。宦官们威风凛凛,忙得不亦乐乎。但是,没出事。
没出事,不等于不出事。原因同样简单:朱棣也是个厉害的角色!试想,能把皇位上的建文帝打得影子都没有,还有什么活做不成?幸运的是,有朱棣这等狠角色的主子,孙子们全都夹紧尾巴。谁不小心露出一截,估计要连头都一块剁了。
朱棣的儿子宣宗朱瞻基,狠抓宦官队伍建设,抽调一流的专家(翰林院学士)办培训班,设“内书堂”,一期教两三百个小宦官。宦官的素质大幅度地提升,宦官不再是没文化的后勤人员,或一群阉割了的大文盲。人家已经有知识,有文凭。朱瞻基的“开掘创新”,算得上为宦官大业画“蛇”点睛。
但乱子终于也来了——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指导”下顺利成为俘虏,武宗朱厚照被刘瑾玩得溜溜转……为啥?就因为皇帝是一帮小屁孩:走马上任时,朱祁镇九岁,朱厚照十五岁。当皇帝没有智力、没有能力来做事、用权时,大权旁落只是时间、多少与形式的问题,比方窃取,比方顺手捡到,把权力当玩具随手相赠。将权力白送给身边的宦官,这种口头授权的后果,只能取决于宦官的素质。
内书堂给了王安良好的素质。正因为这样的素质,太监陈矩认准他是一棵苗子,将其推荐给了皇帝,做了皇长子朱常洛的伴读。“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只要是正常人,是正派人,都能识别金子,陈矩就是这样的人。这一年,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
可惜的是,皇长子朱常洛正处在人生的低谷。他只是皇长子,核心是庶出,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小娘养的”。朱常洛没有一丝名分,万历皇帝的郑贵妃很可能要将其变得前途暗淡。主子都是小娘养的,奴才自是更低人一等。但王安兢兢业业,年复一年,与地位岌岌可危的泰昌皇帝还成了知心朋友。
跟着朱常洛,王安的日子也没有一天是安宁的。“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王安是与朱常洛一起一次次死里逃生。但是,即便是死,他也不逃,王安对朱常洛保持始终不渝的忠诚。朱常洛成为泰昌皇帝后,王安毫无悬念地成了司礼监秉笔太监。
司礼监居“宦官二十四衙门”之首,司礼监掌印太监有“内相”之称。王安距“内相”只有一步之遥。但王安具备冯保之才,已经掌控了宫中大权。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王安也集聚起了自己的“朋友圈”。文雅知书的秉性,让王安与东林党人走到了一起。朱由校登基前的“红丸案”“移宫案”,王安事实上都是幕后一只有力的大手。东林党挫败内阁,没有王安的策应与帮忙,那是不可想象的。在明季,“朋友”与“朋党”,从来都不是泾渭分明。
王安在天启时代,理应再创辉煌。这种可能,有很大的概率。王安生性正直,不喜欢泰昌皇帝宠信的李选侍。不为别的,这女人喜欢欺负厚道人,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人。而被李选侍欺负的王才人,恰恰是朱由校的生母。
情感偏好影响到权力,是必然又是偶然。泰昌皇帝正值壮年,正常情况下朱由校登上皇帝的宝座,应该是二三十年以后的事情。那时,王安注定不再存在。王安同情王才人只是出于厚道,谈不上企图。宦官群体都没有未来,王安也看不到那么远的未来。厚道也是一种机遇,机遇可能不期而来。
天启元年(1621)五月,天启皇帝任命王安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宦官生涯的巅峰,内廷唯一的“内相”,王安对此没有感到意外,外朝也觉得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王安是兴奋的,王安也是儒雅的。他按捺住内心的澎湃:不能太匆匆,不能赤裸裸,要像外朝文官一样,拿起笔写份报告,书面推辞一下;然后,等待皇上的第二个谕旨。
但是,王安没有等到司礼监的大印,而是等到了获罪,等来了死亡。一切毫无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