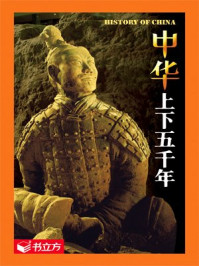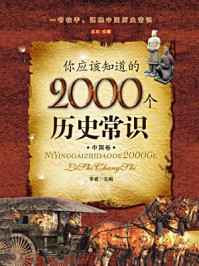备受叶向高关注的人,是东林党首领赵南星,这也是天启朝最引人注目的吏部尚书。
吏部执掌全国文官铨选与考核,除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由廷推或奉特旨外,内外文官皆由吏部会同其他高级官员推选或自行推选。吏部设尚书一员,左、右侍郎各一员,下辖文选、验封、稽勋、考功四司及司务厅。作为官场的组局者,吏部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掌握着文官们的命运。
文官的起家、迁入与迁出皆职在吏部,吏部是官场的组局者,不仅受到言官的监督,也难免为各种官场中人时常“伴飞”。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时吏部也是官场的搅局者。
赵南星(1550—1627),字梦白,号侪鹤,真定府高邑(今河北高邑)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
赵南星的起家,源于科举。对赵南星来说,考中进士简直就是一场梦。传说赵南星参加会试,第一轮阅评试卷时,他的试卷就被阅卷官扔进了垃圾箱。当天夜里,有个考官作了一个梦:一只大鹤,从号房(考场)扑地一声飞了出去。考官一下子就被吓醒了,一摸身子,居然浑身都是汗。
科考阅卷有个“搜落卷”程序,也就是将落选的试卷重新翻一遍,看看有没有被误毙了的优秀人才。在这个环节上,赵南星的落选卷被找了出来,从而避免了落第的命运。后来,赵南星字梦白、号侪鹤,据说都与这个梦有关。
这一科的主考官叫申时行,后来官至内阁首辅。
赵南星当考生时能吓出考官一身汗,当官员后则吓出官场一身汗。
万历二十一年(1593),朝廷例行六年一次的京察。京察的对象是两京(北京、南京)的官员,京察结果直接决定官员的升迁去留。负责京察的是吏部与都察院,吏部具体操作京察的是考功司。
京察中的考功司,在某种程度上比吏部还重要。考功司对被京察的对象作出结论后,后面只有一个“堂审”,也就是吏部堂官集体讨论、复核一遍。但京官那么多,尚书、侍郎谁会一个人一个字地去费脑子,除非那个人正好跟自己是朋友或是亲戚。
京察有个很要命的考核细节叫“访单”,相当于被考核对象的“问卷调查表”。访单发放给哪些人是保密的,访单上填写的内容是保密的,这张访单最终要拿到考功司来,如何汇总、定性在一定范围内也是保密的。考功司相当于“考核组”,为考核对象逐一出一份书面考核结论。
访单还不是填一张表格那么简单,而是要做一份访谈材料。考功司官员选择好访谈对象后,首先必须“闩门屏仆”,让你列一份“劣官”名单。如果你正好有一个对头,然后将其大名报出去,这位仁兄的麻烦就到了。然后再谈官员们的“才守”与“忠厚”,这种环节就更玄了:如果是你喜欢的人,即便工作乏善可陈,你可在其“忠厚”上做文章;如果是你厌恶的人,即便工作出类拔萃,你也可在其“忠厚”上做文章。当然,相同的素材提炼出不同主题的文章,对文章高手来说都是手到擒来的事。
但是,这还不是最玄乎的地方。你怎么说,考功司官员怎么记录,那又是一回事了。你说十句,他记一句;你说一句,他记十句,都有可能,也是可以的。
访单内容的不确定性与选择性,让被考核的每个官员心中都有一只兔子。如果做访单的是自己的朋友,可以找你的朋友做访谈对象。实在要随机,有考功司的朋友帮你现场引导、沟通,做出的访单内容甚至可能比你自己填还满意。“问卷调查表”能调查出什么,负责提问的人很重要。
所以,官场上的人一定要有朋友。而朋友的最高形式,就是朋党。朋党的最高境界,便是死党。
赵南星担任的是考功司郎中,官不大,但太“核心”。
这次京察谁会中枪?赵南星首先拿了两个人来祭刀:都给事中王三余,文选司员外郎吕胤昌。
这一下,整个官场被惊得呆若木鸡。
为什么?王三余,赵南星的亲家;吕胤昌,赵南星的顶头上司、吏部尚书孙鑨的外甥。
拿这两个人开刀,还只是祭旗。接下来,赵南星的大刀砍得更狠:内阁首辅王锡爵的亲信,内阁群辅赵志皋的弟弟,其他没靠山、没实力的落马官员只有哭的分儿。
赵南星这么干能有什么结果?结果且不说,成果很大:内阁首辅王锡爵辞职,吏部尚书孙鑨免职。
干掉最大的官,干掉顶头上司,赵南星不是太强大,而是太神奇了。
赵南星自己赢得了什么?先是被官降三级,接着被削职为民。
“京察”这把利器,直接引发党争,也决定了朋党的官场沉浮。万历三十三年(1605)京察,东林人执掌了吏部与都察院;万历三十九年(1611),东林人仍旧执掌京察大权。这两次京察,东林党对齐、楚、浙、宣、昆诸党实施了大规模压制;万历四十五年(1617),京察大权落入浙党之手,东林党中低品级官员和行事高调的官员,基本上被贬职。相互报复,缺的不是理由,关键是权柄所在。
正常情况下,赵南星应该是把自己玩完了。但是,谁说官场又是正常的呢?
事实证明,赵南星是这场官场争斗的最大赢家:他为自己赢得了巨大声望,为东林党从失败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
明季官场,无可回避的便是“东林党”。究竟什么是东林党呢?
东林党,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地标是江南无锡的东林书院。
东林党什么时候成立的?没有具体时间,因为朋党本就非法,没有人还为自己设一个非法的纪念日,好让对手有把柄可抓。但是,有一个可供参考的时间: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等修复无锡东林书院,建设用地就是宋代杨时讲学地的遗址,顾宪成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
东林党的宗旨是什么?同样没有,也因为朋党是非法,没有人把自己非法的主张公之于众,而广而告之的书院条规基本上是“招生广告语”。可以参考的,是一副东林书院的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读书就读书,科举考试又不考时事政治与国内外新闻,关心那么多干吗呢?但是,正是因这一点,东林书院吸引了士人与学子的眼球,迅速成为议论国事的舆论中心。
东林党的组织架构是什么?不好说,同样因为朋党是非法,没有人把非法名单贴出来等着朝廷来抓。自己人知道是自己人,这才是最重要的。一开始,顾宪成还是赵南星的手下,担任的是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赵南星被罢官赶回家后,顾宪成才接替了赵南星的位子。
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号泾阳,常州府无锡(今江苏无锡)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
赵南星干掉了内阁首辅,顾宪成接替了赵南星。顾宪成像是捡了便宜,没想到麻烦事也跟着来了。
万历皇帝命大臣推荐首辅,吏部尚书陈有年找下属顾宪成商量:你觉得我们应该推荐谁?陈有年这么客气,这么尊重,是因为顾宪成帮过他的大忙——当时陈有年竞争吏部尚书,顾宪成设法让其胜出。
顾宪成也不客气,直接报了个名字给陈有年:王家屏。
陈有年说:好,没问题。
万历皇帝见到推荐名单后,那问题就大了,不仅没批准,连顾宪成都给革职回家。
万历皇帝咋这么大火气呢?因为令万历皇帝头痛了十五年的“国本之争”中,跟他作对最凶的人,就是这个王家屏。皇帝生气了,顾宪成成了出气筒。
从世俗中来,到灵魂里去。回到家乡的顾宪成,一边讲学,一边讽议朝政。顾宪成的学问没有问题,见识也没有问题。无锡在当时只是一个小城市,见识少的人多着呢,顾宪成随便说一句话,立刻成为金句、经典。江南地区很发达,不光是经济,交通也是这样。无锡又靠近“一线城市”南京,顾宪成在无锡风生水起,很快在江南地区风生水起,接着在全国风生水起。
人气爆棚,东林党官员纷纷上疏,要求重新起用顾宪成。万历皇帝后来估计气也消了,让顾宪成出任南京光禄寺少卿。顾宪成说,不干。家里不缺钱,在老家讲学议政这么风光,当那种小官有啥意思?继续讲学议政,一直议论到死。
以顾宪成为东林党创始人,大体是正确的。至少,顾宪成为东林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方针”:在官场争斗中,东林党始终押注“国本”(太子),直至迎来苦尽甘来的一天。
明季的党争,清初学者谷应泰认为,起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京察,以万历三十二年(1604)东林书院的成立为党争起始,这个说法也没问题。从赵南星到顾宪成,一脉相承的东西太多,赵南星的实践贯穿到顾宪成的思想中。
赵南星与顾宪成、邹元标被社会奉为“三君子”,有的是实力与资本。削籍为民的赵南星,由此获得了起复的前提。
万历四十八年(1620),泰昌皇帝起用赵南星为太常少卿,赵南星说:不干;天启皇帝再度起用赵南星为右通政,赵南星还是说:不干;干太常寺卿该行了吧,赵南星说:也不干!
天启皇帝还真看上了赵南星,接着提升其为工部右侍郎,数月后再升其为左都御史。
七十岁的赵南星,不能再不干了,并且要狠狠地干。